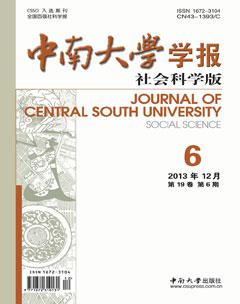“数量+动”与“动+数量”构式的不对称性解析
高亚楠 吴长安
摘要:“动+数量”和“数量+动”构式同为现代汉语动量的表达方式,但两者的地位和功能并非等值,“动+数量”构式是动量的基本表达方式,其表述功能单一,一般只位于句末表述动作的客观量,而“数量+动”构式则是具有一定语用功能的有标记性表达,具有凸显动作情状、表达主观量以及充当句子话题焦点和次话题的功能。汉语动量语序的历时选择过程是造成“动+数量”和“数量+动”构式不对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动量构式;不对称性;语序选择;汉语自身整合;时间顺序原则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259?05
在现代汉语中,动量词有两种句法位置,构成两种常用动量构式,一种为“数量+动”构式,如“多次失败”;另一种为“动+数量”构式,如“消费一次”。汉语学界对动量构式的关注不多,其研究成果仅限于太田辰夫[1]、唐钰明[2]、李晓蓉[3]、殷志平[4]和张赪[5]等几篇文献。这些文章或从历时的视角探求动量构式的发展脉络,或从共时的角度描写非常规动量构式“数量+动”的特点。如太田辰夫[1]认为在动量词产生前,在表示动作数量时直接把数词放在动词前面,动量词产生后动量词则置于动词之后,这种变化同时间表达法的改变和汉语句法表义的明晰性有密切的关联,而李晓蓉[3]认为动量短语常常放在动词之后,在表量多或量少的语义,表并列、对举和假设的句式中以及表时间、肯定、否定范畴的情况下动量短语则要居于动词之前。
本文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构式比较的全新视角考察现代汉语中 “动+数量”和“数量+动”不对称性的表现形式,并力图把历时的、共时的和跨语言的研究结合起来揭示这两种动量构式不对称性的真正原因。
一、“数量+动”和“动+数量”构式的
不对称性表现
(一) “数量+动”和“动+数量”构式的地位
(1) a喝了一次酒 b玩过一把麻将 c扎了他一刀
卖了一次萌 洗了一把脸 挨了一刀
吃过一次螃蟹 体验一把 捅了我一刀
(2) a一次北京都没去过 b一把拽住他 c 一刀砍了他
在现代汉语中,动量词和数词组配常放于谓语动词之后,“动+数量”构式是汉语动量的常规表达。如上例,几乎所有的动量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出现在例(1)一类的“动+数量”的构式中,而只有在特定的语用环境中动量词才会出现在像例(2)一类的“数量+动”构式中。也就是说“数量+动”和“动+数量”构式的地位是不同的,“动+数量”构式是动量的原型表达,而“数量+动”是动量的非典型表达形式。据惠红军[6]对《骆驼祥子》和《围城》的统计,常用动量词“遍”“顿”“趟”“回”和“下”出现在“动+数量”和“数量+动”构式中的次数比分别为31:2、17:3、22:1、15:1和100:8。杨娟[7]对13万字的1 739个动量构式例句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动量短语作补语的(“动+数量”构式)为1 274句,占整个动量构式的 73.3%,动量短语作状语的(“数量+动”构式)为312句,仅占17.9% 。
(二) “数量+动”和“动+数量”构式的表述功能
“数量+动”和“动+数量”构式的表述功能具有不对称性,“数量+动”是一个语用功能多样的构式,它具有凸显动作的情状特征、表述动作的主观量和充当句子的次话题或话题焦点的功能,而“动+数量”构式的功能则相对单一,它常位于句子的末端表述动
作的客观量,下面我们对其进行逐一论述。
1. 从所凸显动作的特征上看
“动+数量”构式只是单纯地从量的层面表述动作的结果,发挥了计量功能,凸显出动作的量特征,而“数量+动”构式的“数量”则居于动词前作谓语动词的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伴随特征,在计量的同时也从动作的量特性层面描写动作行为方式,凸显了动作行为的情状特征。因而,“数量+动”和“动+数量”同所表述的动作特征之间存在以下表述关联:
“数量+动”构式 : 描写动作情状
“动+数量”构式 : 表述动作数量
即“数量+动”构式与动作的情状特征是一组无标记的配对,“动+数量”构式与动作的量特征是一组无标记的配对,如下例:
(1) 没想到这个男人力气还不小,他一把从背后抱住我,嘴里还一个劲儿说:“别急嘛,工作的事我已帮你解决了。(《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2) 她不看时间,不问我们累不累,或者渴不渴、饿不俄,领着我们一溜小跑,在芝加哥的大街上一通转悠。(蒋子龙《芝加哥——建筑艺术博览会》)
(3) 巴金从来不勉强自己的子女继承父业,但是也不像有些文人绝不让子女在本行中吃两遍苦,他期望子女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黄平《巴金和他的儿孙们》)
(4) 在平原上晒惯了太阳,这可好,走一天只见到四回太阳光,风嚎树叫,熊跑虎跳,野猪吧哒嘴,真要碰见红眼狼可就糟了。(王世阁《在长白山森林里》)
例(1)“他一把从背后抱住我”中的“一把”的作用不在于表明“他抱”的次数,而在于表达“抱我”的情状,说明抱的方式,即实现“抱”这个动作所花的动量很少。例(2)“在芝加哥的大街上一通转悠”中的“一通”意在表明转悠了很长时间,而且很尽兴,而非转悠了一次之意。而例(3)“吃两遍苦”、例(4)“见到四回太阳光”中的“两遍”“四回”则表明了动作的次数,即吃苦吃了两次,太阳光共见到了四次。
(5) 马顺向上级反映,不但解决不了,还把他好顿撸。(温树林《顶风》)
(6) 热情的意大利观众在观看彭莉演出时,掌声如潮,一遍又一遍高呼“中国,中国……”(华培明《走向世界的中国时装模特》)
(7) 战友和妻子吵架,他两口子一趟趟地去劝架。(1992年3月《中国青年报》)
(8)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的浩劫。(陈启懋《战后国际关系于的变化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
如上例,“数量+动”构式前可加副词修饰,如例(5)“好顿撸”,还可以重叠,如例(6) “一遍又一遍高呼”,甚至在“数量”后还可加入助词“地”,这些成分的加入无疑使其描写的意味更浓,其动作的情状特征更突出。而例(8)“经历了两次”一类的“动+数量”构式一般不重叠也不加其他修饰成分,只能客观地阐明动作的量。
(9) 扑嗵一声,索泓一脚踩在水窝里,他身子打了个趔趄。(从维熙《鹿回头》)
(10) 一年多,共改造织机五十二台,使全厂生产能力比过去翻了四番,产品质量也提高了。(1979年10月《人民日报》)
“数量+动”主要出现在描写句、陈述句中,而“动+数量”构式主要在说明性、评论性的句子中出现。如例(9)“一脚”是对“踩”这个动作的描述,它与“扑嗵”“ 打了个趔趄”共同描写了“索泓”的动作情态,而(10)“翻了四番”则从量上说明了厂里生产能力的增强,和例(9)不同,该句的注意窗并不在动作上。
2. 从表量的性质上看
语言世界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但与逻辑范畴中只存在客观量不同,语言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描写,而是有客观量和主观量的区分。人们在对量进行表述时,往往会带有对量的主观性评价,认为这个量或大或小,我们把带有主观评价的量称为主观量,不带有主观评价称为客观量。我们认为和“动+数量”主要用来表述动作的客观量不同,“数量+动”更倾向于表达带有主观评价的动量,即动量构式和后置构式和主客观量之间有下述关联:
“数量+动”构式 : 主观量
“动+数量”构式 : 客观量
即“数量+动”构式和主观量是一组无标记配对,“动+数量”构式与客观量是一组无标记配对,如下例:
(1) 被人千遍踏万遍踩出来的路,你再去走,路虽属大道,保险顺当,走过来了,也不过是个庸人。(肖虹《相见仅仅四次……》)
(2) 为此,他曾经把《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一口气看了九遍,才发现三毛要远远比他幸运三倍之多。(大营《鼠趣》)
(3) 安新县决定建立运动鞋厂,县委领导五次三番请张小臭“出山”任厂长。(1990年6月《河北日报》)
(4) 刘铁生走到蛙女跟前,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眉飞色舞地说,“不错!”(胡万春《蛙女》)
(5) 长这么大了,他还一趟远门没出过呢。(李晓蓉用例)
(6) 还好小莲站地离我近,一把就抱住了我,叫到:“小姐!小姐!你怎么了?!”(百度搜索)
如例(1)“千遍踏万遍踩”和例(2)“看了九遍”, 同为动态量词“遍”,“千遍”“万遍”为虚量,有虚说、夸张的因素,表达的主观大量,即说话者主观上认为路已被许多踩过,后人再去实践的价值不是很大。“九遍”表达的则是实实在在的量,是对动作量的客观陈述。同样例(3)“五次三番”表示量多,有主观大量的意味,例(4)“打量了一番”则为实量,即打量一次之意。而例(5)“还一趟远门没出过”用否定的形式来表示动作没有发生,极言其量少,是主观小量的用法。例(5)中的副词“还”和例(6)的“就”都使其主观小量的意味更加浓,凸显了动作的迅速、敏捷。
3. 从话题和焦点的功能上看
话题指后面述题部分所关涉的对象,是一个话语或信息的出发点,它可依据在句中所处的位置细化为主话题、次话题和次次话题三类,位于主语和动词短语之间的称为次话题。焦点指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是句子的语义重心所在,依据所参照的背景焦点可划分为自然焦点、对比焦点和话语焦点三类。话题焦点指以句外的某个话语成分或认知成分为背景,在本句中得到突出的焦点成分,它不能以本句中其它成分为背景,整个句子表达重点仍然在话题后述题上,其功能特征为[-突出],[+对比][8]。
依据句中出现的量构式的个数,我们把动量构式所在的句子划分为单量句(如“脸都顾不上擦一把”)和多量句(如“烫一回才两三块钱”,以双量句为主)两类。我们认为在单量构式中“数量+动”构式表现出话题焦点的特性,与话题焦点是一对无标记组配,而“动+数量”构式则主要充当句子的常规焦点,和自然焦点是一对无标记组配,如下例:
(1) 我就是依仗外婆高高的呐喊声,提起精神、壮着胆儿,走在那寂静的、清晨的山道上,穿过一片树林,跳过一条溪沟,最后,一气爬到坡顶。(李天芳《呼唤》)
(2) 真笨,三下儿都没打开这瓶酒,看我的。(李晓蓉的用例)
(3) 文化队住房紧张,他就每天在距家四五公里的路上往返两三趟。(1987年10月《解放军报》)
(4) 等丈夫出差了,她又请了技术人员来重搞新的样机,她知道丈夫出差半个月,她想在这半个月里再试一回。(尚绍华《悄然寻找另一个天空》)
“数量+动”构式以句外的认知成分为背景,同听说者正常的心理期待量形成对比,表现出话题焦点的特性,凸显了动量的大或小:例(1)中的“一气”是“爬”的动量,它是以句外的“爬几气”“爬多气”为背景,通常爬到坡顶需要多歇几气,而作者中途“一气”都没有休息,“一气”就实现了这个结果,凸显了动作小量;例(2)“三下儿都没打开这瓶酒”,通常情况下打开酒瓶一次就可轻松完成,而这个人却花费了很大的动量,即“三下”都没有实现开酒这个动作,突出了动作量大。李晓蓉[3]在探讨“数量+动”构式时就曾指出:动量短语前置的句子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一种对比关系,动量短语前置,有时表多,有时表少,但不管表多表少,都是建立在“对比”基础之上的。而“动+数量”构式则以本句中的其它内容作为背景,以新信息身份出现在句尾的位置上,如例(3)“往返两三趟”和例(4)“试一回”出现在句末,是句中最突出的部分。
(5) 我在东北,一顿能吃一头野狍子,信吗?(从维熙《鹿回头》)
(6) 珍猴生活在四川、甘肃等地的高山密林中,在快速跳跃中,依靠树枝的反弹力,可一次飞跃40米,有“飞猴”之称。(沈钧《珍猴趣谈》)
(7) 刘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个小公馆,一年也不回天津一两趟。(徐迟《牡丹》)
上述例句显示,多量构式中“数量+动”构式还有话题的倾向,如例(5)“一顿”位于主语“我”、状语“在东北”之后,充当句子的次话题,是“吃一头野狍子”这个述题的关涉对象,在“一顿”后还可以停顿,加“啊”“呢”等语气词(一顿啊,能吃一头野狍子),其话题的性质就更加凸显。例(6)中“珍猴”为整个句子的话题,在“一次飞跃40米”小句中,“(飞跃)一次”为信息的出发点,充当该句的次话题,而“飞跃40米”则是该句的中心,是其焦点成分。而“动+数量”构式则经常位于句子的末端表现出自然焦点的性质,如例(7)“一两趟”。
其实,“数量+动”无论作句子的话题焦点还是充当话题成分,它都是整个句子的重要信息,都是说话人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保证了句子常规焦点的凸显,同时也适应了语言表达的经济性需求,从例(8)和例(9)a、b句的对比中,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出:
(8) a他一次就把这瓶酒喝光了。
b他喝了一次这瓶酒,结果喝光了。
(9) a毛笔字小张一气练了五个小时。
b毛笔字小张练了一气练了五个小时。
总之,动量构式和句子的话题和焦点之间存在如下表述关联:
“数量+动”构式 : 话题焦点或次话题
“动+数量”构式 : 自然焦点
二、“数量+动”和“动+数量”构式
不对称性的原因
我们认为汉语动量语序的历时选择过程是造成“数量+动”和“动+数量”构式不对称性的根本原因。“动+数量”在同“数量+动”语序竞争中获胜而成为动量的常规表达,“数量+动”虽然成为竞争中的失败者,但它并没有完全消退,而是受话语-语用因素的驱动继续保留在汉语中,成为动量的标记性语序构式。
在动量词还没有产生的上古时期,一般采用量前动后的“数+动”构式来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1]。随着动量词的产生和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数+动”和“数量+动”的动量前置语序和“动+数量”动量后置语序处于竞争的共存时期,语言中既有不少“动+数量”构式的用例,也有大量的“数量+动”构式例句,当然也存在相当数量的“数+动”构式[9]。至晚唐时期,“动+数量”语序构式最终战胜了“数量+动”构式,成为动量表达的优势表达,张赪[5]的调查显示,“数量+动”语序和“动+数量”语序在晚唐时期的使用频率比为1:4.2。这之后汉语中“动+数量”语序构式一直是动量的基本表达方式,“数量+动”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那么为什么“动+数量”语序构式会在竞争中获胜发展为动量的常规表达,而非“数量+动”构式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我们认为这是汉语系统自身整合的结果。动补结构是汉语语法系统中极为常见的结构,它的发展成熟给汉语语法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其强大的类推力量使谓语结构发生了改变。在古汉语句子中心动词宾语之后仍有一个句法位置,可以容纳不及物动词、数量词等谓词性成分,唐代后期伴随着动补结构“V动作行为+R结果状态”的发展成熟,汉语谓语结构的信息安排方式发展为“伴随特征+谓语中心+结果状态”格式,即以谓语为参照点,表示动作行为伴随特征的词语居前,表示结果特征的居于其后[10]。由于动量是动作结果特征的一部分,因而 “动词+数量”语序构式在唐代后期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动量构式常用表达方式。
汉语系统内部的整合还表现在名量构式和动量构式语序的对立上。语言内部的语法结构是协调一致的,不同的语法性质的结构采用不同的语序,相同的则采用一致的语序,由于名词数量短语和动词数量短语的语法性质是有本质差别的,因而名词和动词数量短语的语序就应该是对立的[10]。徐丹、傅京起[11]通过历时和句法位置两个角度考察也得出名量词与动量词是相互依存的、两类量词分布呈现互补状态的结论。由于名量构式早于动量构式产生,“数量+名”语序是表达汉语名量结构的主要表达方式,因而从语序和谐的层面看,汉语动量结构的表达更适合采用“动+数量”语序构式。
其次,从共时的认知层面来说,“动+数量”语序构式更符合时间顺序原则。戴浩一[12, 13]提出了汉语词序安排的时间顺序原则,即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如“我们去图书馆学习”这个构式,由于“去图书馆”事件先于“学习”事件发生,所以在句法结构上“去图书馆”排列在“学习”之前。由于动作发生在前,计量次数在后,因此依据该原则“数量”应该位于动词之后。如例(1)“读了一遍”,只有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都阅读完之后我们才能说读一遍,例(2)“往返十五万趟”,在蜂房和花丛之间往返一次我们称之为一趟,即往返的动作是先于动量“十五万趟”发生,“十五万趟”是往返动作的结果。
(1) 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已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了一遍。(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沿着劳动青年革命化知识化的道路前进》)
(2) 姐妹们为了酿一公斤蜜,需要采一百多万朵花,要在蜂房和花丛之间往返十五万趟,相当于四十五万公里。(王金海《小金蜂采蜜记》)
最后从跨范畴的层面来看,“动+数量”构式更有利于语序的和谐。根据饶宏泉[14]对动量词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语序分布的统计,SOV型语言和“数量+动”语序构式是一对无标记组配,SVO型语言和“动+数量”语序构式是一对无标记组配,也就是宾语位于谓语动词前的语言倾向于使用“数量+动”语序构式,谓语动词位于宾语前的语言倾向于使用“动+数量”语序构式,如藏缅语族的载瓦语和哈尼语属于SOV型语言,其动量构式就选择了“数量+动”构式。由于汉语属于SVO型语言,因而更适宜选用“动+数量”构式与整个语言系统的语序相匹配。
三、结语
现代汉语的动量表达存在“动+数量”和“数量+动”两种构式,这两种构式的地位和功能都是不同的,其中“动+数量”构式是动量的无标记表述方式,它一般只位于句末位置表达动作的客观量,表述功能单一。而“数量+动”构式则是动量的有标记表达方式,这个标记就是动量构式的语序,相对于“动+数量”构式,它具有多种表述功能,既有凸显动作情状的功能,也具有表述主观量的功能,从汉语信息安排的角度上看,“数量+动”构式还能使“数量”位于次话题和话题焦点的位置,使整个句子在凸显其动量的同时也不影响其常规焦点表达。此外,由于押韵的需要,有时候也会选用“数量+动”构式。我们认为汉语动量语序的历时选择过程是导致“动+数量”和“数量+动”构式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动+数量”语序构式顺应了汉语历史的发展,同动作发生在前、计量次数在后的时间顺序原则相契合,有利于跨范畴语序的和谐,因而它发展成为动量的常规表达方式。而“数量+动”语序构式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语的发展,但由于它具有特定的话语-语用功能,因而它仍作为动量的非常规表达方式保留在现代汉语中。
参考文献: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54.
唐钰明. 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J]. 古汉语研究, 1990(1): 71?73.
李晓蓉. 浅议动量短语的前置现象[J]. 汉语学习, 1995(2): 37?40.
殷志平. 动量词前置特点论略[C]//语法研究和探索(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99?308.
张赪. 汉语语序的历史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0: 170?203.
惠红军. 汉语量词研究[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189.
杨娟. 动量短语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及意义[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4: 11.
刘丹青, 徐烈炯. 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子句[J]. 中国语文, 1998(4): 244.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石毓智.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25, 191.
徐丹, 傅京起. 量词及其类型学考察[J]. 语言科学, 2011(6): 561?573.
戴浩一.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J]. 国外语言学, 1988(1): 10?19.
张建. 汉语标记配套型并列结构时间关联特征的象似性[J]. 世界汉语教学, 2013(1): 41?50.
饶宏泉. 量词的性质和数量表达的核心[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2(1): 114?115.
An Analysis of Asymmetry “Quantifier+Verb” and
“Verb+Quantifier” Construction
GAO Yanan, WU Changa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of literature,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Verb+quantifier” and “quantifier+verb” construction are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Chinese momentum, but the status and the function between these are not equivalent, “Verb+quantifier” construction is the basic expression of momentum, the function is simple, and it only expresses the objective quantity of verb in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Quantifier+verb” construction is a marked expression of certain pragmatic function, it highlights verbs situational features, expresses subjective quantity and serves as the sentences topic focus or topic function. The word order selection of Chinese momentum is the cause of “verb+quantifier” and “quantifier+verb” constructions asymmetry.
Key Words: The momentum construction; asymmetry; the selection of word order;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cross category harmony
[编辑: 汪晓]
收稿日期:2013?08?13;修回日期:2013?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YY049)
作者简介: 高亚楠(1987?),女,辽宁葫芦岛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吴长安(1963?),男,黑龙江绥化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句法语义学,语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