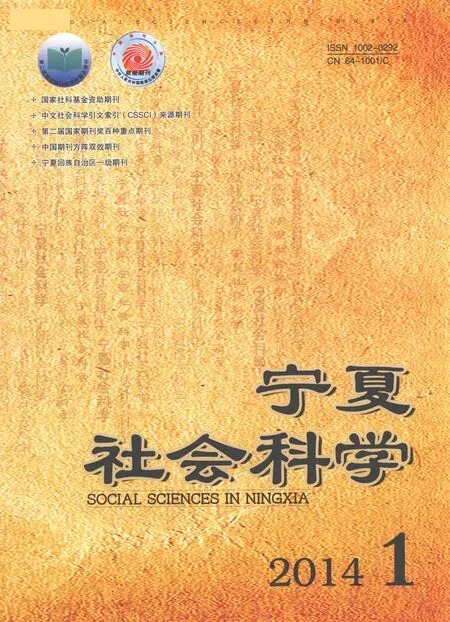“时间”形塑的文化符号——新疆伊犁回族内部身份认同研究
沙彦奋
(1.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20;2.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新疆伊宁 835000)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获得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是个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1]“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它源于个体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以及与此身份相关的价值和情感。”[2]106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部分,在耐尔森·富特(Nelson Foote)看来就是对某一特定身份或一系列身份的占有和承诺。社会身份理论又认为:“一个人所属的社会范畴依据范畴的界定性特征为他提供了一种身份定义——这种界定性特征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3]2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认同,其都“包括村属或家族认同、地域认同、族群(民族)认同、公民身份认同以及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群体意识”[4]6。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群体意识实践和建构的过程。身份认同于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不同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人类学家(如列为斯特劳斯)通过符号互动理论,社会学家(如皮特·伯格、帕森斯等人)通过社会角色、组织、制度等经典社会理论,都对身份认同做了不同解释”[5]。身份认同既有民族群体间“文化空间”范畴比较下的认同,也有民族群体内部“文化符号”差异下的认同。因为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宗教派别(门宦)的多样性,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成为回族内部的一种普遍性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历史移民群体,伊犁回族内部还有“时间”认同。综合起来,当地回族身份认同大体上由此三类构成。前两者与内地回族内部认同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后者则是当地独有的一种认同形式,它是群体特殊移民带来的结果,致使当地回族内部“老新疆”与“黑户儿”泾渭分明,并成为“你”“我”之间的一个鲜明的移民文化符号。
一、伊犁回族内部宗教身份认同
汉斯·莫尔(Hans Mol)在《认同与神圣》(Identity and the Sacred)(1976)一书中,提出了认同的形成与保持是宗教的核心功能的观点,并认为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具有建立个人认同的基本功能。中国学者马建春认为“族群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一群体宗教的、语言的特征”[6]。宗教信仰成为回族身份认同的一个主要“考量”,这是回族群体与其他宗教信仰群体相比较而言产生的一种认同心理,但是在宗教内部由于教派分化,所属不同教派的回族在其内部也有“自我”认同,因教派观念的多样性而导致的认同也呈多元化,正如帕森斯所认为的那样:“当代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导致了社会角色的多元化,使得认同成为一个‘时尚的术语’。”[5]伊犁回族与内地回族一样,教派门宦呈多样性特点,关于宗教认同与内地回族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是由当地回族的移民及其“时间”造就的结果,也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1.“离乡人”文化符号指引下的宗教一致认同
如果从个体或群体的资源出发,伊斯兰教是回族难以缺少的根基性文化资源;从社会关系出发,伊斯兰宗教场所是回族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场域,也是其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者。通过文化资源建构社会资本是回族移民社会初期一条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通道。伊犁回族移民具有持续性、无组织性特点,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的分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特点尤为突出。他们大都是个人或一个家庭自愿移民伊犁,移民初期,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清真寺,而不是宗教派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构成了移民之间的认同,即移民身份认同,进而形塑了“我们都是离乡人”的文化符号。在传统回族乡土社会,宗教文化资源比较丰富,而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以“远亲近邻”为主;移民后,其固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发生“断裂”,异地相同的宗教信仰首先成为他们弥补这种“断裂”的重要媒介,这种媒介又促使他们共同的移民身份认同,进而加强了他们的宗教认同,且对“我的教派是什么?”等不同教派观念认同之追问淡化,表现出宗教认同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共建同一清真寺,对寺坊的一致认同。共同的信仰追求是一致身份认同的基础,虽然教派有别,但清真寺无差异,一日五次礼拜的宗教义务一致。为此,他们共同集资,修建清真寺,并共养清真寺。且在清真寺的理解上,不像内地回族聚居区那样有“新教寺”和“老教寺”等区分。
其次,共养同一阿訇,对宗教神职人员的一致认同。阿訇是伊斯兰教宗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象征,阿訇教派观念也会影响到信教群众的观念,阿訇的此观念滋生的土壤除了其对宗教的自身理解外,信教群众所处的乡土社会也是更重要的“营养”供给地。移民初期的回族乡土社会,离乡情结促使了整体性的回回民族认同和伊斯兰宗教认同之情感,并逐渐取代移民前的宗教派别观念认同。因此,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有阿訇为自己的宗教生活服务,让宗教文化资源不要缺失,阿訇所属的教派并非重要。
最后,同是安拉的“班代”(阿拉伯语,意为信徒、教民),信教群众对彼此的一致认同。身份认同的一个结果是群体或个体之间“边界”分明,将“我”与“他者”对立。伊犁回族内部,在移民初期淡化宗教派别的认同观念,有意识地模糊他们的“边界”,对彼此之间的一致认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生存,这也是宗教文化资源获得、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建构的生存要求使然,结构性认同比较少见。
2.本土观念中的宗教结构性认同
“时间”足以改变群体或个体的社会身份,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随着“时间”的变化,大部分移民伊犁的回族走出“我们都是离乡人”的文化情结,而步入本土观念当中。一般而言,身份认同范围,都经历了由近而远的过程,从不同群体来看,共居一处的群体成分越多,社会认同也就更复杂,身份认同也表现出强烈的“我群”和“他群”意识。随着由“移民”向“本土”转化,伊犁回族群体成分也多样化,如地域分布的不同、人员社会结构的多层次等,致使其内部社会认同趋于复杂,身份认同出现结构性认同。结构性认同也有其当地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新教”和“老教”的结构认同。移民初期的回族内部,“新教”群众加入“老教”寺坊,以及“老教”群众加入“新教”寺坊的现象较为普遍,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这种认同结构,“新教”和“老教”之间的教派观念增强,与之而来的宗教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二者之间的“边界”趋于明显,出现了“新教”和“老教”之间的二元结构对立,也体现在“伊赫瓦尼”教派和“四大门宦”之间的区别。
第二,门宦之间的结构认同。门宦之间的差别细微,据当地一位阿訇讲,门宦都是因对伊斯兰教教义履行的不同认知和理解而形成的,如果门宦之间相互论长短,都是不符合伊斯兰要求的。但是,门宦的宗教身份认同还是比较明显,每个门宦都修建了自己所属的清真寺。
第三,同一教派门宦内部的地域性结构认同。由于伊犁回族社区几乎都是由内地移民而形成,人口的流动也将宗教观念移植于当地,又因来源地的不同,即便是同一教派门宦,也有基于地域上的结构性认同,如“河州寺”“青海寺”“陕西寺”等处于同一地区清真寺的地域性乡土社会称呼,是当地回族内部宗教身份认同的鲜明特征。
由于移民“时间”等诸多因素所致,当地回族的宗教身份认同,经历了由“多元”走向“一体”,再由“一体”走向“多元”的过程,也体现了宗教身份认同由一致性逐渐转向结构性的特点。这一变迁过程是伴随着当地回族由“移民”向“本土”的变迁而变化的,也是回族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转变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宗教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维度,与群体社会其他维度联系紧密,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宗教内部也在分化当中,处于多维度社会中的回族宗教身份认同,宗教本身是其认同产生的核心观念,但其他社会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二、伊犁回族内部地域身份认同
中国学者丁宏认为,回族认同都基于“斯大林定义中‘表现于共同文化心理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虽然许多学者将其纳入主观意义上的心理认同,但由于将这种认同设立在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从而忽略了回族文化的地域性与多样性”[7]。因此,回族文化丰富的地域性特征,又给回族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增添了多样的地域性色彩,处于同一地区的回族内部身份认同的地域性观念相对较弱,而伊犁回族由于来源地的不同,其内部身份认同地域性观念和结构比较突出。
1.“口里”与“口外”:伊犁回族内部的地域身份认同界定
通过伊犁回族内部的地域身份认同界定,我们发现当地回族的地域性身份认同的结构性特点比较突出,表现出地域由大到小的逻辑结构,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西北回族”和“内地回族”。由于移民的历史等诸多因素所致,这两个地域性的回族在当地的“文化空间”分布不同。他们观念中的“西北回族”主要以西北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区为主,且分布在“地方”①上,他们所处的地区,因与周围的哈萨克、维吾尔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相互为邻,处于伊斯兰文化较为丰富的空间;“内地回族”主要以河南、山东等内地省区为主,大都分布在兵团地区,多以汉族为邻,处于汉文化空间之中。这种文化分布格局导致二者在伊斯兰教教义的履行和“看守”方面差异性明显,宗教虔诚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标识着他们彼此之间的“边界”。
第二,“新疆回族”与“口里回族”。新疆称内地为“口里”,内地称新疆为“口外”。当地回族人称去内地为“回口里”,内地回族称去新疆为“走口外”(或“上新疆”)。新疆与内地之间的长距离,成为“口里”与“口外”永恒的地标,并成为一种地理文化符号,标志着二者之间的地理“边界”,也成为二者所属群体间的身份“边界”。
第三,“河州人”与“老陕”。这是从微观方面进行的身份建构,类似的建构方式还有很多,如“宁夏人”“青海人”等。这样的身份建构前提下的身份认同,方言的差异性成为当地回族群体内部“边界”标识的文化符号。当地其他民族称回族语言为“回族话”或“回回腔”,其虽都以陕西方言为基础,但地域性色彩也比较浓厚,大体上有两种,其一是河湟一带的“河州人”和“青海人”比较接近,“老陕”和“宁夏人”同属一个体系。他们的分布情况是普遍按照来源地集中分布,如“宁夏人”多在巩留县和特克斯县,“老陕”主要在伊宁市、霍城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河州人”和“青海人”居伊宁县者最多。这样的分布格局为其内部地域性身份认同又增添了一个无形的“砝码”。
2.婚姻抗拒与仪式摩擦:伊犁回族内部社会交往中的地域身份认同表现
婚姻如“剧场”,主演当属婚姻当事人双方,但离不开其身后双方家庭(家族)等群体“背景”;仪式如“剧情”,离不开不同社会角色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力量”互动的支撑。回族婚姻仪式是一个地方性色彩浓厚的“剧本”,承载着回族宗教文化、社会交往、人生礼仪、世俗生活、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内容,不同地方的回族婚姻仪式,展示不同地方的回族社会。不同地域回族之间的婚姻抗拒和仪式摩擦,不但是回族内部社会交往中的地域身份认同的表现,而且也是我们解读和理解回族内部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
婚姻是回族社会互动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通过婚姻所建构的社会互动,对身份认同较为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婚姻对象的身份认同,成为婚姻的“先决”条件。回族婚姻对象的属性,决定了其婚姻圈的宗教和民族属性,他们的婚姻圈由族内婚(核心圈)、教内婚(中间圈)和教外婚(外延圈)扩展②。族内婚是当地回族的主要婚姻形式。婚姻对象的身份由多种社会因素构成,特别是宗教派别观念成为影响当地婚姻对象选择的主要条件。不同身份的婚姻建构,会受到来自婚姻当事人所在群体集体身份“情景”的干扰,甚至是抗拒,这种抗拒的背后,是担心婚姻仪式和日后生活仪式的“不适应”。
其次,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导致婚姻仪式的摩擦。一场婚姻仪式包含双方多方面的社会“惯习”,“十里不同风,八里不同俗”是乡土社会对社会“惯习”的自我认知与理解,这些社会“惯习”又促成了地域身份认同,不同的地域身份认同者之间的婚姻仪式,因为相同的社会“惯习”而融洽和谐,反之则矛盾摩擦较多。如婚礼宴席的持续时间,地方性特色突出,当地“老陕”(陕西回族)以及移民“时间”较长的回族婚礼仪式持续三天,第一天“娘家人”不参加,其他客人参加,第二天专门招待“娘家人”,称为男方给女方“下面”③,第三天男方约20人到女方家,称为女方给男方“下面”;来源于其他地方以及移民“时间”较晚的回族则只需要一天即可,婚礼当天“娘家人”和其他客人同时招待。诸如此类的地方性差异,在婚姻仪式上出现的矛盾和摩擦也比较普遍。
当地回族虽然都身处一地,但是由于来源地的不同,其内部地域性身份认同观念仍旧比较鲜明,且在回族内部社会交往互动中,彼此地域性身份认同的表象也比较突出,并以移民前所属地方的名称对自己进行身份“界定”,因而彼此“边界”意识浓厚。而且通过“时间”划分出不同群体,如“老陕”的地域性身份认同又透视出“时间”赋予回族移民的文化意义,当地人对“老陕”的理解以移民“时间”为标准,因为其移民“时间”相对较长,并形塑了“时间”文化符号,由此而形成“老新疆”与“黑户儿”的身份认同。
三、“时间”形塑的移民文化符号:“老新疆”与“黑户儿”
“时间”是构成社会延续的“抽象”,而乡土社会对“时间”的认知却是通过一些历史记忆而“具体”,即“时间就是社会”[8]107。“时间”本身于社会身份认同没有意义,而“时间”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会身份的“产生”形塑不同的文化,并成使之符号化。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结果,正是“时间”通过乡土社会历史记忆形塑的文化符号,并成为群体认同的鲜明“边界”标识。作为一个历史性移民群体,伊犁回族因移民“时间”而内部出现两种对比鲜明的身份认同,即“老新疆”与“黑户儿”,并成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符号分别标识着两个不同的群体。
1.“老新疆”与“黑户儿”的形成
内地移民新疆的民族成分比较多,人口数量也比较多,但唯独在回族内部存在“老新疆”与“黑户儿”两类不同的身份认同。当地政府没有这样的身份界定,其他民族对回族也没有这样的分类,因此,这两个“概念”产生于回族内部,并适用于回族内部,也是回族内部身份认同的一个“边界”符号。调查了解可知,这两个不同的身份符号,是彼此对对方的认识与理解而形塑的。只有走近当地人,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认知是理解这两个身份符号的真实诠释。
“黑户儿”眼中的“老新疆”。“老新疆”这样自我表述:“我们嘛已经是彻底的新疆人,只是听说祖先是从内地来的,但是具体是哪里的我们也不知道。还是新疆好,新疆生活舒坦,内地竞争厉害,生活压力大,而且人情味远不如新疆。”“黑户儿”却对“老新疆”有这样的认识:“他们自认为是新疆本土人,与我们比起来有很明显的自豪感。他们比我们开放多了,尤其是妇女的着装打扮,和我们不一样,大多数中老年妇女穿的和维族哈族一样的裙子,也不戴盖头,只是一个纱巾绑在上面,头发也露在外面能看见。他们比较懒惰,就守着几亩地,房子也盖得很一般。他们的习惯已经和内地回族有所不同,饮食与当地的哈萨克和维吾尔相似,最主要的特殊性是食用马肉。
“老新疆”眼中的“黑户儿”。“黑户儿”这样自我表述:“我们是内地人,来到这里时间不长。我们还是感觉这里唯一一点好处就是生活容易,打工养家糊口不难,内地唯一的不好处,就是缺水。总体来说还是内地老家好些,心里一直惦记着老家,所以,我们自认为是内地人。”“老新疆”却认为“黑户儿”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来自内地的,有些时间不长,没有户口。刚来的时候都很穷,但是他们能吃苦、很勤快,越来越好了,大都在这里买了房子,定居下来。有些户口落到这里了,有些没有,不管落没落,我们还是称他们是‘黑户儿’。他们思想都比较保守,这与他们经常回‘口里’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双方彼此对对方不同的认知与理解,并给对方给予了界定,并赋之于不同的身份。因此,这种身份认同不是“自我认同”,而是由对方强加于的“认同”。这种身份“被认同”的标准是基于来到新疆的“时间”。通过他们对彼此的认同,我们认为“老新疆”是来到新疆较早,且与内地没有血缘(族人)联系,即与内地没有任何联系的回族;而“黑户儿”是来到新疆较晚,与内地有血缘(族人、亲戚)、地缘(故乡、邻里)联系紧密,并长往来于内地与新疆的回族。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是因为移民“时间”所致,所以,“时间”成为这些群体间不同的“边界”,并形塑了“老新疆”与“黑户儿”文化符号。
2.对“时间”形塑的“老新疆”与“黑户儿”文化符号的解读
依据上述“老新疆”与“黑户儿”的形成,我们认为具有如下几点文化符号意义:
首先,形塑了“时间”的文化符号意义。“时间”不管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也不管是哪类“时间”,回族都将其视为一种符号意义,而这些符号主要以社会“事象”作为表征,因此,在回族社会中,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某日某年对等起来,尤以一些宗教节日为突出。人类学看来,“无论是作为人生的时间,还是作为‘年’这个社会时间,时间在我们生活中起的作用很大,于是社会要融合为一体,需要依靠时间的关口,需要在把握这些关口的过程中,显示社会的整体意义”[8]107。基于“时间”新疆伊犁回族将内部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将“老”作为一个“时间”符号象征一个群体,并赋之以文化意义。“文化通过一系列符号来标界族群边界,使之‘具象化’。”[9]164最先移民者与后期移民者正是在“老新疆”与“黑户儿”符号指引下划分二者群体之间的“边界”,也体现了不同的移民文化。目前看,“时间”将本来没有区别而为一体的回族割裂为不同的两部分,并没有实现融合为一体,深信这些“黑户儿”在“时间”的作用下也会成“老新疆”,但是我们也在这种现实中,通过回族社会内部的结构分化与结构认同,看到回族社会的整体意义。
其次,体现了由“非我认同”到“自我认同”社会过程。通过“老新疆”与“黑户儿”彼此认同,我们认为身份认同不仅有“自我认同”,也有“他者”赋予的“非我认同”,即“被认同”。这里使用“非我认同”并非指自己不认同“自我”,而是由于“他者”赋予“自我”的一个身份,而不是自己如此认同自己。这两个名称符号所指范畴起初都是由对方界定的,之后二者所属群体“边界”逐渐明朗起来,随着“时间”的改变,由对方界定的身份名称符号,在“我群”中得以认同,进而成为“自我认同”。
最后,反映了传统回族社会分化与认同结构。在移民较多的新疆伊犁,唯独只有回族内部有这样的身份认同,这与回族社会结构分化有密切的关联。由于分布地域的广泛性和宗教信仰的根基性,回族社会结构分化较为细,结构性特征突出,不管在地域上,还是宗教信仰上,都可以划分多层次结构。这种文化传统,使得回族在内部结构分化严重,且结构性认同观念浓厚,最终导致他们“我群”意识较强。这种意识也是回族在内部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增强,尤其在独特的“时间”观念影响下,移民社会中的“先”与“后”、“老”与“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塑造了“二元”刻板印象,
四、结束语
身份认同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学科属性的差异性和研究视角的特殊性,关于身份认同也有不同的研究“考量”和标准。回族作为我国一个少数民族,其身份认同也因研究“考量”和标准的不同,而具有结构性认同的特征。目前看来,回族身份认同有三个层次:最高层当属国家认同,即中国公民或中华民族认同;中间层为族群认同,即回族认同;底层是地方认同,这个层次的认同因为地域性的差异也有多种认同方式。伊犁回族内部多元性认同,也正是基于来自于不同地域的结构性差异性所致。多数学者认为,群体归属感导致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是群体资源竞争导致的结果,伊犁回族内部身份认同不可否认资源竞争增强身份认同这一维度,但这不是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回族内部在社会交往中,因为来源地的不同而与身俱来的差异性突出的地方性文化的相互不适应,导致不同地域性群体之间的不能“理解”,并逐渐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进而带来不同的身份认同。尤其是“老新疆”与“黑户儿”的不同身份认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形塑了又一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标志,即以“时间”为“考量”和标准的认同。伊犁回族内部的“老新疆”与“黑户儿”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回族内部的“相互看不上”,更是强调“自我”的结果。追忆伊犁回族的移民历史,从“时间”本身来看,它是构成回族社会延续的“抽象”,也成为回族乡土社会历史记忆,并使之具体化、符号化,这种“符号”也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为“老新疆”曾是过去的“黑户儿”,现在的“黑户儿”也会成为未来的“老新疆”。
注释:
①新疆现有两种建制,一种是当前的自治区的州县乡(镇)制,另一种是兵团建制。当地人称前者为“地方”,后者则为“兵团”。
②借助王铭铭教授的“中间圈”学术思路和方法,笔者认为基于回族自身的宗教性和民族性特征缘由,回族的婚姻圈由“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延圈”构成。“核心圈”由族内婚构成,即婚姻双方限定在本民族内部,这种婚姻形式为回族婚姻的主要形式,其承载着回族人口繁衍(或血统延续)和文化传承的责任,从回族内部来看,处于核心地位,故可视其为核心圈;“中间圈”由教内婚构成,即婚姻双方限定在共同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其他民族当中,如与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其为多民族地区回族婚姻处于“宗教—民族”选择当中的婚姻,从回族自身发展来看,伊斯兰文化传承可能持续,但人口繁衍(或血统延续)有所改变,故可视其为回族可选择也不可选择的中间圈;“外延圈”由教外婚构成,即婚姻双方延伸至与伊斯兰教信仰不同的民族,如汉、锡伯等民族,其为回族不提倡的一种婚姻形式,因为人口繁衍(或血统延续)和文化传承将会在这种婚姻形式中发生“断裂”,超越了回族宗教和婚姻的禁忌“边界”,故可视其为外延圈。
③“下面”,是当地人在婚礼中的特殊用语,即为宴请的意思,据了解,这种习惯是当地回族延续时间较长的一种婚礼仪式。食材,以前以面条为主,但也有要求,即以长面条为主,这象征婚姻长久和长寿。现在,以各种肉食和蔬菜为主,但长面也不能缺少。女方当男方参加者,必须预先由媒人和新郎带上“四色礼”(核桃、大枣、茶叶和冰糖各1公斤)到女方家的亲戚去请,主要对象是新娘父母双方的亲人。
[1]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美]S.E.Taylor,L.A.Peplau,D.O.Sears.社会心理学(第10版)[M].谢晓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何成洲,主编.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批评与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1).
[6]马建春.浅析族群关系中的文化认同[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4).
[7]丁宏.从回族的文化认同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5(2).
[8]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