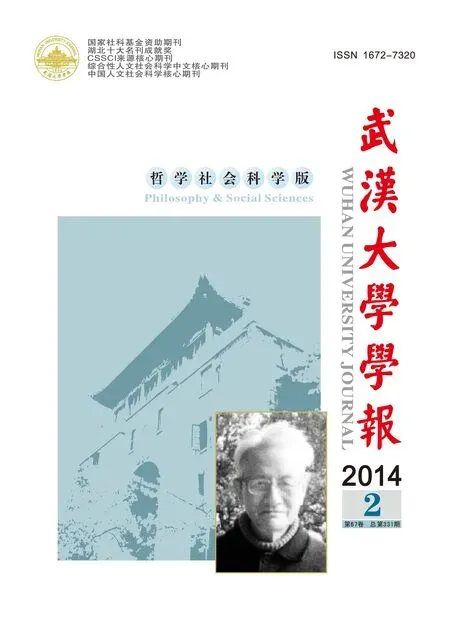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
——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刘小魏 姚德超
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
——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刘小魏 姚德超
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影响不断增强的公民决策参与现象,形成了媒体社会化时代我国的新公民参与运动。城市政府公共管理中“邻避”情绪的显性化则是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深刻反映出公民参与的不完善性,也凸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必要性。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力的理念并合理把握公民参与的限度,将有效的公民参与融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同时,要围绕发展有效公民参与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新公民参与运动; 地方政府; 公共决策; 邻避情绪
一、 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及其特点
新公民参与运动(new public involvement),又称为市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民参与在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的现象,即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不断高涨,公民在公共组织和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公民在许多重要领域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参与行动日益合法化。托马斯认为,与传统的公共参与相比,新公民参与运动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更加强调公民对政策执行的参与,即公民不仅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且一旦政策被采纳,公民也参与政策的实际操作,进入公共项目的实际管理过程,即政策执行;二是大大扩展了相关参与的公民的范围,包括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公民。新公民参与一反传统公民参与的精英主义倾向而转向大众化参与(托马斯,201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级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断提高,公民参与取得了重大进展。进入21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快速普及化与社会化,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我国公民参与迅速发展的催化剂。尽管当前我国的公民参与实践与西方“新公民参与运动”在内涵与外延上并不能完全等同,但毋庸置疑,我国公民参与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特别是较之于传统的公民参与而言,媒体社会化背景下我国的公民参与显然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实践,而近年来在全国各大城市迅速蔓延的“邻避”运动,本质上即是一种新公民参与运动。可以说,我国公民参与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新的公民参与时代已悄然来临。当前,我国公民参与的新发展与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公民参与新媒介化特征日渐突出。一方面,新媒体社会化发展大大拓展了公民参与的主体范围。由于公民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参与的自觉性也不断增强,而新媒体的自主性特点,使得公民参与更加便捷。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拥有一台联网电脑,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就某些公共问题自主表达意见或者参与公共讨论。另一方面,新媒体普及化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参与作用。如今,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视频聊天工具等新媒体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不仅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和公共空间,而且使得公民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998-2010年期间发生的210起重大公共舆论事件中,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105起,占总数的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仅14起,占7% (钟瑛、余秀才,2011:49)。如今,网络表达、网络议政、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新潮流,新媒介化公民参与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二是公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公民参与的领域不断拓展。新媒体传播拥有海量信息内容,这种特性可以帮助公民随时了解社会各个领域的事物或现象,并且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参与公共讨论,发表意见或主张。比如,上述21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涉及了包括官员腐败、政府管理、城市拆迁、生产事故、环境污染在内的13个领域,而政府管理、房屋拆迁、警民对抗事件所占比例呈扩大趋势(钟瑛、余秀才,2011:45)。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已渗透到地方政府公共决策领域。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即时性与互动性特点,不仅可以帮助公民提高信息获取的时效,随时了解政府公共决策情况,而且使公民不论个体或群体都可以从一定的目标出发,就某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实施发表观点与见解,并在公共讨论基础上达成共识,最终影响政府公共决策。2007年厦门“PX事件”就是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典型案例。在这起事件中,厦门市民的参与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而且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的变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及其成因
在地方政府治理变革进程中,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政府和公共管理者无法回避的现实情形。不过,与采取适当措施积极回应公民参与的要求和吸纳公民参与相比,维持公民参与和公共管理效率之间的有机平衡显得更为关键。我国公民参与的新发展与新特点,从实现民主价值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从效能角度来看,我国公民参与的强势状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公共管理的效率。在一些地方,新公民参与运动已给政府公共决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涉及“邻避”公共设施设置的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由于公民参与的强势状态已几乎陷入困境。究其原因,新媒体快速发展引发的环境变化是导致这种困境的外部因素,而地方政府决策系统自适应与自更新能力不足则是导致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 新公民参与运动考验地方政府约束性决策能力
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政治系统受到的压力,一方面,是要求的容量和内容之间相互关系的函数,另一方面,亦是对于满足和处理这种要求的系统作出的适当反应的函数”(伊斯顿,1999:81)。作为系统输入的关键变量,要求可以将系统的基本变量逐出系统的临界线,进而对系统施加压力。直接由要求产生的压力包括容量压力、内容压力与时间压力。“如果要求实质上需要花费过多时间来加以处理,或如果它们超过了某个经验上可以把握的容量,那么,一个系统作出约束性决策的能力,就会受到威胁”(伊斯顿,1999:42)。由此看来,约束性决策能力就是指公共决策系统在相关约束性条件下输出决策的能力,而信息容量大小、信息内容复杂程度以及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这些信息就成为公共决策系统的约束性条件。伊斯顿的思想对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能力所遭受的挑战极具参考价值。
在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中,新媒体成为重要的渠道和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地方公共决策系统的“输入—处理—输出”结构。一方面,新媒体极具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使得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自媒体”特性。“自媒体的核心是基于普通市民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邓新民,2006:134)。新媒体发展的这种“自媒体”特性,学界称为全民DIY时代。所谓DIY,是Do It Yourself的英文缩写,就是指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资质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DIY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产品来。而所谓基于网络的内容生产DIY,其实就是全民出版、全民传播的意思。正是由于新媒体时代的这种全民传播特点,使得从新媒介传播环境中输入公共决策系统的信息在容量上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在内容层面,对新媒介传播环境中输入公共决策系统的大流量信息进行区分、辨识、提炼,以及进行决策处理和转换,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即时性特征,大大提高了“要求”信息从环境输入公共决策系统的速度,同时新媒介传播环境对公共决策系统处理、转换信息并输出政策或行动以回应环境“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时效要求。总之,新公民参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使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发生了要求输入超载现象,进而导致系统在转换、处理信息以及输出环节也遭受了较大压力。
(二) “邻避”情绪致使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处于“高压”状态
所谓“邻避”情绪,源于英语缩略词NIMBY,即“Not-In-My-Back-Yard”的缩写,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之意。在西方,NIMBY一词常常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即“我们都认为社会需要这些设施,但作为个体,希望这些设施设立在别的地方而不是临近我们的家园”(Brion,1988:438)。该缩略词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背后的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市民对不合理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的组织化抵制。90年代以后,“邻避”现象在西方社会已十分普遍,公民持抵制态度的公共工程或项目包括高层建筑、化工厂、军事基地、垃圾填埋、发电厂、焚烧炉等众多领域。1991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提交给布什总统的一份名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消除经济适用房的障碍》的报告中更是将发生在个人、邻里与社区层面的邻避情绪视为经济适用房的最大、最强有力、最棘手的管制障碍。如今,基于环境正义运动的公民“邻避”情绪已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设置公共设施时面临的主要“社会—政治”挑战。国内学者将上述现象称为“邻避效应”,是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不利后果,而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汤汇浩,2011:111)。
我国各级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发展,一方面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进展;另一方面,新媒体快速发展与普及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新媒体的发展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媒体空间有限和管制严格的局限,为普通公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营造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媒介与传播环境。不仅如此,参与的新媒介化方式还使得公民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的参与活动的实际功效进一步被强化,甚至使公民参与处于某种超强势状态。一些地方公共设施选址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邻避”情绪大有对地方政府形成“倒逼”之势,就是这种超强势状态的突出体现。例如,某市拟建的110千伏变电站、垃圾焚烧厂等项目均受到了项目选址附近部分居民的抗议。而以新媒体事件形式出现、集中体现公民“邻避”情绪的案例,则是2007年厦门市民反“PX”项目事件与2008年上海市民反“磁悬浮”事件。这两起公民参与事件均使得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处于严重“高压”状态,其中,厦门市民反“PX”事件不仅最终导致厦门市政府不得不做出项目迁址的决定,而且还引发连锁反应,多个城市出现市民对该项目的抵制行为并且多数都以迁址或撤销告终。
在一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感受到的压力或困境是一个环境与决策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函数。环境变量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决策系统适应性下降正是导致当前地方政府公共决策困境的根本原因。
1.新媒体改变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环境
新媒体对于决策环境的客观影响突出表现为信息资源配置方式与权力配置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新的传播环境中媒体使用更加多元化,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直接和交互能力不仅让公众能够绕过传统媒体的“过滤”而接触到海量的政府信息和政府文件,而且导致“政府最核心的过程也在公众面前曝光”,政府公共决策的神秘外壳被揭开。处于边缘的个人和群体拥有更多机会去影响公共话语,甚至改变公共话语的规则。另一方面,新兴的媒体正在突破传统的以精英为中心的模式,实现权力的重新分配。新的媒体环境中政府决策机构、权力精英主导和控制政策议程建构与设置的局面受到冲击,公众可以自主建构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参与公共讨论,发表政策主张,借此影响政策问题的确认与政策议程的设置,这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新闻“看门人”的传播格局,而“当记者、公共事务官员和其他政治事务‘看门人’等权威日益受到其他政治意图和社会意图的制造者——包括大众本身——的挑战时,由此产生的媒体环境正在重新构建传统的权力关系”(卡尔皮尼等,2011:121)。
2.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自适应与自更新能力不足
这种不适应状态从主观方面看主要表现为决策观念不适应,从客观方面看则主要表现为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不适应。在传统传播媒介环境下,公共决策与公众是一种隔离状态。公共决策机构与权力精英处于公共决策系统的核心位置,独占性地掌控了公共决策权,既在观念上排斥公众参与,也习惯了在有限的公民参与状态下进行决策。新媒体传播环境下,普通公民广泛介入地方政府公共决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在封闭的系统中独立决策既无可能也不现实。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尽管已经感知到了公众参与带来的压力,但由于公共决策系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特性,致使地方政府在应对策略或具体操作方式上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做出调整。当前,很多地方相关居民或组织对“邻避”公共设施或项目的抵制情绪,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的不透明性、整个决策过程缺乏公民的适度参与是密不可分的。
三、 地方政府摆脱公共决策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 恰当处理公共决策中有效公民参与的限度
在民主政治领域,公民参与的价值与效率始终存在无法回避的悖论,公共政策领域更是如此。一方面,没有公民参与的公共决策,根本无民主化科学化可言;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必然会损害公共决策的效率。避免公民参与造成的效率损失,正是威尔逊等第一代公共行政学家与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家极力贬低、排斥公民参与,将公民参与限于“精英”范围的重要依据。此外,公民自身的素质与能力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公众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和对复杂问题的判断仍存在严重弱点……即使在理想的传播条件下,公众意见的形成也暴露出许多令人不安的特征。”“除非公众理解政策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否则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要么将会受到削弱,要么只会常常——但并不总是——导致更坏的结果”(德罗尔,1996:204-205)。可见,不适当的公民参与还极具危害性,没有任何限制的公民参与则最多只是一种美好的民主理想。
所谓限度,从最一般的意义看,就是指一定的范围或者数量。从本质上讲,限度是指范围的极限,是一定标准(最高或最低)的数量或程度。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限度,也就是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必须保持的程度或不能逾越的极限,包括范围、规模与水平层次。其中,范围主要是指公民可以参与哪些层次或类型的公共决策,规模是指参与公民数量的大小,参与水平是指公民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的作用力大小。总之,公民参与应该在确保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当公民参与不能再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反过来妨碍公共决策的有效性时,它就超出了限度。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政府兴建垃圾处理厂、核电站、污水处理厂、精神病院等设施引发的邻避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超越了有效公民参与的限度。
在现代政府治理进程中,如何才能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在公共决策中融入积极有效的公民参与?托马斯认为,界定公民参与的适宜度主要取决于最终决策中政策质量要求和政策可接受性要求之间的相互限制。政策质量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公民参与的需求程度就越小;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吸纳公民参与需求的程度和分享决策权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托马斯,2010:25)。在政策质量的核心需要被鉴定清楚后,政策可接受性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此时吸收公民参与决策制定就成为决策成功与否的关键。那么,在可接受性要求高的公共决策中,如何吸收公民参与呢?托马斯进一步讨论了以增加政策接受性为目标的公民参与问题,并重点介绍、评价了最常用的三种技术方法,即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与斡旋调解,接着分析了三种公民参与形式的使用方法与技巧。
上述思想对于地方政府把握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限度、恰当处理公民“邻避”情绪的重要借鉴意义在于:一是根据政策质量要求程度限定公民参与的主体范围及其方式。尽管政策质量与可接受性很难明确区分,但仍然可以根据政策的重要性程度来评价政策质量要求的高低。比如,一些涉及城市发展全局、与市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决策,就可以在确保政策质量的前提下选择相应的公民参与形式。二是对于主要依赖公众执行的政策,可以适当扩宽公民参与的主体范围,吸收较大范围的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针对不同性质的政策问题,采取不同形式的公民参与,或者广泛吸收公众意见以便设计和选择政策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或者为赢得公众理解开展广泛的政策宣传与沟通,亦或弥合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分歧,最终为某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 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首先,要完善利益均衡机制。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的利益有关,公民参与行为亦不例外。当前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异常活跃的公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人们的利益意识的觉醒。若干地方公民参与中的“邻避”情绪,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担心居住环境质量下降、身体健康状况或者资产价值受损等,但各式各样的表象背后是极为重要的利益动机。“邻避”公共设施所具有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偏离”(金通,2007:79)特性,即社会上多数人获得的利益由设施附近的少数人来承担风险和成本的不对称状况,正是众多居民或组织采取集体抵制行为的主要原因。“公共政策源于利益关系的发展,而且其实质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进行配置的手段”(宁国良,2005:38)。因此,公共决策系统有义务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和健全利益均衡机制,协调公共政策所涉及的广泛对象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功能—过程的角度看,公共政策利益配置功能的发挥即是一个利益均衡过程,包括利益表达、利益协商、利益整合、利益分配与落实等一系列环节,均离不开有效的公民参与和民主协商。
其次,要完善重大决策风险控制机制。依据风险的性质和社会影响的差异,决策风险主要包括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与意识形态风险。在我国已完成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期,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自然成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风险控制的重中之重。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公民普遍的决策参与中夹杂着极为复杂的利益关系乃至利益矛盾或冲突,这种状况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决策风险。在新的传播环境中,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又极易在不经意间向公众传达团体行动意图,将公民塑造成潜在的行动者,并最终酝酿成群体性参与事件。特别是“高预期损失—高不确定性”的风险聚集类“邻避”设施的设置尤其如此。此类设施决策过程中,人们容易受到谣言、传闻以及对相关资讯曲解的影响,容易引发集体行动(陶鹏、童星,2010:65)。近年来,众多凸显“邻避”情绪的公民参与事件,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环境正义主题所开展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已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不能不引起重视。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将涉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纳入风险评估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专家评估、第三方评估以及公众评估等形式加强重大决策风险评估环节。在评估内容方面,则应以社会风险评估为重点。
第三,要完善和优化公民参与机制。“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科恩,2004:219)。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者首先应树立与公民分享权力的理念,建立开放式参与型公共决策机制。按照美国学者安德森的观点,除了政党、政府等官方政策制定者之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与公民个人等非官方的参与者都是政策产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安德森,1990:44-58)。要建立开放式参与型公共决策机制,首先要在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合理分配决策权力。对地方公共决策者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根据政策问题的性质,确定公民参与的适宜范围,并且采取恰当的形式吸纳公民参与决策。其次,要将公民参与融合到公共政策过程即议程设定、政策规划、公共政策决策、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中的每个环节。从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参与已经渗透到上述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传统“政府制定政策—公民按照政策意图执行政策”的公共决策模式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这已在多地“邻避”公共设施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在议程设定阶段缺乏市民特别是利益相关方充分的利益表达,政策规划、政策方案抉择阶段缺乏与市民的民主、友好、平等协商,政策出台之后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政策沟通以便赢得公众的支持与理解,这些都是最终诱发公民参与“邻避”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也是地方政府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安德森(1990).公共决策.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 [以]叶海卡·德罗尔(1996).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3] 邓新民(2006).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探索,2.
[4] 金 通(2007).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探析.当代财经,5.
[5] 迈克尔·X.德利·卡尔皮尼等(2011).给你信息,让你娱乐:新媒介环境下的政治.W.兰斯·本奈特、罗伯特·M.恩特曼.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6] [美]科恩(2004).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 宁国良(2005).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过程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8] 汤汇浩(2011).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中国行政管理,7.
[9] 陶 鹏、童 星(2010).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8.
[10] [美]约翰·克莱特·托马斯(2010).公共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美]戴维·伊斯顿(1999).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2] 钟 瑛、余秀才(2011).1998-2010年中国重大网络舆论事件与传播特征.
[13] 尹韵公(2011).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4] Denis J.Brion(1988).An Essay on LULU,NIMBY,and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ve Justice.BostonCollegeEnvironmentalAffairsLawReview,15(3).
◆
DifficultiesandChallengesinLocalGovernment’sPublicDecision-makingundertheBackgroundofNewCitizenParticipationMovement——Viewing on “NIMBY” Mood and Its Governance
LiuXiaowei(Doctoral Candidat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YaoDechao(Lecturer,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phenomen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mains widespread and significant in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field,forming a new citizen participation movement in Social Media Era.Codifying of NIMBY mood in City Public Management is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Chinese new citizen participating movement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imperfec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but also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optimizing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program.Currently,the primary task of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s to build up the idea of a share decision-making power with citizens,grasp the limi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asonably,and bring effectiv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to public decision-making;at the same time,further optimize the publ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round effective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quirements.This is not only the inner requirement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public decision-making,but also the realistic need of governing “NIMBY” mood.In the final analysis,the governance of NIMBY emotion is adaptive process of city government to improve public decision-making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new citizen participation movement;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decision-making; NIMBY mood
■责任编辑:叶娟丽
■作者简介:刘小魏,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9。Email:ellen1185@sohu.com。
姚德超,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