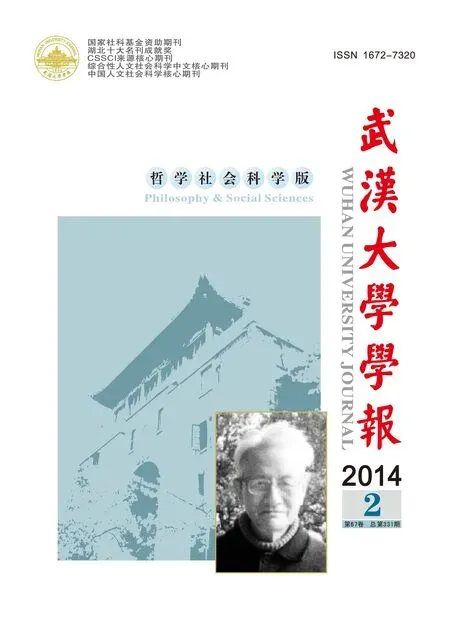论我国法定刑立法的改进与完善
——以明确性原则为视角
张建军
论我国法定刑立法的改进与完善
——以明确性原则为视角
张建军
法定刑是立法者在为具体犯罪配置刑种和刑度时所采取的方式,采取不同的法定刑立法,不仅会影响分则条文明确与否,而且会对司法人员能否准确、适当地裁量刑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法定刑是刑法立法必须重视与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由于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与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无疑是我国法定刑立法的理想选择。为了彻底贯彻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立法模式,有必要对我国现行法定刑立法进行审视、批判和改进。
法定刑; 明确性原则; 法定刑模式; 相对确定的法定刑
作为刑法分则条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定刑是刑法分则对各种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种与刑度,是法官据以量刑的依据和标准。法定刑不仅反映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态度,还反映国家对犯罪的危害程度的评价。所以,法定刑的设置要能够表明罪与罚之间质的因果性联系和量的相适应性关系。在刑法理论上根据法定刑的刑种、刑度是否确定为标准,通常将法定刑分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三种形式(高铭暄、马克昌,2011:326)。在这三种法定刑设置模式中,前两种模式处于法定刑坐标轴的两极,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克服了某些弊害,法官可以在法定刑范围内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相关因素选择相应的刑罚,有利于刑法目的的实现。毋庸置疑,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理应成为我国法定刑立法的理想模式,但也应当看到,我国刑法立法对这种法定刑模式的贯彻并不彻底,存在着诸多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少量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在笔者看来,有必要将后两种法定刑模式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 明确性:法定刑设置的一项基本原则
法定刑是立法者对犯罪定型所设置的量刑空间,它为法官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提供了相应的范围,决定着法官具体裁量的刑种和刑度,这就要求立法者对法定刑的设置必须清楚确定,以便法官量刑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刑法理论上,倡导法定刑设置的明确性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明确的法定刑是制约国家刑罚权的应有之义
权力具有不断蚕食或吞并其他领域的本能,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一个社会中最为能动易变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权力的危险始终存在。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种,刑罚权具有一切公权力扩张性、侵犯性、易受诱惑等共性,理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与规束。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司法机关只能依据刑法明文法定刑给犯罪人裁量刑罚。明确的法定刑犹如把刑罚权这匹野马导入规矩状态的缰绳,而模糊不清的法定刑则无异于使刑罚权这匹野马更加放浪的皮鞭。作为对具体犯罪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依据,清晰明确的法定刑为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标尺,可以减少刑罚裁量中的差别和随意。因此,只有法定刑的规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使立法者所设定刑罚圈成为防止司法专断与任意的鸿沟,使刑罚权在这道鸿沟面前望而却步、戛然而止而不致为所欲为。相反,不明确的法定刑难以划清刑罚轻重的清晰界限,容易造成国家刑罚权的擅断和恣意动用,为司法人员有差别地、随意地适用刑法预留下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样的法定刑不能为法官准确裁判刑事案件提供确定的法律标准和尺度,相当于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置于法官的癖性或偏好之下,其结果必然常常导致刑罚擅断或法外用刑,无异于为司法人员恣意侵犯民众的权益找到了形式上的依据,法官可以轻易依其主观好恶而随意地、有差别地对犯罪人裁量刑罚。同时,如果法定刑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使得一般民众无法理解其含义并预测行为的法律后果,那么法官在将这样的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只能按照自己对法定刑的理解作出相应的裁判,这样,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对此,有学者指出:“不明确的刑法不仅有使无辜者身陷囹圄的危险,而且由于它根据特别的、主观的基础,伴随着司法上任意的差别对待和应用法令或者含糊的基本政策的危险。”(卡威尔因,1989:231)所以,不明确的法定刑无法起到限制和规束国家刑罚权滥用的作用。对此,有学者曾指出:“那些对于犯罪的定义模糊不确定的刑法典,可以被当局用来给每一个批评者标上国家或宪法秩序的敌人的污名,并把它们拘禁起来,因而这种刑法典是与法治背道而驰的,并将侵害法律的确定性和表达自由等人权。”(托马斯·弗莱纳,2008:53)所以,不明确的法定刑可以使法官轻易地入人于罪,导致国家刑罚权不当侵犯民众自由和安全的恶果。
(二) 明确的法定刑是保障民众自由和安全的客观需要
不明确的法定刑不仅使民众无法正确理解法定刑的内容及含义,还使民众事先无法事先预测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导致民众对是否会受到出乎意料的刑罚处罚而焦虑不安。于是,为了避免横遭突如其来的、不可预知的国家刑罚权的侵扰与干预,民众在行动前就不得瞻前顾后、画地为牢而无所适从,因为对于刑罚无法预测的恐惧以及动辄得咎的结果,只能迫使人们在行动上自我设限,于是会产生国民因为害怕自己的行为不经意之间陷入法网而噤若寒蝉的“萎缩效果”( 黎宏,2008:53)。这样,民众的行动自由和安全就会因受到不当限制而缺乏起码的保障。正如罗尔斯所说:“由于一些法规的含糊不清而使无法律即不构成犯罪这一准则遭到了破坏,那么我们可以自由去做的事也同样是含糊不清的。我们的自由权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就这一点来说,自由权由于对它的实施的合理担心而受到了限制。”(约翰·罗尔斯,1991:261)所以,含糊不清的法定刑存在的结果必然是民众深感焦虑、恐惧和不安,就像边沁所指出的那样,模糊不清的法律就好像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危险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吉米·边沁,2004:190),这样的法定刑对民众的自由和安全无疑是一种威胁。
而明确的法定刑含义明白清楚,较少歧义,具有理解可能性,符合“事前告知原则”的要求,法官不得依其主观好恶而擅断。因此,明确的法定刑为国家刑罚权划定了清晰的触角范围,使刑罚权不得逾越法律所预设的界限随意而动,从而为民众阻隔了来自于不确定的刑罚的危险和侵害,使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有了可靠的边界,民众于是可以放心大胆、无所恐惧地开展其生活。因为“如果多一分法律规定与适用的明确性,就会少一分法官个人的主观意识、政治倾向、个人因素等对犯罪和刑罚的影响。”(陈忠林,1999:25-26)此外,明确的刑法规范具有预测可能性,等于为民众提供了一张清晰的罪刑关系“价目表”, 民众可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据此预知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助于保障民众在行动上享有广泛的自由。“对于人民而言,刑法的存在固然是入罪的标准,但另外一方面同时也是人民自由权利的保证书。这里所谓的自由,除了是不受刑罚的自由之外,更重要的是展开其快乐生活的自由。”(黄荣坚,2004:11)在这个意义上,明确法定刑才真正具有一般民众的“大宪章”的作用。而有了明确的法定刑,即便行为人因未能自制而误蹈法网,他也会对自己行为可能的结果有大致确定的预测与判断,能够合理预见将会受到何种刑罚的制裁,因为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任何人只承受刑法为其行为所事先规定的法定刑,而不受刑法之外的任何不正当刑罚。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明确的法定刑具有犯罪人的“大宪章”的功能。
(三) 明确的刑法规范是刑罚后果严厉性的必然逻辑
从本质上讲,明确性是立法语言应当具有的基本品性,任何法律规范都应该足够清晰和明白。不过,由于不同部门的法律其内容和属性不同、制裁手段有别,对民众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有的仅是一般性影响,有些则是根本性影响,故此不同的法律对明确性的要求有弱有强。一般而言,所处分的权利越重要,所规定法律后果越严厉,法律的清晰性要求便应当越高。由于私法强调“私法自治”、尊奉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私法是任意法,任意性规定是私法规范的主体,这就使得在民法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概念和概括性条款,如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等等。相对于私法而言,公法与公权力的行使有关,为了避免和防止公权力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侵略性和恣意性,以及由此可能给民众带来的不当强制与侵害,需要通过清晰明确的立法,对公权力的行使划定清晰的疆界并设置严格的程序。因此,从总体上而言,公法对明确性要求更高。而在公法中,刑法所调整的是国家和犯罪人之间因犯罪而引起的以国家行使刑罚权、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为基本内容的一种权力支配与服从关系,加之刑罚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严厉的强制性: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自由和资格,而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可以说,刑罚关乎犯罪人的生杀予夺。像这样严厉的强制性,是其他法律如民法、行政法所不能比拟的。对此,有学者指出:“刑法规定的法律效果系所有法律规范中最为严厉而具痛苦性、强制性与杀伤性的法律手段。”(林山田,2006:58)
“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和痛苦,是刑罚的本质属性。”(高铭暄、马克昌,2007:237)正因为刑罚是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强制措施,是非战时期国家手中最厉害的权力。刑罚对犯罪人带来的剥夺和痛苦可谓创巨痛深,对犯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既强烈又深远,日本刑法学家西田典之指出:“刑罚这种制裁具有强制力,它同药效大的药物一样伴有副作用”(西田典之,2007:23)。用之稍有不当,则国家和犯罪人就会两受其害。人类历史的发展已证明,保护社会最得力的工具常常也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罚尤其如此。为了发挥刑法的制裁力并防止刑法被滥用,刑罚权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这就要求为法定刑设置确定的界限。而“精确的刑法规定,就像一把精确的尺子,可以用来厘定国家和社会在使用刑法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中的各种要求,由此满足保护人权和发展法治的种种需要。精确的刑法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确的刑法规定,就是在为社会及其成员规定精确的自由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确的法定刑就是为规束极具强制性和严厉性的刑罚权而设。
二、 消除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按照通说,我国刑法中没有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16页;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页。。因为在这些论者看来,所谓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系指刑法条文对某种犯罪不规定具体的刑种和刑度,只笼统地规定对该种犯罪应予惩处。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待商榷,因为法定刑的内容无非包括刑种与刑度两个方面,既无刑种又无刑度,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定刑的存在。既然法定刑都不复存在,何来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之说?因此,“刑种和刑度全无的‘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既不符合法定刑的定义,也与法定刑的‘法定性’相矛盾”(周光权,2000:76)。况且,退一步讲,如果出现既无刑种又无刑度的情况,则应认为该条文规定的行为并不成立犯罪,因为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所以,通说关于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的说法是值得质疑的。
事实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种类有九种,除驱逐出境、无期徒刑和死刑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外,其余六种刑罚均具有可分割性。而就这六种可分割的刑罚方法来看,除了罚金刑以外,其余五种刑罚的上限和下限在刑法总则中都有具体或大致的规定*如管制刑的幅度是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刑的幅度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是6个月以上20年以下;剥夺政治权利的通常期限为1年以上5年以下;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申言之,这五种刑罚不存在幅度上不确定的情况。因此,即便分则条文在对某一具体犯罪设置法定刑时,并未对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的范围和幅度作出明确的限定,也不能认定这些法定刑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因为总则已为这几种刑罚方法划定了相应的最大、最小幅度。法官在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时候,只能在总则限定的上、下限幅度内确定,而不能突破总则所设定的界限。罚金则不同,它虽然是一种可分割的刑罚方法,但总则中并未就其可裁量的幅度作出相关规定,只是在第53条中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因此,如果分则条文中只是规定,“犯……罪,判处罚金”,那么,究竟判处多少数额的罚金,在什么幅度内判处罚金,都是极其不确定的,申言之,这样的规定一种仅有刑种而无刑度的法定刑。而“‘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实际上只意味着某一犯罪有刑种,而无刑度,即刑度完全不确定。”(周光权,2000:76)所以,我国刑法中存在着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具体而言,抽象罚金制(或无限额罚金制)就是其适例,即刑法只抽象地规定判处罚金,并没有规定罚金的具体或大致数额。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单位都是只抽象地规定判处罚金,譬如《刑法》第140条、第15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151条规定的走私武器、弹药罪等,都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至于对单位判处多大数额的罚金,则语焉不详,没有相应的幅度,由法官掌握,造成相同的案件由不同的法院或相同法院的不同法官进行裁量,最后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也有一些对自然人犯罪只抽象地规定判处罚金的立法例,譬如第318条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54条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等等。所以,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抽象罚金实际上是一种只有刑种而无刑度的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对具体案件中的犯罪人判处多大数额的罚金,并无相应的范围限制,完全由法官确定和裁量。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精神意蕴是相悖的,明确性原则既要求构成要件的明确性,也要求法定刑具有明确性,抽象罚金刑制既无法使民众预先预测和判断罚金数额的大致幅度,也不能为法官提供据以遵循的裁量标准。因此,基于刑法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应该结合具体犯罪的特点,将我国刑法中的抽象罚金制修改为比例罚金制、倍数罚金制、特定数额罚金制或者日罚金制,以实现法定刑设计模式由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向相对确定的法定刑转化。
三、 改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
就我国刑法对法定刑的设置来看,存在至少7个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它们分别是:《刑罚》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后段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绑架罪后段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后段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317条第二款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规定,对“暴动越狱或者聚众持械劫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第383条第一款第(一)项贪污罪、第386条受贿罪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难看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基本上都是重刑,反映了国家对极少数严重犯罪行为给予严厉打击的态度。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意味着只有一个刑种,且法定刑的最大量与最小量重合,其幅度为零。故其明确性自不待言,而且可以说,它是法定刑配置模式中最具明确性的一种。但是,由于这种法定刑的刑种刑度确定唯一,刚性太强而缺乏灵活性,不具备在特定情况下变通的可能性和选择伸缩的余地,致使法官难以做到量刑适当,不利于贯彻刑罚个别化原则,在有的情况下难以收到良好的刑罚效果,甚至会出现对犯罪人的处罚显失公平的现象。例如,我国刑法第239条后段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由于绑架罪不仅严重侵害了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与行动自由,而且可能同时侵犯了被绑架人近亲属或其他人的财产权利及其他权利,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所以,在犯罪人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况下,对其直接规定和适用死刑是妥当的。但是,现实中若出现犯罪人在实施捆绑行为时因疏忽大意而捆错了部位、或被害人挣扎而导致被害人窒息而死亡的情形,此时犯罪人并无杀害或伤害被害人的故意仍对其适用死刑,则明显对犯罪人过于严厉。马克昌先生就此曾指出,“将致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规定同样的法定刑,就致被绑架人死亡而言,显然罪刑关系不相适应,应当加以修改”(马克昌,2008:14)。笔者以为,修改的方案之一就是将该条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改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此外,从理论上讲,故意杀人罪是各国刑法中最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的一种,绑架罪最严重的后果也是杀害被绑架人。所以,立法者在为这两种罪配置法定刑时应维持一定的均衡,既然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不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且其最高量刑幅度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法定刑就不能超越故意杀人罪的最高法定刑幅度。职是之故,法定刑的明确性仅仅是相对的,即它只能为法官的刑罚裁量活动提供一个判断的大致而非精确标准。法定刑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刑罚绝对明确,一种犯罪或一种犯罪情节只对应一种刑罚,且该刑罚的幅度绝对确定,没有任何可自由裁量的空间。事实上,“法定刑的明确性往往只意味着它所提供的法定刑是基本确定的、大致清晰的而非含混或完全不着边际的。”(周光权,2000:46)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性而务实的认识,笔者以为,我国刑法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使用的有些过量,故有必要通过立法加以改进,改进的思路就是将我国刑法中的7个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改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 结 语
如果刑法对刑罚的规定不明确,完全交由法官决定,那么关于构成要件的规定不论多么清楚,明确性原则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民众自由和安全的功能则不可能真正发挥,因此,法定刑的明确性无疑是明确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刑罚明确性的总体要求是,立法者对每一具体犯罪法定刑的种类和幅度的规定要明确,也就是说,作为法定刑,必须有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如果刑法对某种行为并没有规定刑罚,那么,根据“没有法定的刑罚就没有犯罪”的原则,该行为便不是犯罪。事实上,如果刑法只是规定对某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没有规定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司法机关因为没有适用刑罚的标准,也不可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张明楷,2007:32)。所以,倘若只规定行为应受处罚,或者虽规定刑种但没有规定刑度,将具体的刑度委任给法官进行裁量,即在仅仅规定“绝对的不定刑”或者“绝对的不定期刑”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应当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控方无法求刑,辩方亦无从请求宽恕,完全由法官裁量,这和明确性原则的要求是相违背的。此外,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表面上似乎更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但在实践中的每一个具体犯罪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违法程度与责任程度,而可以涵摄到某一刑法规范之下的个案,其情况可能有无数多种,犯罪的情节、后果、目的、行为人一贯的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千差万别,不可能完全相同。申言之,具体的犯罪行为与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之间并不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如果刑法对某一行为类型的法定刑作了单一明确的规定,并无一定弹性的刑度空间,反而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亦即由于法官没有伸缩回旋的余地,对于重罪却无法重罚,对于轻罪做不到轻罚,有碍于个别公正的实现,在实践中只会造成实质的不平等。所以,从刑事政策上看,这种法定刑模式也是不妥当的,并不为各国刑法立法所采用。如1791年《法国刑法典》曾对每一犯罪都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取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防止司法专横,但实际上是立法者越粗代庖。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是生动具体、千姿百态的,这种没有任何裁量余地的法定刑,既不利于控辩双方进行合理的辩论与对抗,也不利于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刑罚。因此,1791年《法国刑法典》未及实施,便很快被1810年《法国刑法典》所代替。由此可见,在法定刑的明确性问题上应该避免两种绝对化的情形——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兼采这两种绝对法定刑的优长,并有效克服了二者的弊害,为具体犯罪规定了一定的刑种、刑度,既不失其明确性,又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可以在法定刑的范围内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公正的裁判。不过,为了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必要对法定刑的幅度作出必要的限制,这就要求立法者所设置的法定刑的幅度不宜过大,因为幅度过大的法定刑不仅可操作性差,有时会被法官任意解释和不恰当地运用,导致量刑畸轻畸重。总之,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和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往往会造成许多弊端。因此,“法律效果之明确性也只能在法律之规定与法官之裁量,彼此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林山田,1978:13)故刑法对法定刑的明确性与构成要件之明确性的程度要求并不完全相同,构成要件之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对每一个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应当尽量予以详细的规定;而法定刑之明确,则要求立法者规定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不求刑之绝对确定(曲新久,2000:402)。
参考文献:
[1] 陈忠林(1999).意大利刑法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高铭暄,马克昌(2007).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3] 高铭暄,马克昌(2011).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4] 黄荣坚(2004).基础学法学:上.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5] [英]吉米·边沁(2004).立法原理.李贵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6] [美]卡威尔因(1989).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7] 黎 宏(2008).日本刑法精义: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8] 林山田(2006).刑法通论:上册,增订九版.台北: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部.
[9] 林山田(1978).刑法特论.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0] 马克昌(2008).刑法三十年反思.朗胜,刘宪权等.改革开放30年刑事法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1] 曲新久(2000).刑法的解释与范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 [瑞士]托马斯·弗莱纳(1999).人权是什么?谢鹏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 [日]西田典之(2007).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 [美]约翰·罗尔斯(1991).正义论.谢廷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5] 张明楷(2007).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6] 周光权(2000).法定刑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
OnReformandPerfectionofStatutorySentenceinChina——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Principle of Clarity
ZhangJianjun(Associate professor,Gansu Political and Law Science Institute)
The model of statutory sentence is the form taken by Legislature of kind of penalty and range of penalty for the specific crime.The different model of statutory sentence,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explicitly or not,but also will hav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sentencing,so the model of statutory sentence is a problem when the legislature must pay attention to and take seriously.Because of the absolute determination of statutory sentence and the absolute uncertainty of statutory sentence has the congenital defects in innate,the relative determination of statutory sentence is undoubtedly the ideal legislation mode of statutory sentence.In order to thoroughly carry out the model of relative determination of statutory sentence,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criticize and improvement of statutory sentence in China.
statutory sentence; the principle of clarity; the model of statutory sentence;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statutory sentence
■责任编辑:车 英
■作者简介:张建军,《甘肃政法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法学博士;甘肃 兰州 730070。Email:gszjj197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