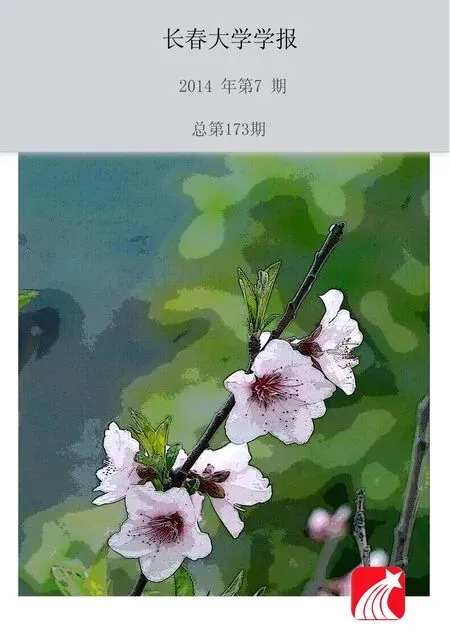从泰戈尔莫言现象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张毅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从泰戈尔莫言现象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张毅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泰戈尔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东方乃至世界文坛有着深远影响。他们文学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于在本土文学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坚守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在文化杂糅时代对本民族文学的扬弃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认同,本土与外来的结合,使他们作品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书写则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对其民族文学拔秀于世界文学之林具有非凡的意义。泰戈尔和莫言现象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文化参考。
泰戈尔;莫言;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普世价值
印度诗人泰戈尔和中国作家莫言相隔近一个世纪,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他们的写作题材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获得了西方文坛的认可,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成为东方和中国的“第一人”。东方国家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其话语仍处于弱势地位。在文化地位不平等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文化如何开辟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呢?本文通过探究两位作家的共同性,为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提供借鉴。
1 文化自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文化自觉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立足世界的基石。泰戈尔和莫言的成功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创作都坚持了东方文化的特色,都扎根于自己的土壤,从而都展现了东方文学文化中令人赞叹的一面。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在写作内容上,还是创作手法上,都浸润着东方气质,而这些独特的气息恰好与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相一致。
庞德曾夸赞泰戈尔的诗歌有宁谧之感,使得他想起西方烦恼、喧嚣和尖叫中被忽视的许许多多东西[1]。诺奖委员会在他的授奖辞中也着重强调了这点:
与一切无力的仓促忙乱相对照,他(泰戈尔)把这样一种文化置于我们面前:这种文化在印度广袤宁静而又秘藏着珍宝的森林里臻于完善。是在同自然生活本身的日益和谐当中,主要追觅灵魂宁静祥和的一种文化。[2]163
这种文化为西方世界带来新的精神净地,他们将东方文化视为宝藏,并将泰戈尔视为福音的传播者。诗人叶芝在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作序时就曾指出,泰戈尔的诗歌具有文化传承性,将“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传下来”[3]。正是这样的诗歌为他展示了一个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因而,将泰戈尔称为印度文化的传承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在泰戈尔的诗中,我们会读出异国风情和民族特色。泰戈尔热爱并乐于学习民间文化,他的诗歌深受印度古典文学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泰戈尔将说唱艺人天然淳朴的话语加以整理、完善,把民间粗糙的格律形式升华为美妙的音律,他还在孟加拉现代抒情诗中引入梵文诗和中世纪毗湿奴颂诗,并将风俗民情和神话传说融入其中。他的爱情诗,就采用了方言口语将恋人慌乱、羞涩、兴奋的心态描写得细腻真实,富有孟加拉地区特有的情趣和色彩。他的哲理诗,以祖国的山河草木、暮云繁星为依托来阐释东方思想。他的宗教诗,渗透着印度神我合一的思想,鼓励人从狭小的世俗樊笼中解放出来,以脱俗的眼光看待纷繁的世事。无论哪部作品,泰戈尔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展现的东方传统文化特色,都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西方读者。
莫言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才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4]。一语道破玄机。他的作品来自于生活,尤其是他早年的记忆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刻。在他小的时候,他曾饱尝饥饿的滋味。有次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莫言和其他孩子不知煤是何物,竟饿得扑上去抢着吃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他根据“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写出了《红高粱》;结合山东“苍山蒜薹事件”和自己四叔的遭遇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以自己生产队里一个单干户为原型构思了《生死疲劳》;把农民孙文率众扒胶济铁路的故事升华成了《檀香刑》;将自己堂姑一生的经历改编成了《蛙》;以母亲的伟大人格为写作灵感酝酿了《丰乳肥臀》……他直逼中国历史和现实,并在写作中触及了别人不敢写的敏感话题,无意间抓住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
莫言坚守民族性,注重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味和延展。他的作品中有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有戏剧的篇章,也有话剧的结尾。他写《生死疲劳》,就是为了恢复古典小说中“说书人”的传统,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5]。对莫言而言,中国文化是他创作的源泉和根基。莫言的同乡、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蒲松龄,对莫言影响就尤为深刻。莫言的家乡高密距蒲松龄的家乡淄博三百多里,他就是听“聊斋”故事长大的。莫言在《学习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中曾暗示过蒲松龄对他文学上的启发和影响。因而,读者会在莫言身上发现蒲松龄的影子。莫言也善于说故事,敢于想象。他的作品中“驴和猪的声音淹没人声”,神魔鬼魅、奇人奇事轮番上演。他的小说还蕴藏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具有促进社会道德的功能。因而,西方读者不仅可以从莫言恢宏的想象里获得趣味,又可以从无情的批判中深受启发。
2 文化认同:“国界”不存,方寸海纳
泰戈尔和莫言都具有国际视野,都善于吸收他国优秀文学文化成果,都善于将异国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同时,当自己的作品被译介到他国时,他们都能够较多地为目标语读者考虑,并不对译文有太多苛求,因而他们的作品更容易被西方接受。传统和外来文化的相融合和再创造,不仅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写作风格,也让其作品更添光彩,从而引起世界范围读者的广泛关注。
泰戈尔与中国学者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在某种程度上缘于泰戈尔的作品中与众不同而又并不完全陌生的文学特质。谢冰心曾在学校图书馆的架子上发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新月集》以及其他诗歌,她十分欣喜,觉得欣赏那些清新流畅并充满了东方韵味的诗歌,就仿佛在沿着山路漫步时发现了一簇幽兰。的确如此,泰戈尔诗中的东方气质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曾有意模仿中国古代的诗歌,取其长处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泰戈尔不仅学习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学精华,还吸取了西方文学的优秀之处。他在14岁时就翻译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并于1878年赴英国留学,后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接受英国教育。他涉猎广泛,但丁、莎士比亚、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济慈、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他都十分熟稔。对于宗主国的西方,他没有一味抵触,而是认可了他们文明中值得学习的方面。因而,他的译本或者说再创作是接近西方文化的,更容易被异质文化所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泰戈尔和莫言有些不同,他既是作品的创作者,同时也身兼翻译者。由于他本身就是英语使用者,因而他可以较好地表达自己创作的初衷,使译文有较高的可读性。而且,他还能够适时地对自己作品作出调整,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和学习了西方文学的精华。他借鉴了英国诗歌,写出了十四行诗如《生命》等佳作。在20世纪30年代,泰戈尔还着力于另一种外国诗品即散文诗的写作。他将部分有韵的孟加拉诗歌翻译成了英语散文,在翻译过程中,他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审美需求,对原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写。不仅如此,他将诗歌格律打破,使得他的诗歌可以用无拘无束的形式表达出诗人在其他形式中难以描述的情感。东方之美经泰戈尔恰当得体的改造,被添上新的“衣饰”后,不仅增添了东方文学的价值,也丰富了西方文学世界,并为泰戈尔打开了快速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
莫言的作品吸引着广泛的读者,他的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西班牙、希伯来、瑞典、挪威、荷兰等多种外语,并赢得了多种世界文学奖项。莫言创作伊始,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大量西方文学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莫言与同时期的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正处于严重的阅读饥渴中,于是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疯狂地阅读”,因此他彼时及后来的小说创作,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来。在莫言列出的十个最喜爱的短篇小说中,有显克支微、阿斯图里亚斯、乔伊斯、劳伦斯、马尔克斯、福克纳、屠格涅夫、卡夫卡等8位西方国家的作家。他们的小说中,有的是莫言在年少或年轻的时候就已读过的。在莫言创作的初始阶段,他曾对自己喜爱的写作风格和创作手法进行模仿。其中,福克纳被莫言视为文学上的知音和恋人,他让莫言坚定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对其走向文学这个想象的王国起到了启蒙和鼓励的作用。莫言曾在一篇回忆性散文中说:“当我得知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时,我立刻感到受了巨大的鼓舞,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也去创造一块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6]莫言运用并融合西方写作手法,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更好的载体。他的文学之路也离不开世界文学这个大的背景。吸纳西方文学的元素使得莫言更容易为外国读者所接受,从而使得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认可。
莫言与泰戈尔一样很重视自己作品的翻译,但莫言不懂外语,他的作品要靠翻译家们的迻译才能传到国外。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莫言十分尊重翻译家的劳动,能够意识到西方和东方在文学、文化上的不同。在对待译文上,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甚至会主动积极地要求翻译家作适当改动。葛浩文的译文实际是中国文化“译出”的表现,谢天振在以莫言获得诺奖为个例谈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时说过:“‘译出’是要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要让人家能够接受,要在别的国家和文化圈里得到传播、产生影响。”[7]23在说到翻译对莫言的影响时,谢天振认为:“假如莫言的作品在翻译时仅仅注重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是由我们国内的出版社翻译出版,那么莫言有没有可能获得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我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7]22因而我们可以说,莫言是聪明的作家,他懂得如何“推销”自己的作品和文化。此外,莫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译性,这也是他与国内其他作家的一些不同之处。翻译家陈迈平就曾作出过这样的评价:莫言的作品就很像“水墨大写意”,“大写意可能很容易展现,西方人也更容易接受。他们有‘虚幻现实主义’这样的参照物。可精雕细琢的花鸟工笔画,他们还真不一定喜欢。”①《1000本,终于卖光——莫言在瑞典的三部小说》,南方周末,2012-10-18。国内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十分忠实的译文才能保留其文章的魅力,如此一来,便不利于文学作品的传播。
3 普世价值: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
泰戈尔和莫言都尤其关注人性。尽管他们作品的主题和艺术表征大相径庭,但他们都赞美了人性之伟大,构筑了文学的精神内核,使得他们的作品超越了故事本身,成为人们渴求的精神粮食。更重要的是,泰戈尔和莫言对人性的描写各有侧重,并且是应时之需的。
对于泰戈尔来说,“文学的内容是人心和人性”[8]5,“培植富于个性的情感,让个人的情感成为所有人的情感,就是文学”[8]14。在泰戈尔的作品中,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精神品质和思想感情贯穿始终,这些人性之美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桥梁。正如诺贝尔授奖词所说的那样,他的诗歌绝不是异国情调,而是具有真正的普遍人类品格[2]161。这一品格的重要体现便是人们心中的爱。泰戈尔对形形色色的爱进行了细微的描摹。例如,他的《吉檀迦利》体现了泰戈尔对神的爱和虔诚;他在小说《戈拉》中,通过主人公的思想表达了他反对宗教斗争的态度,认为印度教、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没有任何对立,宗教的根本意旨在于爱;他的《新月集》描写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表现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骨肉深情;他的《园丁集》展现了恋人之间的爱,读者可以从中品味到爱情的纯真美好。泰戈尔作品中的这些爱,体现了泰戈尔聚焦人性、宣扬人性中美好一面的思想。
莫言也一直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作,十分注重文学作品中的普世价值,并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9]。莫言的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渗透着人性的文学作品,并深入到人的内心最深处。就像《蛙》中暗含的一个问题一样,人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内心深处的私欲,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许多人为了升官便不敢多要一胎,表面上看似是维护国家利益,但实际上是为了个人私欲。因而,计划生育的问题触及到了莫言那一代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莫言就是这样将小说回归人性,从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层面上的描写。
然而,泰戈尔和莫言在人性书写中又各有特点,他们对人性的宣扬正符合了他们各自时代的审美特征。泰戈尔注重对美的渲染,在他的作品里,处处闪现着人性中的善意和美好。他的《吉檀迦利》描写的神具有人心、人情、人性、人品,就连自然都具有人的“善意”。泰戈尔宣扬神的高尚,其实也在强调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他想通过人神合一的思想,将世界引向和谐统一;希望用爱的力量在纷乱的世界中实现协调,使喧哗的社会变得宁静,让罪恶中生出善,使生之琴弦奏出和谐的乐声[10]。因此,跨越国家、种族、宗教、性别和地位的广泛的爱,是泰戈尔作品的核心。我们在他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中都看到他充满爱的思想。他用自己的作品试图唤起人们心中的爱,来填补种族宗教国家之间的仇恨,最终实现和平。这种爱在物质欲望膨胀的西方看来是弥足珍贵的,这些思想无疑有利于缓和社会种种矛盾。
与泰戈尔不同,莫言毫不避讳地描写丑,并描写了苦难之下人性的弱势和沦丧,无情地揭露了美表面下的丑恶,并对伦理问题作出深深的拷问。因而,莫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当下关怀,他作品中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的美德和对违背这些美德的恶行的批判和谴责”[11]。他反映了真实完整而非二元对立的人性,即丑和美、善与恶的共存。他把人当现实中的人来写,将一个人格中高尚和缺憾的多个方面展示无遗。例如,《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为了追求与戴凤莲的爱情,大胆杀人放火。“我爷爷”既是野蛮的,也拥有敢爱敢恨的坚毅。《蛙》中的“姑姑”由“送子娘娘”变为“杀人妖魔”,她一方面在执行计划生育国策,为国卖命,另一方面又扼杀了生命,违背了为人母的本心。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以兽的视角窥探人性,将人心冠以兽形,将兽心冠以人形,揭示并批判了人性中的丑恶面,赞美了人性中善良纯朴的一面……莫言在完整地展现人性时的剽悍,是不同于余华的残酷和苏童的阴郁的。他“用绮丽、死亡、酷刑、神性、魔幻、哀怨共同播种,随之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巨大庄稼——颗粒丰满,早就超越了它同类所应该有的体积,数量繁茂,成为了目力所及范围内最浓密的”①《“容量”最庞大的写作者》,南都周刊,2012-10-17。。也就是说,莫言用最有力、最直接的方式揭示了人性。也正是这种方式提醒了我们,在这个和平安逸的年代提防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
总之,泰戈尔和莫言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创造性地发展诗歌、小说等这些早已成熟了的文学样式。他们从辽阔的东方厚土中汲取营养,从西方的诗学、魔幻现实主义等小说写作手法中探寻解决现代社会和精神危机的有效途径,最后转向人的内心深处寻求新的答案。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代中国,关注泰戈尔和莫言现象,在文化的视域下挖掘泰戈尔和莫言作品中的文化特质和美学蕴含,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大框架下,探寻其作品的当下意义,更深刻地了解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与当下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关联。此外,我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出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文坛如何涌现出更多耐人寻味的优秀作品,这都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必须面临的问题。本文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我国有志之士和方家提出更好的建议。
[1]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M].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
[2]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上[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泰戈尔.吉檀迦利:献诗集[M].吴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朱振武.文化自觉与文学伦理批评的当下意义[N].文艺报,2013-03-22(4).
[5]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J].当代作家评论,2006 (2):155.
[6]莫言.会唱歌的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7]王志勤,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J].学术月刊,2013(2).
[8]泰戈尔.泰戈尔谈文学[M].白开元,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莫言.优秀的文学没有国界: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J].散文选刊,2010(4):50.
[10]彭端智.不着泥土的痕迹没有痕迹的足印:介绍泰戈尔的《飞鸟集》[J].外国文学研究,1982(1):87.
[11]莫言.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J].艺术评论,2010 (6):82.
责任编辑:柳克
On the Export of Chinese Culture by the Analysis of“Mo Yan and Tagore Phenomenon”
ZH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October 11th2012,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nd became the first man who wins this prize with Chinese nationality.While a century ago,Rabindranath Tagore was also the first man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in the East.Their achievement proves that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has won its own place in the world literature.However,with the inequality existing between the ea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how can these two eastern writers won the prize?In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prosperity,we may find some enlightenments from these two writers about how to help our culture go out.Firstly,these two writers adhere to themselves and have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awareness,and they show the unique beauty of the east;Secondly,they both take in the essence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which makes their works more understandable for the westerners;Thirdly,there are universal human nature described in their works so that the works can go across borders.
Rabindranath Tagore;Mo Yan;cultural awareness;acceptability of culture;universal value of literature
I1-19
A
1009-3907(2014)07-0942-04
2014-02-25
张毅(1989-),女,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小说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