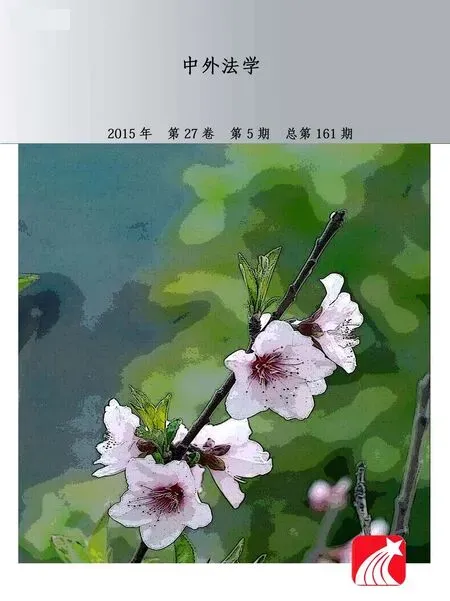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规范体系
马 宁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保险合同现代化与我国立法的完善研究”(15BFX176)的成果。
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规范体系
马 宁**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保险合同现代化与我国立法的完善研究”(15BFX176)的成果。
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在保险背景下因成本过高而未能有效实现保障意思自治的目标,因而亟待转向以内容控制为主的模式。后者以维持给付均衡为价值取向。但是,保险的技术性与团体性也赋予了给付均衡更丰富的含义。据此而建构的内容控制规范应主要作用于背离任意性规范的非核心给付条款,特别是涉及远期不确定风险的条款。在控制范式上,宜采取抽象表述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方法,并考虑保险特质与我国实务,构建具有开放性的多层次不公平条款判断标准。
格式条款 信息规制 内容控制 核心条款 判断标准
一、保险格式条款的规制路径:从信息规制向内容控制的转向
格式条款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私法世界的原有面貌。自由选择和双方合意的契约自由之应有内涵时常面临缺失的尴尬,以程序正义实现实质公平的契约自由之目标凸显实现不能之虞。对此,传统契约法的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救济措施力有未逮,各国遂开始以信息规制或内容控制的方法应对。前者侧重于从程序控制的角度消弭格式条款相对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对条款制定方课加信息提供义务。〔1〕参见邢会强:“信息不对称的法律规制——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若其未能善尽义务,则格式条款不纳入合同。后者则直接控制格式条款的内容,即通过司法审查事后确认诉争格式条款无效。〔2〕合同解释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规制作用。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845。但两者并非绝对排斥,多数国家均兼采两种路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3〕参见解亘:“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
或许是基于对私法优越性的信奉而尽力维护其纯洁性的需要,我国私法学者多对内容规制持怀疑之态,而更青睐于信息规制。“若信息规制能够确保意思自治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则可以减少内容控制的介入频率和范围,使之仅对信息规制失灵起‘补缺’作用……以免内容控制喧宾夺主。”〔4〕马辉:“格式条款信息规制论”,《法学家》2014年第4期。这种倾向也蔓延至保险领域。作者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7条(保险人说明义务)、《保险法》第19条(不公平条款内容控制)、《保险法》第30条(不利解释)为关键词,查询到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相关判决数各为2523件、136件、64件。关于第17条的论文数量也明显占优。〔5〕作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自2009年至2015年,全文中出现“保险法第17条”的文献有239条,出现“保险法第19条”的68篇,出现“保险法第30条”的100篇。再考虑到说明义务自1995年即已存在,而第19条是2009年添加的,即可管窥二者受关注的程度。这表明,理论与实务对通过保障投保人〔6〕严格来讲,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缔结合同,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二者常为同一主体,因此英美法系常用被保险人指代投保人。除非特别指出,本文也不区分二者。知情权以贯彻意思自治的说明义务体现出明显的偏好,〔7〕曹兴权教授在统计了约2500件保险纠纷后,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参见曹兴权、罗璨:“保险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二维视域——弱者保护与技术维护之衡平”,《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而直接控制合同内容,旨在维持给付均衡的第19条则受到冷遇。〔8〕《保险法》第19条源于《合同法》第40条,是一种针对引发权利义务失衡的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规范。参见王静:“我国《保险法》第19条司法适用研究——基于保险格式条款裁判的实证分析”,《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1期。
但是,说明义务的适用却远未达到预期效果。罗璨博士统计了从2009年《保险法》实施至2013年1月6日涉及说明义务的案例348件,保险人仅胜诉14件,败诉334件,败诉率高达96%。在败诉的案例中,有247件称保险人未提交已履行说明义务的证据。其余的87件,法院仍以包括投保人未理解在内的各种理由判定保险人败诉。似乎只要投保人主张免责条款无效,都会得到法院支持。〔9〕参见罗璨:“保险说明义务程序化蜕变后的保险消费者保护”,《保险研究》2013年第4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颁布后,这一乱象亦未明显改观,实践中仍然存在大量保险人因未能举证而败诉的案例,〔10〕例如,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速民终字第1813号判决书。证明已履行义务而败诉的案例中,法院以保险人承担责任为目标的裁判导向依然清晰可见。〔11〕例如,有法院扩大了保险法解释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安徽省宣城市中院(2013)宣中民二终字第00088号判决书即称,条款中癌症含义的规定属于免除责任,也需履行说明义务。“毫不夸张地说,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投保人滥用权利的挡箭牌”。〔12〕吴勇敏、胡斌:“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理论分析也证明,作为信息规制载体的说明义务无法承担起保险格式条款规制的核心重担。信息规制的目标是,确保微观交易中的知情决策,使合意更好地实现,进而形成宏观竞争秩序中对格式条款的外部约束。而说明义务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无法以合理成本达成前述目标。行为法律经济学揭示,受制于信息成本与认知局限,个体在作出决策时不可能将决策涉及的所有信息(交易的全部条款)纳入考量范围,并根据各个条款之于自己目标的满足度确定其在考量中的关注度,而是表现为一种基于不完全信息的简化决策模式。〔13〕See Melvin A.Eisenberg,“The Limits of Cognition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47 Stanford Law Review 211,214-216(1995).毕竟,人在特定时间内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再者,决策者同样受制于信息成本。即便获取了全部信息,他也会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在最大化决策收益与最小化决策成本间寻求平衡。〔14〕马辉,见前注〔4〕,页114-115。
信息成本通常包括信息获取和处理成本。保险人提供保险条款,以及对条款的说明被立法视为投保人获取决策信息的主要途径。为此,立法特别要求保险人对免除其责任的条款进行提示和主动解释(即明确说明),以便于投保人准确了解保险责任范围,避免分散特定风险的缔约目的挫败。然而,除标示为“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以及《保险法解释二》扩充入说明范围的免赔额(率)、比例赔付条款外,保险人还能通过其他手段修改承保范围。如责任分摊与责任竞合、赔偿处理方法等。〔15〕参见马宁:“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再者,保险法对说明义务的两分法是建立在其认为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权益影响更大基础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诸如保险给付办法与争议处理等准权利义务条款,以及保费缴纳、风险维持等权利义务条款直接决定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是否承担以及承担多大的责任,对当事人的影响不亚于免责条款。显然,立法若想消减信息偏在,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不仅要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理解为合同中一切可限制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规定,还应将对投保人影响甚大的权利义务与准权利义务条款、释义条款、特有条款纳入说明范围。这几乎涵盖全部条款类型,〔16〕保险条款可分为公共条款、准权利义务条款、权利义务条款、释义条款、特有条款五类。见吴勇敏等,前注〔12〕,页91-92。成本之大难以想象。保险为射幸合同,保险责任的触发取决于小概率的保险事故的发生,因此,保险人宁可在事故发生后承担不履行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也不愿依照规定逐个履行说明义务。这也可解释为何实践中存在如此众多未能证明已善尽说明义务的事例。
就信息处理成本而言,保险条款冗长复杂,极富技术性。即便保险人愿意善尽说明义务,欲使投保人完全理解条款也是不现实的。例如,在重大疾病险中,对于帕金森氏综合征等疾病,非医学专业人员难以知悉确切含义,寄望于保险代理人完全理解术语并作出足以让投保人理解的说明无疑是不现实的。而术语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专业知识的简略代码,如要将之做通俗化描述,势必导致保单与订约过程的冗长繁琐,且表述的精确性无法控制,极易滋生纠纷。这表明“保单通俗化”可行度不高。况且,保险业历经数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条款措辞。除非国内保险业独立于世,否则此类条款很难与国际惯例对接,进而得以通过国际再保险分散风险。其次,投保人据以决策的信息需求与说明义务的对象并未有效对接,导致其倾听保险人解释的意愿不强。投保人通常更关注近期的现实利益(如保费数额),而非远期不确定风险(如除外责任)。〔17〕Melvin A.Eisenberg,supra note 13,at 220-223.最后,保险条款的高度同质化使得信息披露的意义不大。当投保人无法通过信息获取与处理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时,其对于信息披露也就兴趣寥寥。况且,接收和处理信息也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等成本。美国学者就发现,“在购买保险产品时,投保人并不渴望代理人向自己全面深入地解释承保范围”。甚至“保险买方不会阅读,或期待他们阅读(保险条款)”。〔18〕See Jeffery E.Thomas,“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5 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 ournal,295-309(1998-1999).因而至少在保险领域,立法与司法应从现阶段以信息规制为主的路径转向以内容控制为主的方式。
二、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法理基础:保险交易中的给付均衡
(一)保险法中的核心价值构成及其动态互补性
任何法律都包含价值与实现价值的技术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法律原则,后者体现为法律规则。由于法律制度中内在的独立价值具有多元性,因此不应仅依据某个单一原理来阐释法律。再者,内在于某领域的原则之间具有相互比较的个性,存在位阶之分。〔19〕关于威尔伯格(Wilburg)的动态系统论,请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中的动态系统论”,解亘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页172-266。比德林斯基就将合同法体系化地解释为尊重意思自治;保护合理信赖;维持给付均衡三个最重要原则的组合。〔20〕参见(奥)海尔穆特·库齐奥:“动态系统论导论”,张玉东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在保险领域,保护合理信赖应转换为满足投保人的合理期待,〔21〕See Robert H.JerryⅡ,“Insurance,Contract,and The Doctrin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5 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 ournal,21,37-41(1998-1999).因为投保人支付保费是确定和在先的,保险人实现缔约目的并无困难。再者,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保险已成为一种公共物品。〔22〕参见田玲、徐竞、许潆方:“基于权益视角的保险人契约责任探析”,《保险研究》2012年第5期。它能将个体面临的难以承受的风险在共同体成员间分摊,帮助投保人应对未来的不测,完成对日后生活的合理规划,维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此外,获取保险赔付对受害第三人也有重要意义,因而确保投保人能获取所需保险产品就成了一项公共政策。概言之,意思自治、给付均衡、合理期待〔23〕对合理期待的不同版本、争论原因以及我国法的应然选择的概述,参见马宁:“保险合同解释的逻辑演进”,《法学》2014年第9期。共同构成了指引保险合同法规则建构的核心原理,并对规则做了体系化分工。在《保险法》中体现为:第17条是以提升合意度、实现意思自治为直接目标;第19条是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控制;第30条的不利解释能督促保险人起草含义清晰的条款,使之不会过分偏离投保人的预期。〔24〕我国虽未引入合理期待原则,却存在该原则的支撑规范。即便立法者并无这样的意识,但至少在客观上,如第30条这样的规则有助于满足合理期待。只是与意思自治主要针对缔约程序活动,给付均衡主要针对业已成立合同的实质内容不同,合理期待既可及于缔约程序(如要求条款以明确的方式表达和提交),也可辅助给付均衡,共同完成对合同内容的控制,甚而延伸至合同含义的释清(如不利解释)。因此,支撑或否定保险合同的效力,都需以这三个原理的充足或不充足作为要件。原理与规则的不同在于,它不是要么满足,要么不满足,而是可以理解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并被期待尽可能的得到贯彻。〔25〕山本敬三,见前注〔19〕,页209。原理的另一个特征是,承认就同一事项而言都有妥当性的原理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以一个原理的充盈来弥补另一个原理的亏缺。“一方的原理的不满足或者受侵害的程度越高,另一方的原理得到满足的重要性就必须足够大。”〔26〕同上注,页210。只有当可以相互补充之原理的充足度总和低于一定的阈值时,保险合同的正当性才将遭受质疑。这意味着,即便信息提供义务无法确保投保人对保险条款的充分理解,只要给付的均衡度足够高,或保险产品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投保人对获得风险保障的合理期待,保险合同的效力就应得到承认。
这种立法政策和规范分工在欧盟国家〔27〕See Project Group,“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PEICL),European Law Pub,2009,pp.99-100,122-125.和澳大利亚〔28〕See The Treasury of Australia,Unfair Terms in Insurance Contracts Regulation Impact Statement, 2012,pp.8、49.得到了充分体现。它承认履行成本是提升当事人合意度的刚性约束,因而保险人信息义务皆为形式化,即要求保险人以书面形式将重要信息(不限于免责条款)提供给投保人。后者如有不解,可提出问询。而非如我国法一般不计成本,不考虑投保人需求地对特定条款主动进行解释。同时,这种立法青睐于通过费效比更高的路径来维持合同效力基础,即引入警示义务等举措以维护合理期待,特别是强化对不公平条款的内容控制,以实现给付均衡。
(二)保险交易中的给付均衡
虽然以矫正利益失衡为目标的内容控制应被视为规制保险格式条款的核心路径,但这绝不意味着应将给付均衡的实现等同于对投保人权益的单方无条件倾斜。在此,保险的团体性与技术性尤须加以关注。
保险是“对特定危险事故发生所致之损失,集合多数经济单位,根据合理计算,共同聚资,以为补偿之经济制度”。〔29〕参见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52。这意味着,大数法则的运用,以及由多个面临风险威胁的投保人(危险单位)所组成的危险共同体(危险集合)是保险的必备要素。大数法则是指依据概率论,某些大量重复出现的随机现象会呈现一定规律。我们假定某一数字在反复N次抽奖中出现X次,则N的数值越大,该数字的出现概率(X/N)越恒定接近于同一数值。将此运用于保险,观察由多个相同种类的危险单位组成的危险集合,就可以得出危险单位的损失机率,这就成为保险费率计算的基础。如果以C代表保险金额,P代表保险费,X代表危险发生次数,N代表危险单位数量,则P=CX/N,移项即得PN=CX。即为维持保险营业的收支平衡,各危险单位缴纳的保费总和至少应等于保险金总支出。
由前述公式还可推知,保险人支出的保险金是由各危险单位共同分担的。但是,对个别投保人而言,危险是否会现实化并给自己带来损害是不确定的,若损害发生,投保人将获得远超其支付的保费的赔付。否则,已支付的保费不得请求返还,而是作为对遭受风险现实化的其他危险单位进行补偿的财产基础。这是保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本质的体现。不特定投保人在缔约时对于保险的射幸性有着清楚认知,因而也不期望必定和立即从保险人处获得给付。而一旦损害发生于某一特定投保人,他就期望保险人承担责任,此即特定危险单位对给付均衡的感知。这与作为危险集合的给付均衡感知显然不同,后者“在投保阶段产生,体现了保险的射幸性”;而前者在事故发生阶段产生,回避了保险的射幸性。在对保险人援引的据以免责的格式条款作评判时,“特定危险单位的公平感知应该让位于不特定危险单位的公平预期”,〔30〕方志平:“论保险惯例——以商业车险条款为中心”,《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因为保险内含着一种由参与危险集合的全体投保人贴补发生风险事故的少数人的推定。易言之,给付均衡的考察应从风险共同体层面审视,它应当是对投保时所收保费与所承担风险对价性的整体评估,而非单个危险单位在事故发生后是否获得理赔。
以“高保低赔”条款为例。该条款规定,投保人将旧车投保时,保险人以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并据此计收保费。在车辆发生全损时,保险人仅按车辆实际价值承担责任。该条款被指不公,认为投保人缴纳了较高的保费却只能获得较低的赔偿。〔31〕参见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3)临兰商初字第4040号判决书。而从保险人的角度考察,车辆发生部分损失的概率约是99.9%,发生全损的概率约是0.1%。〔32〕方志平,见前注〔30〕,页534。车辆部分损失时,无论新旧,维修配件价格和维修工时费等与新车无异。保险人的支出不会因车辆的新旧而有所差异;若发生全损,则按实际价值赔偿能避免道德风险。保险人将部分损失和全部损失的车辆合并使用一个均衡费率,并按照新车购置价计算保险金额。这种技术安排已经照顾到了不特定危险单位的公平预期,因为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否发生保险事故或发生何种事故。况且,如果发生事故的特定个体的公平感需要照顾,那么绝大多数没有发生事故的个体的公平感又当如何处置?〔33〕同上注,页535-536。
再者,保险人是由众多投保人组成的风险共同体基金的管理者。若要求保险人为个别成员本不应获赔的损失承担责任,事实上是允许该人从最终归属于全体共同体成员所有的基金中不当得利。保险人会将这部分成本以提高保费的方式分摊,诚实守信的投保人将最终为此买单。因而在处理保险纠纷时,“应立于整个共同团体之利益之观点,不可纯依民法上双务契约之概念将对方置于敌对之地位;判定双方之权利义务归属,须不时以共同团体内其他成员之利益为出发点”。〔34〕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0。
三、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实定规范:《保险法》第19条的理论缺陷与现实反映
由于立法者的轻视,作为内容控制基础的《保险法》第19条存在明显缺憾。依该条规定,“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以及“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首先,它更像是对不公平条款的简单分类,而未提出清晰的判断条款是否有违给付均衡的标准。事实上,即便是作为其模板的《合同法》第40条也面临相同困惑。〔35〕参见范雪飞:“论不公平条款制度——兼论我国显失公平制度之于格式条款”,《法律科学》2014年第6期。其次,保险营业的特性必须考虑,同样的条款,在《合同法》背景下可被视为不公平条款,并不意味着在保险领域亦是如此。保险人虽以风险经营为业,但“并不是对保险标的所发生的所有风险都予以赔偿,而往往基于相应的保费价格,约定予以赔偿的特定风险范围……责任免除条款是从外延上对承保风险范围的具体界定,是保险产品的具体表述方式”,与合同法规定的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并不相同。〔36〕参见中国保监会《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性质等有关问题的批复》(保监办复[2003]92号)。最后,保险法对第19条的适用范围未做限制,似乎只要是格式条款,皆在控制范围之内,而国外先进立法均有适用范围的限制。
实务也印证了立法的不足。作者在查询到的136件以“保险法第十九条”为关键词的判决中遴选出51件(包括人身保险3件,财产保险48件。其中涉及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的有46件),〔37〕为使结果更加客观,作者在同一法院的多个判决间通常只选择一件,除非其在争议焦点上具有明显区隔。争议条款被认定有效的仅有8件。总体而言,法院的裁判既缺乏清晰统一的标准,也显现出相当的不合理性。
首先,法院对同类条款判定不一。例如,有法院认定肇事逃逸免责条款无效,理由是“肇事后逃逸……影响仅及于逃逸之后,不溯及逃逸以前的事实及责任。故投保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承担责任”。〔38〕参见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民一终字第124号判决书。也有法院认定其有效,理由是“如果仍将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转嫁给保险人,则有违公理道义和公平”。〔39〕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4)天民二初字第226号判决书。而对保险人有权依照国家医疗保险标准核定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和医疗费用赔付金额条款,有法院认为系有效条款,〔40〕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三终字第699号判决书。也有法院认为,投保人无法控制医院使用何种药物进行治疗,故其属于加重投保人责任的无效条款。〔41〕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4)亭民初字第1071号判决书。
其次,一些裁判无视保险特质,不合理性显而易见。有法院对投保人车辆系属明确约定的因“自燃以及不明原因火灾造成的损失”视而不见,以既然投保人已经交纳了保费,保险人就应履行义务为由判定保险人败诉。〔42〕参见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运中民终字第1400号判决书。若依此见解,保险营业中基于不同风险分类的危险集合的建构,以及相应危险概率的计算全然无法进行。免责条款也失去价值,道德风险将难以控制。还有法院将合同对承保风险的约定视之为不公平条款。例如,保险人在签发意外伤害保单时,将投保人声称的职业——水利工程设施技术人员明确限定为河道水库管养人员、农田灌排工程建设管理维护人员、水土保持作业人员、水文勘测作业人员、水利工程技术人员,〔43〕参见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2013)陵商初字第590号判决书。而投保人的实际职业是井下施工人员。法院却认定该约定违反第19条,这事实上是强行介入并变更了交易条件,使保险人基于风险概率的精算努力化为乌有。再如,保险免责条款并非原因免责一类,它还包括状态免责等其他类型。〔44〕王静,见前注〔8〕,页90-91。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等免责条款均属此类。但有法院一概以免责事由与保险事故发生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判定条款无效。〔45〕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中法民二终字第163号判决书。这无疑会鼓励酒后驾驶、无证驾驶。此外,保险人是从危险集合的整体视角出发,判定酒后驾驶等行为会导致危险概率的增加,即在整体上,二者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保险人也是以此为据计算保险费率的。而具体危险单位则是以特定事件中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来审视给付是否均衡。这就引发危险集合的公平预期与特定危险单位的公平感受间的冲突。若法院倾向于后者,保险人需要提升保险费率以维持收支平衡。因此而增加的成本将转嫁给未发生保险事故,且多数为依法驾驶的投保人。
不止于此,第17条、第19条、第30条的混用也所在多有。逻辑上,法院应先确定保险人是否已尽到说明义务,若为否定,则诉争条款视为未纳入合同。只有在业已履行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才有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评价的必要。若该条款表述清晰,适用之将导致给付失衡,则其应被认定为无效。若条款存在歧义,则应作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即三者“按照合同缔结、效力及解释的环节依次展开,体现了从程序保障到实质正义的公权介入意思自治领域强度的逐层递进”。〔46〕王静,见前注〔8〕,页91。而有法院先认定条款无效,随后又论证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因而条款不生效。〔47〕参见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2013)吴江商初字第1085号判决书。也有同时认定一个条款未生效和无效;〔48〕参见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2014)桐民初字第00975号判决书。亦有先对条款做不利解释,后又提及该条款免除了保险人的法定义务,〔49〕参见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2014)新津民初字第28号判决书。更有法院论证免赔条款既属于未说明而未生效,又属于排除被保险人权益的无效条款,同时还存在歧义,应作不利解释。〔50〕参见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4)天商初字第1282号判决书。
上述混乱与无序不仅揭示了法院对格式条款的规制路径与规范分工缺乏清晰的认知,也昭示了完善第19条立法,构建清晰而合理的内容控制标准的紧迫性。
四、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范围:任意规范中的非核心给付条款
(一)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控制
当事人间的合同约款虽不得违反强制性规范,却可以排除或变更任意性规范。后者为当事人提供了符合普遍意义下合同利益的法律规则,使其无须承受应就一切交易条件作出约定的繁琐。同时,又不妨碍当事人可根据自己的特殊需求予以调整。但这一定论在格式条款下难以证成。保险人可以自行决定仅将对己有利的规范纳入合同,而排斥对己不利的规范,从而引发权利义务失衡。因而这种可以变更或排除的规范的“任意性”是有界限的。毕竟,任意性规范同样体现着法律的实质性基本思想,而这是不容背离的。〔51〕参见杜景林:“合同规范在格式条款规制上的范式作用”,《法学》2010年第7期。
上述界限在保险背景下不仅更具应然性,而且广泛存在于国外立法的实然层面。〔52〕参见樊启荣、李娟:“论保险合同的内容控制——以对保险约款违反任意性规范的特别控制为中心”,《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32条、42条,以及可能成为未来统一欧洲保险合同法蓝本的《欧洲保险合同法原则》(PEICL)第2:304条等。具体言之,若约定条款违反任意性规范,造成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即不公平条款),〔53〕范雪飞,见前注〔35〕,页106。则该条款无效。PEICL就规定:“非经个别商洽确定的条款,如其有悖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造成合同权利义务显著失衡,则此条款对保单持有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具有约束力。”在去除掉该条款后,若保险合同可以继续存在,则其他内容不受影响。否则,应以理性的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如果知道上述情形后可能会约定的其他条款来加以替代。〔54〕有学者主张,应先用任意性规范替代无效条款。无任意性规范时,依契约解释原则补充。二者其实差异不大,因为任意性规范多是立法者参酌良好的商业惯例设计的。樊启荣等,见前注〔52〕,页17。相较而言,对违反任意性规范约款的审查更为困难。因为仅在造成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时才能否定其效力,这就需要确立清晰的判断标准。《保险法》第19条即是此种内容控制的实定法规范。即该条应被视为主要是审视背离任意性规范的约款效力的依据。因为违反强制性规范无论是否在格式条款背景下,无论是否造成了给付失衡,效果都是不言自明的。
(二)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范围
《保险法》第19条未规定适用范围的限制。依其字面含义,但凡可列入“加重投保人责任”等三种类型的条款皆应认定无效,这显然属于立法疏漏。首先,对于宣示性条款,即复制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并无审查的必要。因为此类条款不仅不会损害给付均衡,相反在很多情形下恰好能体现立法者期待的给付均衡。更重要的是,内容控制不应及于核心给付条款。合同内涵可分为有关要素的合意与偶素的合意。由此合同条款可分为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在格式条款内,后者因市场机制失灵而常常表现出合意度的不足。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价格或主给付义务上,对于从条件则常常忽略。但无论当事人理性如何,通常都会关心核心给付内容,会在对之做认真权衡后决定是否缔约。即在常态下有关核心给付内容的合意度相对充足。从交易相对方来讲,如其提供的核心给付内容缺乏竞争力,他将最终被市场淘汰。〔55〕解亘,见前注〔3〕,页110-111。因此,在解释论上势必要将核心给付条款排除在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外,以免过分抑制市场合理的风险分配和竞争。据此,《保险法》第19条将不能适用于记述核心给付内容的格式条款。〔56〕德国、英国等主要国家均承认保险背景下存在免于审查的核心给付条款,但范围有所不同。See Project Group,“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supra note 27,at 116-117.
那么哪些条款属于核心给付条款呢?私法学者主张将合同核心事项的定义、合同价款的适当性定性为核心条款——这两类条款也很难认定是否公平。〔57〕范雪飞,见前注〔35〕,页109。保险法学者将此移植到保险领域,主张“规定保险金给付事由,即保险人之给付义务具体化之偶然且一定之事实(承保风险)以及保险金给付标准的条款,均应当属于保险合同的核心给付条款……保险费属于价格条款,投保人在考虑是否订立合同时难以忽视,且与保险责任间具有对价平衡关系,也属于保险合同的核心给付条款”。〔58〕王静,见前注〔8〕,页95。而“在学理上用以界定承保风险范围的条款主要有两类,一是危险描述条款,用以描述本保险合同所承保的风险种类与范围;二是危险限制条款,用以修正、调整危险描述条款,主要是对承保的风险种类、范围再作精细化限定,保险实务中的除外风险条款,通常均属于危险限制条款”。〔59〕同上注,页97。此外,还有观点主张绝对免赔率亦属于核心条款。〔60〕解亘,见前注〔3〕,页112。
作者不能认同将除外责任、免赔率等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排除于审查范围外的解释。确定保险人赔付范围可籍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前者如保险金额,后者如除外责任。若除外责任等限制承保范围的条款属于核心条款,那么有何理由将投保人义务、保险期间、保证等可达到相同功能的条款排除在外呢?所谓除外责任关系保险人承担责任的范围,而投保人义务等条款仅是为了担保保险给付的正常履行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投保人的减损义务、危险防范义务等都直接关乎风险的发生概率与损害程度,如何与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范围无关?更重要的是,保险条款中除外责任部分并非仅限于学者所界定的对“承保的风险种类、范围再作精细化限定”的条款,投保人不当行为的损害后果,甚至该行为本身的存在也被视为除外责任。这意味着,很难对所谓“危险限制条款”与“约定义务条款”做简单区分,将前者归入核心条款,而将后者纳入附随条款。例如,车辆损失险中的责任免除既包括被保险人的肇事逃逸行为,也包括被保险人故意行为造成的车辆损失和因自燃引发的车辆损害。〔61〕参见《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http://www.iachina.cn/content_48b4f93a-d126-11e4-aaef-19d3d5b300e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4月10日。而若将上述条款均归于核心条款,内容控制的范围将被极大压缩。保险人也可以轻易地将审查范围内的条款修改成免于审查的条款。对此,凝聚了学者智慧与共识的PEICL第2:304条第3款将不得进行公平性评估的条款界定为:(a)关于承保范围和保险费的价值充分性之条款;(b)对提供的承保范围或者约定的保险费进行必要描述的条款。在该条的注解中,起草者认为,为有效保护投保人,必须对豁免审查的范围严格限定。而免于审查的核心条款是指对保险类型与客体、所承保风险、保险金数额、保险金额或保险利益给出关键性的定义或描述的条款。那些限制、改变或修订保险人应承担义务的条款,如除外责任、保证等皆不属于核心条款。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多数欧洲国家的赞同。〔62〕Project Group,“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supra note 27,at 116-117.而我国实务由于缺乏区分规制的意识,常将核心给付条款,特别是界定承保范围的定义条款宣告无效,〔63〕参见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2013)陵商初字第590号判决书。严重干扰了保险营业——保险人正是基于定义对承保范围的描述而始得计算保险费率的。故而PEICL的规定值得借鉴。
当然,核心给付条款并非完全不受规制。一方面,私法中存在如《合同法》第54条一般的传统类型的规制规范。另一方面,欲豁免审查的核心给付条款首先需清楚透明,易于获取,否则将不被纳入合同。次之,核心条款须不违背投保人的合理期待。〔64〕See The(Ireland)Law Reform Commission,Insurance Contracts Consultation Paper,2011,pp.145 -146.合理期待虽然也是一种将公平理念带入损失分配体系的方法,但其与给付均衡的作用并不等同。后者关注法院面前的具体当事人的认知能力和对条款的理解,其援用受到案情的限制,这使之在存在结构性利益失衡的保险市场中,可能无法确保独立维护投保人合法权益。而合理期待使得法院可以抛开具体条款与当事人的具体情形,在一般意义上贯彻司法政策,实现了对投保人利益和作为整体的保险市场需求在更高层面的考量。〔65〕See Kenneth S.Abraham,“Judge-Made Law and Judge-Made Insurance:Honor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67 Virginia Law Review,1151,1175-1185(1981).况且,合理期待主要适用于若司法不施加干预,会导致投保人系统性的缺乏相应保险产品,或者免除保险人责任就个案而言并非不公平,但却在保险业整体层面上使保险人攫取了不当利益的情形。〔66〕前者如健康保险中,保险人对“疾病”范围的严重限缩与消费者寻求更广阔疾病风险保障需求间的矛盾,后者如投保人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得依据风险不可分原则免除全部责任。参见马宁:“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的制度重构”,《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这意味着,为维护保险的公共物品属性,某些情形下,即便保险人拒赔并非不公平,法院仍得强制其承担责任。
从消极层面限定了内容控制的边界后,于积极层面明确控制重心也是必要的。研究表明,即便是获取了充足且清楚易懂的信息,由于认知局限的存在,行为人(投保人)仍然会对某些条款关注不足。〔67〕Melvin A.Eisenberg,supra note 13,at 211.这些条款因此成为保险人获取不对等利益的主要工具。认知局限主要表现为乐观性偏见(Optimism Bias)、错误的远视与风险评估(Faulty Telescopic and Risk-Estimation)等。前者指行为人在决策时会低估风险发生于己的概率。〔68〕See Oren Bar-Gill,“Seduction by Plastic”,American Law&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 Paper 12,2004,p.3.后者指行为人更关注当下的收益(如保费)与成本,对未来的风险时常予以忽略。〔69〕Melvin A.Eisenberg,supra note 13,at 220-223.保险人以收取保费为对价,将未来的补偿承诺销售给投保人。保险事故的发生虽就危险集合而言属于必然和确定,但对投保个体则属于未来的小概率事件,这意味着投保人极可能忽略风险发生于己,以及因索赔与保险人发生纠纷的可能,进而将如除外责任、合同解除与争议处理等低风险概率条款直接过滤。再者,保险人为了控制危险、评估损害,经常会在合同中约定投保人应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当投保人违反义务时,会产生合同解除、保险责任限免等不利后果。〔70〕这类条款有一部分会被纳入除外责任,但诸如投保人通知义务、协助义务等却多是独立于除外责任的。这类条款属于投保人的违约责任,是否发生取决于合同履行中的多种主客观因素,既具有远期性又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投保人极可能忽略。〔71〕王静,见前注〔8〕,页97。因此在做内容控制时,须对除外责任、投保人义务、合同解除与争议处理等涉及远期不确定风险分配的条款给予特别关注。
五、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范式:抽象表述与具体列举的结合
(一)内容控制的范式选择
无论是在一般私法,还是作为特别私法的保险合同法,各国对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多采取抽象表述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范式。〔72〕Project Group,“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supra note 27,at 116-117;范雪飞,见前注〔35〕,页108。例如,《德国民法典》第307条对不公平格式条款作了提取公因式的表述,第308条与309条则分别列举了8类和13类具体的相对无效与绝对无效的条款类型。而在普通法系保险立法中颇负盛名的澳大利亚亦是如此。其《2013年保险合同法(不公平条款)修正法案》先规定了不公平条款的定义,随后又列举了14类不公平条款。〔73〕See 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House of Representatives,The Insurance Contracts Amendment(Unfair Terms)Act 2013,14C(Meaning of unfair)and 14D(Examples of Unfair Terms),pp.6-8.PEICL虽仅规定了抽象的不公平条款概念,但作为其蓝本的欧盟指令的附件已列明了多种表现形式,可供参照适用。
这一范式的价值在于,单纯列举不公平条款的方法不可能涵盖全部类型。随着实践的发展,新的不公平条款将不断出现,而这种主要源于判例提炼的方式具有无法克服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不利于投保人权益的维护。再者,如果不加以抽象和提炼,越来越长的条款也会使立法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单纯提取公因式的抽象表述虽具有扩大控制范围和避免挂一漏万的优点,但同时也产生了至少二种负面效果:其一,其具体功能发挥的程度受制于裁判者的评价能力,这一点对我国尤具警示意义。李永军教授就认为,民法通则中的弹性条款之所以未能发挥对定式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规制作用,主要原因即在于我国法官的法律素质不足。〔74〕参见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90。此外,裁判标准的不明确还会增加法官个人不当适用法律的风险。在当前外部监督不断强化,而合理的司法评估体系尚未建立的背景下,法官确实有忽略该项规定以规避风险的动因。司法对说明义务的偏爱恐怕也不能排除此种因素的影响。其二,欠缺预防功能。在缺乏具体指引的背景下,拟定格式条款的保险人没有可资参考的规则,以尽可能避免出现不公平条款。其亦没有为保险业协会的内部审查、社会组织的公益诉讼、行政机关的监管提供判断基准。因此,抽象表述与具体列举的结合是最合理的内容控制范式,也是我国立法的应然选择。
(二)对不公平条款的抽象表述
德国法对保险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规范主要参酌民法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07条将不公平条款界定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而不合理地不利于使用人之相对人”。有学者将之解释为构成不公平条款要具备两个要件,即违反诚信原则;造成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二者之间“并不当然存在因果联系”,“合同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仅仅是从格式条款内容中得出的客观结论”。〔75〕范雪飞,见前注〔35〕,页108。这是希望通过对诚信原则的违反来证明格式条款的司法控制具有正当性。它也有助于避免当事人难以满足具体规范在构成要件上的刚性要求,增强规制的灵活性。但这势必会加重法官的论证责任,甚而导致司法滥权。故而又需用格式条款的“合理性”标准——当事人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来加以限制。然而,这一论断意味着在援用内容控制规范时,投保人不仅需要证明给付失衡,还需证明保险人违反了诚实信用,这绝非易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因此受到严格限制。
另有一种解释是,德国法在确定给付失衡的判断标准时,已将诚实信用原则的理念内化于其中,因而违反了上述标准时,就推定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76〕参见叶启洲:“保险契约狭义内容控制之法源及控制标准类型化之检讨”,《第五届中国保险教育论坛论文集》,2009年11月,页691。作者赞同此观点。正如拉伦茨所言,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的整个意义脉络、双方共同承认的合同目的以及双方共同想象的合同利益状态”,〔7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180。它内含的是全部的私法的价值。〔78〕参见叶金强:“合同解释理论的一元模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因而对给付均衡的违反应被推定为对诚实信用的背离。这种方法既具操作便利,也更利于保护投保人利益。澳大利亚也为这种选择提供了比较法的依据。在该国,一个消费者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如果将引起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给其造成损害;并且该条款并非为保护因之受益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所合理地必需,则可能被认为属于不公平条款。〔79〕The Treasury of Australia,supra note 28,at 51.而“并非为保护其合法利益所合理地必需”本身即是违反诚实信用的表现,这与德国法相似。但澳大利亚法同时规定,消费者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应被推定为并非为保护因该条款而受益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所必需,〔80〕Ibid.,at 52.从而免除了消费者对保险人违反诚实信用的举证责任,他们只需证明给付失衡即可引发内容控制规范。
对如何判断权利义务严重失衡,PEICL仅提供了一些考量因素,而《德国民法典》第307条则额外确立了两个标准,“有疑义时,约款若有下列情形之一,推定有不合理的不利益:(a)该约款与所偏离的法律规定的重要的基本思想相抵触,或(b)该约款限制了从契约本质所产生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致使契约目的无法达成”。这种内化了诚信原则与给付均衡原则的控制标准被学者称为实质控制,而形式控制“系指除以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等上位概念外,另外订立数项形式观察之标准。此等标准纯以定型化契约条款与实定法之规定加以比较其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之影响而定……减免保险人之义务、限制被保险人等之权利及加重被保险人等之义务均属之……违反此等控制标准之定型化契约条款,是否违反诚信原则而显失公平,尚须另行判断”。〔81〕叶启洲,见前注〔76〕,页691。
我国《保险法》第19条所列三类条款仅着重于契约条款之形式效果,并不能藉此推定符合各款事由的条款具有导致权利义务失衡的情事。此时,法院仍须另行判断该等条款之实质正当性,不合理处显而易见。易言之,条款应否被宣告无效,应检讨其与给付均衡原则的背离程度,至于是否有“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等情事,并非重点。整个内容控制的重心,应转向诉争条款是否符合给付均衡原则的实质判断标准。在此,德国法的规定无疑颇具价值。〔82〕前一标准在我国早已有迹可寻。中国保监会在《关于保险条款中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含义的批复》(保监复[1999]168)中就称,“根据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则,保险条款中的约定与法律、法规中的授权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虽有不同或重叠,但不抵触者,约定有效,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所谓“不抵触”即隐含了以任意性规范的立法本意来考量当事人约定的原理。
例如,前一项标准可用于判别极为常见的“无责免赔、比例赔付”条款的效力。车辆损失险或者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常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在被保险人无事故责任时,保险人不承担责任。责任保险的目的是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移转给保险人,因而保险人的责任应以被保险人的责任为基础。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比例赔付无可指责。而车损险是将被保险人遭受的车辆损失转移给保险人。若事故由第三人造成,保险人在赔付后可依据《保险法》第60条向第三人行使代位追偿权。而“无责免赔”实质是保险人以放弃对第三人代位权的方式排除《保险法》第60条的适用,将向第三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分配给被保险人。这种约定违反了第60条设立的本旨,使车辆损失险的价值丧失殆尽,故应判定其无效。〔83〕多数法院都持此观点。例如,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4)锡法商初字第0108号判决书。
而对另一种常见条款的效力,则可以第二项标准判定。该条款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险人按照保险单上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总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84〕参见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铜中民一终字第00005号判决书。投保人分别就主车和挂车投保,缴纳保费,约定了各自的责任限额。但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总和却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这显然是剥夺了投保人基于附加险而享有的请求理赔的权利,使其缔结附加险的目的无法达成,因而应认定无效。
概言之,我国保险法应规定,“适用保险人提供的条款缔结的保险合同,若条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合同权利义务造成显著失衡,则此条款无效。格式条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合同权利义务造成显著失衡:①条款与其所排除适用或补充之任意性规范的立法宗旨明显矛盾;②合同的主要权利或义务因受条款的限制,而使合同目的难以达成”。
当然,判断条款是否违反任意性规范,不能仅以个别约款与法律规定是否一致为标准,而必须经过对合同整体的评价。若该任意性规定所欲保护的利益,已在合同其它部分,借由其它方式获得保障或补偿的话,则不得认为该条款为不公平条款。例如,责任保险合同若约定,一旦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协助义务,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这与《保险法》第25条的宗旨不符。但如果考虑到如下因素,该条款的效力似应得到肯定。其一,我国保险实务中,责任保险人有抗辩权利而无抗辩义务,而本合同约定了保险人的抗辩义务;其二,未能善尽协助义务直接影响抗辩的成功与否,决定着保险人是否应代投保人向第三人进行赔偿;其三,违反协助义务与欺诈性索赔密切关联,而后者是对保险营业维持的最大威胁。此外,对违反合同目的的标准,也须参酌本合同的特性,诉争条款之设定目的、违反程度和投保人的可归责性加以考量,不能仅以形式上有无限制保险金给付义务而骤下结论,以免破坏保险营业的对价平衡。这就是“推定”一词的意义所在。
(三)不公平条款具体类型之列举
在抽象表述之外,《德国民法典》第308条列举了8类“有评价可能性的条款”,这些条款能否最终被认定为不公平条款,需要结合相关因素考量。此外,第309条还列举了13种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应被直接确认为无效的条款。前一类型使用的概念相对具体,法官自由裁量余地受到较大压缩,但其中仍不乏不确定的概念。如“使用人为其本身保留之承诺期间……太长或不确定”等。后一类型的概念则相当明确,法官无自由裁量余地。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法事实上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给付失衡的判断标准。即居于第一层次的两项抽象的判断标准;居于第二层次的较具弹性的八种次类型标准;以及居于第三层次的十三种刚性控制标准。法官在审查时,仅需依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将诉争条款与控制标准做比较,即能轻易作出判断。这种多层标准既有利于扩大控制范围,提升控制效率,还可以增强内容控制的预防功能,因而值得借鉴,但具体标准的建构仍需审慎衡量。毕竟德国法的控制标准是针对一般类型交易设计的。在此,作者意欲结合我国保险实务,就较为常见的不公平条款类型做一列举。
首先,在较具弹性的第二层次,可推定下列条款构成不公平条款:
第一,允许保险人免除或限制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其主要表现为两类,其一,免除或限制保险人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通常表现为对保险人迟延处理索赔或支付保险金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进行了排除或限制。其二,要求投保人履行全部义务,而保险人则不必如此。
第二,允许保险人向违反合同或终止合同的投保人施加不适当的惩罚。例如,要求投保人支付违约金,或对投保人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允许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
第三,允许保险人决定投保人是否存在违反合同的情形,或有权按照自己意愿解释合同。例如,保险人宣称保留对全部条款含义的解释权。
第四,允许保险人享有并未授予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权,或者允许保险人解除合同后,不向投保人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保费。
第五,允许保险人在无合同中事先列明的实质性正当事由时,单方变更合同条款。其主要表现为四类,其一,给予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单方变更保费的权利。特别是对此项变更,投保人没有终止合同的权利。其二,保险人可单方决定将合同转让给其他保险人。其三,对规定了固定期限的合同,保险人可单方决定续展。其四,保险人可单方变更合同提供的服务内容。
第六,限制保险人为自己代理人的行为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七,排除或妨碍投保人采取诉讼或其他法律救济方式。主要包括,其一,使保险人获得技术性抗辩的机会,如要求投保人在不合理的短暂期限内履行损失通知义务。其二,要求投保人提供满足保险人要求的证据,这使保险人可以提出不合理的证明要求。如要求投保人提供与索赔请求无关的文件。其三,向投保人施加本不应由其负担的举证责任。其四,限制投保人在起诉时所能提出的证据。其五,要求投保人在向保险人索赔前需先履行特定程序。其六,规定只能通过仲裁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第八,限制投保人选择权利。表现为妨碍投保人选择保险人或其他具有替代可能性的交易内容,前者如要求投保人对于与保险人已承保的风险不同的风险,应向同一保险人投保。或者规定当承保风险消失时,保险合同仅仅中止,当投保人再次面临同一风险时,原合同效力恢复。后者如车险实务中保险人单方指定医疗机构或维修点的条款。
第九,要求投保人承担其无法控制的风险。例如,车险中肇事者不明时的免赔率条款。
前述条款应被推定为不公平条款,但保险人仍有举证推翻的空间。例如,残疾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条款中常将受益人限制为被保险人本人,不允许变更。这可归入限制投保人选择权条款。但保险人可以解释,鉴于现行保险法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体限为投保人,而非有权获取保险金的受益人,这可能诱发道德风险。而前述规定可以消除这种为第三人利益保险内含的风险。况且,前述限制产生的不便也可以通过赠与等形式消减。
其次,在最为具体的第三层次,法院应将下列常见条款直接确定为不公平条款:
第一,主车和挂车连为一体发生事故,保险人的责任限额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
第二,当保险事故是第三者造成时,被保险人应先向第三者求赔,若第三者不予赔偿,被保险人还应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否则不能向保险人索赔。
第三,车辆损失险中的比例赔付、无责免赔条款。
第四,使用各种专用机械车、特种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发生保险事故后,即使已取得相应驾驶资格,保险人仍不承担保险责任。〔85〕参见《中国保监会关于侵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的通报》,http://www.circ.gov.cn/web/ site0/tab5218/info394598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5月8日。
第五,保险人有权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核定人身伤亡或医疗费用赔偿金额。一来,采取何种治疗方案(特别是紧急治疗时)系属医生诊疗行为的应有含义,投保人通常无法控制。二来,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与以实现公共政策为目标的基本医疗保险无论是在保险费率的计算、保险运营模式等诸多问题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保险费率通常会高于后者,其提供的保障范围也应相应扩展。最后,这种对医疗费用的限制可能危及投保人或受害第三人的人身权益。在利益衡量上,它显然高于保险人的获利预期。
第六,将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排除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三者之外。仅仅以两者间可能合谋骗保为由将之排除,将使投保人购买第三者责任险的目的难以充分实现。同样的生命,同样的事故却无法获得同等对待,这与尊重人的生命、维护人格平等的基本价值相悖。
最后,上述三个层次间的判断标准可能存在种属关系,因而在适用时应坚持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即先确定诉争条款是否属于第三层次列明的不公平条款,若不在其列,可上溯到第二层次,以此类推。此外,前述三层标准仅是基于司法经验归纳的给付失衡的惯常表现,其并未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给付失衡的所有形态。因而即便诉争条款不符合前述标准——特别是上溯到第一层的抽象标准时——仍需对其背离给付均衡原则的程度加以考察,以确定其效力。即上述控制标准应具有开放性,允许通过对实践的观察而补充完善。
六、结 论
保险营业的特殊性使得保险人履行信息提供义务(说明义务)的成本远超一般类型交易。投保人处理信息,据以做出最优决策的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这意味着以信息规制为主要路径的保险格式条款规制模式亟待转向以内容控制为主的模式。而以保障给付均衡,兼顾满足投保人合理期待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内容控制规范,与以提升当事人合意度为目标的信息规制规范间,也存在动态的互补关系,可以更高的均衡度填补当事人合意度的不足。但保险的技术性与团体性也赋予了给付均衡更丰富的含义,绝非对投保人利益的单方倾斜。现行内容控制规范在此显现出明显缺憾,对此,应将内容控制聚焦于任意性规范中的非核心给付条款,特别是涉及远期不确定风险的条款。对内容控制的范式,宜采取抽象表述与具体类型列举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具有开放性的多层次判断标准,以利于法院在无碍于保险营业维持的基础上,更有效的保护投保人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许德风)
Due to the high cost,the information regulation path of standard terms in insurance contract cannot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desired purpose of assuring autonomy,so it should be shifted to the content control mode.The purpose of the latter path is to maintain balanced insurance coverage.However,the technicality and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 of insurance also grant the balanced insurance coverage principle richer meanings.Content control standards based on the balanced insurance coverage principle should focus on the noncore terms deviating from arbitrary norm,especially the long-term clause with uncertain risk.In the contract control paradigm,the abstract principle and example emueration should be combined.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urance and the practice in our country,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level and open-ended unfair terms judgment standard is necessary.
Standard Terms;Information Regulation;Content Control;Core Terms;Judgment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