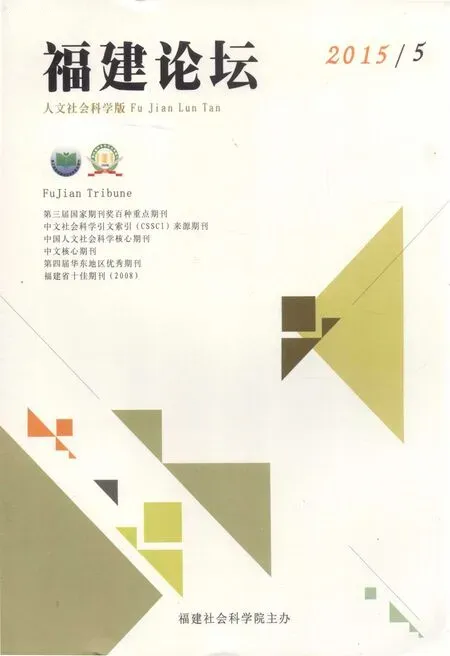从“自动木偶”到受控“代码”:评鲍德里亚对现代“人”的系谱学分析
□王晓升
按照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主义观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史可以概括为人不断实现自由的历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人从束缚自己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革命则把人从封建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而工业革命则把人从物质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鲍德里亚则从系谱学的思路来分析现代文明。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越来越失去自由。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鲍德里亚的这个分析呢?
一、“自动木偶”的形成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第二部分,鲍德里亚分析了仿像的三个等级。这个三个等级既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又不是严格按照历史的进程来进行分析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第一级仿像和第二阶仿像也会在第三级仿像中出现 (这表现了系谱学分析与历史学分析的差别。或者说,现代文明以来出现过三种类型的仿像,这三种类型不存在一种类型取代另一种类型的关系,系谱学的分析就是要找到那些被边缘化了的类型)。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只讨论仿像的三个“等级”,而不是仿像的三个“阶段”。
文艺复兴是“自动木偶”形成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成为“自动木偶”。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理解鲍德里亚系谱学的分析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个进步表现在人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只有贵族、封建主才能享受各种物质财富,平民对于物质福利的追求是被禁止的。人和人之间有严格的等级。而文艺复兴运动要求,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追求物质满足。有别于这种历史学观点,鲍德里亚用符号解放的角度重新剖析了这一历史境遇,将人们追求的物质财富理解为符号,将启蒙思想家所说的人性的解放理解为符号的解放。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符号原来只是与特定的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是某些特定等级所专有的,而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符号,并根据需要来创造这些符号,使用甚至玩弄这些符号。当那些新兴资产阶级炫耀自己富有时,财富失去了使用价值,实际只是在玩弄符号。因此,鲍德里亚把这种符号解放标识为“强制符号的终结”。他认为,当所有人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的时候,“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就形成了,这是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比如,如果仅仅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衣服的话,那么衣服上的某个特定的符号是没有使用价值的。造此说来,人们在购物的时候如果只是注意衣服上的符号,那么其购物消费就是符号消费,是不注意使用价值的时尚消费。用人们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人成为时尚的奴隶。当新兴资产阶级玩弄物质的符号,特别是纯形式意义上财富符号的时候,人就成为无用物的奴隶。在文艺复兴时代,新兴资产阶级在炫耀财富的时候,那些物质的符号是模仿自然界的东西的,比如,假牙等。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现代符号正是在‘自然’的仿像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资产阶级思想家强调,他们要通过改造自然来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当他们玩弄符号并试图借助于玩弄符号炫耀财富而与封建贵族一比高下的时候,这种需要就不那么自然了。在这里,财富就不是满足“自然”需要的物。比如,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胸前的假背心、假牙、仿大理石室内装潢、巨大的巴洛克舞台布景装置,所有这些都不是使用上需要的,而是用来“炫耀”的,表演的,具有“戏剧性”的特点。在这种戏剧的表演中,我们发现,在人改造自然而取得的辉煌成就中,人所改造的不仅是外部的自然,而且是人自身,人的自然需要。正是从财富的炫耀和表演中,鲍德里亚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的秘密:给人灌注一种爱炫耀和表演的精神气质。人的自然(天性)被改造了,人的劳动、生活等等不仅要满足自然需要,而且要进行表演和炫耀。这种表演和炫耀一开始是以满足自然需要的名义出现的,是以对人的自然崇尚的形式出现,这个时候的符号确实有真实的参照——“自然”。为此,鲍德里亚说:“仿大理石是一切人造符号的辉煌民主,是戏剧和时尚的顶峰。它表达的是新阶级粉碎符号的专有权之后,完成任何事情的可能性。这是向一切新奇的组合、一切游戏、一切仿造开放的道路——资产阶级普罗米修斯式野心首先进入自然的模仿,然后才进入生产。”可以说,资产阶级就是依赖于这样一种精神气质或者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来改造世界的。这种精神气质绝不是韦伯所说的那种清教思想中形成的,而是在模仿贵族和封建等级势力的精神形成的,是在巴洛克艺术的氛围以及耶稣会教士的努力形成的。我们知道,巴洛克建筑往往以其豪华和气势来彰显宗教精神的神圣性。它从一开始就是和清教徒的精神气质相对立,它是以反对宗教改革的面目出现的。清教徒主张节俭、淳朴,而巴洛克艺术则渲染奢华和气派。从巴洛克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用奢华和气派的艺术风格塑造了一大批的“天使”。而耶稣会教士就是要致力于塑造这样的“天使”,并借助于这些天使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宏大事业。为此,鲍德里亚说:“巴洛克风格又与反宗教改革运动相联系,与耶稣会教士试图第一次按照现代权力观念建立政治和精神世界的霸权这一事业相联系”。
那么耶稣会教士是如何按照现代观念建立政治和精神世界的霸权呢?这和“理想的自然”有关。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这里包含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培养绝对顺从的精神,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合成实体”来代替“自然实体”。我们知道,耶稣会当年把整个世界区分为若干教区,并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正式会士除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外,还发第四愿,即绝对效忠教皇。鲍德里亚认为,这些人像死尸一样,绝对顺从。除了这种绝对顺从之外,耶稣会还在世界各地创办学校,其目标是要“重新塑造儿童的理想自然”。由此所重新塑造的自然是按照耶稣会的精神所塑造起来的,是一种“合成实体”。这就类似于用“合成实体”代替“自然实体”。这些儿童就成为用合成实体塑造起来的“天使”。耶稣会的企图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这样的天使,不过这样的天使就像教堂中用合成材料(仿大理石)做成的天使一样。这种天使任由人来塑造,因而“绝对顺从”,没有自然的天性。这些没有自然天性的人是在巴洛克艺术风格中培养起来的人,追求奢华和表演的人。这些人是高贵的“天使”。但丁认为,“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度”。与但丁对“天使”(人)的颂扬不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些“天使”是仿大理石天使,是失去自然性的死尸。而这种仿大理石天使的塑造才是资本主义 “普遍控制和普遍霸权”策略的核心。
当代社会的斗富行为,多少与这种精神气质有关。虽然穷人不能像土豪那样斗富,但是斗富的心理一点也不少。抢购各种名牌服装首饰的姿态与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贵妇并无差别。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气质的人就像巴洛克艺术风格中所塑造的“天使”,奢华而又气派。有了这样一批“仿大理石天使”,这种精神的统治方式就被默许,资本主义就永远不会灭亡。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不是通过购买劳动力剥削个人而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而是靠“仿大理石天使”的精神气质实现的绝对控制权。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的永恒不灭的 “精神实体”。他说:“人类的奇迹难道不是发明了塑料这种难以降解的材料并因此而打断了腐烂和死亡把世上一切实体从一处转入另一处的循环吗?一种处于循环之外的实体。甚至火烧之后留下的也是不可摧毁残渣——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种仿像中凝聚着一种普遍符号学的抱负。这与技术的‘进步’或科学的理性目的不再有任何联系。这是一种政治和精神霸权的设想,一种封闭的精神实体的幻想——如同那些在曲面镜中手脚相连的巴洛克式仿大理石天使”。
如果仔细思考这些“仿大理石天使”,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赶时髦的人没有自己的灵魂。别人购买什么,他们也购买什么,什么时髦,他们就赶什么时髦。这样的人如同受到别人操控的木偶。木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用来进行舞台表演的,而赶时髦的人也追求相同的舞台效果。那些穿着时尚的明星,她们的衣服既不保暖也不遮丑,但是,有人却趋之若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赶时髦的人虽然都是“木偶”,但与舞台上的木偶还是有所差别。舞台上的木偶毕竟有一个具体的人在操控,而赶时髦的“木偶”却没有具体的人在操控,所以他们是“自动木偶”。最后,还应注意,不赶时髦的人也摆脱不了赶时髦,比如牛仔裤是反时髦的,但是最终也成为时髦。所有人都无法逃避时髦。既然所有人都是赶时髦的人,那么所有人都是 “自动木偶”。
二、“机器人”与“自动木偶”的差别
人从“自动木偶”转变成为机器人,这是在工业革命中完成的。从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它认为,这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从鲍德里亚系谱学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一种倒退。人们在塑造自动木偶的时候,总是力图使自动木偶像“人”。或者说,自动木偶还需要具备人的形象,而人们在制造“机器人”的时候,只顾它的活动效率,而不管它是不是像人。或者说,在文艺复兴时代,虽然人也被塑造了,但是,人的理想目标是“自动木偶”,他还是要努力像“人”一样“生活”;而工业革命中,人已经失去了“人”的形象。人的理想目标是“机器人”。为此,鲍德里亚说:“自动木偶是人的类比物,而且仍然是人的对话者(它可以和人下象棋)。机器则是人的等价物,并且在操作过程的统一性中把人作为等价物占为己有”。人在操作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机器,而且从机器的同一性中来看待自己和其他人。这就如同生产线上的两个工人相互比较“它们”谁更有效率,更像机器。人已经放弃了“人”的形象。沃霍尔的“我要成为机器”体现了这个时代人的自我理想。
在这里,“机器人”和“自动木偶”的差别还不在于它们的外在形象上是不是像人,而且还在于自动木偶有自己的模仿对象。或者按照鲍德里亚的思路来说,自动木偶遵循的是自然的价值规律,是仿造,而机器人所遵循的是商品的价值规律,是生产。人们在仿造的时候,总是模仿某个东西来仿造。文艺复兴时代,那些赶时髦的“自动木偶”所仿造的对象是“宫廷里的人和有教养的人”。鲍德里亚说:“自动木偶扮演宫廷里的人和有教养的人,它在大革命前参与戏剧和社会的游戏”。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新兴的资产阶级认为,只有这些贵族和有教养的人像“人”,这些人是他们模仿的对象。贵族们视金钱为粪土,过着悠闲自得的怡然生活。而在大革命之后,他们开始鄙视这些贵族,一个个成为守财奴,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劳动。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积累和劳动的精神。有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开始了一场谁更像“机器人”的比赛。“机器人”不吃不喝不穿,而只有不停的劳动。既然他们开展了谁更像“机器人”的比赛,那么他们就只能相互模仿,而失去了模仿的真实对象。
“自动木偶”在进行模仿的时候,它模仿贵族或者有教养的人。“自动木偶”不是真正的贵族,是赝品。这里存在着赝品和真品之间的关系,存在表象和真实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动木偶”总是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它总是要问表象背后的真实(本真的生活)是什么?它总是要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机器人”不再有这样的追问。被资本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机器人”放弃了形而上学。他们甚至挖苦形而上学,认为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毫无意义、毫无作用。然而从鲍德里亚的角度来看,“机器人”的这些高效率的活动正是把自己放在一种无根的状态。这里所谓的无根状态就是机器人没有要模仿的对象。对于机器人来说,他所应该模仿的真实(没有人的本真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用鲍德里亚本人的话来说,机器人已经“清除真实”。或者说,对于“机器人”来说,真正的生活对于“它们”来说已经不可能了。“自动木偶”在赶时髦的时候是贵族怎么生活,他们就怎么生活,而“机器人”在模仿的时候就不同了,它是像其他机器学习。它从来不问,为什么要像其他机器学习。“真实(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对于它来说已经被排除了。
虽然“自动木偶”还有形而上学的追求,但是在“自动木偶”中就已经包含了“恶魔”,这个恶魔就是“模仿”(simulation)。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当原始人类看到相片的时候,感到非常可怕。他们以为照相机具有巫术般的作用。不过这种“巫术”从自动木偶中就开始出现了,而在“机器人”中被进一步扩展。我们知道,工业化大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批量生产,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可怕的恐怕不是供人消费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这也可怕,在公共场所,我们常常无法区分各自曾经饮用过的杯子),而是一模一样的“机器人”。马克思认为人都是生产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人可以被量化,可以被像商品一样买卖。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等同。而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这种相互等同主要还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相互等同,而是人的精神气质上的相互等同。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主要不是劳动力的买卖,而是通过仿真,也就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模仿。他说,仿真是“操纵、控制和死亡等这些巨大事件的场所。”正是由于这种仿真,资本主义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些人也会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于是,在工业化的大生产中,资本家不再需要皮鞭来勒令工人劳动,他们会按照机械系统的要求劳动。
当笛卡尔按照“我思故我在”的哲学逻辑设想人的时候,这个人是“无影”的。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否存在的人也是如此。这个人没有身影,只是在镜子中观看自己(在思想中自我反思)。这就是在精神中的自我复制,这种人就是在理性精神中自我复制的人。这是一个没有肉体的纯粹理性化的“机器人”。只有这样的机器人才可以无限复制。显然,社会生活中的那些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永远都无法简单复制的,也永远无法批量生产。“机器人”的批量生产是真实的、具体的人的彻底丧失。可以说,这是“人”的“死亡”,是主体性原则的消失。这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悖谬。他们要把人放到神圣的祭坛上崇拜,而结果却使人成为没有血肉之躯的“理性”存在。当他们高扬主体性原则的时候,人成为“机器”。这个机器人所遵循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模仿原则。虽然从“自动木偶”到“机器人”,人的形象变了,但是贯穿在人之中的“精神实体”却没有变。
三、受控代码
在这里,人们或许会提出质疑。难道现代社会中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吗?应该承认,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止的时候,人不能再被简单地描述为“机器人”。人越来越多样了,越来越有各自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鼓励人们具有多样的思想、多样的价值、多样的生活方式,人们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多元主义时代”。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工业革命的时代,人虽然变成了机器人,虽然人受控制了,但是人毕竟还是劳动力,还是对社会有用的,而在后工业时代,人连机器人都不是了。在这个时代,人的劳动已经由机器取代了,人成为“无用”(仿真意义上的有用性)的符号。从符号的角度来看,虽然工业时代的劳动者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都是符号,但是前者毕竟还是有意义的符号,而后者是无意义的符号。如果说在工业化时代,人作为劳动者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受到控制,那么在后工业时代,人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受到控制。人成为完全受控制的代码。
人们或许会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比以往更加自由了,一个人甚至不必劳动也可以自由地生活。而且生活更加多样化了。如果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是完全不同的,都是自由的。这些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体系。然而从鲍德里亚的思路来看,这是表面现象。虽然每个人都是一个符号,但是符号是由代码构成的。现代社会不是控制符号的组合方式,而是控制代码的编码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于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来说明代码控制是如何调节符号的意义的。有意义的符号组合是一种表层结构,比如,我在电脑中输入的有意义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有意义的句子。这些具体的文字是完全可以自由组合的。但是我输入的文字背后有代码,即0/1这两个代码,这两个代码控制了所有的文字。为此鲍德里亚说,人类所建构的仿像世界从仿造、生产“走向结构和二项对立的世界”。这里出现了“非决定论和代码的形而上学”。在表层结构中,人完全是自由的,没有受到决定性东西的控制,但是在深层结构中人受到了代码的控制。在这里,鲍德里亚吸收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来说明这种情况。从表面现象来看,我们每个人都长相不同,而且每个人究竟会长得如何,这完全是偶然的。但是,每个人的长相又都是由遗传密码控制的,遗传密码也是按照0/1的数字编码过程来传达和遗传信息的。如果把这样的思路引入社会过程的分析,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都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自由的,其中没有任何必然性的规则,但是在这些表面的自由行动背后都有深层结构的东西在控制着人,这种深层结构也具有二元代码的形式。因此,鲍德里亚说:“这就是第三级仿像,即我们的仿像。符号延续着‘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这就是符号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意指的终结。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或操作仿真。”在鲍德里亚看来,在深层结构中所进行的代码操作是一种仿真 (这种仿真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模仿、伪造。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模仿的精神气质,一种不死的精神实体。这种精神实体像遗传密码一样在当代世界出现)。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现代社会如何通过代码操作这种新的模仿形式(仿真),从而控制人。鲍德里亚说,根据遗传密码模式进行的调节“占据了最平常的生活。数字性就在我们中间。正是这种数字性纠缠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信息,一切符号,它最具体的形式是测试、问/答,刺激/反应”。
按照鲍德里亚对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解,在后现代社会,由于商品生产以及信息的生产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基本需求。于是,各种商品或者信息就要不断地刺激人们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根据这种刺激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当然,在正常情况下,人会对各种刺激进行理性的反思,并根据这种反思而做出判断。但如果一个人所面对的刺激如同电影给人的刺激一样,那就来不及做出判断了。我们知道,电影所提供的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刺激,人对于电影中所提供的每个画面都必须做出及时的反应。它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想像和反思的空间。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指出的那样:“电影观赏者如果不想漏掉连续的事件,就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思想”。同样,在当代社会,由于过多的信息或者过多的广告刺激,人们无法判断真假。这就如同看电影的人一样,人们无法对于这些东西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连续的碎片化的图像对人进行了连续的刺激,它不给人留下思考的时间。人们对它只能进行简单的是或者否的反应。在能这样的情况下,人都只能进行简单的“是”或者“否”(0/1)的反应。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分析所谓的全民公决,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在全民公决中,参与其中的公民是不是不受任何干扰的公民呢?或者说,他们的选择是不是不受到任何信息的刺激的影响呢?显然不是,他们已经在信息的过度刺激中调整了自己的需要。或者可以说,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社会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了。当全民公决正式实施的时候,公民类似于看电影的观众,只是从他们所获得的信息的角度来公决中提出的问题。作为“观众”,他们只是接受了各种刺激,并对刺激做出反应。这就如同电影观众在看电影时对图像做出是或者否的反应一样。在全民公决中,人们对提出的问题也只能做出是与否的反应。实际上,全民公决中所提出的问题表面上需要答案,而实际上答案早就包含在人们之前所提供的信息中了。在这里,不是问题索取答案,而是答案吞噬了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人们在这里是自由选择的,而且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的,而实际上人不过是在所提供的各种信息的操纵下而给出是或者否(0/1)的反应。因此,在全民公决中,人表面上是自由的主体,而实际上变成了“0”或者“1”这样的代码。全民公决中公民所给出的是或者否的回答看上去实际上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讨论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按照鲍德里亚的方式,把这里所提出的问题理解为仿真的问题,而把这里的回答理解为仿真的回答。从表面上看,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真问题,而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和政治操作中的问题。比如,一些政客为了获取选票而进行的政治操作。在当代社会中,人就处于这样一种回答者的位置。在经济领域,商家通过各种刺激要人们做出买还是不买的回答;在文化领域,过多的电影、电视作品的刺激要人做出看还是不看的回答。而“整个政治领域进入传媒和民意调查的游戏时,即进入问/答的集成电路时,就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从表面上看,公民是进行了自由选择,而实际上公民的选择是在政治炒作的背景下展开的。
四、一点反思
鲍德里亚对于仿像的三个等级的区分说明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人在更高的等级上受到的控制越来越多。如果说在第一个等级上,人不过是在生活中受到了他人的影响,而模仿他人。人虽然模仿他人生活,还是注意自己的“自然”需要。而在第二个等级上,人已经不关注生活的意义问题,而只是像机器人一样拼命生产。而在第三个等级上,人不过是代码,完全受到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刺激的控制,没有任何自主性。
传统上,我们认为,我们所受到的控制是外部的控制,比如,各种政治、经济权力的控制。在封建社会,人受到了无限制的政治权力的控制,在资本主义阶段,人受到了无限制的经济权力的控制。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权力都加以限制,那么我们就自由了。在鲍德里亚看来,人不仅受到外部的权力控制,而且还受到人自己内部因素的控制,这是人自己对自己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即以自身为目的的自律,而是自己对自己的伤害。比如,在第一级仿像中,人努力模仿贵族来生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实力来过自己的真实生活,比如死要面子活受罪地去购买名牌产品。这种“自动木偶”式的生活有意义吗?人不顾自然性,不顾自己的丰富情感,而把自己变成像机器人一样,努力生产,而不顾生产的目的,这样的生产有意义吗?最后,在过多的外部符号刺激的社会中,人完全跟着别人的诱导跑,而不能进行自己的理性思考,人在这里被训练得像巴浦洛夫的“狗”,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在所有这些不同的仿像等级中,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模仿”,跟风跑。我们被这种“模仿”精神所束缚。人在这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
如果仅仅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一定是普通衣服更合算。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中生活的人们却会违背市场经济中的理性核算的精神,居然出现一种共同的趋势:去购买不合算的东西呢?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资本主义精神:等价交换的交易原则可以被违背,但是等价交换的精神却不能违背。人们购买某个名牌产品不是因为他的使用价值而购买,而是因为它的交换价值而购买。一种东西越贵越有人购买。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比别人更有“面子”:一种按照等价交换精神所理解的“面子”。值钱的东西穿在身上就有“面子”。有些人会觉得,用这种方法来表现自己的面子还是太“土豪”了,这就如同把黄金穿在身上那种“土豪”气。于是,我们必须换一种更加“高雅”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面子:跟有钱人一起吃饭有“面子”,跟高官在一起拍照有“面子”。然而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有一种“价格”的核算在其中发挥作用。所有这些方式都不过是变换了一种方式的“土豪”(新兴资产阶级),“土豪”的精神(等价交换的精神)没有变。我们恐怕不仅需要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且要进一步反思每个人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土豪”精神、模仿精神、同一性的精神,如此等等)。因为这种精神恰恰建立在人格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在重新塑造人格上的不平等。在探讨自由和平等的时候,我们恐怕必须思考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给我们所带来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1]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2]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