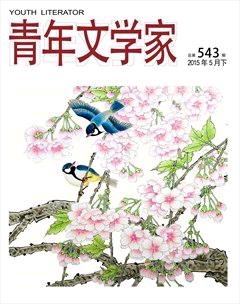从洒脱的“云”到卑微的“水”
摘 要:《偶然》和《云游》是徐志摩前、后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两首诗中均以“云”和“水”的意象来抒情,但抒情主人公却由“云”变为“水”,从这一“症候”入手,我们可以窥视到诗人在这两个时期情感世界和心理状态的隐秘变化——由洒脱积极到卑微消极。
关键词:徐志摩;《偶然》;《云游》;症候式分析
作者简介:卢志娟(1978-),女,副教授,现任教于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5-0-02
如果将诗人徐志摩作一比喻的话,“云”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浪漫一生的诗人就像天空中飘荡不定却舒卷自如的云朵,仿佛漫不经心,却以其深挚动人的诗篇洋洋洒洒地将自己的游走轨迹深深浅浅地涂抹于生命的天幕上。
诗人亦钟情于云,在许多诗作中都借“云”抒情,在其名诗《偶然》与《云游》中也同样出现了“云”的意象。更巧的是,这两首诗中,还有一个相同的意象——“水”。而且,两诗皆以 “云”与“水”的关系表情达意,有某些相似之处。除了“云”和“水”的意象,两首诗中还各出现了一对人物意象:《偶然》中是“我”和“你”,《云游》中是“你”和“他”。虽如此相似,两诗传达的诗情却是天壤之别。
《偶然》写于1926年5月,初载于同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镌》第9期,属其前期的作品。《云游》写于1931年7月,初以《献词》为题辑入同年8月上海新日书店版《猛虎集》后改此题载同年10月5日《诗刊》第3期,是其后期的作品。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距徐志摩遇难辞世仅4个月左右。古语云:诗言志。这两首诗也应该是徐志摩前后期心境的真实写照。
同为第一节,《偶然》是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惊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而到了《云游》中则变成“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在《偶然》中诗人自拟为“天空里的一片云”,不经意间将自己的影子投到地面上某处水面的波心。而对于这样的遇合,诗人说“你不必惊异,/更无须欢喜——”,“我”将“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们看到的是“云”(我)的洒脱和“水”(你)的卑微。而到了《云游》中在空际云游的那片云彩已不再是抒情主人公“我”的化身,而成为“你”的代言;并且,“你”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倩影投射在“卑微的地面”上的“一流涧水”中。于是虽然从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云”的洒脱和“水”的卑微,但事实已截然不同——是“你”的洒脱,“他”的卑微。而此处的“他”不过是“我”的替身。也就是说,在第一节中,抒情主人公在人称上出现了差异:《偶然》中是第一人称的“我”,《云游》中则是第三人称的“他”;此外,抒情主体和抒情对象的位置进行了互换,即抒情主体由《偶然》中的“云”变为《云游》中的“水”,而抒情对象则由“水”变为“云”。
在《偶然》的第二节中,徐志摩说“你(水)”、“我(云)”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我们如同各自有着不同轨迹的两颗星,虽然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们彼此照亮对方的生命,但我们注定各分东西。之后,他劝诫对方:“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而在《云游》的第二节,诗人用了如下的诗句来进一步抒发内心的情感:“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如果说《偶然》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在错过后的略带惆怅的释然的话,在《云游》中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失去后的彻骨绝望了。
这些变化和不同到底寓示着什么?胡适对徐志摩的一生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爱、美和自由。其实这也是对徐志摩诗歌的精要概括,在徐诗中,这三者往往又是合而为一的。徐志摩大多数的诗歌都与他的个人情感生活有密切联系。这两首诗亦是如此。那么,两诗创作时徐志摩的感情生活处在什么状态呢?《偶然》写作之前,徐志摩的人生和个人情感经历了较大变迁。1922年,徐志摩和原配妻子张幼仪离婚,并下定决心要得到林徽因的爱情,但是阴差阳错,林徽因和梁思成订婚,并于1924年双双赴美国留学。紧接着,徐志摩生命中的第三个女子——陆小曼走入徐志摩的情感世界。写作这首诗时距徐志摩和陆小曼订婚(1926年8月14日)仅有3个月左右,距二人结婚(1926年10月3日)也只有5个月左右。此前陆小曼为了徐志摩冒天下之大不韪,冲决各方压力,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和高贵的身份与王赓离婚,并搬到徐志摩的住所,伴其左右。徐、陆正处在神仙眷侣般的热恋之中,此诗是二人合作的剧作《卞昆冈》中老瞎子的唱词。而据林徽因讲,这首诗是写给她的。从诗歌所流露的感情来看,它确实应该和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恋情有关,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徐志摩在下定决心要和陆小曼终老一生之后,对于上一段感情的一个了断。虽然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感情纠葛中徐志摩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动位置,更谈不上主宰,但由于此时诗人正处在新的恋情当中,人生有了新的寄托,新的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在这首诗中他大胆坦率地运用了第一人称的“我”去抒发情感,且用“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这样的比喻让自己始终处在主动、甚至主宰这段感情去留的位置。在诗的结尾诗人以他惯有的洒脱和不羁豁达地劝诫对方:“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其实也是在劝慰自己。在这首诗中,我们还是能感到一丝爱而不得的酸涩,只不过由于诗人正处在一段新的爱情坦途之上,所以这种酸涩便被大大地淡化隐藏起来了。
个性内向羞涩的诗人戴望舒曾说,诗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但像徐志摩这样单纯明朗的诗人何以也突然会在《云游》里变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呢?为何第一人称的抒情主人公 “我”被第三人称的“他”所取代呢?这种抒情策略的变化是有更为内在的原因的。就两种人称而言,“我”给读者的印象是“我”的故事即是诗人的故事,诗中抒发的也是诗人的情感,即所谓“表现自己”;而“他”给读者的印象是诗人讲述的别人的故事,抒发的情感当然也并非诗人的情感,即所谓“隐藏自己”。开朗自信的人勇于表现自己,内向自卑的人则愿意隐藏自己。那么,是什么让徐志摩开朗自信变得内向自卑了呢?熟悉徐志摩的人都了解,徐、陆二人的婚姻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美满幸福,而是充满了各种不和谐的因素,陆小曼的任性、奢靡以及孱弱的身体和二人婚后的经济压力这样的生活令徐志摩身心俱疲。
1931年,在经历了几年的痛苦挣扎之后,徐志摩决心离开上海到北京任教,借此重新振作起来,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因此忍痛离开;母病妻弱,我岂无心?所望你能明白,能助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拔,脱离痼疾;彼此回复健康活泼,相爱互助,真是海阔天空,何求不得?”[1]P798当然,他也希望陆小曼能一同北上,但陆小曼已经沉迷在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无意北上,于是徐志摩只得更加疲惫地奔波于京沪两地,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赚钱,总是赶不上家里的花销,为了养家他四处举债,甚至不得不将“来回票卖了垫用”[1]P817,其窘境可想而知。
但是,在北京工作的这段日子,苦是苦,累是累,还是有乐趣的。丰富充实的工作,志趣相投的朋友使徐志摩从上海的污泥浊淖中拔出脚来,“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2]P238 特别是徐志摩一直深爱着的林徽因此时也因病辞去了东北大学的教职,在北京养病。此际,徐、林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其实,早在1927年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请你回国后告诉志摩……昨天我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时的志摩现在真真透彻地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3]P319。在经历了那么多世事的变迁和沧桑之后,两颗心真正达到了相知相惜的默契。但是,此时,徐、林二人都已有家庭,林徽因又是对家庭极负责任的人,所以尽管激情澎湃,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智,只把这份感情深藏在心底“永远纪念着”。在徐志摩遇难后不久,林徽因对胡适说“但是他活着,我待他恐怕仍不能改的” ,很可能在两人的这段相处中,徐志摩也已经感觉到了林徽因对他“恐怕仍不能改”的态度,这无疑又增加了他情感中的苦痛——和陆小曼的婚姻看不到希望,对林徽因的爱恋又是这般无望。在这样的境遇之中写就的《云游》除了绝望,夫复何求?
于是,诗人便采用这样一种曲折迂回的抒情方式——抒情主人公由第一人称的“我”变成了第三人称的“他”,抒情主人公也由积极主动的“云”变为消极被动的“水”。如果说在这首诗里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几乎同时创作的另一首诗《你去》中,便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这是徐志摩在给林徽因的信中附的一首诗作。诗中,诗人直言“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有我在这里,/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目送你归去……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株树,/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有乱石,有钩刺胫踝的蔓草,在守候过路人疏神时绊倒!……”不必做过多分析解释,这首诗和《云游》互相印证。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飞机失事徐志摩接下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可以断言的是,在1931年间,徐志摩的“单纯信仰”已经到了危机边缘,在他看来“爱”、“美”、“自由”离他渐行渐远了,而且几乎永无可能再次走近,他所向往的如云朵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生活理想也化作了泡影,生活如同“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的“妖魔的脏腑”般“阴沉,黑暗”, 诗人的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4]P324当然也就不难理解在《云游》中的这些变化乃至诗中流露出来的自卑和绝望情绪了。
仿佛是谶语,四个月后的一天,当诗人“翩翩的在空际云游”之时,如同一朵云彩,“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十六年后,林徽因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个个连环,永打不开,/生是个结,又是个结!/死的实在/一朵云彩。……一曲溪涧,日夜流水,/生是种奔逝,永在离别!/死只一回,/它是安慰。” 在这首诗中,我们再次看到“云彩”、“溪涧”,这当然不会只是“偶然”。在世人为徐志摩这样杰出的诗人英年早逝扼腕叹息时,林徽因却说“死是安慰”!这不禁会让我们想起张爱玲那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慈悲,所以不忍,所以会说“死是安慰”!
云与水,本是同源。在徐志摩笔下便成为诗人情感生命的象征,无论是《偶然》中的“云”的洒脱,还是《云游》中的“水”的无奈,都是诗人最真实的生命体验。读懂云,读懂水,我们便可读懂诗人虽短暂却真实的生命。他来过,真实地爱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这人生,也许算不得完美,可一定够得上完整、丰满!
参考文献:
[1] 来凤仪.徐志摩散文全编·爱眉小札(1931年3月19日信)[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2]林呐.胡适散文选集·追悼志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 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4] 梁仁.徐志摩诗全编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