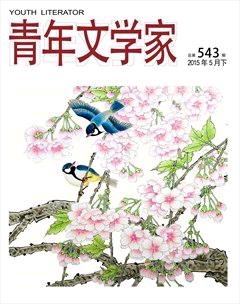佛教艺术中的“孔穴与胜境”
樵馨蕊 江颖杰
摘 要:佛教艺术博大精深,佛教思想艺术和佛教绘画艺术是佛教精神的集中体现,佛教倡导的修行与得法之间存在着由孔穴进入胜境的叙事主题,意在通过修行感化达到极乐世界或顿悟的境地。本文从佛教思想艺术和佛教绘画艺术具体分析佛教艺术中体现出的孔穴与胜境的转变。
关键词:孔穴;胜境;佛教思想艺术;佛教绘画艺术
作者简介:樵馨蕊(1994-),女,山西省太原市人,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职务:学生,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5--02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从广义上来看,“艺术”领包涵多种艺术门类,如文学、舞蹈、建筑等,甚至思想理论也可以被视为艺术的一种;从狭义上看,“艺术”又指造型艺术,如音乐、绘画、雕塑等。所以佛教艺术属于宗教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体现了佛教的教义内容、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孔穴与胜境”也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一是狭义上,借助一个“孔穴”的结构,包括“孔”、“穴”、“阙”、“门”,以通向一个未知的、美好的洞天胜境 。另一说是从广义来看,可以由很小的点发展到大事物,亦或是由思想的死胡同忽然豁然开朗走向一个新境界。“孔穴”和“胜境”间也可以存在相互转化,由孔穴窥探秘籍走向胜境,也可从胜境咎由自取奔向南墙,走入了孔穴。
佛教思想艺术
佛教道义博大精深,常给人以顿悟之教诲,最终达到感化的目的。而生存、修行和得法对于信佛之人也好像“孔穴与胜境”:生存是短暂的孔穴,通过修行,最终可以达到得法升天的胜境。
佛教中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有情众生的生命都是苦。佛教“四圣谛”的第一条便是“苦谛”,“三法印”最后一条是“一切皆苦”,这是佛教对人生本质的价值评判。生命和生存本身就包含着烦恼和痛苦。佛教中对苦的定义,不仅仅指情感遭受痛苦,而是泛指对精神的压迫,即心理层面上的压迫烦恼的意思。佛教中有六苦、八苦、十苦等说法,其中八苦最为普遍: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
《杂阿含经》第437经记载:“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诸行变易法故,说诸有所受悉皆是苦。”即世间万物变化无常,这样与人祈求永恒安乐的本性趋求相违背,所以人生来所承受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苦。人生之苦的根源在于“无常即是苦”。
如何从苦中脱离出来,只有通过因果报应,轮回之所,即佛教所宣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劝诫人们爱利他人,这在佛教艺术主题中也反复出现。在经过轮回之后,还需勤奋修行,只有不畏艰难困苦,才能最终达到涅槃的境界。
佛教艺术的最高主题是涅槃——修行者通过修行和觉悟,就可以达到超出尘世的理想境界。即本文中所提到通过修行的“孔穴”,最终达到理想中的的“胜境”。在佛教教义中,涅槃即为“四圣谛”中的“灭谛”。涅槃的意义是寂灭,通过修行消除了苦因,通过消除苦因而进入寂灭常乐的状态 。
笔者认为想达到只修行是不能达到涅槃的,何时能对佛法有所领会,消除人与万物的有限性得到的圆满、清净、寂静的状态。甚至肉体和心灵都绝对的消失,了灭烦恼,净心犹存,才能达到无余涅槃的境界。这样就需要在某一时间节点上,修行参禅时恍然大悟,洞见真谛。即“悟”的境界。仿佛从孔穴的困境中突然豁然开朗开启了通往胜境的大门。
佛教中国化后,禅宗兴起,“悟”进一步被推到“顿悟”的极致,“悟”也因此成为佛教艺术和美学的重要范畴。教禅宗六祖慧能大力宣扬顿悟成佛说,从中便体现了从“孔穴”到“胜境”的转化——成佛是人对自身具有的本性的觉悟,众生对本性由迷到悟的转变在一刹那间,一念顿悟则成佛。
佛教绘画艺术
佛教绘画是宣扬佛教思想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佛教绘画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佛教教义,供佛教信徒礼拜敬奉以及供寺院殿堂庄严之用。佛教画像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绘画已有独立的发展;佛教绘画传入中国之后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收阶段,即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画家吸取佛教绘画的技术,推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第二阶段为大发展时期,隋唐时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画家们进一步汲取了各方传统优势进行使佛教绘画创作;第三阶段为衰落阶段,宋代佛教由盛转衰,佛教绘画也推出主要历史舞台。
佛教壁画的题材可分为六种类型:经变、本生故事、装饰图案、佛传故事、佛教诸神图像、供养人像。经变和本生故事是佛教壁画中最常见的题材,其中经变又更具中国特色,特在此浅析几句。
经变,全称“佛经变相”,是用图画形式表现佛经。佛教壁画中经变题材是由佛经决定的,又说佛经图画本,有维摩变、涅架变、西方净土变、降魔变、地狱变相等等。佛教绘画利用宏大的场景,雄浑的气势,带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和感染力,使人在观赏中领悟佛理。“维摩经变”因题材的趣味性和其中所包涵的佛法道义之深厚精妙,在石窟寺壁画和后代的佛像绘画中都有体现。
“维摩经变”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壁画的一常见题材。描述的是神通广大智辩过人的维摩诸居士与诸菩萨中智慧辩才第一的文殊菩萨辩论佛理的场面。由于这场辩论非常精彩,所以许多菩萨、天神、帝王群臣及男女信众都竞相来观战。随着双方的往复舌战,空中出现了种种奇迹。最后,双方都去礼渴佛陀。“维摩变”的流行始于六朝,当时维摩话多被措绘为“清威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的南朝士大夫风度;至唐代,画家笔下的维摩洁则变为一个身体健壮的老头,一个热情而善变的“学者”形象 。莫高窟第220窟是有贞观十六年(642)题记的重要代表性洞窟窟,其中的维摩诘经变极大地体现了其价值:此画画于东壁窟门两侧,面积比隋代大了许多。画面仍以《文殊师利问疾品》为中心。按经文,维摩诘本来就没病,而是“其以方便,现身有疾”。文殊师利菩萨问他:“居士是疾,何所因起?”维摩诘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画家用“伸二指”表达了维摩与文殊对不二法门的讨论,既合乎佛教哲理,又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手段。
唐代中期以后,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因此佛教壁画题材中宗教成分明显减少,反而世俗色彩目趋浓厚:经变画中的极乐世界也好似幻想中的王宫,画中的菩萨则变成了唐代贵妇人。至晚唐五代,世俗生活题材的壁画所占比重大大提高,往往占据了石窟或寺庙中的重要位置:如敦煌第156窟中的唐代壁画“张义潮夫妇出行图”以及敦煌第100窟中的五代壁画“曹议金夫妇出行图”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宋代儒学占据文化主导地位,佛教地位衰微,同时随着都市经济发展,受市民文化的影响,佛教壁画的主要目的也转为招徕游客。宋代中期以后,“院体画”或“文人画”兴盛,文人学士多不屑于壁画创作:于是佛教壁画就主要由民间工匠绘制。佛教壁画创作队伍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壁画题材的世俗化,罗汉群像开始流行以常人作为模特:“说法图”中大量地穿插着世俗生活的情景,有些壁画几乎就是山水风景画,如敦煌第61窟中的北宋壁画“五台山全图”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宋代以后,大多数佛教壁画的题材已变得更加程式化、图案定式的佛教诸像群像,甚至还出现了道教的神仙、儒家的孝子贤人乃至中国民间信奉的神灵。
这样的变化对于佛教道义本身的发展确实一种束缚。上文提到,佛教的终极追求是超言绝象的纯粹寂灭的状态——回归自己的本心,回到一种没有执著分别,没有外物困扰也没有个人情感活动的空寂心态。佛教绘画对于佛法的宣传虽然形象,但因艺术本身的特点,绘画中不可避免带有丰富、强烈的情感。在这一点上佛教和艺术又是对立矛盾的,从本生、经变到世俗主题,越发失去了本身道法的“禅意”,这样的具象过程又导致了佛教艺术从“胜境”落回了“孔穴”之中。
佛教艺术的“孔穴”与“胜境”因其本身的多重含义和道义精神,与其他事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并且佛教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佛教思想不能割裂开来,否则只是空谈。而这其中的玄妙又似乎只能用佛教这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心态境界才能体悟。
参考文献:
[1]彭肜. 中国佛教艺术研究[D]. 四川:四川大学, 2002.
[2]施萍婷. 敦煌经变画[J]. 敦煌研究, 2011, (05): 1-15
[3]徐峰. 汉魏六朝文献与文物视野中的“孔穴与胜境”[J]. 中华文化论坛, 2013 , (03): 6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