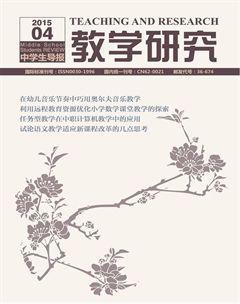“替考入罪”之冷思考
袁林林
摘 要:如今,“替考”现象的猖獗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立法界随之呼应,提出将替考入罪。本文从“入罪标准”的视角分析认为不宜轻易将替考入罪,刑法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介入,应当是有限度、有标准的。
关键词:替考;入罪标准;不宜入罪
一、“替考入罪”释义
“替考”是考场中的一种舞弊行为,是指考生使用用各种欺骗手段,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
而对于什么是“入罪”,学术界和司法界都没有明确界定,生活中不断出现“超生罪”、“人肉检索罪”、“网络暴力罪”、“替考罪”等新罪名,立法界也遥相呼应,在刑法修正案中新罪名不断出现,似乎“入罪已成为一种习惯”。[1]那么,入罪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制定统一的标准适用?
二、从“入罪标准”角度分析替考不宜入罪
鉴于以上分析,对于一行为要进入刑法圈必须符合一定的入罪标准,那么,入罪标准具体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指标?有没有统一的考量因素据以判断行为的“入罪标准”?通过对现存犯罪的研究,笔者认为应具体考量以下因素:
1.行为的发生率,即一行为发生数量/总人口数。这一指标的统计是要在数量上考量行为的危害程度及是否会对社会形成新的不良导向。当然,此时我们需要一个对比基数,这个基数需要我们在现存犯罪中统计出来,这样,当新行为出现,我们只需要将其发生率与对比基数比较,当大于对比基数时,说明该行为已对社会形成不良导向,需要法律予以调整,此处的法律指的是非刑事法律。实践中,“替考”行为还是占少数的,而且通过严格规定监考人员的义务与责任,同时加强电子系统监控,相信是可以避免“替考”现象发生的。
2.行为的处罚率,即该行为受处罚的数量/行为发生数量。该“处罚”是指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而非刑事处罚。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新的违背道德诚信的行为不断出现,但不能一出现新行为,就立即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应该有一个量变到质变过渡的过程。在行为出现的开始阶段,应该先由道德自行调整,当道德并未改变该失德行为的发生,行为的发生率不断上升,直至达到行为发生率的对比基数时,将其纳入非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范畴,如民事或行政处罚等。只要在该阶段的处罚率处于一定的幅度范围之内,说明其行为得以有效规范,即不需要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同样,只有当行为处罚率高于处罚率的对比基数——可称之为“犯罪临界点”时,才将其归入犯罪圈,有刑法来调整。当然这需要以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与执行为前提。对于“替考”行为,我国目前的规范体制并不完善,关于此点将在后文予以详述。
3.社会的容忍度,即对该行为予以容忍的人口数/总人口数。法治化要求我们尽量排除融情于法,减小舆论、道德对法律专业化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法律是不会完全排除道德、舆论影响的,就犯罪圈界来说,道德标准事关犯罪标定的实质标准问题。[2]对于“替考”行为,据调查,还有大部分人表示是可以理解与宽容的,因为无论是“替考者”还是“被替考者”,其并没有太恶劣的动机。
当然,以上提到的行为的发生率、处罚率和社会的容忍度需要更精确的统计数据支持,这需要国家收录数据并建立大数据系统,并不断更新,为“入罪”标准提供技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5条规定:“国家加强对统计指标的科学研究,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提高统计的科学性、真实性。”这为指标分析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3]
4.刑罚的可替代性。替考行为固然可恶,但真的只有“入罪”才能得以遏制吗?除了刑罚已经别无选择吗?那么来看看我国对于“替考”类似考试作弊行为是如何规定的。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替考”等作弊行为及处理办法,如警告、取消考试成绩、停考一到数年参加考试或限制其今后参加考试的资格等行政处罚措施。可见,目前我国关于考试作弊的立法层次较低,且无论是司法界还是学术界,都将重点置于国家考试立法宏观方面方面,比如大多数学者建议国家应该制定《考试法》,规范混乱的考试制度现状,对于其中考试作弊处罚制度却嫌少提及,导致实践中对于“替考”等考试作弊行为的处理也都草草了事,一般都由主考方单方面仅针对作弊者作出处理决定,无论是事实依据还是法律依据都不明确,从而出现了很多考生不服处理决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表面上,作弊行为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遏制,实际上是现行对作弊行为的处罚制度并没有有效有力的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是作弊处罚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执行不力。基于此,国家应先加强非刑事法律规范对“替考”规制的完善,尽量不动用刑法。
5.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严厉性性与最终性决定了“入罪”标准必须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即“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4]首先,从经济性角度必须限制刑法规制的广度与深度。如前所述,实施“替考”行为的很大一部分主体是高级知识分子,“入罪”不仅会严重影响“替考者”和“被替考者”的人生方向,而且对于国家而言,是一笔更大的损失。其次,从最后性角度必须严格限制考试舞弊行为的主体与范围,不能将刑法作为调整所有失德违法行为的唯一手段。再次,从有限性角度看,刑法并不能将其他法律所不能规制的行为全部纳入,刑法有其自身特定的作用范围与功能。最后,从宽容性方面,刑法应当最大限度的尊重公民的受教育权,“替考”行为违背诚信道德,但我们可以期待以宽容、合理、有效的措施或手段达到立法目的。
6.西方法律的借鉴。目前大部分主张“替考入罪”的学者都是效仿国外做法,扩大刑法规制范围。其实西方“入罪”标准确实很低,但他们“出罪”也很容易。西方的基本做法是:在刑事立法上扩大处罚范围,在刑事司法上限制处罚范围。[5]这种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适当分离,有利于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反观我国刑法,一直以来都是奉行刑法规制范围的合理化,保持刑法作为最后的法律屏障。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规制的范围必然会随之扩大,刑法修正案(一)到(八)及修正案(九)草案的出台是最好的作佐证,但不能因此就完全效仿西方的做法,这和我国的整个法律体系是不相协调的。如果“替考入罪”,将“入罪”标准降得太低,使得犯罪常态化,那么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之下,“替考者”与“被替考者”矛盾、双方家庭矛盾、当事人与监考人员及学校的矛盾都将爆发,刑法的作用就失去了。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刑法属性、立法现状及国情现状,不宜将“替考入罪”,应坚持刑法严厉性的同时保证刑法的最终性与宽容性,如边沁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6]
参考文献:
[1] 张国轩.漫谈立法的“入罪”习惯[J].人民检察院,2006,(5上).
[2] 张远煌.现代犯罪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218.
[3] 汪明亮.“严打”的理论评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6-47.
[4]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53.
[5] 张明楷.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J].人民检察院,2014,(5上).
[6] 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J].法商研究,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