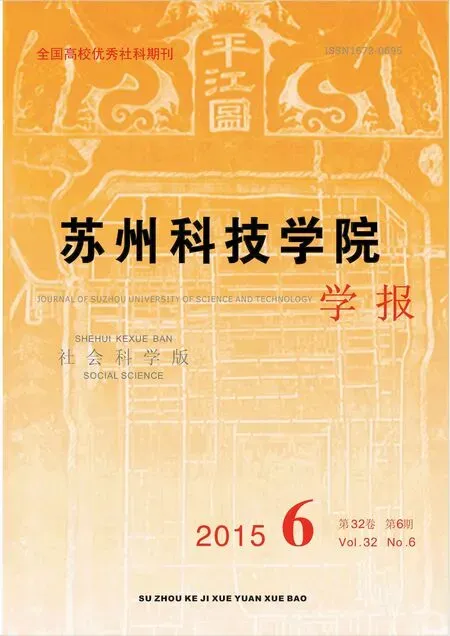工业化时期大伦敦的失序困局与警制改革论析
许志强,程 慧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工业化时期大伦敦的失序困局与警制改革论析
许志强,程 慧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工业化时期,英国大伦敦的社会治理变得愈加困难。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与人口的剧增,各类犯罪与失序问题明显增加,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传统治安力量非常薄弱,执法效率低下,犯罪治理严重依赖社会力量的协助。早期的治安体制改革虽经历了局部调整,但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教区自治体系,直到1829年《都市警察法》的出台才确立了统一的、专业化的大伦敦警察制度,使大伦敦的治安环境大为改善。
大伦敦;失序;传统治理;新警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治理重要性的凸显,历史上的社会治理——警政史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作为现代警制的滥觞之地自然也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国内学者对英国警察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从警政实务、社会功能及历史演变等视角展开探讨,对其警制改革的最初缘起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参见谢闻歌:《英美现代警察探源及其社会调控职能透析》,《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吴铁稳、张亚东:《英国大伦敦警制建立初探》,《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吴铁稳:《论19世纪英国新警察社会形象的变迁》,《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李温:《英国警察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现行体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传统的英国社会以地方自治为主,警察制度的确立与普及则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兴起,标志着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曲折的改革过程,大伦敦警制的确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对新警制在英国其他城市乃至全国的推行具有先行示范作用。
警察史专家理查德·伦德曼(Richard Lundman)把警察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在非正式警察阶段,社会成员共同分担社会治安的职责;在正规警察阶段,专职警察担负起社会治安的任务;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传统治安体系与社会力量相互协作的时期。[1]2171829年英国《都市警察法》的颁布是由非正式警察向正式警察转变的重要分水岭,它确立了英国第一支现代化的警察队伍——大伦敦警察,对许多国家现代警制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大伦敦警察的诞生是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双重压力的结果。工业生产的扩大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起人口的大规模集聚和流动,传统的社会治理机制则逐渐式微,城市治安环境趋于恶化。在社会大转型背景之下,犯罪、冲突、暴乱的增加客观上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制衡力量以取代传统的治理体制。
一、大伦敦城市化背景下的失序问题
18世纪中后期,大伦敦逐渐形成了包括伦敦城、威斯敏斯特自治市(Westminster)、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以及萨斯沃克(Southwark)、萨里郡(Surrey)部分地区的大都市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伦敦”(Greater London)。1750—1801年间,伦敦的人口从67.5万增加到90万,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容纳了整个英国近1/10的人口,而同时期的巴黎仅容纳了法国总人口的1/40。[2]126城市扩大与人口剧增使伦敦的治安环境趋于恶化。治安法官菲尔丁指出:“整个伦敦就是一片广阔的森林,盗贼可以安全地藏身其中,就像野兽在非洲和阿拉伯的沙漠一样。”[3]144-145这一时期,大伦敦经历了严重的失序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类犯罪活动猖獗、骚乱现象频仍、民众集会引发的混乱层出不穷,而传统治理体系在这些乱局面前却显得捉襟见肘。
首先,日益猖獗的犯罪活动,特别是盗窃与抢劫成为伦敦政府深感忧虑和棘手的问题之一。曾经遭受过抢劫的大贵族霍勒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就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伦敦,即便白天出行也像参加一场战斗一样。”[4]1761786年,伦敦市长在向国王提交的请愿书中强调:“最近3年来,首都及其周边的犯罪和堕落之势迅猛而惊人。”[5]598根据治安法官帕特里克·科洪(Patrick Colquhoun)的分析,伦敦每年大约有11.5万人参与了各种形式的犯罪,也就是说,每9个生活在伦敦的人中就有1人是潜在的罪犯;每年因各类犯罪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多达210万英镑。[6]515-518在一些贫民窟地带,像惠特查普尔(Whitechapel)、斯皮塔菲尔德斯(Spitafields)、贝斯纳尔格林(Bethanal Green)、 旧尼克尔(Old Nichol)等区域的治安状况更加堪忧,普遍存在着盗窃、酗酒、赌博、卖淫等犯罪活动,被《泰晤士报》称为“疾病之温床,窃贼之巢穴”[7]117。进入19世纪,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量英国军人复员待业,严峻的失业问题曾一度导致英国特别是大伦敦的犯罪率陡然猛增。[8]138-139有学者认为,当时英国日益严峻的犯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象,而伦敦则是名副其实的犯罪之都,“犯罪是这座城市最大的产业”[9]27。由表1可以看出,伦敦罪案数量在19世纪初所占全国的比例(近1/5)的确远远超过其人口所占比例(近1/10)。

表1 1811—1826年英国与大伦敦起诉罪案数量
其次,伦敦的聚众骚乱在18世纪中期以后变得愈加频繁且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在近代早期,许多骚乱的发起者都是妇女,她们经常通过此种方式迫使暴涨的粮食价格回落到大众可接受的水准上。[10]233-2371660—1779年间,伦敦米德尔塞克斯法庭上被起诉的415名骚乱者名单中,七成以上都是女性。[11]138但18世纪中后期,骚乱越来越成为各类群体表达诉求、引起关注的一种方式。大多骚乱都混杂着各种喧嚣仪式和“嘈杂音乐”(rough music),有些则引发了严重的暴力破坏活动。1765年,许多纺织工人聚集在伦敦东区,一些人还敲锣打鼓,为了让议会通过禁止进口外国丝绸的法案,他们数天彻夜在街上敲打游行,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11]148在1784年的选举活动中,一些骚乱者一边游行一边用骨头和切肉刀敲打着,制造出刺耳的声响,表达他们的不满。[12]35据《绅士杂志》(Gentleman’sMagazine)报道,1800年9月,伦敦的谷物商、屠夫、面包师和奶酪商因对粮食价格疯涨问题不满而发起一场骚动,治安法官果断制止才避免了更大范围的破坏活动——仅有几扇窗户和几盏路灯遭到损坏。[11]1481780 年7月,伦敦发生的“戈登骚乱”导致了持续一周的严重混乱,连治安法官的办公场所亦遭到暴民洗劫,整个伦敦政府几乎陷入瘫痪状态,最后经国王乔治三世亲自召集军队才将骚乱平息。这次骚乱导致300多人死伤,毁坏财物价值近10万英镑。[13]93戈登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层社会对传统骚乱的看法,伦敦政府开始由宽容转向严控。历史学家罗伯特·舒梅克(Robert Shoemaker)在《伦敦暴民》一书中认为,聚众骚乱是18世纪伦敦大众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但随着社会恐惧的扩大,这类暴力行为也越来越不被官方和民众认可。[11]xiii
再者,进入19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因各类公共仪式、节日庆典、传统集市等所出现的大规模民众聚会也引起政府的忧虑。比如,每次公开绞刑,伦敦的绞刑场都会汇聚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围观,政府为此要雇佣大量治安人员以防不测。1807年,纽盖特监狱(the Newgate)广场的一次公开绞刑吸引了近4.5万名伦敦市民,由于人群的拥挤和混乱导致27人死亡,百余人受伤。[14]1361812年,在约翰·贝林厄姆(John Bellingham)接受审判和绞刑期间,官方不得不雇佣500名临时治安人员负责老贝利法庭(the Old Bailey)、纽盖特监狱和绞刑场附近的秩序维护。[15]62每年11月5日的“盖伊·福克斯(Guy Fox)之夜”*1605年,福克斯等极端天主教徒企图用炸药将国王和议会成员炸死,11月5日,该阴谋被治安法官识破,策划者皆被逮捕行刑。后来,人们在每年11月5日都庆祝这个密谋被粉碎的日子,并形成传统。,官方也会严加防守,因为许多人会在这天高举火把涌向街头,以焚烧“福克斯”的纸像和燃放爆竹来庆祝这一节日。每年的巴托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ir)*这一古老的集市自12世纪开始设立,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取消。期间,伦敦都要增加治安力量对集市上的下流歌曲、情色木偶戏、粗俗音乐以及二手货市场上的赃物交易进行审查。1812年,有242名临时治安人员参与了市场管理,而几年前仅靠30名治安人员就足以保持秩序。一位巡查官解释说:“近几年来,参加集市的人数迅速增加,需要扩大治安力量进行监督。”[15]63可见,19世纪以后,伦敦政府的治安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和繁重,原有的治安力量已经难以应对各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政府因聘用临时治安人员的相关开支明显增加,伦敦城在19世纪最初5年内的相关开支就增长了近1倍。[15]65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失序问题,英国政府曾一度通过加强“血腥立法”来威慑各类犯罪。刑法体系中的死刑条款自18世纪到19世纪初已经增加到了200多条,比之前几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甚至有些小偷小摸也会被送上绞刑架。[16]ix并且,死刑以公开绞刑的方式执行也意在威吓、警示众人,伦敦泰伯恩绞刑场、纽盖特监狱广场上的绞刑仪式已成为当时英国最引人注目的公共活动之一。但是,如此严苛的法律很难得到切实执行,其威慑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二、大伦敦的传统犯罪治理体系
伦敦失序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与其传统治安力量的相对薄弱、不具专业性以及效率低下有很大关系。治安人员数量与其管辖人数严重失衡,比如,马尔伯勒街区(Marlborough Street District)人口近30万,却只有8名警役;沃斯尼普(Worship)人口16.3万,也只有6名警役。伦敦城分为26个治安区,每个治安区大约选出10名警役,由1名治安法官(也是市议员)统领。伦敦城之外的大伦敦地区主要以教区为治理单位,每个教区选出1名警役。这些警役杂事繁多且不领薪资,实际上扮演着义工的角色。由于传统公共服务精神的减退,越来越多的教区成员不愿承担这一杂役,他们经常通过缴纳罚金或雇佣他人代替的方式予以逃避。1796年,伦敦城区243名警役中仅有98人是本人履职。[6]209各区还招募自己的守夜人(watchman)负责夜间巡逻,每人年薪在13~20英镑之间。[17]21这些守夜人大都从老弱贫民中选出,主要为了使他们有所收入以减轻教区的济贫负担,因为根据济贫法规定,这些弱势群体应由其所在教区负责照养。为增加收入,许多教区警役经常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守夜人也经常在获得好处的情况下对盗贼视而不见。他们的渎职和腐败行为经常受到民众的指责。1785年,威廉·布利泽德(William Blizard)公开批评一些警役被底层社会的盗贼收买,“与他们称兄道弟,共同饮宴,并为他们通风报信”[15]10。
在传统教区自治体制下,大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公共执法力量严重匮乏,犯罪治理必须借助社会力量才能实现,这样,长期以来形成了警民协作的治理体系。在很多情况下,治安法官和教区警役只有借助民间力量方能成功追捕盗贼,在严重骚乱或失序状态下只有求助民兵或军队才能平息混乱,这种严重依赖社会力量的治理体系在急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也日益暴露出其缺陷所在。
为鼓励民众参与抓捕盗贼,英国社会自中世纪以来便形成了“呐喊捉贼”(Hue and Cry)的传统。1258年的《温彻斯特法令》(The Statue of Winchester)规定:在百户区内,无论警役还是普通民众倘发现犯罪活动,应立即大喊并追捕罪犯,其他成年男性也要加入追捕队伍,直至罪犯被逮捕归案,袖手旁观者将受到惩罚。这一规定后来又经过伊丽莎白女王、乔治二世、乔治四世时期相关法令的重申与确认而在英国延续下来。[18]347“呐喊捉贼”的队伍可由受害人召集,亦可由地方警役召集。1735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地方警役应及时有效地组织民众捉拿窃贼或劫匪,未能履行职责的警役可被罚款5英镑。[19]27由于只有将窃贼抓获队伍才会解散,随着参与捉贼的人越来越多,会逐渐形成一种蔚为壮观的捉贼场面,但民众的大量汇聚也会妨碍盗贼的抓捕。“呐喊捉贼”主要是借助社区集体力量来抑制犯罪。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民众参与精神的衰退,“呐喊捉贼”的传统在18世纪正日渐走向衰落。
公布悬赏启事是鼓励或褒奖社会力量参与犯罪治理的重要方式。悬赏启事的发布者可能是王室、政府,也可能是民间社团以及私人(特别是受害者),悬赏金额则根据犯罪类型而定(见表2)。

表2 18世纪检举各类犯罪的悬赏金额
1795年10月29日,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在赶往议会的路上遭到一群“暴民”攻击,他的马车被损坏,本人也大受惊吓。事后,枢密院在《伦敦公报》(LondonGazette)上登载启事,悬赏1千英镑寻找证人揭发袭击国王的暴徒。1810年,乔治三世还亲自签署公告,号召民众勇于检举各类重罪犯人,最高可获得500英镑的奖励。[19]443同年,威斯敏斯特的官员在暴乱中受到攻击,政府立即登载声明,凡能提供相关信息或将暴徒绳之以法者可获得500英镑的奖励。[19]100对许多受害者来说,通过“悬赏启事”求助“捉贼者”(thief-taker)可更为迅捷地追回赃物或逮捕盗贼。1781年,拍卖商理查德·彼特(Richard Pitt)有一批丝绸和锦缎质料的窗帘被盗。起初,他力图自己展开调查,但询问了多家当铺依然毫无头绪。后来,他在一家报纸上刊登“悬赏启事”,声明悬赏5基尼金币(Guinea)索回物品,立即有“捉贼者”回应,并很快将罪犯抓捕归案。通过公开悬赏来破案的做法在18世纪越来越普遍:在20年代,伦敦老贝利法庭所审理案件中,有51起是凭借这种方式破案,而到50年代则有285起案件依靠这种方式破案。[11]3719世纪初伦敦政府用于奖励抓捕盗贼的开支不断增加。1813年,奖励开支不到1 500英镑,1814年增加到2 600英镑,1816年迅速增至4 960英镑,短短4年间,增幅高达2倍多。[19]71伦敦各类悬赏启事的出现提高了民众参与犯罪治理的积极性,同时也促生一些职业“检举人”(informers)和“捉贼者”,他们为获取赏金不择手段,伪造证据、陷害他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人经常被英国民众贬称为“社会的寄生虫”、“无耻的讼棍”。
在传统治理体系下,倘遇到严重骚乱,治安法官必须依赖民众或军队的帮助方能将其平息。根据当时的《骚乱法》(Riot Act),在治安法官公开警告1小时之内,聚众骚乱者(12人以上)应自行离去,在这一时间段内,政府不采取任何暴力举措。倘1小时后,骚乱者仍未解散,政府和市民应将聚众行为视为犯罪,合力将其平息。[20]335倘情况更为严重,治安法官可通过手写的特许状召集军队将骚乱镇压,但他们对此项权力的使用慎之又慎,因为召集军队会招致民众的强烈抵制——他们“宁愿忍受暴民的骚乱,也不愿接受常备军的统治”[21]37。在1780年的“戈登骚乱”中,正是因为治安法官迟迟不敢做出召集军队的决定才导致了更大范围的破坏,最后由国王通过枢密院召集军队将骚乱平息。英国议会对召集军队的做法亦持保留态度,认为它既可以用来维系“王之和平”,也可能会危及民众自由甚或转变为反叛政府的力量。当时的著名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议会辩论中指出,召集军队是“一种任意、危险和恶作剧般的应对方式”,这种做法与英国宪政自由的理念格格不入。[22]这样,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可用于平抑骚乱的军事力量亦非常有限,而英国各大工业城市此起彼伏的罢工与骚乱使得秩序维系更加棘手。有警察史专家指出:“如果骚乱在各地同时爆发,恐怕政府动用全部军队也无济于事。”[1]221可见,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政治精英对诉诸军事力量的做法怀有深深的抵触情绪。这种情况下,在大伦敦组建一支规范、高效、平民化、现代化的治安队伍日渐提上英国政府的改革议程。
三、大伦敦警制的确立
早在18世纪30年代,为方便市民举报和捉拿盗贼,伦敦政府成立了 “流动治安办公室”(rotation office),可视为伦敦警察局的雏形。其中一个办公室设在考芬特花园旁边的弓街(Bow Street),专门负责伦敦城的治安管理,被称为18世纪的“苏格兰场”。18世纪中后期,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与约翰·菲尔丁(John Fielding)两兄弟先后担任伦敦弓街的治安法官,对首都的治安体制做了重要变革。第一,通过雇佣手段将一些民间“捉贼者”转变为官方的“跑探”(runners)。这不仅保证了抓捕盗贼的效率,也杜绝了传统“捉贼者”的腐败和舞弊行为,使其更加规范化。菲尔丁的“弓街跑探”逐渐誉满伦敦,像约翰·塞耶(John Sayer)、约翰·汤申德(John Townshend)等官方“跑探”都因表现出色而深受市民欢迎。第二,建立罪犯信息库。广泛收集伦敦和地方各类嫌犯的信息,与地方治安机构建立关联,力图打破地区限制,促进联合执法。他们还出版了一份专门登载罪犯信息和悬赏启事的报纸,即后来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治安公报》(PoliceGazette)。这样,弓街治安办公室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大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重要刑事情报中心。第三,组建骑兵巡逻队。鉴于伦敦及其周边的盗匪活动猖獗而抓捕工作异常困难,菲尔丁兄弟组建了骑兵巡逻队,主要打击抢劫犯罪,提高追捕效率。这些举措都为专业警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大伦敦社会失序问题日益严重,而地方治安体系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调度,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1785年拟定了一项法案,主张建立整个大伦敦的警察队伍,因受到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而流产。[23]301792年,《米德尔塞克斯治安法令》(Middlesex Justice Act)颁布,伦敦新成立了7个治安办公室,确立了治安法官的领薪制度。19世纪初,为抑制泰晤士河码头猖獗的盗窃犯罪,治安法官帕特里克·科洪组建了泰晤士河治安办公室,招募了一批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警察队伍,短短8个月,使得该区域因盗窃造成的损失减少了95%。[24]30这使伦敦政府意识到,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要比传统的教区警役和守夜人更加高效。科洪还曾主张建立由内政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的全国性警察体系,但由于此项改革建议远远超出了当时英国民众的接受程度,赞成者寥寥无几。总之,早期的改革举措大都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实施,未能打破传统的教区自治体系,也没有将各区域的治安力量整合起来。
19世纪初,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颇不稳定。英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加强法律与刑罚体系来威慑犯罪,另一方面在爆发严重混乱时还得依靠军队来平息,但每次调集军队都会激起民怨,特别是“彼得卢事件”*1819年英国军队为镇压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的民众集会而导致1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因不少军人参加过几年前与法国的滑铁卢战役,这次事件发生在彼得广场,因此被称为“彼得卢屠杀”(Peterloo massacre)。后民众对军队的抵触情绪更加强烈。这也使一些政治精英意识到英国建立一支有别于军队的治安力量的必要性。1820年,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在给利物浦勋爵(Lord of Liverpool)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政府应立即组建一支警察队伍,但在称谓上要严格与正规军队区别开来。”[25]181一些下院议员也认为,建立一支治安法官统领下的警察队伍,有利于在必要时集结行政力量和维系社会治安,这种方式将比诉诸军队更受欢迎。英国民众对新警制则充满疑虑,他们将警察制度等同于法国式的宪警或宪兵制度,认为这势必危及英国的自治传统和自由理念。有位女士甚至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不满:“警察的的确确是个可怕的东西,英国人宁可要小偷和暗杀也不要警察。”[26]420虽然改革派精英已经意识到建立新警制的必要性,但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层面都还存在一些阻力。
1822年,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接替西德默斯(Sidmouth)担任英国内政大臣,这成为伦敦警制改革的重要转折点。皮尔曾在1812—1818年间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Chief Secretary),负责镇压当地接连不断的暴乱事件。他在爱尔兰骚乱地区建立了一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警察队伍,治理效果颇为明显。跻身内政大臣以后,皮尔力图将爱尔兰的治理经验用于对大伦敦的秩序维系,但他发现,大部分英国人固执地将警察制度等同于专制和暴政。1822年,英国议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考察伦敦治安体系的现状及其改革的可行性。该委员会在调查之后作出这样的总结:“自由在英国社会已成为广为认可的特权,要在有效的警察制度和免遭政府干涉的彻底行动自由之间达成妥协实属困难;本委员会认为,以取消和削弱这种特权来改进警察制度或威慑犯罪将是一种巨大的牺牲。”[27]20这次报告使皮尔的改革设想初次受挫,他不得不继续调和各派观点以待时机。
1828年,支持警察制度的威灵顿公爵出任英国首相,为皮尔实施改革提供了机会。皮尔倡议建立一支由英国内政部直接领导的首都警察队伍,以提高在预防骚乱和犯罪方面的效率。同年,他组成了一个以改革派为主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改革使人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获得更大程度的保障。”[28]291-292为说服议员支持改革,皮尔在议会下院的辩论中指出,1811—1818年和1821—1828年两个7年间,伦敦人口增加了19%,而犯罪率上升了55%,进行治安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29]24他在改革议案的序言中进一步强调:
近来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财物犯罪急剧上升,而现在的守夜人和警役组织未能充分发挥预防和侦察罪犯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传统)治安队伍素质低劣、人员不足、权力有限以及他们之间缺乏联系与合作。建立一种新型而有效的警察制度,以取代传统的守夜人和警役已是当务之急……[24]35
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皮尔的警制改革计划有意将反对最为强烈的伦敦城暂时排除在外。这样,1829年4月,《都市警察法》(Metropolitan Police Act)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顺利获得议会通过。新式警制主要在伦敦城以外的大伦敦地区实施,伦敦城仍然保持传统的治安体系。新招募的大伦敦警察队伍约有3 200名,负责伦敦城外方圆7英里的治安维系,10年后其巡逻半径进一步扩展到15~16英里。这些警察管辖着伦敦近200万人口的辖区,辖区以下划分为若干区,每个区成立一个警察署(division),设1名警监和4名督察,每名督察手下有4名警长,每个警长领导9名警员。每个警察署区又分为若干巡逻区,有警察24小时进行巡逻。巡逻区的位置和大小尽量能够使警察在15分钟内巡查任何一处角落。新警员一律身着蓝色燕尾服,之所以是蓝色而非军服的红色,目的就在于要和军队严格区别开来,淡化警察的军事色彩,以缓解民众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在头衔上,伦敦警察也尽量与军衔区别开来,除“警佐”(sergeant)沿用“中士”以外,其他各级称谓都为警察体系所独有。新警员大都来自普通工人群体和退伍军人,凸显了其平民化色彩,与传统治安法官的绅士背景形成鲜明对比。大伦敦警察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伦敦街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非军事化、职业化、文职化的现代警察队伍。
为缓和警民矛盾,树立公共服务形象,大伦敦第一任警察厅厅长查理斯·罗恩(Charles Rowan)和理查德·梅恩(Richard Mayne)共同起草了新警察队伍必须遵守的《警察训令》(General Instructions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Force),即著名的“皮尔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警察的性质、职能、权限以及与政府、民众之间的关系,首创了“文明执法”、“最小限度使用暴力”、“政治中立”、“预防性警务”等先例准则,形成了独具英伦风格的执法模式。[26]430-431“皮尔原则”意在塑造警察为民服务的崭新形象,力求改变民众对警察的固有偏见,缓解民众对警察队伍的抵触和反感情绪,直至今天仍为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警察体系所遵循。
在防治犯罪的实践中,大伦敦警察比传统治安体系更加高效。传统的治安法官、警役、“捉贼者”都是在罪案发生后才采取行动予以调查、抓捕或审判,而伦敦警察实行24小时巡逻,随时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或事故。正如警察总长梅恩所说:“一支高效警察队伍的首要目标就是预防犯罪;其次则是在罪案审理过程中侦察和惩罚罪犯……以及保障生命与财产安全,维系公共秩序稳定。仅通过犯罪活动是否减少这一项标准,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否到位。”[30]62事实证明,大伦敦警察的确在预防和抑制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泰晤士报》刊文指出,自从伦敦街头有了警察之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和偷盗的案件明显减少,酗酒、暴乱等失序问题亦得到及时整治。1834年,英国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也肯定了新警察的作用,宣称伦敦因抢劫和盗窃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已经由建立警察制度之前的年均90万英镑降低到2万英镑。[24]41随着伦敦警察制度的完善和犯罪治理水平的提升,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公共服务形象和社会地位亦不断得到提升,到30年代末,已在伦敦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
大伦敦警制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的地方自治体系,确立了统一、规范、高效的现代治安力量。地方治安办公室被取消,曾经活跃于伦敦街头的“捉贼者”被解散,古老的教区治理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警制的确立还改变了伦敦依靠军队来平抑暴乱的历史,消除了民众对武装力量的恐惧和疑虑,使伦敦及其周边城市的治安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另一方面,大伦敦警制的确立标志着英国政府职能和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通过现代警制改革,英国政府进一步凸显了公权力的公共服务职能,国家逐渐取代地方自治机构和民间力量开始承担起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职责,过去那种维系“王之和平”的治理体系也逐渐被服务民众的城市警察所代替,大伦敦的公共治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综上,英国传统的教区自治体系在工业化时期遭遇严重挑战,薄弱的治安力量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各类犯罪、骚乱、群体性集会等失序问题。传统犯罪治理模式对民间力量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也因此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诸多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参与举报、抓捕罪犯的机制,如“呐喊捉贼”、悬赏机制等都有相关法律依据。尽管在出现严重混乱时英国政府不得不依靠军队或民兵来恢复秩序,但悠久的自治传统和自由观念使英国人对任何武装力量都深恶痛绝,这也是大伦敦乃至整个英国警制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伦敦警制的最终确立既是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客观形势使然,也是改革派精英积极推动的结果,特别是皮尔的改革策略绕开了伦敦城的阻挠,并形塑了新警察的服务形象。新警制确立伊始便非常重视警民矛盾的化解和警民协作的重要性,尤为强调警员的平民化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治传统的遗产。所以,英国的新警制与传统自治体系也并非是完全割裂的。
[1]吴必康.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L. Schwarz. London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3]Andrew Barrett, et al.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ngland: A Sourcebook[M]. London: Taylor ﹠Francis Group, 1999.
[4]Oscar Sherwi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ngla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1946,5(2):169-199.
[5]John Beattie. Crime and the Courts in Englan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6]Patrick Colquhoun. A Treatise on the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M].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11.
[7]Michelle Allen. Clearing the City: Sanitary Geographies in Victorian London[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8.
[8]Douglas Hay. War, Dearth and Thef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J]. Past and Present, 1982,95:117-160.
[9]David Ascoli. The Queen’s Peace[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10]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M].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1]Robert Shoemaker. The London Mob: Violence and Disor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M]. London: Macmillan,2004.
[12]John Stevenson.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England 1700-1832[M]. London: Longman, 1979.
[13]Leon Radzinowicz. 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Vol.3[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6.
[14]David Taylor. Crime, 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England[M]. London: Macmilan,1991.
[15]Andrew Harris. Policing the City[M].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
[16]Frank McLyn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1991.
[17]Hereward Senior. Constabulary: The Rise of Police Institutions in Britain[M]. London: Dundurn,1997.
[18]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4[M].London: John Murray,1857.
[19]Leon Radzinowicz. 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Vol.2[M]. Lonson: Stevens and Sons, 1956.
[20]John Archbold. A Summary of the Law Relative to Pleading and Evidence[M]. London: Nabu Press,2010.
[21]Ben Whitaker. The Police in Society[M]. London: Eyre Methuen,1979.
[22]House of the Commons. Debate in the Commons on the Mutiny Bill[G]∥The British Parliament. Parliamentary History(1765-1771):Vol.16.London: British Parliament,1770:1331-1335.
[23]Hereward Senior. Constabulary: The Rise of Police Institutions in Britain,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United States[M]. Toronto: Dundurm press,1997.
[24]菲利普·斯特德.英国警察[M].何家弘,刘刚,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
[25]David Philips. A New Engine of Power and Authority[G]∥V. A. C. Gatrell et al. Crime and the Law: The Social History of Crime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1980.
[26]程汉大,李培锋.英国司法制度史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7]David Taylor. The New Pol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28]Stanley H. Palmer. Police and Protest in England and Irelan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9]Clive Emsley. The English Police: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M]. Lodon: Longman, 1996.
[30]Ian McKenzie.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England and Wales[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98.
(责任编辑:王艳芬)
2015-07-15
国家社科基金“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犯罪治理体系变迁研究”(15CSS02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贫民窟治理研究”(2014SJB776);公安部项目“英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系统研究和启示”(2015LLYJBWWWBO08)
许志强,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在职博士后,主要从事英国近现代史、犯罪与社会治理研究;程 慧 ,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K561.43
A
1672-0695(2015)06-007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