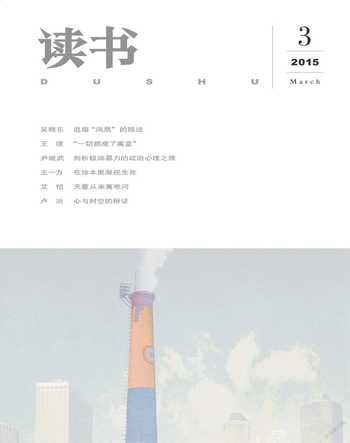文章·文体·文运
魏泉
王风的《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做到了以一种难得的干净、整饬而又明晰的文风,曲径通幽,从传统“小学”的语言文字所涉范畴着眼,由“文字”而“文章”、而“文体”、而“文运”,构建出一个庞大而又细密的文学史景观,堪称是近代文学研究的补天之作。
这本书由若干篇论文组成,其写作时间前后跨了将近二十年,不止是十年磨一剑。其中《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一文,代表了作者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通盘看法。通过对“文学”、“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等基本概念的追根溯源、条分缕析,王风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与同时所蕴含的广阔空间:
在经过“资源重组”的古代文学和具有“自足传统”的现代文学之间,有这么一个所谓近代文学,难以被“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叙述框架兼容,仅从这一点看,它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理由。但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叙述策略相距甚远,“近代文学”处于两个远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学术传统之间,既无法对二者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更不可能从这一领域的思考出发,影响并改变相邻学科的学术路向,这是近代文学研究长期无法取得根本性进展的直接原因。
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给研究者提供的广度是足够的,旧有文体的整合、新兴书面语的崛起,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乃至“文学”被作为概念和观念,无不出现在那时,而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埋没的资源,可以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依据。这些特质使得近代文学完全有可能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说得更明确点,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基础,而一旦出现独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联,将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看法。
王风所谓“独有的研究思路”,迥异于以往各种宏大叙事的研究格局,也不同于任何形式的流派研究或文本细读,而是转而追溯细致、多元、富有深度的“局部空间”,试图寻找能够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并足以质疑整部文学史的出发点。
这样一个非常独特又极具挑战性的思路,大致导源于他对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人文学观的形成与转变的研究。《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是这部论文集中最早问世的一篇。此文从辨析刘师培与章太炎关于“文言”、“质言”的学术论争入手,上溯十九世纪在汉宋、骈散之争背景下阮元的立论,中经刘师培与章太炎从“小学”入手,构建各自庞大而严密的不同文学史观,最后落实在周氏兄弟关于魏晋文章、新文学源流的论述,论述之清晰,眼光之独到,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纵观本书,可以发现作者极为注重书写语言问题。书写语言并非语言学领域工作的重心,而同时也为文学研究领域所忽视,但其实极为重要。因而他留意到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所谓“国语运动”,据王风所言有广狭两种界定:广义的国语运动可以从晚清拼音化运动算起,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国语罗马字、三十年代大众语和拉丁化甚至更晚。此以黎锦熙的 《国语运动史纲》 为代表。狭义所指,则从“国语研究会”始,至国语罗马字运动之前,由当时教育部中人士发动,并组织广泛的同盟,有一系列明确的目标,到二十年代初获得全面成功。
“国语研究会”成立之时,正是《新青年》以《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发起“文学革命”的一九一七年。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王风笔下,从最初的各行其是,到开始发生联系,到以标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为标志,二者合流。在双方的配合下,才有了后来白话对文言的全面替代:
二十年代初,国语运动的成功,为白话文争得至关重要的初步的合法地位,使它成为正式书写语言的候选人;然后由新文学不断丰富锻造,到共和国时代,终于依靠政权力量彻底取代了文言。(《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
论文不仅能发人所未发,将这个过程叙述得清晰完整,胜义纷呈,而且还颇觉跌宕起伏。艰辛的考证被融入环环相扣的描述、引征和点评,其强大的逻辑性和强烈的真实感,将一个相当艰深的学术问题论述得引人入胜。
与“国语运动”相关联,作者还上溯晚清拼音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在纷繁复杂如一团乱麻般的晚清历史语境中,王风以一种难得的冷静和细密抽丝剥茧,因难见巧,以“辨名正词”的“正名”功夫,将晚清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来龙去脉及与国语运动的关系,梳理得清晰而又确凿。正如他自己说的:“事实只有经过描述才能成为历史,而描述必须依赖一定的逻辑。”这个逻辑,由独特的研究思路和详实的史料征引所决定。虽然你很清楚这也只是建构历史的一家之言,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个“局部空间”中,他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理清楚了。这种建构能力以及不足两万字的论文背后海量的资料阅读(且不论所涉领域的深度),使得读者除了洗耳恭听之外,无论是想要对话,还是攻错,都相当地困难。
王风的论文写作,极其另类。两万字以内的长文,没有小标题,多数也不设章节,围绕问题,从头至尾,一气贯注,全以文章内在的逻辑推进,冥搜孤往,排难决疑。“文气”之强,为论文写作所罕见。这种写作形式的难度和挑战性有目共睹,王风不选择趋易避难,而是迎难而上,背后应是他强大的自信和“做第一流”的自我期许。
循此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模式,王风由拼音、国语、文字问题推展到文体研究,其《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一章,远溯近代报刊之初,从王韬、郑观应,到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到陈冷血、包天笑、章士钊,再到《新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令人信服地推证了从梁启超的“自由书”到鲁迅的“随感录”,论说性报刊文体在近现代之间的转折与演化:
近代报刊文体兴起以来,论说文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先是,传统的著作之文被移到报章上,亦即王韬、郑观应时期;至甲午战后,梁启超崛起,他的论说文汲取资源至广,将著作之文演化为报章之文,余力所及,为“自由书”,这种“短论”将“论说”个人化了,但终于并未产生影响,更没有成为现代散文的资源—此为“论”之演变。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日益多元化和分野,“短评”开始作为依附于新闻的评论兴起,逐渐发展出独立的“时评”和“闲评”两种体式—亦即“评”之系列。到“随感录”时期,鲁迅扭转了此类文体中新闻与评论的关系,确立了议论的主体性,由此在报章论说文的广泛背景下开始催生先被称为“杂感”,后被称为“杂文”的现代论说文体。(《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
对于文体演变的考察分析,不仅议论新颖,且有非常难得的分寸感和深透的洞察力。这种分寸感和洞察力在《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一文的论证中,有更加令人振聋发聩的发挥。
这篇超过三万字的长篇论文,说是作者积十年之功而成应该不夸张。慢则慢矣,但是慢工出细活儿。此文说得上是在现代文学的“显学”—“鲁迅研究”领域(也还要包括周作人研究)做出了推进。
该文从书写形式入手,对于“段落”、“标点”与“句读”在性质和功用上貌同实异的分析颇能启人心智。但即便如此,标点符号与句读的使用,究竟是如何与周氏兄弟挂上了钩,并进而对已经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有所深化呢?这就是王风的拿手好戏了。从二十世纪之初的林译、梁(启超)译及陈冷血的“冷血体”对周作人早期小说创作尝试《好花枝》的影响一路道来,通过不厌其烦的文本举证,得出了以下结论:
有关分段和标点这些书写形式的问题对现在的阅读者来说,早已习焉不察。但在晚清的汉语书写语言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过分。此类变化在文言和白话系统内部都在发生,总体而言尤以文言为甚,或者可将之称为近代文言。这当然与口语没有关系,完全是书写的问题,所以不妨将其看成“文法”的变化。可以这样认为,就“词法”和“句法”的层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文法”。而真正全体的变化在于整个篇章层面—姑且称为“章法”,出现了新的文章样式,这是由段落标点这些书写形式的引入所造成的。周氏兄弟的文本也是这一历史环境中书写大革命的产物。
在此基础上,王风将周氏兄弟以“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为诉求的《域外小说集》做了显微镜下的细读,就标点符号的引入对译和鲁迅“直译”的翻译理念,如何在这本译著中做到“移徙具足”,“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来话长,但最后的结论很明确:
鲁迅的译作,实际上是将西文的“章法”引入—亦即“对译”到汉语文本之中。句法的变化,甚至所谓 “欧化”的全面实现端赖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域外小说集》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汉语书写语言革命的标志性产物,尽管那是文言。
在周氏兄弟的早期小说翻译和文言小说的创作实践中,对于“引号”的使用及前后变化引起王风的特别关注,他有惊人的发现:
汉语古典文本,无论文言还是白话,实际上是无法从形式上区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因为没有引号这个形式因素来固定口说部分,从文法上也无法分别。无论是“曰”是“道”,其所引导,只能从语言史的角度判断其口语成分,一般的阅读更多是从经验或者同一文本内部的区别加以区分。唐宋以来文白分野之后,文言已经完全不反映口语,文言文本中直书口语是有的,但那只是偶尔的状况。如今对文言句子直接加引号,从形式上看是直接引语,但所引却是现实中甚至历史上从未可能由口头表达的语言。由《怀旧》的文本揣测,鲁迅在这篇小说开笔时似乎并未预料到后面会写法大变,只是进入有关“长毛”的情节时发现不得不如此。结果新的表达需求必须新的书写形式的支持,而新的书写形式的实现又带来了语体上的巨大矛盾,所显示的恰是文言在新形式中无法生存的结果,简直预告了文言的必须死灭。
在这已经够让人目瞪口呆的结论面前,王风犹不自足,进一步考究“逗号和句号”的重要性:
句号和逗号是最常用的两种标点符号,但其实最晚被引入汉语书写中,就因为汉语文本原就有施以句读的历史。句读和句号逗号都有断句的功能,虽然断句方式并不相同,但表面上看似乎差别不大,不过句号逗号的配合使用有时可以反映某种文法关系,为句读所不备……
句号和逗号的引入,终于全面实现了书写形式的移入,使《域外小说集》所说的“移徙具足”,或者说令国人颇不习惯的“欧化”的汉语书写得以全面实现:
在周氏兄弟手里,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在文言时期就已经进行,因而进入白话时期,这种改造被照搬过来,或者可以说,改造过了的文言被“转写”成白话。与其他同时代人不同,比如胡适,很大程度上延续晚清白话报的实践,那来自于“俗话”;比如刘半农,此前的小说创作其资源也可上溯古典白话。而周氏兄弟,则是来自于自身的文言实践,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从口语,也不从古典小说获取白话资源。他们的白话与文言一样,并无言语和传统的凭依,挑战的是书写的可能性,因而完全是“陌生”的。
作为新文学创作的开端,鲁迅的《狂人日记》奇特的书写语言相信给每个读者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何以如此,王风此文是我所见到的最别出心裁而又有说服力的解答。
尽管如此,关于周氏兄弟的研究在我看来,还不算是此书最精彩的部分。从刘师培、章太炎,到林纾、严复,到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凡所论及,都说得上精彩可观。但我觉得王风做得最好的,还是王国维。
王风曾在《追忆王国维》一书的“后记”(收入本书的《新时代的旧人物》一章),围绕王国维之死是“殉清”还是“殉文化”展开论述,言必有征,条理秩然,视野开阔而又析事精微。尤其难得的是,在冷静雅洁的文字背后,有种不可掩抑的如诗意般的情感,十五年前读来荡气回肠;此番重读,仍多感喟,觉其分寸之精准、体贴之入微及行文之隽雅,依然是难以企及的学者之文。而完成此文的十年之后,王风却能再进一步,拿出王国维研究的新作《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对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细密考察,仍以“辨名正词”的“小学”功夫入手,追溯王国维学术入手处与东洋之教育的关系,从醉心于叔本华、康德哲学,关注教育,接受西洋之分科逻辑,到移情于文学,标举“古雅”,倡言“境界说”,以至对宋元戏曲的大规模研究,及后期的转向国学研究,王风都有从语词、文体和语体方面的精彩纷呈的论证和发覆,并能进一步断言:
所以通观其一生治学,哲学则以西学重理中国思想,文学则在西学的观念下以中国本有的范畴进行研究,史学则全由中国自身学术传统而发扬光大之。
王国维数度学术转向也正说明他与中国传统学者的追求有所不同,传统上中国学者于所谓无学不窥外,自我期许的是诸学会通,循环相证。远之不论,即以同时之大学者章太炎而言,《国故论衡》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意在结构完整的自我学术构架。反观王国维,数度转向,而每每掉头不顾,可见早期由教育入手所形成的“学科”或“科学”的观念还是终身留下了烙印。
站在这样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高度去评价王国维、章太炎的学术变迁与知识谱系,显然仅有勇气是不够的,学养、才华、性情、文采、功力,甚至时间,都是缺一不可。王风的王国维研究,以一种难得的分寸感摹写出了王国维学术人生真实而又高明的境界。他自己于其中浸淫体味多年,一定也是受益匪浅的吧。
(《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王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