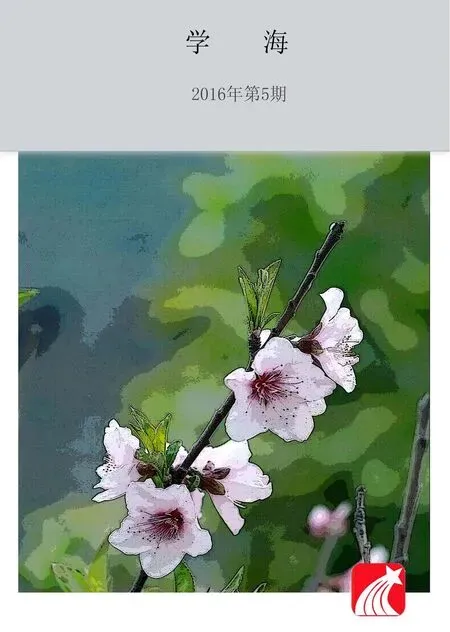迈蒙尼德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
董修元
迈蒙尼德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
董修元
内容提要中世纪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在其两部主要的哲学-神学著作《迷途指津》和《律法再述》中,就宇宙生成论和先知论问题作出了两种相互歧异的观点表述。就前者论,《律法再述》持宇宙永恒观,而《迷途指津》则系统批判宇宙永恒论而支持从虚无创世说;就后者看,《律法再述》暗示先知是人类理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的自然结果,《迷途指津》则着重指出神握有阻止具备资质之人成为先知的否决权。实际上,两书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表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分别代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一神论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迈蒙尼德为何在两部著作中持不同观点,他究竟倾向于何种立场,则成为中世纪哲学研究界长期争论的焦点。
宇宙生成论先知论迈蒙尼德辩证论证教化意识
《迷途指津》与《律法再述》(Mishneh Torah)是中世纪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前者成书较早(约1178年),后者(Dalālat al-Hā’irīn)则是其晚期著作,约完成于1190年。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都探讨了宇宙生成论(cosmogony)和先知论(prophetology)问题,并暗示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关联。但两部著作对同一论题的观点表述却有较明显的差异。
两书在宇宙生成论与先知论上的表述歧异
1.宇宙生成论的不同表述
迈蒙尼德关于宇宙生成论的论述散见于《迷途指津》各处。总括来说,他陈述了三种意见,分别是一神教所主张的神在虚无之后创世说,柏拉图所代表的神从永恒质料创世说,和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天体及宇宙秩序永恒论(II 13,260-263);①并给出了三种论证,分别是凯拉姆(Kalām,或译伊斯兰经院哲学或辩证神学)的建基于原子-偶因论的宇宙有始论证(I 74,201-9),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从因果必然性出发的宇宙永恒论证(II 14-21,264-92),和迈蒙尼德本人的论证。值得一提的是,迈蒙尼德没有给出支持或反驳柏拉图式创世论意见的论证,他认为这种意见与第三种意见无实质差别、其实是宇宙永恒论的一种变相(II 13,264)。
迈蒙尼德本人的立场是在陈述和批评前两种论证的同时表述出来的。他一方面根据可以被经验和理性证实的事物的可见本性及世界的稳定秩序来驳斥凯拉姆否定因果联系的偶因论(I 73, 181-201;I 74, 201-9),另一方面又从天体运动及星体分布的偶然性与不规则情况(II 19, 285-7;II 24, 297-300)、流溢生成论的推演困难(II 22,292-3)以及从宇宙现有状态推论创世之初情况的逻辑效力局限(II 17,272-5)等几个方面质疑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宇宙按必然法则从神派生、从而与神永恒共在的论证。他最终提出自己的观点:(1)宇宙具有可察知的合目的性秩序(II 19,286;III 19,435),但这个秩序本身是偶然的且可以有例外(II 29,318),从此推出存在一个有意志有目的的安排者;(2)意志选择的对象必是可能存在者而非必然存在者,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必然与永恒相互蕴含的原理,世界作为神选择的对象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永恒的。
与《迷途指津》中的陈述恰成对照,他在《律法再述》中关于宇宙论的论述集中于第一篇《论知识》的第一单元《律法之根基》的前四章,而且只陈述了一种确定的观点。关于神之存在的证明,迈蒙尼德作出以下陈述:
“这个存在者是世界之神、全地之主。他以无限的能力驾驭着天体。这个能力是永无止息的,因为天体持续不断的旋转而它必然需要一个动因来促使它旋转。正是他(赞颂归于他)——不用手也不借助任何形质——促使它旋转。”②
这显然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第一推动者论证,相当于《迷途指津》(II 1,226-30)中详述的哲学家的第一种论证,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天体永恒论,因为在此论证中只有从天体永恒旋转才能推出推动者的能力无限,从能力无限才能推出他是单一、无形体的神。迈蒙尼德在此处对天体永恒论(亚里士多德主义宇宙永恒论的核心)前提的肯定,与他在《迷途指津》中对宇宙永恒论的质疑是直接冲突的。对于这个关键的出发点歧异,他有明确的认识和说明(《迷途指津》I 71,176):之所以在律法著作(主要指《律法再述》)中从宇宙永恒前提出发论证神之存在,不是由于他相信世界永恒论,而是因为他试图提供一个无法动摇的两面证明(dilemma argument,即从相反前提出发皆能推出一结论,从而证成此结论)。但这个解释又衍生出新的问题:他为什么在《律法再述》中仅仅给出(且是以确定无疑的方式给出)两面证明的一面(从世界永恒前提出发的一面)而对另一面只字不提,而在此书流行十余年后才在《迷途指津》中给出完整的论证。
2.先知论的不同表述
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II 32(332-33)中列举了关于先知论的三种意见:(1)庸众的意见认为神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德行良好的人给他预言的能力,无论其老少智愚;(2)哲学家的意见认为预言是人处于完善状态下的一种能力,只要一个人通过学习和训练达到理智、德行和想象力三方面的完善,他就自然具有了预言的能力;(3)圣经的意见认为一个人达到哲学家所说的完善境界(迈蒙尼德在后文又追加了身体健全、专注于神圣条件、勇气和直觉能力等条件,II 36,342;II 38,346)就具有了成为先知的自然趋向,但这并不保证他成为先知,神仍握有否决权,就是说神的意志可以阻止具备条件者成为先知。他明确支持第三种也就是他藉圣经之名陈述的意见,这背后暗含着他对先知预言之本质的理解,即神主动给出的理智流溢经由人的理性官能达到想象官能而形成的产物(II 36,341)。
《律法再述》中的先知论陈述集中于《律法之根基》的第七至十章,关于先知的条件,他是这样表述的:
“先知预言的能力,仅授予那些十分贤明的智者,他们具有坚定的品质,总能凭自己的意志征服自己的自然倾向而不被其征服。同时他们必须具备广大而精微的智力。一个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并且身体健全,就有可能成为先知。……当他完成了这一切准备,神圣的灵将立即降临在他的身上。”③
这里所列举的德性-条件与《迷途指津》基本相同,但差别在于,此处指出具备条件之后此人即刻承受流溢成为先知,并没有提及《迷途指津》所强调的神的否定性干预。④
对于两书宇宙生成论-先知论(cosmogony-prophetology)歧异的分析
1.他宇宙生成论与先知论陈述的内在关联
迈蒙尼德在陈述先知论三种意见之前做过一个类比性的暗示:“我们已表明,依据其对宇宙是否是永恒的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主张,可以将那些认为上帝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人划分为三类。同样,关于预言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迷途指津》II 32,332)。
20世纪70至80年代,凯普勒(Lawrence Kaplan)、达维逊(Herbert Davidson)、哈维(Warren Zev Harvey)等人就宇宙生成论-先知论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其中,开普兰持所谓传统解释,主张C1(宇宙生成论第一种意见,即一神论神学的从虚无创世论)对应P3(先知论第三种意见)、C2(宇宙生成论第二种意见,柏拉图主义的从永恒质料创世论)对应P1(先知论第一种意见)、C3(宇宙生成论第三种意见,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世界永恒论)对应P2(先知论第二种意见);戴维森主张C1对应P1、C2对应P3、C3对于P2;哈维主张C1对应P1、C2对应P2、C3对应P3。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迈蒙尼德所陈述的宇宙生成论和先知论观点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但至今对三种宇宙论和三种先知论如何具体对应的问题仍莫衷一是。⑤
迈蒙尼德指出C1是所有信奉摩西律法的人的意见,P3是“我们的律法”的意见,二者之间的对应性十分明显。而且从义理上讲,他所理解的圣经的宇宙生成论观点(即目的-设计论)在保存事物自然本性的同时承认神奇迹性干预中断自然进程的可能性,这与先知论第三种意见基本接受哲学家对先知预言的自然主义解释但加以一点限制(神可以阻止具备资格者成为先知)的思路完全一致。C3与P2观点也很显然具有亲缘关系,从哲学家的自然主义宇宙论出发,一切存在者皆有其恒定的本性,神作为宇宙的最高形式源源不断且无偏私的给出流溢,人如果发挥其理智与想象力的本性潜能就能够接受和读解普遍常在的神性流溢而成为先知。
传统解释之中,唯一看似勉强的对应是第二种“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与第一种“庸众的先知论”之间的配比。但如果我们细加辨析迈蒙尼德的具体表述,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线索:
“这个人是智是愚、是长是幼都没关系,但他们还是规定他要有某种德性(khairiya mā)及良好的品德。这些人还没愚顽到相信上帝能使恶人成为先知的程度,按他们的见解,除非上帝首先使这人变好[否则他不能成为先知]。”(《迷途指津》,II 32,332;DH, 253)
据此,迈蒙尼德所提及的第一种先知论并非对先知资格毫无限制,一个人要成为先知必须具备起码的德性,神不能让恶人成为先知。而这与迈蒙尼德所描述的柏拉图所主张的神从先在质料中按意志创造世界的意见具有某种平行性:在此语境中,可以把先知候选人所具备的起码德性资质理解为质料,自由赐予预言能力的过程则可被看作是将某种完善形式赋予质料的创造行为。而且,此处所说的“某种德性”和II 13(262;DH, 197)陈述柏拉图主义见解时所说的“某种质料”(māda mā)也有一种构词上的对应性。此外,II 13所陈述的柏拉图创世观点是神从同一种质料中任意创造天地万物,而迈蒙尼德所认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宇宙论则坚持天体与月下事物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质料构成,⑥前者的观点中神的创造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或随意性,这也符合迈蒙尼德所描述的第一种先知论的基本意向。
2.宇宙生成论-先知论的歧异表述
我们还应当考察两书所表述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在论证形式上的差别,《律法再述》在宇宙-先知论上的论述基本上是采取一种从自明(或看似自明)前提出发进行演绎的方法,一切判断和推论都呈现一种明晰确定、毫无疑义的面貌。而《迷途指津》则首先陈述针对相关问题的诸种分歧观点,然后从经验事实及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去推论,还原和检验诸种意见的前提和论证,然后折中去取、选择或建构最具解释力、最少疑难的观点;在《迷途指津》中,《律法再述》的论证所应用的前提被剥去了看似自明的面纱,建基其上的论证仅仅成为诸种可能的论证之一种。两书在论证形式上的差别关涉到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所区分的证明论证和辩证论证的差别。⑦前者指从自明前提或已证命题出发作出推理的论证方法;后者是指从可接受的意见出发作出推理的论证方法。在证明论证的条件下,由于前提必真,只要推理过程不出失误即可保证结论必真,所以不需要考虑别种意见;而在辩证论证的条件下,由于作为出发点的可接受意见只是或然为真,所以必须随时参考、借鉴从其他立场出发的不同论证思路。
依上述论证形式的区分和定义,来审视迈蒙尼德的两部著作的论证方法,会很自然地趋向一种意见、这也正是作者欲使读者形成的一种意见:他在《律法再述》中论述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时运用了证明论证,而在《迷途指津》中处理同一问题时用的是辩证论证。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判断其实是不兼容的:如果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真的能够得到一种证明论证的支持,那对这个论题所进行的全部辩证论证就都是徒劳无益的;反之,如果上述观点的前提被检验为并非自明或必真,那就不仅说明进行辩证论证是必要的,还说明先前那个所谓的证明论证不是一个真正的证明论证,⑧只是借取了证明的外表。
对两书宇宙生成论-先知论歧异表述之原因的探究
面对作者中对宇宙生成论-先知论的不同表述,一种最方便直接的解释是其思想发生了变化。西斯金(Kenneth Seeskin)和兰吉曼(Tzvi Langermann)认为,从早期律法作品到后期的《迷途指津》,迈蒙尼德调整了他的相关立场:出于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反思以及维护犹太信仰根基的考虑,他修正了早期的自然主义哲学观点。⑨但是,《迷途指津》中多处引用《律法再述》,对后者的态度相当肯定,且从《律法再述》成书到《迷途指津》的写作,其间超过十年,如果迈蒙尼德自身的思想发生变化,那完全有机会且有必要改写《律法再述》。事实上,他后半生在不断改写早期著作《密释纳评注》。而《律法再述》的定位乃是准备向整个犹太世界传播并垂范后世的宪法式典章,他更是决不会放任其中的错误流传。但他并未对其作出修改,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他思想发生变化造成前后矛盾的可能。


上述区分和针对受众的教化意识,为我们理解这两部著作中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歧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律法再述》导言明确指出这是一部面向所有资质读者的书,但事实上普通大众根本无力亦无暇来读这样一部大作,它最终面对的还是大众中具有求知能力和欲望的拉比学徒。对于这样的受众,迈蒙尼德的目的是要诉诸和激发他们的自然理性,而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中的第一推动者论证和涉及先知论的德性完善理论建基于现有存在者的可见本性(II 17,274),是最适合人的自然理性、最易于被自然理性所接受的(II 15,268)。从迈蒙尼德一神论形而上学的终极立场来看,哲学家们的宇宙论和先知论(更确切的说是自然哲学和德性理论)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有局限和适用范围的真理(II 22,294;II 24,300-1),他们的过失只是忽视了其局限和条件而将其无限放大了。至于采用证明论证的外表,也是为了树立研习者对人类理性的信心——迈蒙尼德不准备在需要培育自然理性的启蒙阶段过早引入对自然理性的质疑或对人类理性能力局限的揭示,以免淆乱研习者的头脑、动摇其求知志向(II 24,299)。这就是《迷途指津》导语所谓的“有必要掩盖一部分、揭示一部分”(19)。
当研习者们通过习行律法而达到德性坚定、经由修习哲学(从逻辑、数学到自然哲学)而达到理性成熟(I 34,73-4;III 52,580-1)的阶段时,迈蒙尼德则将他们带入《迷途指津》所揭示的神学-形而上学的领域(III 51,570-571)。他向他们表明第一推动者论证的天体永恒前提以及更基本的因果必然性法则都不是自明的,先知预言不仅仅是人类德性自然完善的结果,而且是还有待于某种人力不及的天命。这里不再有先前所修习的律法的严密性或逻辑和数学学科的自明性、确定性(I 31,66),但却有了接触关于更崇高的上界对象(天体、分离理智乃至神)的知识的可能。对自然理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能力的废弃,迈蒙尼德所排除的只是把握上界对象的本性并据此作出证明论证的可能,而并未断绝对形而上学对象的形迹-作用进行经验观察、审查各种可接受意见而开展辩证探讨的道路。事实上,他主张在对人类理性的局限有自觉意识的前提下积极而审慎地运用理性能力作神学探索(I 32,69;II 24,301;II 25,303)。
①以下《迷途指津》引文及章节页码均出自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迷途指津》(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译文参照希伯来-阿拉伯原文(Dalālat al-Hā’irīn, ed. S. Munk and I. Joel, Jerusalem: Junovitch, 1931, 以下简称DH)有改动处以斜体标出。
②Maimonides, Mishneh Torah: The Book of Knowledge, ed. and trans. Moses Hyamson, Jerusalem: Feldheim Publishers, 1974, “Yesodei ha-Torah”, 1:5.
③Mishneh Torah, “Yesodei ha-Torah”, 7:1.
④在《律法之根基》下文7:5关于先知弟子、7:6关于摩西与其他先知差别、7:7以下直至第10章关于先知之真伪鉴别的陈述中涉及多种具备先知资质却未现实承受神之流溢的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迈蒙尼德在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却没有把神之意志干预这个限制条件加入到7:1对先知条件的列举中。这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这些人并未真正达到承受神圣流溢所要求的完善程度;其二是对神之干预这个条件的认识超出了作者在此处所欲宣示的知识原理的范围,但为了避免无视这个条件带来的流弊,他把它分散置于该知识原理的适用说明之中。
⑤见Lawrence Kaplan, “Maimonides on the Miraculous Element in Prophesy”,HarvardTheologicalReview, 70 (1977), pp. 233-56; Warren Zev Harvey, “A Third Approach to Maimonides' Cosmogony-Prophetology Puzzle”,HarvardTheologicalReview, Vol. 74, No. 3 (Jul., 1981),pp. 287-301; Davidson, “Maimonides’ Secret Position on Creation”, in Studies in Medieval Jewis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2-7. 关于此问题的较近探讨见Thierry J. Alcoloumbre的 “Prophecy Revisted: A New Approach to Maimonides' Cosmogony-Prophetology Puzzle”,ReviewofRabbinicJudaism, 11.2 (2008), pp. 243-76,他的所谓新解决思路实质上是戴维森观点的翻版,他所提出的真正新异见解(迈蒙尼德的宇宙生成论和先知论意见叙述遵循相反的认识论顺序)则完全架空了两种理论间的对应关系;以及Roslyn Weiss, “Natural Order or Divine Will: Maimonides on Cosmogony and Prophecy”,JournalofJewishThoughtandPhilosophy,15 (2007),pp.1-26,她主张此处宇宙生成论和先知论的三种立场都可以被归结为两种意见即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对立,这种解释同样与迈蒙尼德本人明确建立的“三三”对应相冲突。
⑥《迷途指津》,II 26 ,305;迈蒙尼德在评述拉比以利泽介于柏拉图主义质料永恒论和萨比教式流溢论(有形事物从神之属性流溢而出)之间的暧昧观点时强调天地质料的差别。关于迈蒙尼德对萨比教(Sabianism)神学的评述和态度,见董修元《迈蒙尼德论萨比教》,《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⑦亚里士多德:《论题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6年,第353、364-365页。关于迈蒙尼德对这种论证形式分类的理解,见Maimonides’ Treatise on Logic, ed. and trans. Israel Efros, New York: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Studies,1938,p.48;据Israel Efros考证,这部著作的基本来源是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法拉比(al-Farabi)的Perakim和Iggeret,,见此书编译者导言,p.19.
⑧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II 24中(301)指出,通过天体运行推出神之存在的证明是人类理智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第一推动者证明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证明,它的前提(宇宙永恒)不是必真的。
⑨Kenneth Seeskin, “Metaphysics and its Transcendenc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imoni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3; Tzvi Langermann, “Maimonides and Miracles”,JewishHistory, 18 (2004), pp.155-159.
⑩Leo Strauss, “The 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in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p.38-94;“How to Begin to Study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rans. Shlomo Pin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xi-lvi.



〔责任编辑:姜守明〕
董修元,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博士后,dongxiuyuan@gmail.com。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