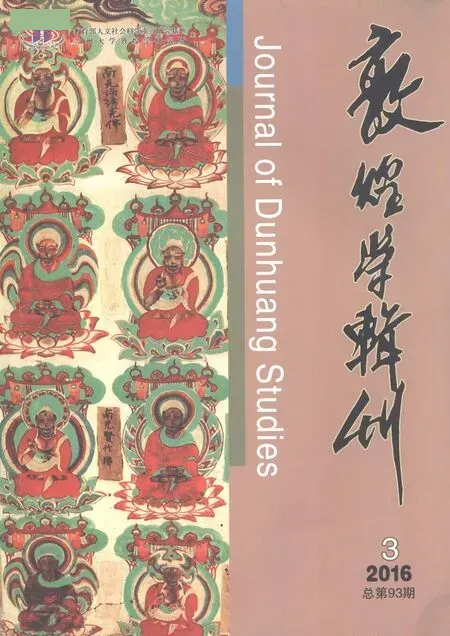西夏佛教灵验记探微
——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观世音经》为例
赵 阳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佛教自其诞生之初,便与艺术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由文学发轫,盛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各个方面。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与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尤其被僧伽偏爱,逐渐成为了佛教宣传的利器。自佛学东进后,在广大译师、教徒乃至骚人墨客的努力下,各个宗派渐次发展并与中国社会相融合,关于释教的文学作品也因此繁盛起来,如诗、赋、词、文等等。而在多种体裁的作品中,灵应传记以其通俗易懂的特质以及夸张荒诞的艺术风格,颇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并由此流传广远。
西夏作为以佛教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庶黎仆役,均对佛教抱有一份虔诚。正因如此,在西夏故地黑水镇燕军司旧址出土的珍贵文献中,佛教文献占据了很大比例。其中就有一些佛教灵应传记类作品,如TK61《华严感通灵应传记》、TK174.2《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ф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M1·1460[F280:W101]《金刚索菩萨》等等,这些作品中最有特点的便是TK118《高王观世音经》。
对于西夏佛教灵验记,前贤有过不少论述。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小荣先生《〈高王观世音经〉考析》一文,该文以敦煌本《高王观世音经》(P.3920)为底本,以西夏本、房山石经本及《大正藏》本为参校本对《高王观世音经》进行了校录,并分析了该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撰写依据。然该文着力点在经文堪比方面,虽对序文中的灵验记有所介绍和分析,但尚有一些值得补充之处。[注]李小荣《〈高王观世音经〉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4-108页。此外,崔红芬、樊丽沙、方广锠、张九玲、郑阿财等学者亦曾对西夏观世音信仰及相关灵验记的发展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注]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樊丽沙《从出土文献看西夏的观音信仰》,《西夏研究》2013年第3期,第49-54页。方广锠《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藏外佛教文献》第7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372-415页。张九玲《〈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63-73页。郑阿财《〈佛顶心大陀罗尼经〉在汉字文化圈的传布》,《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3期,第1-19页。但也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对此类灵验记有所涉及,并未有更深入的讨论。本文不惴浅陋,拟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观世音经》序文中的灵验记为例,同时结合史料记载,对西夏佛教中灵验记的发展与特点略陈一二。囿于学力所限,若有不当之处,望请方家指正。
一、佛教灵验记在西夏的流传

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年代基本为宋辽金夏时期,偶有五代。其卷貌特征与敦煌文书相类,且佛教类文献占多数,这对研究宋夏时期上层贵族和下层庶民的佛教信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文献中也有灵应传记一类的作品,或置于经末,或冠于经首,行文长短不一,却颇具特色。
如ф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乃宋刻本伪经。在经文后施印题记中有一则灵验记,记载元丰二年(1079)太常少卿薛公仲孺已死三年却不得往生,求陕西都运学士皮公之女寻《竺兰陀心文经》,终于民间访得古本,后设坛请僧诵之,薛公仲孺遂得生天,后三秦士民竞相传颂此经。
还有TK174.2《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卷下》,本为残卷,记载有两则灵验记,其中第一则完整,第二则仅余起首部分。前者记载有一妇女因常持诵此陀罗尼经,前世冤家三次投胎,前来索命却不得,后观音出现为二人化解冤仇。此后妇人请经千卷,活至九十七岁,托生为男子。后者记载一人赴怀州做县令,遂向泗洲普光寺借钱作盘缠,后缺。关于这两则灵验记,后文另有说明,此不再赘述。
又如M1·1460[F280:W101]《金刚索菩萨》,分上下两栏,上栏为金刚索菩萨像,下栏右下侧又有绣像,画中心横隔院门及院墙,院内为一人读经图,院外二僧执烛,导引一人前行。绣像上、左侧刻文讲解:隋人文荣身死,入阎罗殿,阎罗问其生前做有哪些善恶之事,文荣答常持《金刚经》。阎罗听闻,遂放其归。此时有二僧人前来引路,带文荣重返阳间。
而最具特点且比较完整的西夏佛教灵验记,莫过于《高王观世音经》序文中的记载。西夏刻本《高王观世音经》,共计有TK117、TK118、TK183三件。其中唯TK117冠佛画,其内容为观世音菩萨于画面右侧以女身像闲坐,右臂侧方置净瓶,内有柳枝。左下方有男女居士二人,身着西夏服饰,男手执香炉,脚下供奉有奇珍异宝,女双手合十。画面左上有跪地临刑者,双手合十诵经,其后有执法者,表情疑惑,且手持断刀,侧有断刃三截。画面上方云间有飞天像,手持莲花台。TK118纸质较厚,无佛画,首为序文,与TK117大致相同,后接经文与咒偈,有首尾题。TK183下部残损严重,原序仅存末行,有首题,尾部残缺。在《大正藏》第85卷疑似部中载有《佛说高王观世音经》,其经文与黑城本并无二致,然无前序,因此黑城本经文前序应为后人所增。而TK117与TK118序文相较,后者又更为详尽,因之迻录如下,以观其全貌:
高王观世音经
昔高欢国王在相州为郡。有一人姓孙名敬德,为主宝藏官。犯法囚禁在狱中,知需就死,持诵《观世音普门品经》,日夜不辍。忽于睡中梦见一僧言曰:“汝持此经不能免死,我劝汝持取《高王观世音经》,一千遍当离刑戮。”敬德曰:“今在狱中,何时得见高王经本?”僧曰:“口授与汝。”睡觉便抄,更无遗失,志心诵持,得九百遍,文案已成。事须呈押,王遂令付都市斩之。敬德怕惧,问使人曰:“都市近远?”使人曰:“何故问我?”敬德曰:“昨夜梦中见有一僧,令教受持《高王观世音经》一千遍,当得免死。今欠一百遍,求使人慢行。”随路急念,并前所持经数满一千遍。监使乃高宣王敕,遂令斩之。敬德身都不损,其刀却为三段,将刀呈王,王唤敬德问曰:“是汝有何幻术,令得如此?”敬德曰:“实无幻术。狱中怕死,梦见一僧,令教持《高王观世音经》一千遍,获福如是。”王谓敬德曰:“汝胜于我,与圣何异?”王便唤法官,处分狱中更有合死之人,将此经各令诵持一千遍,然即斩之。是人悉得如此,其刀尽成三段,身都不损。高王敕下,其国人民悉令持诵此经。家无横事罗纲,普寿百岁,水陆怨债讬化梵天,更无轮报矣。
上文可以看出,黑城本《高王观世音经》序文是一篇典型的关于佛典信仰的灵验记。其文人物形象刻画细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不仅道出了孙敬德畏死求生的本能欲望,更是描绘出高王最初不信神邪的固执以及最后服于观音神迹、推广佛典的坚决。
上举几则灵验记都是以转生、免灾等百姓的日常期望为主题,用平直易懂的语言进行描述,借以宣扬奉佛供典的神奇效果。在西夏这种少数民族政权地界,文化普及程度并不高,因此义理深奥、晦涩难懂的佛教想要有所发展,就需要借助佛教灵验记这种媒介,暂不论其可信度如何,至少它们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是速成且牢固的。当然,这类灵应故事并非创制于一朝一夕,它们也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发展的,或由简入繁,或去繁就简,有所传承,却并无定式。且看观世音信仰在西夏乃至中国的流行度便可知,佛教灵验记的宣传功效并非虚式。下文就以《高王观世音经》为例,简要探讨佛教灵验记在西夏的发展。
二、《高王观世音经》序文灵验记之源流
通过考证观世音信仰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原百姓对观世音的神通早有认知。自西晋竺法护翻译《正法华经》后,观世音信仰便随着其卷十《光(观)世音普门品》得到宣扬。东晋天竺居士难提译有《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其言曰:“诵持此咒者,常为诸佛诸大菩萨之所护持,免离怖畏刀杖毒害,及与疾病令得无患。”[注]CBETA.T20,No.1043,P.35,a17-18.CBETA:《大正藏》的数据引用是出自“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简称CBETA)的电子佛典系列光盘(2014)。引用《大正藏》(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出处是依册数、经号、页数、栏数、行数之顺序纪录,例如:CBETA.T20,No.1043,P.35,a17-18,表明引自《大正藏》第20册,第1043号经,第35页,上栏第17-18行。下同。北周时优婆国人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其文曰:“持此咒者现身即得十种果报。何等为十?一者身常无病;二者恒为十方诸佛忆念……七者一切刀杖不能为害……”[注]CBETA.T20,No.1070,P.149,b14-19.由此可见,这种念诵观世音相关经文可以现得果报的说法自东晋时便已出现,持诵其经便可“刀枪不入”的概念也随着观世音信仰的传播得以被广大信徒所了解。但仅凭一句“刀杖不能为害”尚无法令一般民众信服,为了招徕更多信徒,使广大民众相信观世音信仰有这种“神通之力”,便有了释徒们进一步的解释与渲染。
正史中最早提及《高王观世音经》的是北齐魏收所撰《魏书》,该书卷84《卢景裕传》载:
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注]《魏书》卷84《卢景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60页。
《魏书》所载之事,已有罪人将赴斩、梦中沙门授经、刀折刑场而后经文广行的要素,其神迹感应之事已初具雏形,但叙述仅是点到为止,故事情节较为简略。
在隋僧智顗叙说、门人灌顶记录的《观音义疏》有载:
应验传云。晋太元中彭城有一人被枉为贼,本供养金像带在髻中。后伏法刀下但闻金声,刀三斫颈终无异,解看像有三痕,由是得放。又蜀有一人檀函盛像安髻中,值姚苌寇蜀,此人与苌相遇,苌以手斫之,闻顶有声,退后看像果见有痕。[注]CBETA.T34,No.1728,P.926,b13-19.
从《观音义疏》中的记载可以看出,文中之人虽是因供养观音像而致“刀枪不入”,但也是因机缘巧合,并无神通可言,相比前文刀折三段的叙述更加贴近现实。但也由此可以看出,此类折刀主题的故事已经开始出现在观音信仰的经论中,且成为一种颇具特点的桥段。

荥阳高苟年已五十,为杀人被收锁项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诵观世音。苟云,我罪至重甘心受死,何由可免。同禁劝之,因始发心,誓当舍恶行善,专念观音不简造次,若得免脱,愿起五层佛图,舍身作奴供养众僧。旬月用心钳锁自解。监司惊怪语高苟云,佛神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之日举刀未下,刀折刃断奏得原免。[注]CBETA.T52,No.2110,P.539,a13-16.
这时关于折刀主题的灵验记已趋于成熟,其文描写也更加细致。前文所举孙敬德临刑刀折之事在唐时颇多,但于唐之前却很少见到且主人公并未定型,这至少可以说明,从叙事手法上讲,这些折刀主题的故事受方内小说的影响逐渐细致化,其目的便是令更多人去相信信奉佛教可以带来免死的福报。由此也可以看出唐时《高王观世音经》已开始流行,且于《开元释教录》中已出现《高王观世音经》或云“折刀经”的说法,可见其经由来也有了一种固定、确切的说法以服众人。经过不断发展,后人对此亦多有增补,于是扩展为另一版本并逐渐定型。如唐道宣所撰《续高僧传》有载:
又高齐定州观音瑞像。及高王经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孙敬德,于防所造观音像。及年满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所引,禁在京狱,不胜拷掠,遂妄承罪,并处极刑,明旦将决。心既切至,泪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当是过去曾枉他来,愿偿债毕了。又愿一切众生所有祸横,弟子代受。”言已少时,依稀如睡。梦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觉已,缘梦中经,了无谬误,比至平明已满百遍。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折为三段,三换其刀,皮肉不损。怪以奏闻承相高欢。表请免刑,仍敕传写,被之于世。今所谓高王观世音是也。德既放还,观在防时所造像项,有三刀迹。[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9,《中华大藏经》第6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46页。
又唐道世撰《法苑珠林》载:
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孙敬德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妄承其死,将加斩决,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经,千遍得脱。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刑满千,刀斫自折,以为三段,皮肉不伤。三换其刀,终折如故。视像项上有刀三迹。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勅写其经,广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自晋宋梁陈秦赵国,国分十六,时经四百。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获得救者,不可胜纪。具诸传录。故不备载。[注][唐]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65页。
另有诸如《大唐内典录》卷十、《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北山录》卷七、《贞元新订释教目录》卷二十八以及《佛祖统记》卷三十八、《释氏稽古略》卷二等典籍皆载有关于《高王观世音经》得名之由,除表述略有差异外,主人公俱为定州人士孙敬德,其事也与上文基本一致。这说明自唐以降,该灵验记已基本定型,不仅有了固定的主人公,故事情节亦相对完整,只是历代略有增删。
黑城本《高王观世音经》的序文较之唐五代时期的记述,又有细节上的增补和情节上的改编,但对后世流传的影响却并不够有力,该故事在元明时的流传仍与道宣时雷同甚至一致。只是在《卍续藏经》第35册《高王观音经注释》(清代悟静注)中记载有“高王经原起”的故事,其与黑城本大致相同。另于君方教授曾提到:“在民国78年由板桥明善天道堂印赠的《高王观世音真经》的序中,有如下的记载:‘昔五代时,有高欢国王为相州郡主,好杀。适宝藏官孙敬德误犯重法,囚禁就死。专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日夜不歇,忽梦见一僧曰:汝持此经不能免死,我勤汝持诵《观世音经》一千遍,为脱刑名。敬德曰:今在禁中,安得经典?僧曰:吾口授汝,睡觉敬书便无忘失……’”[注]于君方《“伪经”与观音信仰》,《中华佛学学报》第8期,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1995年,第136页。这两则记载虽与黑城本所记高度相似,然俱为后世所传。可见,黑城本的故事可能也曾流传至后世,但就其影响来说,显然不如唐宋正统典籍的记载那样流传广远。
三、《高王观世音经》序文灵验记与别本之异同
关于孙敬德之事的记述,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提到源自李德林之《齐书》,惜此书今已散佚。如上文所述,自唐时各类佛教典籍中多载有孙敬德之事。考其诸文,大都记载元魏之时孙敬德为定州募士,返家时被枉获罪将斩,因为诵念观世音经临刑刀折,时丞相高欢请表免死,由此《高王观世音经》得以定名并广布流传。诸文都有两位具名人物,即孙敬德与高欢。孙敬德,各类史书无传,但凡出现,必为此事,且其身份设定为募士,可以想见其人只是托名而已,实际代表的则是社会底层民众。高欢则不同,作为北齐奠基之人,他于北魏时便权倾朝野,以大丞相之职掌控皇室。中兴二年(532),高欢灭尔朱氏,立平阳王元修为帝,并嫁其长女给元修,自己成为国丈。永熙三年(534),高欢与元修决裂,后者投奔宇文泰,高欢则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傀儡皇帝,建立东魏,改元天平并迁都邺城,专擅东魏朝政16年。黑城本《高王观世音经》前序也以这二位为主人公,但从字面上讲,黑城本的记述显然有失实之处。高欢于北魏及东魏时尽管做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统治阶层内部尚不稳定,又惧于称帝而导致人心相悖、给西魏宇文泰出师以口实,因此至死未曾称帝,只是在死后由其子高洋追封为献武皇帝。黑城本动辄称其为国王,或有两种解释:一来高欢先后被节闵帝和孝静帝封过渤海王,虽两辞,但孝静帝下诏不许,所以“高欢国王”或指此称;再者高欢专擅东魏朝政,乃为实际掌权者,虽为臣子却胜似君主,由此称为“国王”,亦可说通。黑城本前序与唐宋时记载虽内容相类,细节却有所不同,这里以前文《续高僧传》所引内容进行比较,以较其异同。
首先在时间上,黑城本并未提及,只言“昔高欢国王在相州为郡”,而《续高僧传》以及其它记述此事之古籍大都记为“魏天平年中”。“在相州为郡”,时间上似指孝静帝迁都之时,《魏书》载:“(天平元年)十有一月,……庚寅,车架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注]《魏书》卷12《孝静帝纪》,第298页。。自此东魏再无相州之称。再看《续高僧传》记载的“魏天平年中”。“天平”为东魏建立时之年号,历时四年(534-538)。据《魏书》记载,天平年间东魏不仅因饥荒而迁都于邺,且内平叛乱,外御敌侵,连年征战,世间并不太平。在如此背景下,民众将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寄托于观世音菩萨也是情有可原。因此关于孙敬德之事,无论黑城本或《续高僧传》等版本,时间都设定在天平年间,是较为符合历史背景的。
其次为地点与人物身份。黑城本说相州有一人名孙敬德,为主宝藏官。《续高僧传》等则言其人为定州募士。《魏书·官氏志》中并没有“主宝藏”及相关官职,或其职仅为吏员之属而并未入品,虽名为官,实还为社会底层人物,这样也符合孙敬德其人的人物设定。而“定州募士”这一说法则更凸显孙敬德低贱的身份。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种设定,都说明其并非什么大人物。对于地点,黑城本说孙敬德在相州任职,犯法入狱,因此事发于相州。《续高僧传》等典籍俱言其年满而还,被误认为是劫贼,抓捕后屈打成招而入狱,但并未言及孙敬德“还”向何方。《魏书·刑罚志》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注]《魏书》卷111《刑罚志》,第2888页。迁邺之时是天平初年,京畿则是相州及周边。因此,作为定州募士的孙敬德很有可能是相州人士,服役年满返回相州,偏赶上盗贼群起,又律法森严,逼供屈招后判为斩刑,合情合理。由此可见,在黑城本与其它版本的记述中,孙敬德身份虽有小异,但其实质都为下层人士,且事发之地都应是相州。各个版本在这几方面的叙述上并无太多不同。
黑城本与其它各书相比,除细节上的刻画更加细致外,尚有三处明显差异。首先,黑城本中孙敬德为主宝藏官,未修建过观音像,且因何入狱也无说明,最后也就没有了如《法苑珠林》中佛像替其受刑的情节。其次,黑城本中孙敬德向高王陈述获救原由,高王并不轻信,反而斥责道“汝胜于我,与圣何异?”同时又找来若干死囚,命其诵经千遍,随后处斩但刀折依旧,高王通过对孙敬德所述之事二次检验才信服,此经遂传。而在其它各本中,并无检验该经灵异神力等情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黑城本中孙敬德先持诵《观世音普门品经》以求免死,但梦中被沙门否定,称念诵《高王观世音经》才能获救,孙遂弃前者转诵《高王经》。《观世音普门品经》全称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乃姚秦时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里三分法流通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妙法莲华经》作为天台宗的主要经典在汉传佛教典籍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如此权威的《普门品》在这则故事中被无端放弃,此中之意颇耐寻味。《高王观世音经》自唐以来各路典籍虽多有载录,传世已久,但作译者不明,来源亦不清,历来都被认定为伪经。既是伪经,它在佛教典籍中的地位及对庶民的吸引力便与真经有所差异,为了“抢夺地盘”,更为招揽信徒,伪经有必要使用一些“技术性手段”来为自己正名:《高王经》在传播初期以编造神奇的灵验故事来鼓吹其效用,如其它各本中记载的孙敬德之事便是如此。随着这个故事的逐渐定型与不断发展,至黑城本时简单的灵验记已无法满足其信徒的虔诚与狂热,为提升其地位,不惜否定真经的效用。黑城本中对于《普门品》的“攻击”虽是一笔带过,但种种独特之处的真实用意即是在兹:不用修造观音像、平时不用礼敬、临刑诵满千遍便可免死,说明它即称即报、简单易行;高王检验其经时,不仅孙敬德一人获救,凡将死之人愿意持诵者都可得福报,说明它法力无边,绝非偶然;否定《普门品》,则说明其经胜真经一筹,更值得民众去信仰。由上所述,黑城本《高王观世音经》序文部分的灵验记确为隋唐演化而来,故事主线采纳了之前版本的结构,沿袭了时间、地点与人物的主体设置,但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更为突出,叙事节奏上有所减缓,在故事情节上又多有增补,使全篇故事更富有可读性,也更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这种变化不仅符合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会由简至繁这一普遍规律,同时也加大了对这部疑伪经的宣传效果。
四、西夏佛教灵验记的特点
前文已述,《高王观世音经》序文中的灵验记并非完全写就于西夏时期,它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有传承,有修订。其创制过程具有很长的历史延续性,并且没有确定的“终点”,这不仅是西夏佛教灵验记的特点之一,同时也是众多佛教灵验记的普遍特征。
如上文提及黑水城出土TK174.2《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卷下》,存有一则完整的灵应故事及另一则故事的起首部分。该经本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一部分,是流传于民间的重要伪经之一,虽不为历代大藏所收,却在百姓中影响颇大。除这一件外,宁夏拜寺沟西夏方塔中亦有同名经文出土,编号F035,惜残损严重。其中所载的灵验记虽亦难言完整,但可看出经文后半部分实有四则灵应故事。该版本经方广锠先生识读,并校以房山石经中的两个金刻本,在《拜寺沟西夏方塔》一书中刊有精校版录文。[注]宁夏文物考古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2-179页。另据张九玲的研究,该经至少还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的若干件西夏文写本,结构与内容都相对完整。[注]张九玲《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41-143页。除西夏出土的这些版本外,据郑阿财先生考述,该经在敦煌遗书中有全本传世(P.3236号及P.3916号),且“宋以后的传本不少,西夏时有汉文本及西夏文本,辽代也有汉文刻本,金代有石刻经文,朝鲜、日本、越南也保有汉文刻本、解谚、喃字本等,甚至还有回鹘文本的保存,足见其流行之广远”[注]郑阿财《〈佛顶心大陀罗尼经〉在汉字文化圈的传布》,第2页。。就与西夏汉文本关系最近的金刻本及敦煌本来看,西夏汉文本的内容与前述版本大致相当,只有个别用词上略有不同。这说明该经中的灵验记并非本地人士所创,而是随着经文的流传,受到西夏佛教信众的崇敬从而广布,具有明显的传承性。
又如上文所提M1·1460[F280:W101]《金刚索菩萨》中的灵验记,也是随着《金刚经》在西夏的传播而出现的。该故事较短,录文如下:
隋文荣常持此经,身死。王问文荣在生善恶,对云:“一生已来常持金刚经。”王闻敬叹,赐言:“放汝却归。”忽有二僧执烛锡引至一横坦塞路,僧以锡扣,即开示云:“从此而去。”遂即活矣。[注]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766页。
此则灵验记虽然不长,却也具备了身死(遭灾)、申诉(奉佛)、还阳(免灾)这些一般灵验记皆备的基础性噱头。在法藏敦煌文献P.2094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中也记载有类似的故事,主人公为隋朝开皇十一年时的太府寺丞赵文昌。与上文不同的是,敦煌本的记载有五百余字,语言更为生动,且多出些许上文没有的情节。如在还阳的路上,赵文昌遇到前朝灭佛的周武帝向他求情,望他向今朝皇帝乞少许功德用以还罪。这显示出西夏灵验记在流传过程中,不仅有像《高王观世音经》序文那样增润的情况,也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这样内容变化不大的情况,更有《金刚索菩萨》如此删节的情况。这种删节固然有刻印纸张版面有限的原因,但也说明灵验记在西夏故地流传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无定式。
西夏佛教灵验记另一个传承性的表现是图文并茂。前述TK117《高王观世音经》在序文前冠有佛画;《金刚索菩萨》上半幅为菩萨像,下半幅除灵验记外也用图像进行表现;而《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汉文版虽无图像,却在西夏文的版本卷首存有版画,其中俄藏ИНВ.No.6535号甚至在图像上还有八则对经文内容进行描述的榜题。这种以图配文的宣传形式很早就出现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在雕版印刷普及后则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灵应传记与图像具有不同的说教功能。前者作为宗教与文学的结合体,可以通过佛教徒的公开宣讲、民众的口口相传或自行阅读来进行推广,负担着弘传宗教思想、吸引听众或读者兴趣的使命,上文所列举的诸多传记作品莫不如此。而版画作为佛教本土化的另一种艺术形式,自唐兴起,盛于宋元,将壁画的施教功能从不可移动的墙面、岩石转移至方便携带、复制的纸面上,尤其对目不识丁的受众,可以直观且有效地表达奉佛后的成效。灵验记与图画,两种形式相得益彰,对佛教信仰的宣传可以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西夏佛教灵验记的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这些故事基本都服务于伪经。上文所述几则灵验记,除《金刚索菩萨》为宣传《金刚经》而作,其余《佛说竺兰陀心文经》、《高王观世音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均为在宋元之际比较流行的伪经。李小荣先生认为,如果说佛教真经是源自印度佛教东传而来,那么所谓伪经则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直接的文本体现。[注]李小荣《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之检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86-94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伪经,是中国人自己写就的佛经,并无真伪可言,且更符合中国人自身的审美标准。这些经文在职业僧尼的眼里也许价值不大,却被世俗百姓所供奉,而这其中图像、灵验记对于伪经的形成及流传功不可没:借助它们在民众间的口口相传、印刷刊行,伪经的流传便有了一定的民众基础;对于长篇累牍的佛理与说教来讲,中国人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或旁人述说之事,文学的表达于此可以产生震慑世人、展示神迹、令人信仰的效果。黑城本《高王观世音经》及上述灵验记所描述之事,有脱刑、治病、长寿、升官和往生等。这些主题俱为普通民众的欲望所在,因其带有明显的现世利益,所以民众对此具有普遍的接受心理。郑阿财先生指出,各类灵应故事均与现世利益有关,此乃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世俗化的必然现象,也是中世纪疑伪经形成的主要原因。[注]郑阿财《敦煌写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研究》,《新国学》第1卷,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313-333页。《高王观世音经》是观音信仰中出现较早且较为著名的伪经之一,它能够历经千年流传至今,那些相关的灵验记功不可没,无论卢景裕、王玄谟还是孙敬德,每个人物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但都有着相同的目的,起到类似的效用。黑城本《高王经》序文以及其它几则灵验记,作为这些故事在传颂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不仅是疑伪经传播的重要助力,也是佛教文学发展中的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对于西夏文学的研究和收获远不及社会经济文献研究那般繁荣。就目前来看,西夏文学研究尚侧重于世俗文学。同时由于资料的缺乏,针对单篇文献的研究比较多,且多倾向挖掘文献的历史价值,但很少关注其文学价值,因此不易从整体进行把握,进展比较缓慢。如西夏文《新集锦合辞》与拜寺沟方塔所出汉文残本诗集是为数不多的大篇幅文献,故而与这二者相关的研究比较全面,但对于西夏诗歌与格言的整体面貌而言,目前很少有宏观的描述。佛教文学作为宗教与文学的结合体,其本质属性在于文学。黑水城出土的这类佛教文学作品很好的为我们展现了西夏文学的另一处风景,相信通过对更多佛教文献的爬梳与深入,西夏佛教文学势必会成为西夏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