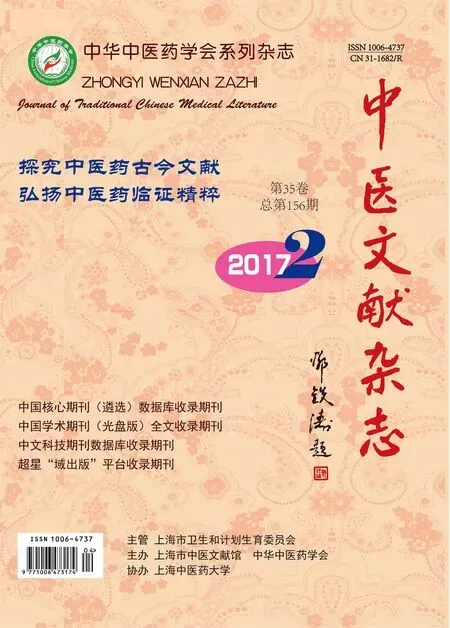岭南医家苏世屏《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学术特点初探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舒海涛 郑 洪
岭南医家苏世屏《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学术特点初探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舒海涛 郑 洪
广东近代名医苏世屏的《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发扬仲景杂病学术,是重要的《金匮》文献。其学术特点有如下几点: 逐节串注,直贯全论;对比串解,贯通前后明经义;论《金匮》与《伤寒》为虚邪与正邪之异;悟仲景言外之旨,举一反三论病。
苏世屏 金匮要略原文真义 学术特点 岭南
苏世屏(1894- 1961年),号离尘,新会县小岗梅岗乡人。1920- 1924年师承于时广东四大名医之一黎庇留门下。学成后,曾悬壶于江门、新会、开平、新昌等地。1958年在新会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1959年新会县中医研究院成立(新会中医院前身),任副院长。曾为县开办中医班及中医进修班,并亲自选材讲学,为中医教育及中医人才培养做了大量工作[1]。而据《新会市卫生志》记载[2],苏氏治病,每起沉疴,声名远扬,其擅长内科、妇儿杂症,治病四诊合参,八纲俱备。晚年就诊者远至省、港、澳、佛,近至邻近县境,病人慕名接踵而来,治愈者众。诊余之暇,或阅览各家著作,或撰著医籍,一生著有《伤寒论原文真义》、《金匮要略原文真义》、《痉病真义》、《医药论文选》、《经络新韵》、《舌诊要诀》、《医史提要》、《中医拨云集》、《苏世屏医案选》等,其著述以经勘经,言必有据,文词简朴,不以辞害义。
作为伤寒派医家,苏世屏在学术上尤宗仲景之说,《伤寒论原文真义》、《金匮要略原文真义》二书可谓是苏世屏对仲景学术研究的毕生心血。其中《伤寒论原文真义》写成于抗战期间,其既成之后苏世屏一度计划从此休息,“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随岩壑以老去”,但继而又觉得有必要完成对《金匮要略》的诠解,他说:“继思《伤寒》与《金匮》,原为一表一里,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相辅为用,缺一不可。且《金匮》为医杂病之祖,文深义古,头绪甚繁,有简略不详者,有异同错综者,有文气不属者,有理路潜通者,较之伤寒,尤为难读,岂可无注乎?”(《金匮要略原文真义》自序)于是又写成《金匮要略原文真义》。《伤寒论原文真义》曾于1960年由新会县中医院印行,而《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只有手稿存世,最近才由其弟子方恩泽整理出版。笔者有幸参与部分整理工作,研读全书之后就其主要内容作一简单概括,并对其学术特点作一初步探讨,不揣浅陋,求正于方家。
《金匮要略原文真义》主要内容
《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全书分4卷,共22篇,其中卷一有5篇,分别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痉湿暍病脉证并治第二”、“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疟病脉证并治第四”、“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卷二有6篇,分别为“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第七”、“奔豚气病脉证并治第八”、“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第九”、“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第十”、“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卷三有5篇,分别为“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第十六”;卷四有6篇,分别为“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跌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并治第十九”、“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对《金匮要略》作了一定的删减和补充。苏世屏认为《金匮要略》原书自经络脏腑至妇人杂病共22篇皆为仲景原文,而其后3篇则可能为后人所加,为避免目珠之混,苏世屏将此3篇加以削之,不予注解。
对于《金匮要略》的附方,说法不一,有云为后人所增补,亦有云出自仲景。苏世屏认为无论附方是否出自仲景,因其具有历史价值,并且能为治病提供更多方法,所以对附方也进行了详细地串注。此外,苏世屏还另附其医案5则穿插在注释或其按语中,在卷末转附了陈修园所载考古2则以便今人考量。
此书以《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经典医籍为依据,加以己见,力图阐发《金匮要略》原旨。
学术特点初探
1.逐节串注,直贯全论
苏世屏在全书多处强调要谨遵仲景本意,主张力保原书本貌,发扬圣道。故全书以“串注”为基本特色,即将自己的语言串联在《金匮要略》原文中,以逐节串注的方式贯穿全文论注,在保证语句通畅连贯的前提下,将注文与原文相结合,而又能阐发经旨,以“务求与仲师心法契合无间”(《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凡例)。
这种注法与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有所相似,即注解都是以注文与原文相融合的形式呈现,但又有不同之处。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是将注文以小文字的方式衬加在《金匮要略》原文中。而苏世屏《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则是在逐节条文下再将注文与原文进行串解。相比之下,各有不同亦各有千秋。陈修园的“浅注”极具特色,其以小文字注文衬加在大文字原文中的方式使得“深入浅出”的意味尤为突出,而苏世屏的“逐节串注”也颇为独特,其“逐节”而又连贯,注重章节联系,前后对照皆从注中说明,一线到底,方便学者阅读领会,其“串注”而又流畅,全文所注,简繁得当,义取分明。全书之中虽有多处提及注家所注之欠妥,如《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苏世屏注曰:“此节注家,说得惝恍迷离,全无是处,试玩‘故称’二字,乃假定之词,非三阴三阳之外,身内另有个厥阳气体也,又注家每以寸为阳,尺为阴,如此,是寸有脉,尺无脉。”诸如此类的论述,似有用辞过激之嫌,但亦无可厚非,细读苏世屏所列诸注家不妥,确可发现其中尚存牵强附会之弊,故笔者认为苏世屏借此旨在告诫学者对经文理解要注重考据的重要性,而不能故为高深,说理空滑。
2.对比串解,贯通前后明经义
对比手法,历代注家也都有使用,不同于其他注家的是,苏世屏《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将此手法作了一定的发挥,不仅对比的方面多样,在数量上也是相当之多,而其对比视角亦是颇为独特,往往在细微之处给人以启迪。
以对比释字义 如《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中:“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其中“脏”字,苏世屏释为肾脏,其注云:“邪入于肾脏,肾脉通于舌下,气厥不至,舌即强而难言。廉泉穴不能收摄,则口吐涎,脏指肾脏而言。”为进一步说明,苏世屏引《妇女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所论以相参照,其云:“《妊娠篇》有少腹如扇,当以附子汤温其脏,少腹子脏,皆属于肾,故用附子汤,可以比例而明。今人用地黄饮子,治风痱舌强不能言,注重治肾。亦颇有效,其义可思。”苏世屏运用本证以比类相照,再结合临床相关,使得对条文字义的理解更加深刻明朗。
以对比明辨证 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第十》:“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苏世屏特引《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所云:“若心下满而鞕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通过对比辨证可知,前者之证,按之心下满痛,满而不鞕,则非结胸,满而有痛,则非为痞,非痞则可用柴胡,因其为热实证,所以当下之,故用大柴胡汤。
以对比阐病机 如条文“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此为水气病脉论,苏世屏在注中云:“消渴第二节,有寸口脉浮而迟,趺阳脉浮而数,与此同一脉法,彼则因营卫虚竭,胃气强而消水过速,则成消渴,此则因营血下潜,胃气强而生热,热阻其水,则成水肿,经文奥晦难通,参看消渴所注,比例其义。”由此可看出,苏世屏将脉象相同的两种疾病进行对比,同中求异,进而阐发其二者间病机的不同。
以对比论方药 如《妇女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用狼牙汤治疗阴中蚀疮烂,苏世屏注云:“狼牙根以苦能燥湿,寒能清热,湿热除,则虫自消灭。”并将其与苦参汤作对比,苦参汤用于治疗狐惑证,其气味亦属苦寒,苏世屏认为:“狐蚀于下部,其热循任脉上挟咽喉,故有咽干一证,苦参功同黄连,能折火热下降,与狼牙之具有毒性专事劫夺湿热杀虫者,颇有不同也。”即论述了两方药间作用机理的不同。
3.论《金匮》与《伤寒》为虚邪与正邪之异
历代学者皆公认张仲景之《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一论伤寒,一论杂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正如陈修园所言:“《金匮要略》,仲景治杂病之书也,与《伤寒论》相表里。然学者必先读《伤寒论》,再读此书,方能理会。”[3]陈伯坛在论述两书关系时亦有云:“诗三百,孔圣蔽之以一言。长沙全集,原序则蔽之以一‘合’字。论合卷亦合,分之则书亡。”[4]由此可看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须相互对参,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证候、病机、治法和方药等方面既存相通又有差异。
苏世屏亦将《金匮》与《伤寒》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其二者之间的比类参观在全书中彰明显著。苏世屏在认识《伤寒》与《金匮》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更注重两者之间的区别,其中最为强调的是二者之间存有虚邪与正邪之异。
《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有云:“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这里讲的“实风”即为“正邪”,“虚风”即为“虚邪”。苏世屏则概括为:“大气之变化,合时令方向而来者,谓之正邪实风;不合时令方向,从冲后而来者,谓之虚邪贼风。”因此,苏世屏认为,《金匮》皆论杂病,是虚邪贼风伤形,《伤寒》所论则正邪实风伤气,为经气自病。其在《金匮》开宗明义第一篇中即提出了此学术观点:“《伤寒》所说者,是以三阴三阳无形之经气为基础,其经气自病,卒遭者是正邪实风,以正邪能伤人经气也,其病源一致,故统称三阴三阳之为病,更从证状上别之,则名曰伤寒,名为中风。《金匮》所说者,是以脏腑骨肉、经络血脉、营卫腠理等有形之体质为基础,若逢身形之虚,所患者是虚邪贼风,以虚邪能伤人身形也,其病源复杂,各证有各证之不同。”并以此为总述,将此学术观点贯穿在整个论注中,如在《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篇中,苏世屏在篇首即论述了疮痈与伤寒之区别,其释曰“本节为论疮痈之总纲。有初起似伤寒而实非伤寒者,以伤寒乃正邪实风,病在无形之经气;疮痈乃虚邪贼风,病在有形之体质。”并在篇末总结中再次强调:“本篇论诸疮,为病在有形之体质,与经气自病无关,故以营卫为系统,营卫无处不达,稽留于肌肉,则生疮痈;稽留于大小肠,则生肠痈;稽留于皮肤,则皮肤溃烂浸淫。”
可见苏世屏分别从病邪的属性、病邪所侵犯的部位、病源及证候的规律性等角度论述了《金匮》与《伤寒》存有虚邪与正邪之异,不仅加深了对仲景学术的认识,更为临床辨证提供了新的思路。
4.悟仲景言外之旨,举一反三论病
“注家自明以来,能遵守原文为解者少,勇于改经就我者多……试思自汉至宋,上智贤哲,大不乏人,未有敢自作聪明删改移易者,何故乎?”(《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凡例)由此“遵古守经”则成苏世屏立注之根本,然而苏世屏虽遵古,但绝非泥古,诚如其所言:“治分多法,学贵圆通,未有执一板法而可以御无穷之变者。”故对《金匮》的注释,苏世屏常悟仲景言外之旨,其基于仲景所论之上加以总结而举一反三,又成其发仲景未发之特点。
如对痉病的论治,原书中只出三方,苏世屏以原文为基础,认为文内已指出的多种致痉原因即暗示着多种治法,并加以总结提出了治痉六论:如表虚兼挟热者,用竹叶汤;表实挟热者,则用麻杏石甘汤加葛根,以开太阳之阖;表邪已过,燥气内盛,须泻阳救阴从下夺论治;贼风化热,阴液愈虚,宜补阴泻火,方用黄连阿胶汤加竹茹;上身发热而又有恶寒,忌用下法,而宜清燥舒筋,方用竹叶石膏汤,去半夏粳米加羚角钩藤治之;血虚致痉,宜补血,血虚有热者,用当归散去白术加生地治之;血虚有寒者,用胶艾汤加炮姜治之。
又如论暑篇,原书只出二方(白虎加人参汤,瓜蒂汤),张仲景独以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为暑病之正证,苏世屏在此基础上加以延伸,认为暑病由伤寒所致,亦不出伤寒之治法,除汗出恶寒,身热而渴四证外,又提出:若出现心烦脉虚,唏嘘溺赤等证,重则用白虎加人参汤,轻则用竹叶石膏汤;若谵语懊,反复颠倒,烦躁不得眠,则用栀子豉汤;心中烦,不得卧,则用黄连阿胶汤;热利不止,则用葛根芩连汤。
再如《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篇,苏世屏对吴茱萸汤见证进行总结:“仲师用吴茱萸汤,凡四见,一曰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二曰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三曰干呕吐涎沬头痛者;四曰呕而胸满者。此皆阴寒化浊,浊气上乘之病,用之即效。”在此基础上,苏世屏则加以推广其治法,认为:“凡阳虚之人,雷龙之火上升,头痛如破,大晕欲倒,目肿如桃,眉棱骨痛,耳鸣迫塞,目昏清泪等,皆获奇效,不可不知。”
综上所述,苏世屏《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全书详略得当,取义鲜明,其学术特点与历代《金匮要略》注家有所不同,为丰富岭南医学文献,发扬仲景学说理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更多的学术思想尚待深入研究。
(本文引文除参考文献外皆据《金匮要略原文真义》稿本。)
[1] 方恩泽.苏世屏先师学术思想及其辨证用药特点[J].新中医,1984,(4):17.
[2] 新会市卫生局.新会市卫生志[M].广东:新会市卫生局,2000:265- 266.
[3] 林慧光.陈修园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85.
[4] 陈伯坛.陈伯坛《读过金匮卷十九》:附《麻痘蠡言》[M].何丽春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2.
R222.3
A
1006- 4737(2017)02- 0022- 04
2016- 1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