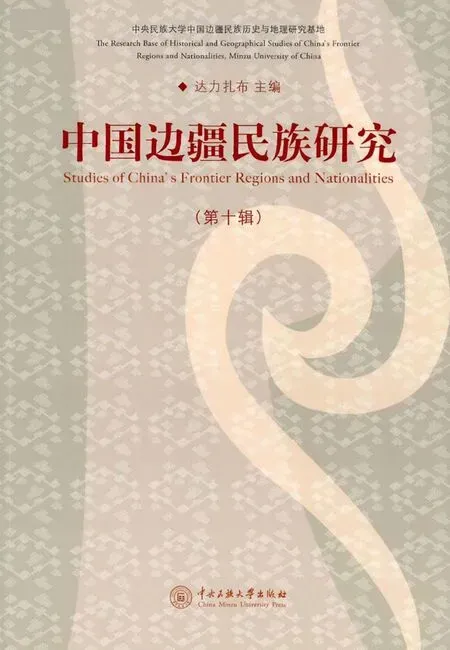清朝平定准噶尔战争中一个准噶尔宰桑的命运*
赵 毅
内容提要:哈萨克锡喇系准噶尔噶勒杂特三宰桑之一,其在清朝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归附清朝,并受到乾隆帝的重用,仅半年时间就从散佚大臣跃居参赞大臣,并得封公爵,然而不久就反叛清朝。现利用满汉文文献试图从清朝对其招抚、反叛后的剿捕、反叛之缘由等方面,来窥探乾隆帝对归而复叛之人的政策。
清朝平定准噶尔的叛乱过程中,多次出现归而复叛之人,然而学界大多关注于大人物,对于小人物却关注较少,准噶尔宰桑哈萨克锡喇就是一例。哈萨克锡喇(亦作锡拉、沙喇),满语为hasak sira,主要出现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的清朝文献记载中。仅从姓名上看,易被后人误为哈萨克之人①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上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22—55、147页;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哈萨克族卷》(索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418、420—421页;孙文良、董守义《清史稿辞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95页。,或哈萨克和锡喇二人②如,吴忠匡校订《满汉名臣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45页;塔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塔城市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页;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塔城直隶厅乡土志》第七卷,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617页;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塔城直隶厅乡土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9页。。据《清高宗实录》载:“噶勒杂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户,为一鄂拓克。”③《清高宗实录》卷695,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795页。而哈萨克锡喇实系准噶尔旧十二鄂托克噶勒杂特三宰桑之一④准噶尔旧十二鄂托克噶勒杂特之三个宰桑:哈萨克锡喇、都噶尔、特克勒德克(见《清高宗实录》卷514,乾隆二十一年六月辛丑条,第495页)。。故“哈萨克”是其人名的一部分,并不代表其族属。其归附清朝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从散佚大臣升为内大臣,再至参赞大臣并晋封公爵,可谓恩宠优渥,然而最终还是走上反叛之路。吴阿木古楞曾利用满文档探讨过额林哈毕尔噶路台吉和宰桑的归附及反叛原因⑤吴阿木古楞《准噶尔覆亡若干史实考证》,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第16—38页。,曾涉及哈萨克锡喇,但仍有对哈萨克锡喇专门探讨的必要。其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反叛道路,而其反叛又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
一、清朝对哈萨克锡喇的招抚与重用
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阿睦尔撒纳归诚时曾称,台吉诺尔布、宰桑玛木特、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喇等带兵抢掠其属众①《平定凖噶尔方略》正编卷3,乾隆十九年夏六月丁酉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五八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45页。,此为清朝首次听到哈萨克锡喇之名。后将军班第报称,克尔努特台吉阿布达什及其弟巴图尔归附,亦称其曾被哈萨克锡喇等人抢掳,故暂时居住扎哈沁地方②《清高宗实录》卷476,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己卯条,第1149页。。清朝在招抚扎哈沁之后,因顾虑到哈萨克锡喇可能会抢掠扎哈沁,故在对扎哈沁是就近安插还是移住内地问题上而争持不下。③《清高宗实录》卷477,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壬辰条,第1158页。次年,因得木齐哈喇勒岱诈称:“噶勒杂特之宰桑哈萨克锡喇、都噶尔领兵二千欲掳包沁人众”④《清高宗实录》卷480,乾隆二十年春正月丁亥条,第9页。,此时的哈萨克锡喇成为清朝进军途中的一个障碍。故阿睦尔撒纳乘机上奏:“厄鲁特侍卫达什敦多布系哈萨克锡喇一处宰桑都噶尔之兄,其户口尚在噶勒杂特,今伊情愿前往招服噶勒杂特人等。”⑤《清高宗实录》卷480,乾隆二十年春正月丁亥条,第10页。此建议得到乾隆帝的肯许,并赏赐达什敦多布副都统职衔,开始对哈萨克锡喇实施招抚。
不久,归降之噶勒杂特齐伦告称:“宰桑哈萨克锡喇、都噶尔等,俱向伊犁迁去。”⑥《清高宗实录》卷483,乾隆二十年二月庚申条,第42页。然班第认为:“噶勒杂特人等,闻我兵收服包沁,虽迁移他去,我兵彻(撤)回,伊等自仍归原游牧居住,且此际牲畜疲瘦,又安能遂至伊犁?”⑦《清高宗实录》卷483,乾隆二十年二月庚申条,第42页。继而,阿睦尔撒纳又称哈萨克锡喇等人向额林哈毕尔噶方向迁移,其属人来降甚多。然此时清朝正在进军途中,无暇顾及安置赏赐,故令阿睦尔撒纳详悉记明归降之人地点,即令在居住原处。清朝在招抚哈萨克锡喇过程并未发生冲突,十分顺利。乾隆二十年四月,哈萨克锡喇率众来投。但因连年战争,生计困顿,希望清朝拨给牧地,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将其安置在吐鲁番之北接木垒河源处驻牧。⑧《清高宗实录》卷487,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条,第105页。
哈萨克锡喇归降后即被授予散佚大臣,分封四部汗时升迁为内大臣,并办理图什墨勒事务,管理噶勒杂特鄂拓克人众。然而,清制:户口三千以上方能授予内大臣⑨《清高宗实录》卷492,乾隆二十年七月丁酉条,第197页。,而哈萨克锡喇归附时的人口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据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二十日,定边右副将军萨喇玛查明哈萨克锡喇归附人口折中称:“baicaci, gelzat i jaisang hasak sira se,eje i gosingga hese be ujifi, uthai dahame dosifi, ceni gaiha juwe minggan baigun i dorgide hūnta.”⑩《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等奏遵旨查办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拉(锡喇)归附人口户籍折》,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日,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〇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0页。直译即“查得,皇上仁慈,有旨养育,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喇等,携带属众二千户请求归附内迁。”此处二千户包含宰桑都噶尔之属众。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报:“hasak sira i niyalma minggan boigon”①《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报哈萨克锡喇巴雅尔所属人等数目折》,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一册,第282页。直译即“哈萨克锡喇人千户”。因而其属众仅有千户左右,可见其为加恩授封内大臣。
同时,安排其入觐朝圣,以示对其恩宠。然而,其在入觐途中因湿热而出痘,乾隆帝听闻后,特令其留在当地台站养病,并派头等待卫乌勒登前去慰问,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②《理藩院左侍郎参赞大臣玉保等奏报移咨达尔党阿速派侍卫到达罕德勒驿站看望哈萨克锡喇等病情事折》,乾隆二十年十月初四日;《头等侍卫乌勒登奏报哈萨克锡喇等人出痘及玉保率兵先行情形事折》,乾隆二十年十月十四日,皆见《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上册),第22—23、24—25页。。不久,病愈后入觐,受到乾隆帝的亲自召见,且向其询问准噶尔内部情形,并赏赐银三百两③《平定凖噶尔方略》正编卷17,乾隆二十年九月甲戌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五八册,第274页。。在面圣期间,听闻阿睦尔撒纳叛变之消息,即刻向乾隆帝奏请到军营效力,以此来报答圣恩④《头等侍卫乌勒登转奏哈萨克锡喇等呈请到军营效力以报答圣恩事折》,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见《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上册),第32—35页。。而此时正是进剿用人之际,且哈萨克锡喇又熟悉该处情形,故得到乾隆帝的赞许,而被授予参赞大臣前往西路军营效力。
为了剿灭阿睦尔撒纳宁辑边疆,乾隆帝令将军大臣商议进剿之策。作为新降之人哈萨克锡喇等抓住时机,提出“由闼勒奇、博罗布尔噶苏、珠勒都斯进兵,山岭皆大,此三处内,惟珠勒都斯地方空虚,并无阻搁。”⑤《清高宗实录》卷501,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乙未条,第315页。故由珠勒都斯进兵较为方便。乾隆帝对此方案大加赞赏:“相度目前情形,所见甚是,其感激朕恩,实心奋勉,朕甚嘉予。”⑥《清高宗实录》卷501,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乙未条,第316页。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哈萨克锡喇因擒获察衮父子及克什木等,特加封其公爵。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定西将军策楞等奏哈萨克锡喇之弟塔斌抢掠马驼之事。⑦《署定西将军策楞奏报哈萨克锡喇之弟塔斌于其游牧处抢掠马驼等情事折》,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见《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上册),第40—43页。因正在进剿阿睦尔撒纳之际,故并未予以深究⑧《定西将军等奏参赞大臣哈萨克锡喇所属兵丁抢劫马匹事宜暂未深究以便进军伊犁事片》,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见《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上册),第54—55页。。
起先,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唐古忒曾称“哈萨克锡喇迁至哈布塔克拜达克等处居住,意似观望。”乾隆帝对其汇报予以训斥“哈萨克锡喇乃系阿逆仇人,必无从贼之事”⑨《清高宗实录》卷503,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乙丑条,第350页。。后为消除前次唐古忒诬陷哈萨克锡喇之事,特令策楞在擒获唐古忒时,“即于众人前,指出其造言诬陷哈萨克锡喇之罪,因其言不足为据。”⑩《清高宗实录》卷507,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丙辰条,第401页。企图以此来消除哈萨克锡喇的疑虑。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兆惠提出令哈萨克锡喇、尼玛、吞图布等,派兵二千名,前赴军营,共同防范哈萨克。但乾隆帝认为:“若哈萨克锡喇等,经年效力军营,甫回游牧,岂可即行调遣,使之仆仆道路。”⑪《清高宗实录》卷526,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条,第630页。令哈萨克锡喇返回游牧进行休整。继而,乾隆帝就接到雅尔哈善等的奏报称:“哈萨克锡喇、尼玛等,负恩谋叛,现拟领兵抢掠巴里坤,并擒拏噶勒藏多尔济等语。”①《清高宗实录》卷527,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条,第637页。始听消息之乾隆帝对此并未相信。后和起派人报称巴雅尔、哈萨克锡喇、尼玛、莽噶里克等同谋为逆,方才得以确信。
二、清朝对哈萨克锡喇的剿捕
乾隆帝接到哈萨克锡喇反叛的消息时,正为策楞谎报阿睦尔撒纳被擒令其颜面大失之事恼火不已之时,此可谓是火上浇油。故而将哈萨克锡喇的反叛皆归结于策楞、玉保“心存观望,坐失事机”②《清高宗实录》卷528,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己巳条,第649页。所致。即刻着手布兵进剿,并下谕:“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③《清高宗实录》卷527,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条,第637页。自此,开始大力剿捕哈萨克锡喇等。这种剿杀情况,据《啸亭杂录》记:“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④昭梿《啸亭杂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015年重印),第80页。虽然不乏夸张,但也反映了乾隆帝对于厄鲁特人悉数剿杀的做法。次年正月,派西路大军专门办理进剿哈萨克锡喇之事,同时传谕杜尔伯特汗车凌、内大臣阿克巴集赛及宰桑达什车凌等,派兵防守游牧,并将通向哈萨克地方隘口,严加堵御,倘遇贼人逃窜,即行擒献,谨防其逃窜哈萨克等处。不日,守备高天喜与哈萨克锡喇交战,但因兵力有限仅剿杀部分属人,收获一些驼马而已。
乾隆帝对哈萨克锡喇等处理办法:“果在阵前立毙则已,如可生擒,则舒赫德等务将伊等擒解前来,不得即行正法。”⑤《清高宗实录》卷531,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壬戌条,第698页。对其属人“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⑥《清高宗实录》卷532,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丙寅条,第706页。。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将军成衮扎布奏称:“哈萨克锡喇等,带领噶勒杂特百余户,迁往额尔齐斯。”⑦《清高宗实录》卷535,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戊申条,第741页。即传信唐喀禄会同车凌等剿灭噶勒杂特人众。四月,又得哈萨克锡喇由额尔齐斯逃向伊犁等处之信。乾隆帝认为此投入伊犁则易于剿捕,令两路大军一路由珠勒都斯进军,一路则由闼勒奇前往,形成包抄会剿之势。⑧《清高宗实录》卷537,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丙子条,第772页。五月,将军成衮扎布又称哈萨克锡喇逃至和博克萨里,此距将军兆惠所率大军较为方便,故专委兆惠办理。同时,令“唐喀禄、车木楚克扎布等,应先至和博克萨里,擒获逆贼哈萨克锡喇等,办理完竣之时,亦可得阿逆确信,八九月间,若复前进。”⑨《清高宗实录》卷541,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己卯条,第845页。可见乾隆帝对剿杀哈萨克锡喇甚为重视。
继而,图伦楚报称哈萨克锡喇由布勒哈齐向博罗塔拉方向逃窜,并欲前往伊犁。为了切断哈萨克锡喇的后路,参赞大臣唐喀禄与纳木扎勒分别派官兵践踏和烧毁哈萨克锡喇所种之粮⑩《参赞大臣唐喀禄等奏闻追剿阿睦尔撒纳并派官兵践踏哈萨克锡喇所种之粮折》,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五册,第97—106页;《参赞大臣纳木扎勒等奏派遣官兵烧毁哈萨克锡喇所种禾折》,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六册,第37—39页。。后兆惠称图伦楚带兵一百名于阿尔噶凌图地方击败哈萨克锡喇,乾隆帝加恩补授其为副都统。乾隆二十三年(1758),俄罗斯来文称阿睦尔撒纳出痘身死,将尸送验等情,但乾隆帝下谕:“逆贼阿睦尔撒纳虽死,而哈萨克锡喇、舍楞等,尚未就擒,兆惠等勿因此稍存懈怠,务宜加意奋往,速奏肤功。”①《清高宗实录》卷515,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巳条,第16页。因而捕获哈萨克锡喇等方为完成剿逆事业。同年二月,顺德讷等自哈萨克边界撤兵途中,将哈萨克锡喇之党摩罗、达什扎布等生擒,而被加恩授予世职。
同年三月,定边将军兆惠奏称:“至库尔喀喇乌苏捉生询问,据供厄鲁特鄂拓克人等,去年俱聚于沙喇擘勒。十二月间,哈萨克遣兵二千,将巴尔达穆特绰和尔抢掠其昻吉岱,哈萨克锡喇等筑垒固守,因诱哈萨克云,玛哈沁等。欲以妻子易换马匹,哈萨克存留百人,后,为伊等诱杀。”②《平定凖噶尔方略》正编卷52,乾隆二十三年三月辛丑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五八册,第849页。不日,又探听到哈萨克锡喇等渡过伊犁河到达闼勒奇地方,并由萨玛勒河分路向伊犁方向逃遁。同时,哈萨克阿布赉汗之子额尔类属人向清朝报称“额尔类领兵五千名,于伊犂遇哈萨克锡喇所携余众,将及百户尽行掠取,哈萨克锡喇惟带一人逃走。”③《平定凖噶尔方略》正编卷54,乾隆二十三年夏四月戊辰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五九册,第16页。然而,乾隆帝认为:“哈萨克人等所言,哈萨克锡喇只身逃走,及伊母渡河溺死,殊不足信,或借此浮言,懈我军心,因而潜行招引,亦未可定。”④《清高宗实录》卷564,乾隆二十三年六月丁巳条,第149页。令各将军大臣极力搜捕。
四月,车布登扎布与富德等探知哈萨克锡喇潜遁和落霍斯,即督兵逐之。哈萨克锡喇及鄂哲特等“闻追急,度不得脱,悉众据髙冈,侍卫玛琥等,以我兵少,请待其走攻之,车布登扎布特不可,麾兵击,擒鄂哲特,哈萨克锡喇仅以身免,斩获甚众。”⑤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第一辑)卷71《扎萨克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4页。此次交战哈萨克锡喇损失惨重。此后,清军连年进剿都未能擒获哈萨克锡喇。故乾隆帝下谕于兆惠:“若向特克斯等处,即宜迅速追剿,若已逃入哈萨克,亦应勒兵索取。”⑥《清高宗实录》卷561,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丁丑条,第115页。此时,回疆战事兴起,兆惠为抢军功而领兵直奔回疆。乾隆得到消息后即行训斥:“前经屡降谕旨,令兆惠等将伊犁等处叛贼渠魁全行擒获,再往回部,今来奏业已遄行。……伊犁无兵驻守,或哈萨克锡喇等乘间复出亦未可定,可传谕兆惠等平定回部后,仍遵前旨回扺伊犁,尽剿遗孽,如渠魁一人未获,不可谓之蒇事。”⑦《清高宗实录》卷563,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丙午条,第139页。
不久,车布登扎布称哈萨克锡喇投向西哈萨克之特柳克地方,其与阿桂、富德合兵向阿布勒噶尔索取哈萨克锡喇。继而,据差往右部哈萨克之章京纳旺口中得知“厄鲁特哈萨克锡喇,挈眷二十余人,逃入尔布鲁特之萨雅克、萨喇巴噶什鄂拓克”⑧《清高宗实录》卷579,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丁未条,第388页。。故在颁给布鲁特车里克齐等敕书中声明:“哈萨克锡喇系负恩背叛之贼,不可宽宥者,今逃入尔等游牧,似属实情,尔等自应晓示该鄂拓克人等,将逃贼夫妇,即行拏送,其属人不妨存留。”⑨《清高宗实录》卷579,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丁未条,第388—389页。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在预为安置土尔扈特归来,再次提及“倘有哈萨克锡喇,并一并率来”①《谕伊勒图等若土部来归属实需妥善安抚》,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合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6页。,可见乾隆帝对其重视程度。此后再未获哈萨克锡喇之消息,到底是否擒获文献缺载,抑或被当作玛哈沁所剿杀,不得而知。
实际上,清朝有三次捕获哈萨克锡喇的机会。第一次,守备高天喜与哈萨克锡喇交战,因军力不济而未能成功,仅剿杀其属众,获得马驼而已。第二次,图伦楚带兵一百名与哈萨克锡喇之三百兵丁交战于阿尔噶凌图,击杀其百余兵丁,但因山险马乏兵少未能追及。第三次,车布登扎布和富德与哈萨克锡喇交锋于和落霍斯,兵力太少,仅擒住鄂哲特,使哈萨克锡喇得以逃脱。可见兵力不足为十年内三次皆未能捕获的主因。究其兵少之原因,除了分路进剿兵力分散原因外,还有用兵回部牵制清朝大量兵力所致。
三、哈萨克锡喇叛逃的原因
哈萨克锡喇作为归降之人,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从散佚大臣到内大臣,再至参赞大臣,继而晋封公爵,且令其担当大任,协助追剿阿睦尔撒纳,并遭唐古忒的诬陷时,乾隆帝还是给予极大的信任。观其仕途,可谓平步青云,然而清朝对其如此恩宠优渥,其又为何反叛呢?其背后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关于其反叛的原因,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据零星记载可以大致窥探其原因。
据《西域图志》卷首二《天章二·西师》条记:“时呢吗(尼玛)、哈萨克锡拉(喇)皆以受职从征,见达尔党阿为贼所卖,笑其无能,自哈萨克还,复生变计,与巴雅尔、莽噶里克等密谋构乱,以害将军和起。”②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查此为达尔党阿误信阿布赉将执阿睦尔撒纳以献,纵使阿睦尔撒纳脱逃事件,然果真因此事被讥笑可欺而叛?
据尼玛满文供词中记载:
拉丁转写:duleke aniya hasak de cooha ibeme dosika manggi, abural i jergi bade isinafi, hasak sira, dasicering, basang, dakba be ishūnde hebešefi, meni jun gar i ūlet se gemu omihon de amcabufi, niyalmai yali yendechūn yali be jedere de isnaha bime,jiyanggiyūn ambasa umai meni ere turgun be giljame gūnirakū, amba ejen de donjibume wesimburakū, umesi suilaha turgunde, be hebešefi, amasi mariha manggi ubaški sembihe.③《奏报审问尼玛缘何反叛情形片》,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一册,第94页。
汉文直译:去年吾等进兵哈萨克,抵达阿布拉尔等地后,吾等哈萨克锡喇、达什策凌、巴桑、达克巴共议,我们的准噶尔厄鲁特等全体饥荒,已至食人肉、吃狗肉之境,将军大臣不怜悯此情,不奏闻大皇帝,困窘至极,故吾等商议,返回之后反叛。
从此满文档案可知哈萨克锡喇等人因生计困顿所致,不得不反叛。其实,清军前线将领也曾向乾隆帝反映过降人的困苦情况,但是,因阿睦尔撒纳叛乱而被激怒的乾隆帝完全不顾降人生死,反而斥责将领们找借口,贻误军机。只顾催促迅速捕捉阿睦尔撒纳。对于稍有怀疑之人即令“办理”(剿灭或处死),以其牲畜作为军需。乾隆帝心态已失常。后来一些人的再叛,是与清朝对降人的错误政策密切相关,并不是他们响应或支持阿睦尔撒纳。反叛逃走后,又招致被剿杀。而此时准噶尔内部到底是什么状况?
据阿睦尔撒纳归降后曾报称:“去年十月内巴特玛车凌、额林沁、阿布赉带领厄鲁特、哈萨克兵一万有余,将博罗塔拉等处所有游牧人众尽行抢掠,阿布赉于闼勒奇岭东将掳掠人带回,巴特玛车凌、额林沁带兵四千余直入伊犂,将居住伊犂河北达瓦齐之厄鲁特、回子尽行掳掠。”①《平定凖噶尔方略》正编卷9,乾隆二十年夏四月丙午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五八册,第146页。可见准噶尔既被哈萨克抢掠又被巴特玛车凌、额林沁等洗劫,加之数年平准战争,准噶尔已经越来越凋敝衰败。噶勒杂特部亦是如此,急需清朝的接济,然而自哈萨克锡喇带领属人归附以来,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赈济,反而需要自备粮草随军征剿,这和哈萨克锡喇预想相差甚远。同时,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因长时间用兵,内地粮草供给紧张,故在进军途中推行“凡可渔猎资生之地,俱行搜捕”②《平定凖噶尔方略》正编卷59,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甲寅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五九册,第104页。的补给政策,故准噶尔之地遭到搜刮。“如有遵谕即行换易,及沿途协助马匹、口粮者一一登记,俟事竣后酌量加恩。倘稍有勉强,或故将疲瘦牲只交易者,其人即属可疑,应留心办理。”③《清高宗实录》卷509,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庚寅条,第429页。沿途换取粮草时,只是一一登记,给予口头承诺,并未实物可供交换。而对于勉强交易态度不积极者可能受到处理,而这些马匹粮草自然主要是由厄鲁特所供应,这种政策具有一种变相征缴的性质,这些种种成为促使哈萨克锡喇反叛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乾隆帝对哈萨克锡喇的这防范心理一直存在。早在哈萨克锡喇归降初期,乾隆帝曾下谕称:“至朕以哈萨克锡喇,稍有疑窦者,盖彼系北路之人,如欲投诚,何不即由北路前来,反避走西路,其迹似有可疑。”④《清高宗实录》卷486,乾隆二十年乙亥夏四月庚戌条,第86页。乾隆帝不时提醒定西将军策楞“于哈萨克锡喇、尼玛、吞图布等数人,止宜善为抚驭,使之感激效命,若加以督责,致失众心,则于事更为无益。”⑤《清高宗实录》卷509,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庚寅条,第429页。而在晓谕哈萨克锡喇唐古特诬陷其事时,“仍将晓谕后、哈萨克锡喇言语情形奏闻”⑥《清高宗实录》卷507,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丙辰条,第401页。。可见一直存在着防范心理。而乾隆帝推行:“此次进兵所至之处,台吉宰桑有附从阿逆,宜剿戮者,即行剿戮,宜抚绥者,即行抚绥。所得马匹物件,可充军实者,即分与兵丁以壮军力。”⑦《清高宗实录》卷498,乾隆二十年十月辛亥条,第268页。这些无疑加剧了哈萨克锡喇的恐惧,此亦是促成哈萨克锡喇反叛之原因。
最后,哈萨克锡喇的反叛与一个人有直接关系,即辉特汗巴雅尔。巴雅尔系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一叶克明安的台吉⑧《清高宗实录》卷487,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条,第105页。,且为哈萨克锡喇之同母异父之子⑨《清高宗实录》卷524,乾隆二十一年十月戊寅条,第610页。,清朝分封四部汗时,曾被封为辉特汗①《清高宗实录》卷496,乾隆二十年九月癸未条,第237页。。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兆惠等奏称:“据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等咨称,巴雅尔抢掠洪霍尔拜、扎哈沁等五百余户,杀伤人众,劫夺牲只。”乾隆帝收到消息即做出判断:“巴雅尔原系不可深信之人,今果肆行吞澨,情甚可恶,应即行擒拏治罪。”②《清高宗实录》卷524,乾隆二十一年十月戊寅条,第610页。这种亲缘上的关系使哈萨克锡喇考虑到自己即使不反叛也难免会被牵连。
可见,哈萨克锡喇的反叛是由众多因素所促成的。其中,内部生计维艰是其反叛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因素则是促其反叛的外部条件。
四、结语
起初,哈萨克锡喇作为准噶尔旧十二鄂托克噶勒杂特三宰桑之一,享受属众之贡赋,生活悠哉。归附清朝后,其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从散佚大臣到参赞大臣并晋封公爵,可谓平步青云。不过这些皆为表象,并不是哈萨克锡喇所急需的,此时其所期望的是清朝的大力接济,然而清朝正在进军途中,自身的粮草供给还需从厄鲁特索取,并未有能力对其进行赈济,加之各种因素的作用,最终促使哈萨克锡喇走上反叛之路。
哈萨克锡喇由巴里坤起事后逃向额尔齐斯,再南下和博克萨里至布勒哈齐(今乌苏百泉镇),继而西逃博罗塔拉渡伊犁河至闼勒奇,自萨玛勒河分路南下伊犁,最终可能逃入哈萨克或布鲁特。经过清朝的追剿,其属众千户基本被剿杀殆尽,最终仅以身免,下场可谓甚惨。乾隆帝这种痛加剿洗的政策,是哈萨克锡喇归而复叛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