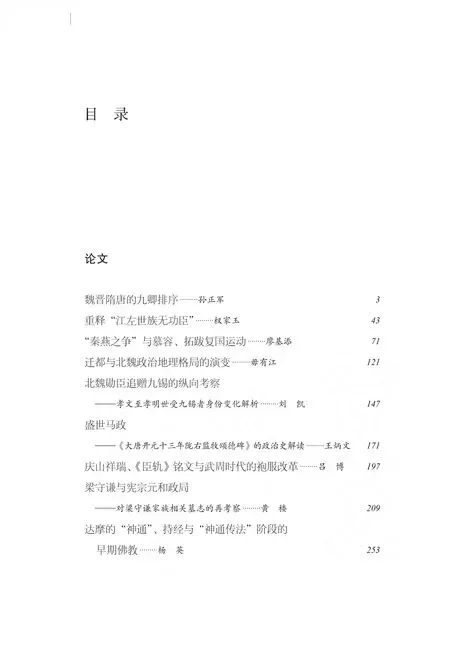《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
本书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部相当厚重的作品。
虽以“造像铭研究”为题,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却是北朝尤其是北朝晚期地域社会中的佛教实践与佛教信仰问题(第6、18 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表述中强调了研究对象为地域社会中的佛教,同时刻意回避了相关研究领域比较常见的“民众佛教”概念。在序论中作者对这一立场进行了说明,提出虽然造像铭所体现出的对佛教的理解往往不及佛教精英在著述中所表现的思想,但是造像团体中却不乏州县僧官及僧传留名的高僧等人物,因此无法简单以低俗的民众佛教来把握(第8—9 页)。相对地,作者以地域社会的概念来描述研究对象,则是希望凸显地方性信仰社团对造像活动以及相关的佛教实践和信仰的重要影响,以及强调这种影响在空间上的受限性。民众佛教之类的概念在佛教史研究中颇有渊源,如北朝佛教史研究的巨擘塚本善隆在研究《提谓波利经》时即使用了“庶民佛教”的概念。[1]〔日〕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载《塚本善隆著作集》第2 卷,大东出版社1974年版,第187—240 页。这类概念强调了一般人生活中的佛教同我们在藏经文献中所见的教团与社会精英笔下的佛教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并且提示前者的研究意义。这在佛教研究史中无疑具有进步意义。长期以来,以此为旗帜也涌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佛教史的理解与认识。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似乎也逐渐显露出来。将佛教区分为精英的(或统治阶级的)佛教与庶民的佛教,在相当程度上预设了两者之间存在本质性的不同甚至对立。因此相关的研究往往不经意间便会强调研究对象与精英佛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但就笔者拙见,当我们讨论信仰、仪式实践等往往为各阶层所共享的内容时,这种倾向便会造成很大的妨害。因此本书另辟蹊径的做法,我想或许可以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此外,造像铭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数量多,且不少出处可考。因此从地域方面加以把握也是比较能够切合研究资料特性的考虑。本书的研究也始终贯彻了这一思路,强调了佛教信仰与实践在地域上的丰富性,以及义邑之类的地域性宗教社团在其中的作用。
在分类整理既往造像铭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本书主要的研究时段为北魏分裂之后到隋代的时期。总体来说,专注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并不多见。佐藤智水先生曾经指出在此一时期出现造像题材多样化的情况,但并未深入分析。美术史方面的研究则已经指出北朝佛像造型方面存在强烈的地域性差异(第16 页)。作者由此提出这一时期造像题材的多样化,与中央的佛教和地方上的信仰混合后产生的信仰、实践的多样化和地域化情势有关,因此地域性正是研究此一时期造像铭研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第17—19 页)。
在研究资料方面,作者从造像实物、图录、拓本(及其照片)、传统金石书以及各种近人著作中所提供的录文等五类资料中,总共收集了造像铭资料近三千件,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关于处理这些资料的方法,作者只是做了非常朴素的说明,主要是强调对造像铭按照地域、年代进行分类再做统计,以及对造像铭语句出处进行细查,并根据地域、时代进行分析(第22 页)。造像铭的研究往往会使用统计的方法,本书的特点则在于以造像铭中固有内容为参数,基于统计结果划分造像铭区域类型的做法。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证性,而且也将行政区划等外在因素对统计分析的干扰限缩在了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所得出的区域划分很有启发性,对于理解北朝时期各地域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有独特的参考意义,可供其他方面的研究者再做进一步的发掘。造像铭文句的细查则似乎是既往研究中比较不注重的方面。其原因可能与“民众佛教”的研究范式有关。然而通过这样的基础工作可能会发现之前研究中未尝注意到的问题,说明这样的工作仍然是研究展开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本书的总体结构包括一个简短的序论、两部共十章的正文以及一个综括性的结论。在全书的最后则附录了一组表格,主要根据邑义头衔的不同,分地域对作者所掌握的北朝有纪年义邑造像铭材料共四百余件的情况进行了罗列,作为本书第一部第二章的延伸,为本书所做的地域性研究提供统计基础。当然,对于有兴趣进行相关研究的读者,这组表格以及书中各章所列的一些其他表格也有重要的资料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书的最后还附上了本书的中文提要,其中对各章节的内容都进行了介绍,便于中国学者参考。
本书正文分为两部。第一部共有三章,主要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造像及义邑相关的地域性问题,是全书研究的基础。第一章讨论义邑的定义、长篇铭文的文体结构和造像的理论基础三个基础性的问题。第二章则是根据义邑的特征进行区域划分,明确各地义邑的特点。第三章关注了关中地区较为特殊的所谓佛道混合造像的问题,由此讨论相关义邑的情况以及区域中佛道二教关系的变化。本书第二部分为七章,主要是结合同时代的敦煌遗书等资料对铭文的思想内容、供养者头衔以及佛名等内容进行分析,说明其与经典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尝试做佛教思想史的考察。这七章又可分为两组:第一到第四章主要是以造像铭中的佛名、菩萨名及神王名为对象,说明其与忏法等佛教实践的关系及其地域分布上的特点。第五到第七章则考察了此一时期流行的观音造像和阿弥陀造像,说明这两类造像勃兴的原因(第22—23 页)。以下笔者将对各章略做评述。
本书第一部第一章是希望从总体上鸟瞰北朝佛教造像铭的基本情况。作者首先讨论了北朝造像铭所见信仰集团的名称及其意义。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义”、“邑”、“邑义”、“法社”等词汇概念。其结论是认为北朝的信仰团体并不能以“义邑”一词完全涵盖,而是有“义”和“义邑”、“法义”等不同名称,情况颇为复杂,并且根据地域不同又有所差别。有些情况下指人和指团体的词汇也会互用。但是总体上,如刘淑芬曾指出的,“邑义”这个名词一般多用来称呼信仰团体的参与者。因此本书中一般也以“义邑”来指宗教集团,而以“邑义”来指涉其中的个人。随后作者以一个比较长篇的北齐造像铭为例尝试分析造像铭的文体结构。作者将这篇造像铭分为九个部分,并对各部详细进行了分析。这种做法有些类似太史文对斋文的分析,是依据学者的意见以及研究目的所做的非常细致的分段,比较有利于作者研究的展开。[1]〔美〕太史文:《试论斋文的表演性》,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307 页。需要说明的是太史文的分段仍然参考了S.2832 等敦煌资料中所见的分段以及郝春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总体上并非以说明时人对斋文文体的分段为目的。然而就笔者来看,如果考虑当时人对造像铭文体的理解,或许还可做不同思考。同样以斋文来做类比,郝春文先生等根据敦煌遗书中所见当时人的分段方法对斋文文体进行整理,便可说是此一类的尝试。[1]郝春文:《敦煌写本斋文及其样式的分类与定名》,《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郝春文:《关于敦煌写本斋文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 期。之所以援引斋文作为例子,是考虑到斋文和造像铭的文体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当然,除斋文之外,疏文、像赞乃至其他类型碑铭等文类也和造像铭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斋文等斋会中使用的文书可能与之具有最强的亲缘关系。如根据P.2940,《斋琬文》中述功德一部即包括了造绣像、镌石、造木金铜佛像、画像等情况下所用的文书。此类文书与造像铭的关系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讨论,不过由此可以了解斋文和造像铭风格上的类似并非偶然。在《广弘明集》等文献中也保存了一些南北朝时期仪式文书的实例,可供比较和分析。如果结合这些资料来讨论造像铭的文体问题,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时人对这种文体的认识,而这种理解本身也不啻为造像铭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章最后作者讨论了造像和感应思想的关系。关于南北朝佛教中的感应思想,近来已有船山彻和菅野博史进行过讨论。作者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造像作为感应媒介的作用与其流行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对侯旭东先生以“成佛像身观”作为民众造像思想基础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第二章以作者收集到的北朝造像铭中四百余件有纪年的义邑造像材料为中心,对北朝造像铭进行了区域的划分,并对各地区不同时代造像铭的特色进行了分析。本章对造像铭进行分组的主要依据是造像铭中义邑成员的头衔。具体的做法是先区分出一般会员称邑子、邑生、邑义、邑人、母人、法义,主导僧人称王主比丘等的类型,再按照其他人员的头衔以及地域关系进行分组,最后再将各个组别中的造像铭依据时代做细分。在分析过程中,作者非常关注各种称号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例如邑师集中出现在龙门石窟和陕西地域,其他地方较少见,甚至山东、河北根本找不到有此类名称的造像铭。对于同样的头衔,作者也仔细鉴别其实际的地位,如在对“像主”一词的讨论中,作者提出存在以亡人为像主的例子,说明像主并不一定是指出钱最多的人,有时也可指功德回向对象。总体而言,本章分析方法的特点在于以造像铭本身的内容为主要依据,可说是特别针对造像铭而做的历史地理研究。一方面,本章的研究成果为后文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本章中基于造像铭资料所描绘的地域关系图景对于北朝史尤其北朝佛教史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会成为将来讨论北朝地域和地缘关系问题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
第三章所讨论的是关中佛道二教造像及相关义邑的问题。所谓二教造像碑,由于涉及佛道两教关系的议题,因此是学界长期关注的对象。关于这些造像碑所体现的对于佛道二教关系的理解,有着颇为不同的观点存在(第173—175 页)。本章提出应根据造像的具体情况,将这些混有佛道内容的造像碑分为佛道像(以佛教为主)、道佛像(以道教为主)两种类型。从时代上说,关中地区北魏、西魏造像以道主佛次的道佛像为多,北周以下则以佛道像为多。对于二教造像,最令人感兴趣的恐怕就是这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有怎样的宗教身份认同,以及如何理解二教关系的问题。柏夷先生尝就这一问题做过研究,提出这些造像是基于以道教为基础、融摄佛教的构想而产生的。对于这一观点,作者提出二教造像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很难完全以道教经典存在的这种思想来解释。但另一方面,他又认同这种解释对北魏、西魏时期的二教造像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北周以下情况出现了反转,佛道像和佛像的数量大大增加,道佛像和道像则有所减少,似乎出现了以佛教来包摄道教的意图。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可能与信仰佛教的氐、羌族地位的上升有关。同时,他还提出为了因应这一变局,道教方面的传教方针或许也有所变化。可惜的是现阶段我们对北朝道教史的研究仍非常不足,似乎尚无法细化到能够充分说明北魏与西魏更替时期道教教理或教团是否存在变化的程度。因此这一问题有待将来再做讨论。本章的研究中,作者提出将二教造像碑简单认为是基层社会佛道不分的信仰状况的表现是过于简化的理解。笔者对这一观点也非常认同。很多情况下,当佛道的要素共同出现时,研究者会简单套用佛道混淆或基层社会信仰特点等观念来进行解释,不免有些过于草率。这或许是将来佛道关系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克服的倾向。
本书第二部以“造像铭和佛教经典”为题,主要是希望探讨造像铭的思想内容。北朝佛教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于文献资料相对匮乏而造像铭等考古资料则相对充足。然而造像铭总体来说是制式化的写作,因此如何将其活用到佛教研究的领域便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本书中作者将造像铭与经典结合,就北朝晚期净土教的变革等佛教学界关心的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在方法上也会给从事北朝佛教史研究的同仁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第二部的第一章讨论了北朝时代的多佛名石刻。之前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曾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对笔者的研究也有颇多启发。南北朝时期佛名类典籍的翻译和撰作都非常繁盛,这一点与礼忏仪式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到唐初则出现了以十二卷《佛名经》为基础的各种《大佛名经》的改编本,对日本的佛教礼仪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些佛名类典籍,之前曾有井ノ口泰淳、盐入良道、郭丽英等前辈学者做过研究。近年来汪娟、山口正晃以及笔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1]关于佛名类典籍的研究情况可参看拙文:《南北朝佛名类抄经研究——以其与礼忏的关系为中心》,《佛教文献研究》(待刊)。但是这些讨论主要是以佛名类典籍文本(尤其敦煌遗书中的抄本)为对象,对于石刻中的佛名则较少注意。作者的研究正可弥补这一不足。尤其石刻资料往往有明确的时、地信息,有助于了解佛名类典籍、佛名组合的产生与盛行的时代及其在地域上的流布,提供文献资料难以揭示的信息。
本章首先分类讨论了各种佛名信仰的基本情况,以及七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千佛、十方佛、十六王子佛等佛名组的经典依据、文献记录和造像情况。其中所讨论的佛名组都是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要的佛名类型,分类加以条贯确实颇有必要。不过对于十方佛的介绍似乎稍有不足。与七佛、三十五佛等佛名组的情况不同,十方佛的形态非常多样,从十方十佛到百七十佛、千五百佛,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即使是在十方十佛这一类中,又包括了出自不同经典的多种佛名组可供选择,因此似乎有必要更细致地加以梳理。本章的第二节是以个别具有代表性的造像铭为线索讨论多佛名石刻的情况。使用的资料包括了最早明确的多佛名题记的炳灵寺169 窟中的千佛和十方佛、可能是最早使用五十三佛加三十五佛组合的云冈石窟第11 窟太和七年(483)造像、最早提及千五百佛的水泉石窟太和十三年(489)造像题记、有复杂佛名内容的嵩阳寺碑、佛名来源颇为古怪但似乎和《金光明经·功德天品》有密切关系的务圣寺碑、和伪经《大通方广经》有密切关系的陈海龙造像碑等共11 种/组佛名石刻,最后则专列一类,介绍前述事例之外值得注意的有多佛内容的造像。在上述整理的基础上,作者对多佛名题刻的一些特色做了归纳,提出多佛名题刻在地域上以今山西、河南省为多,在时代上则以东西魏分裂以后为多。佛名的选择方面虽然并无定准,但以七佛、无量寿佛以及十六王子佛等广义上的十方佛为多。与特定经典有关的多佛名题刻则往往与实践性强烈的《大通方广经》等经典有关,显示了造像活动与仪式实践之间的相关性。
总体上说,本章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北方佛名信仰兴起和流传的重要信息,值得重视。然而佛名信仰以及相关的实践并非北朝佛教独有的内容。同一时期南方也流行此类忏仪,并且有相关经典的编撰实例,如《大通方广经》就是在荆襄地区编撰,萧子良也曾主持十卷本佛名集的编撰,而这些内容对北朝佛教也曾有所影响。因此若能结合南朝佛名信仰的发展来讨论,或许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此外作者对于佛名和礼忏的关系颇为关注,但南北朝时期礼忏仪式本身也有很大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礼忏仪式中,佛名内容的重要性以及使用方法又有所不同。因此在讨论佛名内容的出现与流行过程时,似乎有必要将礼忏仪式本身的变化也纳入考虑之中。
第二章以十二梦王石刻图像为中心,讨论北朝时代的方等忏和称名信仰的问题。《大方等陀罗尼经》在南北朝时代是非常重要的经典,和实践的结合尤其紧密。以此经为根据衍生出的方等忏后来还被列入天台四种三昧之中,是天台佛教的重要行法之一。由于方等忏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于梦相的体验,因此智顗还将其作为取相忏的代表。从文献和石刻资料都可以看到在北魏时期方等忏实践的例子,而本章主要着眼点正在于方等忏中的神秘体验,主要资料则是保存有十二梦王和十法王子图像的石刻资料。在第五节中作者还讨论了敦煌本《大方等陀罗尼经》的情况。一方面,作者注意到现存的敦煌本大多写于6世纪初期,而此后同样和忏悔仪式有关的《大通方广经》似乎更加流行。另一方面,作者对敦煌写本中插入的仪式内容进行了录文和讨论,并强调了其中偈颂提到的面睹诸佛菩萨的内容与方等忏的神秘体验有关。在结论部分,作者强调了《大方等陀罗尼经》与《大通方广经》等经典的流行表现了称名和忏悔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同时,方等忏相关石刻的出现也说明有专注于专门性的忏法的义邑组织,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作者结合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提出山西东南部似乎存在特别重视方等忏的神秘体验的风气。
第三章作者讨论了南北朝时代《大通方广经》的撰作与流布及其忏悔思想的问题。和前章所讨论的《大方等陀罗尼经》相似,《大通方广经》是在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的一部与礼忏仪式有密切关系的经典。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大通方广经》抄本。在文献中则可以看到南朝皇家修设方广忏的实例以及日本宫廷中举行方广忏会的记录。甚至此经还被翻译成藏文,并在藏文藏经中保存至今。本章首先对《续高僧传》中“梁初方广,源在荆襄”等内容做了辨析,说明其中“方广”当即是指《大通方广经》,而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方广经》撰作情况的重要记录。这一点笔者也赞同。随后作者对与此经有关的三种石刻材料进行了说明,并主要对其中的陈海龙造像碑进行了分析,说明造此碑的比丘尼法藏所主持的义邑当举行过方广忏,并根据其仪式手册做了这个造像碑。随后作者又对阿纯章曾经讨论过的敦煌遗书S.4494 号中的方广忏法残文与经文的关系做了一些考论,并结合《净住子》、萧纲《唱导文》和《慈悲道场忏法》中礼敬三宝的内容,说明南朝礼忏中普遍存在列记三宝名号进行礼拜的做法。不过此处的讨论或许有一些暧昧之处。笔者之前曾经撰文研究过《净住子》的仪式问题,注意到在南朝礼忏中流行别礼住持三宝的做法。《净住子》中对应段落即礼舍利宝塔门、敬重正法门和奉养僧田门三门。萧纲《唱导文》末三段也正是礼此住持三宝的三门。[1]曹凌:《〈净住子净行法门〉的仪式研究——以道宣〈统略法门〉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 期。南朝礼忏中出现这种做法的原因不详,但很可能与感应思想以及关于住持三宝的灵验故事的流传有关。无论如何,这类有别礼住持三宝节次的礼忏仪中的佛名内容并不直接与经典、菩萨相连接。而《大通方广经》是顺次罗列佛名、经典和菩萨(僧),其中并无对塔像的礼敬,显示出与前述资料不同的取向,而与伪《大佛名经》对礼忏仪式的规划更为相似。因此简单将《大通方广经》中礼三宝的内容与前述资料中礼拜三宝的内容进行类比,统称为三宝名号的礼拜,似乎失之过简。将来如果可能,似乎有必要结合南北朝礼忏仪式的演化对其中的不同类型及其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讨论。随后作者又对《大通方广经》的思想依据进行了讨论,通过对文字内容的细查确定了它与《涅槃经》有密切的关系,并有强调一阐提救济的内容。这是之前《大通方广经》研究中并未注意到的内容,颇值得重视。笔者之前曾经讨论过昙静《提谓经》中的仪式内容,并注意到其中忏悔文与竺法护所译《舍利弗悔过经》有密切关系。[2]曹凌:《东晋到南北朝初的佛教忏法》,载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4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184 页。将这两部与仪式有关的伪经进行比较,也可发现一些地域上或时代上的差异,提示了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礼忏仪式在所依经典方面的多样性。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阳阿故县村造像记及其所体现的北朝《菩萨璎珞本业经》的实践问题。《菩萨璎珞本业经》中关于菩萨修行阶位、菩萨戒等问题的论述对后代影响很大,因此与本经有关的研究持续有所推进。自望月信亨以来,本经普遍被认为是中土所撰,船山彻更是将其撰作的时间推定到480 到500年的短短二十年间,因此此经可说是情况较为清楚的一部经典(第379 页)。作者首先对本经的研究史以及基本情况进行了说明,再对阳阿故县村造像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考定其原址以及供养者的构成,并特意说明了其与净影寺慧远的教学存在关联的可能性。随后,作者提出造像记中的内容与《菩萨璎珞本业经》中贤圣阶位及观法内容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并列表做了比较,充分说明了此造像记是以《菩萨璎珞本业经》为基础造作的。虽然如此,造像记又和经典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作者也做了说明和分析。随后作者又对北朝造像中与轮王有关的内容以及此则造像记和菩萨戒受戒仪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轮王是近年来颇受学界瞩目的一个问题,作者对北魏佛教造像中相关的内容进行收罗和整理,并提示《菩萨璎珞本业经》中轮王内容表现了祈求出现以佛法救济世间的理想国王的愿望(第401 页)。这无疑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关于菩萨戒的问题,由于《菩萨璎珞本业经》本身和菩萨戒关系非常紧密,因此作者认为造像记中提到的设斋事可能就是授受菩萨戒时所做的斋会。可惜的是造像记并未提及仪式的具体内容,因此要加以确证似乎仍有一定困难。不过正如船山彻以及作者所提示,造像、礼忏以及菩萨戒等相关仪式的关系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五章以《高王观世音经》的成立和观音像为题,主要讨论了《高王观世音经》的撰作与高氏政权在河北地方的经营之间的关系,并就此经的撰作提出了自己的假说。《高王观世音经》由于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而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也是学界长期以来特别关心的伪经之一,此前已经有不少前贤做过专题的研究。其中,桐谷先生曾经提出《续高僧传》中孙敬德诵经的灵验故事是出自道宣之手[1]〔日〕桐谷征一:《偽經〈高王觀世音經〉のテキスト之信仰》,《法华文化研究》第16卷,第1—67 页。,作者对此并不认同。作者首先探讨了“高王”这一名称在北齐时的意义,强调在高欢在世时,“高王”这一名称已经被用于和佛教关系密切的场合,因此《高王观世音经》经题中的“高王”当确指高欢。随后,作者重新梳理了北朝隋唐相关灵验故事的资料,提出《续高僧传》中这则故事的出典《齐志》很可能是指王劭的《齐志》,并非来源暧昧的内容。而正史转引此则故事时可能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节略,导致相关记录并不完全相同。此外,北朝时期造观音像的活动往往和生人现实的利益有关,表达治疗疾病或平安等愿望。因此孙敬德为求兵役平安归来造观音像的做法也符合当时观音造像的基本情况。次节中作者以河南省五岩山南麓所见造像和铭文破题,围绕高氏掌权时期观音像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五岩山南麓原有名为高王寺的寺院,且存在高王寺寺主及大檀越尔朱姤在兴和元年(539)所造的以坐姿观音为主尊的石窟。这一极为罕见的造像同样是将高王和观世音连接起来,令人浮想联翩。作者的解释是认为迁都之后掌握实权的高欢在僧人们的建议下利用河北地方流行的观音信仰,将自己比附为观音的化身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其具体作为包括在冠自己名字的高王寺建造观音像,以及利用孙敬德的灵验故事推广冠有自己名字的《高王观世音经》。与之可相印证的是,在东魏、高齐时代观音像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尤其为皇帝祈愿的观音像增加非常多。虽然现阶段这一观点似乎仍只能作为假说,但确实有相当的证据基础,对于中古政教关系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本章的最后,作者利用相关的石刻对《高王观世音经》的原始文本以及文本发展的过程做了讨论,大体的结果是认为本经以《救苦观世音经》为基础,加以灭罪功德、般若经中的咒文以及《大方等无想经》等处的佛名,最后再加入《除恐灾患经》中强调现实利益功德的偈颂,而构成了具有巨大功德的用来诵读的短小经典。入唐之后,此经又被加入一系列的内容,形成了更广的文本。
第六章是以《观世音十大愿经》为中心,讨论观世音久远以来既已成佛的“观世音佛”信仰。作者首先介绍了南北朝时期流传的有观世音成佛说内容的四部经典(包括两部伪经),并说明伪经《观世音十大愿经》(《弘猛慧海经》)特别强调了观世音和阎浮提的关系,为观世音的现世救济功能提供根据。随后作者对敦煌遗书和佛教造像中与观世音以及观世音十大愿有关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和观世音有关者包括敦煌遗书中的S.795《观世音佛名》写卷,以及山东省博物馆藏《十方千五百佛名经》写卷题记,造像则包括了5世纪末到6世纪中晚期的造像和摩崖佛名共十二件。和观世音十大愿有关的石刻则有涉县木井寺武平四年(573)刻经碑以及曲阳八会寺刻经龛两件。在结论的部分,作者提出,从敦煌遗书和石刻来看,观世音成佛说在南北朝时期流传颇为广泛,而《观世音三昧经》与《观世音十大愿经》这两部伪经在这种信仰的流传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观世音十大愿经》强调了观音在阎浮提发下誓愿,成佛之后要拯济称名者,最直接地提出了观音与我们所处世界的关系。而《观世音十大愿经》相关石刻的配置则是将观世音作为佛陀灭度后本世界中的救济者。这种思想即是观世音佛信仰的核心内容。
第七章以造像铭内容与《观无量寿经》的关系为中心,讨论了北朝、隋代造像铭中所见生天、净土信仰的变化问题,尝试说明此一时期造像铭中西方净土教主的名号从“无量寿”变为“阿弥陀”的原因。以造像铭来研究净土思想的变化是塚本善隆所开创的研究路径。尤其塚本善隆所提出的佛名由无量寿佛向阿弥陀佛演变的问题,始终是相关研究中核心的问题之一。最近石川琢道和斋藤隆信等学者也有新的研究发表,尤其斋藤氏提出根据僧传文献和金石资料可以以6世纪中叶为界将净土教分为两个时期,而这一转变的基础在于6世纪中叶以《观无量寿经》重整净土教理与实践的工作。作者则通过细读造像铭中的相关内容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假说。
首先,作者分析了北朝到隋代造像铭中和生天及净土信仰有关的定型句,印证了侯旭东先生所提出的529年之前以生天的信仰较为流行、此后则以净土思想较为流行的结论,并补充了更具体的用语变化实例来说明从生天思想向净土信仰转化的过程。随后作者分析了有无量寿和阿弥陀两种尊名的有纪年造像铭,提出从无量寿到阿弥陀的变化发生在北齐后半到隋代,在地域上则以河北地区为中心。而邺城周边新出土造像中的禅定图像,以及以僧稠禅师的思想为指导造作的小南海石窟中与《观无量寿经》有关图像内容的出现,则提示了僧稠一系的禅师不仅有西方净土的信仰,并且是以《观无量寿经》为净土实践的核心。由此作者提出北齐时代阿弥陀造像在河北地方的兴起缘于与昙鸾系统有别的以《观无量寿经》为主要思想依据的僧稠——智舜系禅师们在太行山脉周边的活动。尊名的变化以及新净土信仰的普及是这些禅师的实践传教活动的结果。就笔者所见,之前的净土研究中似乎并未强调僧稠一系的僧人以及禅师群体在净土实践以及教理发展方面的作用。然而这一群体在北齐时代确实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尤其僧稠在北齐地位更是非同一般。禅僧以禅修作为最主要实践内容,《观无量寿经》的重要特点之一则在于强调观佛的禅定实践,而相关的实践又需要以佛像作为观想的对境,因此与《观无量寿经》有关的净土题材造像的涌现似乎正可由禅师们的活跃得到解释。在地域上,可以看到北齐时代新型造像铭的分布也正与禅师们的活动区域有很大的重合性。因此这一群体在净土思想方面的意义很可能被长期忽略了。这一假说的提出引申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地论宗思想与净土思想的关系,僧稠系的禅法与净土实践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关注的问题。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先顺次整理了各章的基本情况与结论,接着回到本书的主题,尝试归纳东西魏分裂以后到隋代,地域社会中的佛教信仰与实践以及造像活动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包括:造像尊格的多样化、有地域特色的义邑造像活动的全盛、通过活用伪经在地域社会普及佛教实践、佛名信仰的兴起、基于伪经宣扬观音信仰、阿弥陀造像的兴起、教学与实践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最后,作者回到塚本善隆根据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所提出的重要论断,即云冈石窟代表了以“印度的悉达太子是如何成佛的”为中心问题的佛教,龙门的北魏石窟代表了以“印度的佛说了什么”为中心问题的佛教,龙门的唐代石窟代表了以“我们中国人如何得救”为中心问题的中国人的佛教。在对这一线索表示认同的同时,作者提出本书的研究说明东魏、北齐的时代,“我们中国人如何得救”的问题已经成为北朝佛教的基本问题。正是为了响应这一根本问题,各地域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索和实践。到了隋代,这些地方性的实践又被汇聚到了统一帝国的中心——长安(第543—544页)。这一简短的结论显示了本书非常细致的研究背后作者对于中国佛教发展历程的深入思考。其对塚本善隆先生观点的修正不仅是将第三阶段的时代提前而已,更是尝试说明其如何通过地域性的“试验性的”实践得以丰富,并最终汇聚起来的过程。
本书以造像铭为主要资料,故长于地域性的分析,却也受到资料的限制,无法更深入地分析教义教理的发展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本书仍然不失为一部尝试在北朝佛教史领域寻求突破的重要著作,展现了北朝佛教史研究的新的可能,对于将来的北朝乃至隋唐佛教史研究应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外,作者将造像铭资料活用于佛教史研究领域的方法与视角也令笔者印象深刻。本书的作者通过个案研究、地域分析以及文献对读等多层次的分析,尝试发掘出造像铭在佛教史研究中的意义,提出了许多新颖有趣的观点,展现了造像铭资料对于佛教史研究的贡献。在论述中,作者还多次强调将相关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佛教思想研究——尤其和相关时代及地域关系至为紧密的地论宗研究——领域的可能性,这些内容将会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