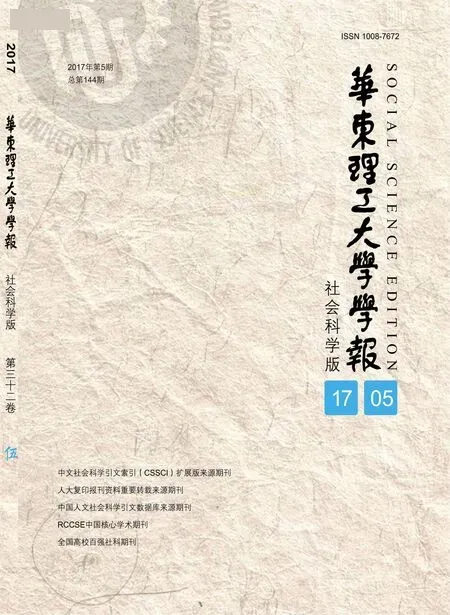社会工作教师社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兼对教师“领办机构”的反思
林诚彦
社会工作教师社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兼对教师“领办机构”的反思
林诚彦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广东广州 510642)
通过对某高校社工系专业教师的访谈,提出了在专业早期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教师的认同经历了从职业认同、专业认同到集体认同的三个阶段。认同发展解释了社会工作教师在面临外在制度环境约束时,如何建构其行动策略的主动性。讨论认为在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三化进程中,实务参与过程推动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形成,集体认同推动社会工作教师领办机构。因此,社会工作三化政策制定不仅应重视对从业者群体的利益驱动,还应注重将社会工作从业者们“组织起来”、实现集体认同的建构。
社会认同 社会工作 专业认同 职业认同 集体认同
社会工作作为西方舶来品,其赖以发展的本土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尚未臻完善。环境制约也导致了从业者高流失率以及专业“内卷化”问题,即社会工作本应作为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工具,最终反被现有制度结构所同化。因此,如何激发社会工作从业者①狭义的“社会工作者”应当是同时满足四项条件:(1)经历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2)具备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照;(3)在各类社会服务机构中任职;(4)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显然很难。因此,使用“社会工作从业者”更能表达该群体的身份特征:边界模糊不清、群体内部差异大、存在各类型子群体。在环境制约下的道德自觉、专业自主成为关键。高校社会工作教师(下文简称“社工教师”)无疑是广义“社会工作从业者”群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群体,无论是从“教育先行”的本土社会工作发展战略,还是对2012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中“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等文件的解读,社工教师都被期许能在实务推动、机构创办、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等多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发挥引领作用。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伊始的第一批社工教师,他们几乎是在内部专业知能不足、外部环境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他们是如何形成自身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感,从而能在不利环境中保持自主能动性的,了解这一点对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极具裨益的。
本文试图以对参与创办H大学社会工作系的社工教师工作历程的访谈,以泰弗尔及温特的认同理论为解释框架,理解社工教师从入行到领办机构整个职业发展阶段中社会认同的发展及建构过程,并借助认同为中介变量理解环境制约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关系,即认同形成如何受环境(如制度、资源、认知度等)的影响,以及面对不利情境时个体如何通过认同建构自主能动地突破环境限制。
一、文献回顾:社会认同作为分析框架
“认同”(Identity) 又可译为“身份”、“同一性”,指主体对自身身份的解读、反思,“直接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①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认同研究在各学科中的兴起、流行,一则与“现代性的后果”密切相关,即学者们在社会日益原子化、个体化的进程中,对个体和共同体之关系的反思。二则与社会理论遭遇结构-行动、宏观-微观的对立有关,“认同”成为了研究者用于超越二元对立的重要概念。泰弗尔(Tajfel)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②豪格、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与其对应的概念则是“性质上更加个人的、通常标示个人具体特征的”个人认同,而个体的自我认同(自我概念)则是包含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两种成分的连续统。自我认同与个体行动、集体行动的密切关联,令社会认同成为解释个体和环境互动的重要框架,一方面特定的社会认同形成既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又对个体行动策略形成制约,限制了个体行动的可能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认同和自尊密切关联,因此个体亦会出于维护自尊、降低认同威胁的动机,主动地通过“范畴化”、“社会比较”等方式形成特定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理论从个体层面入手,将认同建构过程作为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的衔接面,强调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构过程,既肯定了结构的制约作用,又为个体行动的差异性、不确定性留出了空间。Kreiner等学者基于情境-个体的关系视角对个体多重认同或认同危机的论述,亦充分说明了结构-行动之间的互构关系。③④Kreiner G E.The Struggle of the Self:Identity Disfunc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kplac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Dysfunctional Workplace.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7,PP.75-89.因此在当前社会工作发展背景下,以社会认同作为分析概念研究社工教师的自主性发展是极具意义的。社会认同可被视为在外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促进社会工作从业者成长和发展的内驱动力,被视为在不利环境下稳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关键因素,甚至是社会工作者用以克服现有制度结构制约,反向推动国家社会治理转型的力量源泉。
社会工作者的认同获得/建构一直是国外学界的研究热点,例如社会支持、⑤Wu C,Pooler D.“Social Workers'Caregiver Identity and Distress: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Social Work Research,2014,PP.237-249正式教育、⑥⑦Miller,S.E.“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of Social Workers”,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Vol.20,No.7,2010,PP.924-938.职业场域⑧⑨Coffey,M.,Dugdill,L.,amp;Tattersall,A.“Wor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A Case Study of Social Services”,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9,2009,PP.420-442.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认同生成或导致认同危机,⑩Green,D.amp;Mc Dermott,F.“Social Work from Inside and between Complex Systems:Perspectives on Person-inenvironment for Today’s Social Work”,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40,No.8,2010,PP.2414-2430.以及社工如何主动通过认同构建进行抗争。①②Glaser,G.“Reflections of a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Bridging the 19th and 21st Centuries”.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Vol.11,No.2,2001,PP.190-200.虽然研究着力点各异,但其共性假设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认同作为多维、多义的学术概念,其具体内容是因时间、背景而改变的。第二,必须在关系视角中把握认同的动态生成过程,社工对于跨专业合作关系、工作-家庭关系甚至是国家-社会-市场之间关系的解读都会影响到认同构建的结果。
回顾近5年国内相关研究,对社工教师群体乃至社会工作从业者群体的社会认同研究极少。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准社会工作者群体——社工学生,而且对“认同”作为学术名词的内涵尚存在很多混淆、模糊之处。例如有的文献中所指“专业认同”、“职业认同”、“社会认同”真实含义为“外界对社会工作的认知、认可、承认”,而非其作为“归属身份”的学术含义,也有学者将从业者对社会工作学科知识体系(价值伦理、理论和实务、学科特殊性)的认可角度视为专业认同,③慈勤英:《专业认同: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体系的建构》,《社会工作》2013年第6期。也显然忽略了认同作为身份归属的社会性面向,以及认同与个体情绪、行动激励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一些文献在上下文中出现截然相反“认同”含义的情况。在为数不多的从业者身份认同研究中,主要是借鉴相关行业的认同模型,基于测量学理论探索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现状、结构。④安秋玲:《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王惠卿:《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结构与测量》,《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杨旭华、杨瑞:《专业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结构与分析——以北京市为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过往研究最为忽略的一点在于:社会工作从业者社会认同的多元结构和建构过程。过往研究大多以职业认同(或称专业认同)指代社会认同,假定了社会认同结构的单调性、稳定性。社会工作行业尚未完成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进程,行业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的内涵、角色、使命依旧要被摆出来讨论,构成社会认同的成分始终是在一种不确定性中,因此社会工作从业者的社会认同获得过程更应该给予重视。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社会认同的多重性、多元性,身份应当是复数形式(identities)而非单数形式(identity),尤其应意识到认同不仅分为情感、承诺、认知、行动等多种成分,还包括不同的类型: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ty)、专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 职 业 认 同(occupational identity),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甚至高专业认同和低环境认知之间的冲突,比低专业认同更有可能解释社会工作人才的流失现象。⑤林诚彦、张兴杰、曾细花:《专业认同影响从业意愿路径的实证分析——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例》,《高教探索》2013年第3期。这意味着社会工作从业者的认同结构和建构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二、案例分析:社工教师的认同发展进程
H大学社会工作系成立于1999年,其成立带有很强的偶然性,由于其前身“社会主义建设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因此所在学院决定向教育部申办社会学专业,但最后获批复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学院对该专业未曾听闻,专业办学更是毫无头绪。而且当时国内尚未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博硕士点,因此学院领导只能逐年引进人口学、社会学的博硕士毕业生,并从其他部门(思政部、哲学系)调入教师以补充师资不足。1999年合计学生81人,教师5人。其后每年该系师资皆有流出和引入,至2005年师资队伍已发展至10人,在校生(2002级至2005级)合计674人。同年学院另外成立社会学系,其中部分社工专业教师以自身不太适应社会工作教学或对社会学研究更有热情为原因,自主选择调动到社会学系,大部分教师选择留在社工专业。2007年,社工系开始和某省民政厅展开实务项目合作。2008年,社工系几位“创系元老”共同创立某社会工作机构,开始承接政府购买项目,或以政府专家身份参与实务评估。本研究选择该校社工系四名教师进行访谈,其中两名教师(Z、Q)是 1999年“创系元老”,Y老师是2000年加入的,F老师则是2005年加入社工系,现担任系主任一职。四位教师不仅都亲历了从专业萌芽到其后创立机构、参与实务的全过程,而且积极参与推动当地的社工教育、实务发展,在所在区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笔者选择这四位教师作为个案,除了方便调查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该校社工系的十七年发展历程相对成熟、具备较强代表性,无论是其专业办学发展还是教师个人发展,皆可为全国其他高校社工院系提供经验借鉴。
笔者首先邀请受访教师分别讲述从入职至今所经历的各种生命事件,他们在彼时彼地的心路历程、态度看法,以及此时此地对过去历程的再诠释。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梳理,提出社工教师从入行到成熟的发展阶段,其社会认同所对应的“内群体(归属群体)”、“外群体(参照群体)”经过多次变化,本文据此将社会认同界定为职业认同、专业认同、集体认同三种类型。不同认同类型能较好解释制度环境制约性与社工教师自主性之间的互构关系,即在不同认同类型中,推动其认同建构的外部因素以及所带来的相应行动策略也有所差别。
(一)职业认同作为入行、学习的初始动机
首批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兴办,并非研究领域成熟或研究队伍壮大带来的自然结果,而是新兴学科、新办院系在教育市场化大潮下为学校寻求办学突破口、获得生存空间的理性行为。1999年至2005年,最早一批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设置以来,从事社会工作的教师多数是跨专业进入的。在访谈中四名教师都认为自己投身社会工作专业充满了偶然性,主观上出于对高校教师身份的认同,客观上是教育产业化背景为高校新办专业提供了机会,从而懵懵懂懂地迈进了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自发,他们“被赋予”了高校社工教师身份。哲学背景的Z老师是1999年的创系元老,她回忆说:“我原来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学院要办新的社会工作专业,院长就说要我转过来,我就转过来了。当时我都不知道社会工作是啥,社工导论我都不知道怎么上。”
也有教师在进入社会工作专业前思考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质,但几乎都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社会学专业出身的Y老师于2000年加入社工专业教师队伍,她说:“当时社会学专业毕业时家人和我都希望在高校找工作,但是当时导师说整个广东社会学系都很少,说要不你就去H大学,他们有个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学也挺近的。这样就给我写了封推荐信,我就过来这面试了。”人口学背景的Q老师于1999年加入社工专业教师队伍,她说:“出于家庭的一些原因,对心理学、社会学的东西比较喜欢。正好H大学也找不到社会工作老师,去我们学校要人,于是就去面试了。”
在这个阶段,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尚属一片空白,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根本无从谈起。四位教师对自身的身份归属实质上是“高校教师”,高校教师的职业形象、工作规范成为指导其行为选择的关键要素。Z老师是基于高校教师“服从学校安排”的职业规范作出转专业决定,而F、Y、Q三位老师纯粹是受“高校教师”身份吸引,社会工作专业与个人志趣的吻合度几乎没有被考虑过。因此,教师“选择”社会工作专业,与其说是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认同,不如说是对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
认同生成的第一步就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即通过和参照群体的社会比较将内群体的积极特性凸显出来。范畴化包括社会范畴化和自我范畴化,前者是指我们对其他物品、他人的范畴化,后者是指对自身的范畴化,个体主动靠近和吻合群体原型(prototype)的定义性特征,并再现出来。①豪格、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职业认同不仅令教师做出了职业选择,还推动他们进行自我范畴化,主动积极地吻合“高校教师”群体的身份要求。“当时我们也主动参加各种培训,都是那种速成式的课程……不过知识归知识,没什么实务。后来我们学校联系上了香港的师资,也请他们来给我们的学生带课,我们全部老师就一边跟着听。”(Q、Y老师)
和外界环境的互动则给予了个体调整群体参照的机会,随着该校开展与发达地区同行的业务交流活动(学校师生前往香港见习、香港同行参与学校实习督导),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逐渐从其他学科背景中被勾勒凸显出来,社工教师的“独特形象”也从中浮现。“当时带学生去香港见习一个星期,虽然当时我听不懂粤语,但会去观察。比如看到屋村下面的架空层都是社会服务机构,还去到老人院看那些老人服务,就感觉到他们做的真得不仅仅是心理辅导的东西,而且那种价值理念渗透在服务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场地设置、桌椅摆放。”(F老师)
社工教师都把香港社工视为自身学习、专业发展的榜样。他们主动选择香港社工形象作为自身归属群体的原型,对于自我形象提升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这个认同建构进程受初期的职业认同驱动,但又与职业认同有差别:其选择的内群体原型是“香港专业同行”,而且逐渐把自己从“高校教师”大群体范畴中凸显(并不意味着分离)出来,在此不妨将这种新发展出来的、萌芽状态的认同类型称为专业认同。
从认同建构的范畴化进程来讲,这是环境压力、专业价值的“推拉”作用共同导致。首先是环境的“推力”。对于社会工作这个新兴专业而言,由于多数教师都从社会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专业转型,进入社会工作专业并承担起教学育人之职责,不仅自身对学科缺乏理解,而且学科资源和学校支持往往显得不足。“社会群体承受着一定的驱动力和压力,它们使一个社会群体将自身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而不是寻找彼此间的共同性”。①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在这个过程中,社工教师为维护内群体生存的需要,通过多种策略主动构建出区分于其他高校教师的专业群体形象。其次是专业的“拉力”。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建构社会认同时,会主观能动地选择及界定其归属群体原型,但核心目标都是为了塑造附属群体成员的积极社会认同从而提升其自我形象。①发达地区(香港)作为现代化、文明进步的符号象征,在其中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专业形象,以及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受广大市民的高度认可,无疑给对社会工作充满迷惑和怀疑的教师们树立了信心,也为他们动力不足、方向模糊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参照。
总的来看,在社工教师的早期专业进入、发展历程中,自主能动地选择内群体参照、积极回应环境挑战的认同建构过程得以体现。但这种自主更像是无可奈何的自主,是在资源、制度不足的情况下对自身专业知能的主动拓展。主要体现在对专业教师身份的主动构建上,虽然学校聘任给予了他们“高校教师”的先赋身份,相应的制度、资源并不足以支撑“独特专业形象”的形成,但他们主动从高校教师中凸显出“社工教师”的后致身份。因此,他们从对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起步,自发构建了对社会工作的初步的专业认同。另一方面,这种专业形象是根据教科书知识、发达地区经验等外在于教师个人经验的权威观点而构建的,即其后致身份依然是在结构框架中被形塑。
但对于其后发展而言,对香港社工形象的专业认同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教师、学生带来了信心和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自身能力与“香港形象”之间的“名不副实”也导致了学生的质疑,反过来也令他们产生自我怀疑。Y老师说:“一方面是和香港社工的接触,就觉得他们非常得好。另一方面就是从书本上讲,社工就是表里如一的、真诚的、不批判的、全然接受别人的、追求社会公正的,这样就给我一种道德压力的感觉。所以,当时对社工的理解是相当神圣的,是有道德光环的,感觉社工就是一个圣人……由于我们灌输给学生的也是这样,于是学生就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老师,这给老师很大压力。”Q老师说:“学生跟我们说,一看到香港社工,就有社工的感觉。她说我们的老师没有……所以我们压力也很大。”
学生的质疑何以对教师带来如此大的心理冲击?有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是学生作为重要他者对教师社会认同建构的影响。认同建构过程不仅强调归属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还强调外群体中重要他者的认可。社工教师的早期实践场域由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等构成,其中教学是比重最大的实践内容,师生关系因此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学生群体就成为了社工教师的“重要他者”,学生群体对于社工教师形象的承认就显得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则是社工教师对传统教师职业形象的认同。“学校的话语建构了热情、敏察与深负正义感的教师专业形象,但多数教师在英雄式的意象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①廉兮:《从个人到公共——抵抗与转化的教育行动研究》,《应用心理研究》(台湾)2012年第53期。访谈中Y教师提到的“灌输”、“以身作则”、“营造”、“孩子”、“幻灭”等词汇,都潜藏了其所内化的传统教师形象典型。教师职业认同要求高校教师成为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完备者,社会工作专业还进一步要求从业者必须是追求理想的“道德楷模”,社会工作教师则“自觉地”承受起了两种社会认同所给予的沉重压力。
面对社工专业认同、教师职业认同的双重危机,呈现出来的是“理想-现实”割裂、“自我神话-自我怀疑”并存的认同状态。这种认同状态必然不可能是稳定的,仅仅能在单一的课堂环境保持脆弱的平衡状态。社会工作教师通过教学生产出模糊的“社会工作者”专业身份,并将其加诸在学生身上。这个模糊,是因为实务的萎靡,让学生永远没有机会去检视该形象的“真切”与否。这个身份只是用来确保现有状态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张力,以维持自尊的需要。尤其是当面临学生实习场所的匮乏、毕业后的“流失”,面临学校以就业率、对口就业率来“证明”专业“办学合法性”时,教师、学生必须再一次地面对认同危机。
(二)专业认同成为实务、实习反思的结果
社会工作专业对专业实习的强调,迫使师生要走出单一课堂环境,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检验自己的“专业形象”。与其他专业教学相比,教学实习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S校参考了港台高校的经验,教学计划中规定学生人均必须完成不少于800小时的实习。然而在专业创办之初,安排学生实习成为了大问题。为此,社工教师唯有“公事私办”,主动利用个人关系网络开发各种实习岗位。这些实习单位虽然也有少量的NGO和企业,但主要还是主动“嵌入”政府原有事业机关单位(司法所、街道办、学校等)的工作中。对于刚开始的实习岗位开发,Y老师深有感触地说:“刚开始的时候广州都没有专业实习机会,全凭院长靠过去的关系,找了一些街道、行政部门……当时同学给我们的反映就是打打杂什么的……当时好像是Q老师的一些同学资源,我们就跟司法局一个处长联系上了,他其实对社会工作也不太了解,最后给我们写的感谢信还把我们称为志愿者。”(Y老师)
由于社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工,社工专业师生在实习过程中再次集体感受到现实环境和理想形象的冲突和割裂,实习进程常常成为师生矛盾冲突、自我怀疑等认同危机显性化的导火线。Y老师很痛苦地说:“2004年实习时,有一个事件对我打击很大,当时在CX街道实习,学生说在CX街道没法实习,只能傻坐在居委,啥也做不了。我看这样子不行,就给他们强行压了任务:要做一个调查,再做一个老人活动,再跟一个个案。其实后来他们都做到了。但当时有个学生就在学校论坛上写了帖子,大概意思就是老师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借实习之故使用他们,利用他们做研究,把他们当免费劳动力,和街道有利益输送……当时我的压力有多大!受的委屈有多大啊!现在想起来都想哭!非常恼火,又伤心、又委屈、又惊讶……后来事件愈演愈烈,有直接针对整个社工系的意思了,给人感觉整个系都没有好人了。”(Y老师)
实习安排令社工师生都必须像实务工作者那样参与实务、不断反思。在这种关系互动中,教师的归属群体不再是教师,而是社工实务的本土践行者。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身份在实习场域中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共同的“重要他者”反而让他们归属为同一个群体:社工专业人士。所以,与其说是学生单方面的实习,不如说是教师、学生都在同一战线上争取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权”。①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F老师说“有位去电视台实习的学生,他们提出说有些受困扰的家庭,他们去报道了,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有一种无力感。所以要去开导他们,就在答疑的过程当中逼着自己去思考。”
在实习的挫败、怀疑和成长中,专业认同也被逐渐巩固:社工教师一方面积累了信心,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双重认同危机下塑造的“神话式”社工形象。Y老师说:“刚开始我对自己本身都有非常深刻的怀疑,因为我的道德水平,道德标准都没有达到那个光环。但是我现在思路不一样了,可以坦然面对。现在我会更有自信,而且能感受到其实学生还是认可的。教学工作中我有了一些底气,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从“深刻怀疑”、“没有达到”、“否认”、“逃避”到“坦然面对”、“底气”、“自信”,以及承认社工首先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这说明传统教学场域赋予教师的“道德圣人形象”被逐步认清、剥离,理想形象和现实环境得以和解,双重认同带来的压力在这个阶段得到化解。由此带来的非预期后果则是对被专家鼓吹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专业办学评价标准的反思和再审视。
“通过实践性的教、学(teaching/learning),让学生和教师的行动主体在鲜活的生活世界中被召唤,从而推动民众批判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民众一起探索社会变革的可行道路”。②古学斌:《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转型》,《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社工教师开始从高校场域的结构约束中解放出来,降低了高校制度体系中“重要他者”的地位,不再将其评价体系视为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准,显然是主体意识觉醒的典型过程。
在此不妨将他们历经实务或实习场域后形成的社会认同称为“专业认同”。其内涵与上文所指的职业认同截然不同。首先从最核心标准“内群体选择”来看,职业认同侧重高校教师群体,专业认同侧重专业实务工作者群体;其次从场域关系来看,职业认同是学校教学管理场域中形成的师生关系、教学行政关系,因此重要他者是学生以及高校评价体系。专业认同则是由实习场域中专业-社会关系所推动,重要他者是实习单位、社会大众,高校体系的“重要他者”影响被降低,学生不再是外群体的重要他者,而变成内群体(认同共同体)的成员。再次,从对内群体形象的建构及情感反应来看,专业认同萌芽阶段的内群体形象具备“自我神话和自我怀疑”的双重性,其后巩固阶段则真正体悟到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取向”,走向“以人为本”;最后,从主体性呈现方式来看,职业认同阶段接受教师职业形象,接受高校场域主流评估标准,并以此约束自身,专业认同则意味着经过本土化反思而重新建构专业形象,从而自我解放的意识被唤醒。因此,意识醒觉应被视为专业认同建立的标志,“以意识觉醒作为社工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核心目标,……我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意识觉醒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社区民众和学生,也有占据教育者位置的我们,因此说这是一个三向能力建设的实践”。③古学斌:《召唤行动者的归来》,载杨静、夏林清主编《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84页。
(三)集体认同成为承担“份外事”的初衷
2008年,Y老师和Q老师与其余两位社工系老师合作,共同成立了一个社会工作机构,这并不属于社工教师的“份内事”,他们何必“自找麻烦”?解释为功利动机是行不通的,访谈中了解的情况和功利主义假设相反,受访教师认为领办机构实际上是自我利益的牺牲。Q老师说:“体制对社工教师暂时不那么公平,我们发文章很难发,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实务领域,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上没办法体现,评职称也很难,这些对社工系老师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没有一定的自我牺牲,如果过分功利,对自己、对团队都有影响。”
简单以专业认同的内群体规范作为理据也是无法解释的,内群体或许有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专业能力的规范,但没有要求教师必须领办机构。在创办机构之前,上述几位教师都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参与了实务探索,并非没有参与实务的途径,况且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承担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实务督导等角色未尝不可。
亚历山大·温特(Wendt,A.)的认同理论则试图通过提出“集体认同”(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以克服功利主义假设的狭隘性。温特认为,利益虽然会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但身份反过来也在建构个体的利益感知。为此,他提出团体(corporate)、类 别(type)、角 色(role)、集 体(collective)四种身份(认同),①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其中集体认同表示对他人利益的认同,而产生具有利他特征的行为。集体认同既有明确的我群和他群界限,同时也超越并模糊了两者的边界。温特认为,影响其形成的主要因果变量有三个:相互依存、同质性、共同命运。
访谈中受访教师普遍认为,真正驱使他们参与实务的,并非利益,而是创办机构前以个人身份(督导、研究者、教师)面对体制、大环境时遇到的无力感。Y老师说:“当时有一个刚从戒毒所出来的吸毒者,之前在戒毒所就认识我,他也很认可我们社会工作。所以一出来就找了我……我只是一个社工的老师,我啥都不是,我咋能帮到他?……强烈的无力感,而且如果没有机构支撑的话,就是个人行为,何来专业性?谁监督你?谁知道你?谁给你资源?谁给你政策?难道就是(凭)爱心在做事吗?而且你的激情也未必能保持啊,可能只是为了研究、为了教学。所以,机构就是职业人的归属,就不是一个人了。”
集体认同理论可为教师领办机构的行动提供分析框架,社工教师在实习指导过程中为师生共同建构出“实务工作者”的群体身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对集体身份、集体话语的需求。教师-学生本来作为对应的角色身份而相互依存,在实习、实务过程中共同面对着社会认可度低、自身实务能力羸弱的困境,尤其是对对方立场、处境的理解和代入反而激发起“集体命运感”,为双方超越原有身份边界,形成集体认同提供了条件。要形成专业身份,获得社会承认(合法性问题),就必须依靠不同群体间形成话语共识来实现。集体认同形成大家对处境进行“解读”的共同体,共享着同样的体验、话语形式和理解处境的框架。Q老师说:“社工教师也是社工从业人员,所以社工教师的角色和社工的角色(处境)其实是相通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有两者之间怎么去平衡的问题。”
Armour提出,社会工作者会通过强化专业认同、淡化组织认同和个体认同,以抗争主流的社会控制话语。②Armour,M.P.“Alternative Routes to Professional Status:Social Work and the New Careers Programs under th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Social Service Review,Vol.76,No.2,2002,PP.229-255.本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首批社工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努力,与其理解为是政策推动下的社工教师作为个体的功利性、潮流性行为,不如说是社工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共同身份建构的集体行动。领办机构不应当被视为社工教师单方面的行动,而应被视为在社工教师引领下的实务工作者、社工学生、社工教师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
随着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机构成立,社工发展的外界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逐渐好转,随着社工教师各自找到自身的研究领域,社工人才队伍逐渐壮大增多。社工教师-机构(学生)的相互依存程度降低之后,社工教师反而再次意识到身份冲突,开始淡出机构实务领域,转而以研究、督导等间接方式参与实务。Q老师说:“我在这个位置(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已经被琐事所缠住了,所以我要做适当的抽离,退出机构管理层的位置,只做督导。”
三、对教师领办机构的反思
当前党和政府大力推动社工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政策引发学界热议。究竟是“示范效应”,还是“大谬不然”?③周玉萍:《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生存处境与发展前景》,《社会福利(理论版)》2013年第3期。如何确保教师领办机构能坚守专业理念、做到道德自觉,而非“大量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占据着特殊的位阶和权力,享受着坐而论道,把专业变成获利的工具,忘记了社会工作的根本”,①古学斌:《召唤行动者的归来》,载杨静、夏林清主编《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反而侵蚀掉作为“道德实践”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合法性。最关键的是,就算要推动实务发展,为什么要领办机构?“领办”和“开办”、“协办”、“创办”有什么不同涵义?领办带来的身份冲突如何解决?无论是政策还是学术界,都未能较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从访谈中可以看到,对集体认同的追求及建构,是社工教师投身实务场域的原初动力。集体认同之所以在现阶段如此之重要,是因为社工教师唯有通过该身份,才能将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将制度给予的合法性——先赋身份,转化为社会承认的专业性——后致身份。在集体认同的构建中,社工教师的个人身份、职业身份和实务身份都能得到较好的整合,教师之间、教师-学生之间、社工-教师之间,形成跨群体的联盟。国家、社会正是出于对社会工作从业者集体认同的“想象”,才将社工教师视为首当其冲的担当者,而“领办机构”也就自然成为必由之策。由此可见,集体认同为领办机构提供了道德冲动,也为领办机构提供了监督力量,也能解决领办机构过程中的身份冲突问题。最重要的是,集体认同既是领办机构政策的前提,也应是领办机构政策的目的。领办机构不仅是为了孵化更多承接社会服务的组织主体,或是为了树立实践典范或深化本土研究,而且其核心作用在于以此为平台,建立从业人员的专业话语体系,协助从业人员自觉建立自身主体性地位,以个体行动推动结构环境的发展。
这对当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则是,政策制定不应仅考虑到对专业人才队伍的利益驱动,还应当考虑到如何将广义社会工作从业者们“组织起来”,推动从业者群体集体认同(身份)的发展。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Identity of Social Work Faculty:Reflections on Teachers Establish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LIU Chengyan
(School of Sociolog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China)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college facul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teachers’identity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occupational identity,professional identity,and collective identity.The theory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explains how social work teachers proactively select strategy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our country,the process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ereas collective identity facilitate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work teachers leading social organizations.Therefore,the author thinks,when making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policies,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practitioners,but also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s’collective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social work;professional identity;occupational identity;collective identity
本文为2014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者培养目标的行动研究”(项目编号:2014GXJK012)成果。
林诚彦(1981-),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在读,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教育,农村社会工作。
C916
A
1008-7672(2017)05-0054-09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