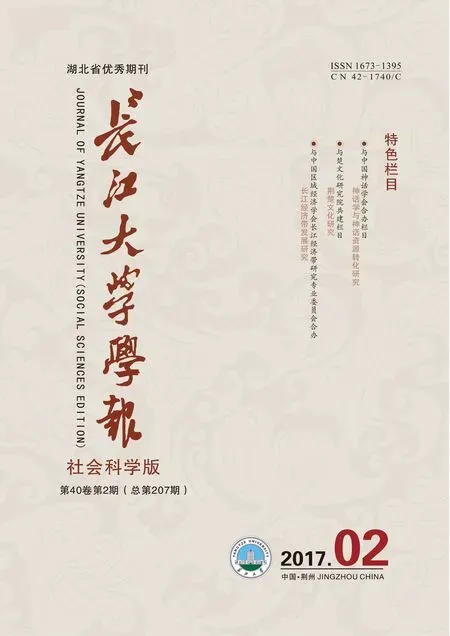《花园茶会》的文学语用学解读
刘文洁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花园茶会》的文学语用学解读
刘文洁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文学语用学将文学语篇当作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既包含了文本中角色之间的交流,又涉及作者与读者基于文本的交流。通过文学语用学的视角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花园茶会》进行分析,可看出作者通过叙事者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向读者传递了语用含意,引导读者解读故事中所表达的阶级对立与人物的内心成长;而通过故事角色交流时产生的会话含意,作者更生动地塑造出人物的形象,深化了故事的主题。
花园茶会;等级观念;文学语用学;语用含意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是20世纪初英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其创作的独到之处在于,从平淡琐碎的小事中给读者呈现出值得深思的问题。曼斯菲尔德的后期短篇小说《花园茶会》(TheGardenParty)[1]被公认为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花园茶会》中,作者以第三人称叙事者的角度讲述故事,通过对叙事者叙述方式的把握、角色间的对话及角色内心独白的刻画,讲述了谢里丹太太(Mrs.Sheridan)家一位穷苦的近邻,由于偶然的事故不幸身亡,其遗属正悲恸欲绝,谢里丹太太却在园中奏乐大宴宾客,小说从侧面反映了阶级对立和贫富悬殊。对《花园茶会》的研究评论,有的从叙事学、美学的视角出发,有些基于传统文学批评视角。本文将从文学语用学的视角分析《花园茶会》,旨在为理解这一作品提供新的思路,也以此说明从语用学理论出发分析文学文本的可行性。
文学语用学是一个较新的交叉学科。Verdonk认为,文学语用学是用语用的方法和原则阐释语言(包括文学语言),寻求解释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形式结构怎样由作者和读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其交际行为而被实际使用和体验[2]。文学语用学将文学语篇视为交际的一种形式,它“既表现着人物角色之间的交流,又表现着作者通过文本对读者的交流”[3]。本文主要以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为基础对《花园茶会》进行分析,旨在说明:作者通过叙事者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向读者传递了语用含意,引导读者解读故事主题;读者通过推测故事角色交流时产生的语用含意,可了解角色的性格特点及思想,对故事的主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花园茶会》中叙事者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及所产生的语用含意
Grice认为,交际的双方都应遵守基本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以下简称 CP),它包含四条准则: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4](P41~58)若违反CP的一个或多个准则,则会产生语用含意(Implicature)。尽管CP是在会话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同样也适用于分析文学语篇。通过文学语篇与读者进行交流时,作者如日常会话中的讲话人一样,占有支配地位,但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得不到读者的反馈,因此,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更要顾及所有的交际规约,如合作、礼貌因素,等等。[3]而对读者而言,阅读是发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合作活动。[5]在阅读文学语篇时,读者相信作者会遵守交际原则,给他们足够的、恰当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最终会证明与故事的主旨是有关联的。而当作者违反了CP的一个或多个准则时,便促使读者寻求其违反准则所带来的语用含意。在《花园茶会》中,作者以第三人称叙事者角度讲述故事,通过叙事者违反CP的相关准则引导读者解读语篇的主题。
(一)叙事者对方式准则的违反
与CP其他三个准则不同,方式准则规范的是交际信息的表达方式,它要求交际话语要简练、有条理,避免晦涩或歧义。就文学语篇这一特殊的交际形式而言,作者经常有意违反方式准则,以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语篇结构上的不按时间顺序叙述故事,或使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都是作者违反方式准则的体现。[6](P67)在《花园茶会》中,作者对方式准则的违反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对萝拉(Laura)的心理叙述。第三人称叙事者从情节外超然旁观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7](P214),以自由间接引思(FIT)方式和多种引思方式*根据Leech & Short的划分,引思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自由直接引思(Free Direct Thought,即FDT),直接引思(Direct Thought,即DT),自由间接引思(Free Indirect Thought,即FIT),间接引思(Indirect Thought,即IT),思维行为的叙事表述(Narrative Report of a Thought Act,即NRTA)。组合使用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萝拉的内心活动。FIT既不带引号,也没有引述句,仅通过话语中动词时态的倒移以及人称指示语等的变动来呈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这种引思方式尽管能使行文流畅,将人物的想法自然地交织在叙述话语中,却给读者的解读带来困难,需要读者付出更多的努力,方能将叙事者的声音与人物的想法区分开来;多种引思方式相互切换,则对读者的解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叙事者违反了方式准则。作者通过叙事者对这一准则的违反,吸引了读者对萝拉的关注,不仅成功地将萝拉推向了故事主角的位置,还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人物的距离,使读者对这一角色更易产生共鸣。以下将选取较具代表性的例子,分析叙事者违反方式准则所带来的语用含意。
(1)①They looked impressive……②What nice eyes he had,small,but such a dark blue!…③How very nice workmen were!…④Oh,how extraordinarily nice workmen were,she thought……[1](P2~3)
故事通过对天气、花园的描写切入,继而讲述萝拉与工人商讨如何放置花园茶会所需的大帐幕。在情节推进的同时,还夹杂着对工人的一些评价。句①~③均表现了对工人阶层的赞赏,然而句中无引号或引述句,特别是句①夹杂在叙事者的描述中,使读者难以区分其声音到底是来自叙事者还是萝拉。句②、③使用了感叹句,依稀体现出主人公的个人语气特征。Black认为,感叹句是自由间接引思的一个重要标志。[6](P67)直到句④中叙事者以间接引思(IT)方式点明萝拉对工人的赞赏之情,读者才能肯定句①~③为萝拉的心理活动。叙事者采用间接引思的方式使读者不得不在解读的过程中付出更多的努力,这种对方式准则的违反增加了读者对萝拉内心活动的关注,突出了萝拉虽身在中上层阶级,却是一个怀抱理想主义的女子,甚至想跨越阶层,与工人们打成一片(She felt just like a work-girl)。
在进行茶会最后的准备工作时,萝拉得知一位穷苦的近邻意外死亡,便意图说服母亲取消茶会,母亲却不同意,认为“那种人不配得到我们的牺牲”,并顺势将她正在试戴的一顶帽子送给了萝拉。当萝拉沮丧地走出母亲房间时,意外地在镜子中发现自己戴着新帽子非常漂亮。此时,叙事者对萝拉展开了大量的内心描述:
(2)…(①NRTA)Never had she imagined she could look like that.(②DT) Is mother right? she thought.(③NRTA) And now she hoped her mother was right.(④DT) Am I being extravagant?(⑤FIT) Perhaps it was extravagant.(⑥NRTA) Just for a moment she had another glimpse of that poor woman and those little children,and the body being carried into the house.(⑦NRTA) But it all seemed blurred,unreal,like a picture in the newspaper.(⑧DT) I’ll remember it again after the party's over,she decided.(⑨FIT)And somehow that seemed quite the best plan……[1](P11)
作者没有通过叙事者之口直接指出人物内心的挣扎,而是通过增加读者推理包袱、违反方式准则,使读者体会其产生的语用含意:引思方式的交替多变从形式上反映了萝拉当时内心的矛盾。萝拉对于取消茶会这一想法开始动摇,也体现了她内心的成长——从一开始理想化地想与工人打成一片,到直面现实,重新调整对阶级观念的认识。
(二)叙事者对量准则的违反
CP的量准则规定了交际的话语应具有适量的信息。在《花园茶会》中,当叙事者讲述萝拉与朋友凯蒂(Kitty)的通话这一情节时,叙事者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了萝拉的话语,而完全隐去交际的另一方——凯蒂的话语:
(3)The telephone.“Yes,yes,oh yes.Kitty? Good morning,dear.Come to lunch? Do,dear.Delighted of course.It will only be a very scratch meal,just the sandwich crusts and broken mer-ingue-shells and what’s left over.Yes,isn’t it a perfect morning? Your white? Oh,I certainly should.One moment,hold the line.Mother’s calling.” And Laura sat back.“What,mother? Can’t hear.”
Mrs.Sheridan’s voice floated down the stairs.“Tell her to wear thatsweethat she had on last Sunday.”
“Mother says you’re to wear that sweet hat you had on last Sunday.Good.One o’clock.Bye-bye.”[1](P4)
在这一情节中,叙事者没有提供足够多的信息,因此读者无法得知她们通话的完整内容。从这一层面来讲,叙事者违反了量准则。这种有意减少信息的方式为读者创造出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萝拉的话语中,读者可猜测她们在讨论一起吃午餐和为茶会准备服装),同时也向读者传递了语用含意,即萝拉与凯蒂的通话内容并非作者意图传达的信息,重点在于由通话引出的信息:其一,谢里丹太太打断她们的通话,要求女儿的朋友“戴上上周日那顶帽子”,这反映了人物强烈的控制欲,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情节中也得到证实——尽管从一开始谢里丹太太声称将茶会完全交给女儿打理,而她却忍不住干涉茶会的准备工作,私自为茶会订了大量的鲜花;其二,萝拉几乎一字不差地向凯蒂传递了母亲的话,而用“sweet”一词进行了强调(“sweet”一词特别使用了斜体,体现其音调有异于谢里丹太太的原话),通过声调的改变,萝拉巧妙地加进了些许个人的感情和想法,从这一细节可看出她不想如一个无主见的小孩一样,而是在顺从母亲之余,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这种微妙的心理为后文的情节埋下了铺垫——尽管她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充斥着阶级意识,但她仍在这一氛围中努力对等级观念进行独立的、较理性的思考。
(三)叙事者对关系准则的违反
关系准则要求交际内容与交际目的之间是有关联的。《花园茶会》是曼斯菲尔德已出版且广受好评的作品,仅依据这一点,读者似乎便可以肯定故事中的一切叙述都是相关联的,因此,一些表面上看似违反了关系准则的,显然微不足道的描述,会激发读者去寻求作者意图传达的语用含意,找出这些描述的用意。如萝拉结束与凯蒂的通话之后,叙事者描述了她的所听、所感、所见:
(4)…She was still,listening.All the doors in the house seemed to be open.The house was alive with soft,quick steps and running voices.The green baize door that led to the kitchen regions swung open and shut with a muffled thud.And now there came a long,chuckling absurd sound.It was the heavy piano being moved on its stiff castors.But the air! If you stopped to notice,was the air always like this? Little faint winds were playing chase in at the tops of the windows,out at the doors.And there were two tiny spots of sun,one on the inkpot,one on a silver photograph frame,playing too.Darling little spots.Especially the one on the inkpot lid.It was quite warm.A warm little silver star.She could have kissed it.[1](P4)
对于短篇故事而言,这一整段的描述所占比例已然不少。从内容上看,它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似乎毫无贡献。然而,若读者结合整个故事细究这一看似过于详细且微不足道的描述时,便会发现作者意图通过这些描述,将萝拉塑造成一个感知力强、有艺术气息、有灵气的女孩子形象,为后文萝拉面对不幸去世的邻居的遗体时,对死亡的顿悟打下基础。
(四)叙事者对质准则的违反
CP的质准则指出,会话各方不说虚假或无证据的话。但由于文学语篇是由作者创造出来的,即于现实世界而言,可能是虚假的,因此,在这一特殊交际方式中,质准则强调的是语篇中的话语在它所在的文本世界必须是真实的。[2]
在《花园茶会》中,萝拉家的穷苦近邻猝然离世,她在茶会之后将剩下的食物送到这个不幸的家庭,并来到遗体旁。
(5)Laura came.
There lay a young man,fast asleep…sleeping so soundly,so deeply,that he was far,far away from them both.Oh,so remote,so peaceful.He was dreaming.Never wake him up again.His head was sunk in the pillow,his eyes were closed; they were blind under the closed eyelids.He was given up to his dream.What did garden-parties and baskets and lace frocks matter to him? He was far from all those things.He was wonderful,beautiful.While they were laughing and while the band was playing,this marvel had come to the lane.Happy…happy….All is well,said that sleeping face.This is just as it should be.I am content.
不幸的邻居已然离世,叙事者用“fast asleep…He was dreaming…He was given up to his dream”来描写他,显然是不真实的。此外,叙事者使用直接引语(划线部分)似乎道出了死者的思想。然而,在这个写实性故事中,死者是不可能存在思想的。如此一来,作者通过违反质准则引起读者对这部分的格外关注,促使读者付出更多的努力推测作者的语用含意。“Laura came”独立成段,指出萝拉来到死者身旁,因此,读者可猜想“There lay a young man”为萝拉所见的客观描述,而随后的“fast asleep”实为萝拉对死者的主观评价,“so soundly,so deeply,… Oh,so remote,so peaceful”等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更接近萝拉的语言特点,可推测出这部分叙述的是萝拉见到死者时内心的想法及其对死亡的领悟,而并非叙事者的观点。面对遗体,萝拉忘记了刚到邻居家时的惶恐,领悟出死亡所带来的平静和满足。此部分也体现了作品的两个主题——阶级对立与死亡——的交融:世间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由于死亡而烟消云散。
二、《花园茶会》中故事角色会话所传递的语用含意
Leech等认为,文学语言来自日常语言的运用,是人们言语交际的一种方式,因此,与日常语言没有本质的区别。[8]文学语篇中人物的语言交流“可以看作是对我们日常语言使用的直接模仿”[9](P17)。因此,用于分析日常会话的语用理论也适用于分析该短篇小说中的会话。
在《花园茶会》中,作者使用直接引语有选择性地呈现了角色之间的会话,这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叙事者的参与度,使读者从对人物塑造有重要意义的对白中更直接地去体会角色的个人话语特征及其内心想法。此外,角色的个人话语也使故事的陈述更为生动,语言特色更加丰富、鲜明。如故事中对底层人民——萝拉家的佣人、布置茶会的工人、穷苦近邻——的话语呈现尽管不多却特色鲜明:使用俚语、简单的词汇和语法,特别是发音的不规范(“Yer ma won’t know;I’m ’er sister,miss.You’ll excuse ’er,won’t you?…I’ll think the young lady….You’d like a look at ’im,…’e looks a picture”),这些语言特色从侧面反映了说话者所受教育的不足,塑造了底层人民的形象。萝拉一家及朋友的话语则展现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如使用较长句子、复杂句法与丰富的词汇等。作者在故事中不仅有意凸显两个阶层人民的不同语言特点,对于萝拉一家及其朋友的话语呈现更刻画了萝拉的朋友及家人对底层人民的轻视,同时反映了萝拉潜在的等级观念。
(一)萝拉的朋友及家人对底层人民的轻视
萝拉的朋友凯蒂在故事中仅出现两次,是中上阶层的代表之一。第一次出现时,作者有意省略其话语,她在故事中唯一一句话出现在她来到萝拉家参加茶会时:
(6)…The green-coated band had arrived and was established in a corner of the tennis-court.
“My dear!” trilled Kitty Maitland,“aren’t they too like frogs for words? You ought to have arranged them round the pond with the conductor in the middle on a leaf.”[1](P11)
凯蒂将身着绿衣的助兴乐队比喻为“会说话的青蛙”,并调侃应该将指挥者安排在池塘中央的叶子上,其他成员围着池塘表演。这种对表演者衣着的讽刺,将他人贬低为动物的行为方式,违反了Leech礼貌原则中的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即减少表达对他人的贬损,尽量少贬低别人,多赞誉别人)[10](P81~83),可见在凯蒂看来,乐队是为她们助兴且比她们低等的,表现出其极强的等级观念及对劳动阶层的不尊重。谢里丹太太将穷困近邻的住所称之为“poky little holes”,同样也违反了赞誉准则,其对下层人民的鄙视跃然纸上。
在对萝拉家人的描写中,作品对萝拉的姐姐乔斯(Jose)与母亲谢里丹太太着墨最多。通过分析她们会话中的语用含义,可看出她们对下层人民的偏见。譬如,当听到邻居因事故意外身亡、留下妻子与五个年幼的小孩时,萝拉将乔斯拉到一旁,提议取消茶会。
(7)…“Jose!”she said,horrified,“however are we going to stop everything?”
①“Stop everything,Laura!” cried Jose in astonishment.“What do you mean?”
“Stop the garden-party,of course.” Why did Jose pretend?
But Jose was still more amazed.②“Stop the garden-party? My dear Laura,don’t be so absurd.Of course we can’t do anything of the kind.Nobody expects us to.Don’t be so extravagant.”
“But we can’t possibly have a garden-party with a man dead just outside the front gate.”
…
…③“You won't bring a drunken workman back to life by being sentimental,” she said softly.
“Drunk! Who said he was drunk?” Laura turned furiously on Jose…
句①~③乔斯的回答均违反了CP中的质准则。句①中,乔斯使用感叹的语气重复了萝拉的话,显然她已经知道萝拉的意思,却仍用疑问句反问萝拉,表面上是寻求萝拉的解释,而实际是通过违反质准则表达她对萝拉的这一想法感到荒谬。而在萝拉更直接地说明她的想法后,乔斯使用反问句(句②)但意不在寻求回答,这同样违反了质准则,进一步表达了对萝拉想法的反对。由此可知,尽管乔斯与萝拉一样,知道茶会的欢笑声定会传到正陷于悲痛之中的邻居耳中,她仍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下层人民的死而取消茶会。而句③中,乔斯违反了质准则,臆造车夫因为酒醉(drunken)而丧命的信息,她认为车夫的死是自食其果,不仅如此,乔斯使用“man”的下义词“workman”,强调了死者充其量只是一个下层工人,身处上层社会的她们无需因为一个“咎由自取的”车夫而改变自己的计划,由此可看出乔斯对下层人民的不屑与凯蒂无异。
(二)萝拉潜在的等级观念
在《花园茶会》中,萝拉对下层人民的看法表面上似乎与她的家人、朋友截然不同,然而通过对萝拉话语的分析,结合叙事者的评述与对她心理活动的描述,可看出萝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背后潜在的等级观念。
在开篇叙述萝拉与工人商讨布置大帐幕之时,工人提议将大帐幕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a bang slap in the eye),作者通过思维行为的叙事表述(NRTA)的方式描述出萝拉的内心想法:Laura’s upbringing made her wonder for a moment whether it was quite respectful of a workman to talk to her of bangs slap in the eye.[1](P2)这种引思的方式不仅传达了萝拉的内心活动(琢磨着一个工匠跟她说怎么引人注目是不是合乎礼仪),也带着叙事者的评论(萝拉这一内心活动是因为她所接受的教育)。萝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表明家庭教育使等级观念根植在她的心里。然而,萝拉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她内心潜在的等级观念,从叙事者对其心理活动的描写可看出,萝拉甚至认为所谓的等级观念是可笑的,不同阶层间并不存在任何差异(It’s all the fault,she decided,…,of these absurd class distinctions.Well,for her part,she didn’t feel them.Not a bit,not an atom…[1](P3))。萝拉潜意识反应与她心理活动的不一致在后文的叙述中仍有出现:出于对邻居的同情,她试图说服母亲取消茶会,却又再次显示了潜意识中的等级观念(The band and everybody arriving.They’d hear us,mother; they’re nearly neighbours)。“nearly”一词暗示了潜意识中对邻居的态度,尽管邻居家与萝拉家只有一路之隔,然而,萝拉却不愿意与他们混为一谈,这再次体现了萝拉潜在的等级观念。
三、结语
在《花园茶会》中,曼斯菲尔德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及因此引发的人物心理反应,借此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对立与人物的内心成长。本文从文学语用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花园茶会》中故事外叙事者的叙述方式与故事中人物的交流进行语用探讨,分析了作者以叙事者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引领读者深入地解读语篇主旨,并通过人物间交流所产生的语用含意刻画出人物的性格与思想。尽管文学语用学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在国内文学语用学研究尚未形成健全的研究范式,许多对文学作品的语用学研究仅针对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本文尝试将人物的对话与叙事者的叙述方式一并纳入文学语用学的分析中,力求更深入地阐释作品的特点。
[1]Mansfield,K.The Garden Party[A].Milton Crane.Fifty Great Short Stories[M].New York:Random House,2005.
[2]涂靖.语用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语用学探索之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6).
[3]封宗信.语用学、文体学与文学研究[J].国外文学,1997(3).
[4]Grice,P.Logic and conversation[A].Cole,P.Morgan,J.Syntax and Semantics,Volume.3:Speech Act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
[5]陈海庆.文学语篇的语用学阐释:互动性及其取效行为[J].外语教学,2009(1).
[6]Black,E.语用文体学[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7]Leech,G.& H.Short.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M]Lond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7.
[8]赵婉孜,刘风光.文学语用学的理论特征与范式[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9]宋成方.语用文体学[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10]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New York:Longman Inc.,1983.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2017-01-02
广东省惠州学院本科教学工程项目(JG2013032)
刘文洁(1986-),女,广东揭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用学研究。
I106
A
1673-1395 (2017)02-0061-05
——20次钱塘茶会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