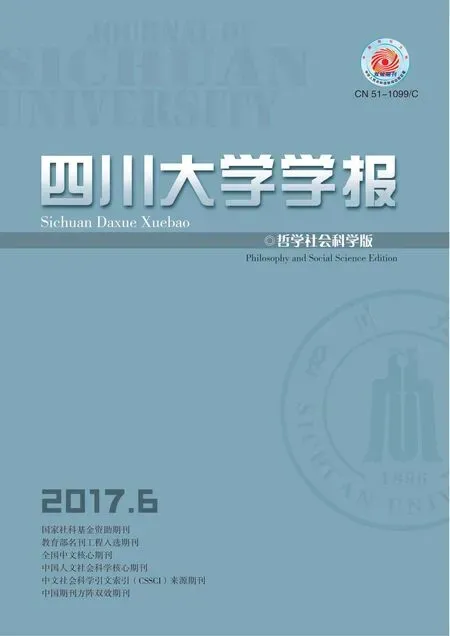多元文化与犍陀罗艺术:再论贵霜时代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
§世界史研究§
多元文化与犍陀罗艺术:再论贵霜时代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
庞霄骁
长期以来,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问题,学者们围绕“希腊起源说”“罗马起源说”“本土起源说”“伊朗起源说”和“塞人起源说”等观点争执不下。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贵霜帝国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与融合才是犍陀罗艺术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贵霜人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成果并加以融合,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但客观上却为佛教艺术吸收希腊化文化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和贵霜本族传统等因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也是上述各种关于犍陀罗艺术起源的观点得以存在的基础。
多元文化;犍陀罗艺术;贵霜帝国
自19世纪中期西方考古学者在阿富汗喀布尔地区首次发现佛陀冥想的雕像以来,有关佛教艺术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就一直吸引着考古学者、艺术史家,甚至是思想史学者的目光。虽然,有关犍陀罗艺术起源的研究目前依然存在巨大争议,但犍陀罗艺术蓬勃发展于公元1世纪前后,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学者的共识,而公元1世纪恰好是贵霜帝国崛起和扩张的关键时期,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为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贵霜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状况,揭示贵霜帝国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对犍陀罗艺术的诞生所起的推动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有关犍陀罗艺术起源的争议
1874年,以著名的巴尔胡特佛塔(The stupa of Bharhut)被发现为契机,时任印度考古勘探局负责人的坎宁汉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在当年的印度考古局年度报告上就提出过西北印度的雕刻很可能沿袭自希腊雕刻的猜想,由此掀开佛教艺术的研究序幕。*A. Cunningham, Report for the Years 1872-73, Vol.5,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874, p.123.不过,坎宁汉并未对犍陀罗艺术的起源问题进行过多的揣测。在其发表于1879年的《巴尔胡特佛塔》一书中,他仅是详细介绍了巴尔胡特佛塔的建造时间和建筑特点。虽然,其中也提及巴尔胡特佛塔上出现的带翅膀的神祇形象,但坎宁汉并未将之与希腊胜利女神尼喀相联系,而是将之比定为《耶柔吠陀》(YajurVeda)中提到的印度神Menaka和Urvasi。*A. Cunningham, The Stpa of Bharhut: A Buddhist Monument Ornamented with Numerous Sculptures Illustrative of Buddhist Legend and History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London: W. H. Allen and Co., 1879, pp.27-29.
最早明确提出外来文化对犍陀罗艺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学者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wedel)。在发表于1893年的《印度佛教艺术》一书中,格伦威德尔详细分析了当时印度地区所发现的佛教艺术图像,认为狮子、圣树和莲花等形象主要来自波斯和两河流域,它们是佛教艺术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A. Gruwedel, Buddhist Art of India, Trans. by A. C. Gibson,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01, pp.28-74.1914年,被称为“犍陀罗艺术研究奠基人”的法国学者福歇(Alfred Foucher)发表了其代表作《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印度与中亚考古学论文集》。*A. Foucher, Beginnings of the Buddhist Art and Other Essays in Indian and Central Asia Archology, Trans. by L. A. Thomas and F. W. Thomas,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1917. 译文可参考福歇:《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印度与中亚考古学论文集》,王平先、魏文捷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书中,福歇总结了坎宁汉和马歇尔等人在巴尔胡特佛塔和山奇大塔的考古成果,将犍陀罗的艺术诞生归根于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他认为,流传于中亚的希腊化文化沿着从阿姆河到塔克西拉的商路进入印度,最终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在其成书于1951年的六卷本法语著作《犍陀罗希腊式佛教艺术》中,福歇还首次使用了“希腊—佛教艺术”(Greek Buddhist Art)一词来指代犍陀罗艺术。*A. Foucher, L'art Greco-Bouddhigue du Gandhāra, Paris: ImprimerieNationale, 1905, p.51.1960年,英国学者马歇尔(John Marshall)出版了《犍陀罗佛教艺术:早期流派的起源、发展和衰落》一书,该书以其多年来在塔克西拉的考古发掘为依据,系统阐述了在印度—希腊人、印度—帕提亚人所带来的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下,犍陀罗艺术逐渐从本土艺术中分离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并重申了希腊古典艺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J. Marshall,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dra: The Story of the Early School, Its Birth, Growth and Dec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以此为基础,犍陀罗艺术起源中的“希腊说”逐渐开始确立,并成为了关于犍陀罗艺术起源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与“希腊说”几乎同时,犍陀罗艺术的“罗马起源说”也逐渐出现。早在1889年,英国学者文森特·史密斯(V. A. Smith)就在《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上发表过《希腊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之影响》一文,详细考察了希腊罗马文化对古印度的影响,他认为“犍陀罗艺术主要还是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非直接受晚期希腊艺术的影响”。*V. A. Smith, “The Graeco-Roman Influence on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India,”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8, No.3,1889, pp.160, 172.1942年,美国学者本杰明·罗兰德(Benjamin Rowland)发表了《犍陀罗与晚期古典艺术:佛像》一文,明确提出犍陀罗艺术是罗马帝国艺术在东方的一条支脉,犍陀罗雕刻风格之所以与帕尔米拉(Palmyra)和高卢(Gaul)的雕塑有很大相似性,应当归因于罗马帝国境内发生的商贸活动以及通过帝国交通干线所进行的文化交流。*B. Rowland, “Gandhāraand Late Antique Art: The Buddha Imag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46, No.2, 1942, pp.223-236.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莫蒂默·惠勒(R. E. M. Wheeler)和亚历山大·C·索普(Alexander C. Soper)。惠勒在1949年发表了《罗马式佛教艺术:一个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通过比对罗马雕塑与塔克西拉等地雕塑的相似性,进一步强调了罗马艺术在犍陀罗艺术形成中的作用;*R. E. M. Wheeler, “Romano—Buddhist Art: An Old Problem Restated,” Antiquity, Vol.89, 1949, pp.4-19.而索普则在其文章《犍陀罗艺术中的罗马风格》中,通过分析贵霜塔克蒂·巴希佛寺遗址的雕像和建筑风格,最后提出,在贵霜时代犍陀罗艺术的成形过程中,起最主要作用的因素应该还是来自罗马的艺术风格。*A. C. Soper, “The Roman Style in Gandhār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55, No.4, 1951, pp.301-319.此外,德国籍犹太学者布克塔尔(H.Buchthal)以及牛津大学教授皮特·斯特沃特(Peter Stewart)也同样支持这一观点。
1947年,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摆脱。受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两地的学者们开始注重印度本土艺术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犍陀罗艺术中的“本土起源说”应运而生。其实,早在1926年,印度籍斯里兰卡学者库马拉斯瓦米(A. K. Coomaraswamy)就专门撰文指出,犍陀罗和秣菟罗的艺术流派是在两个不同地区同时产生的,是佛教在犍陀罗和秣菟罗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个地区的艺术家按照文学和口耳相传的图像,依据自身的风格和传统,创造出带有自身特点的雕塑类型,而秣菟罗的艺术风格,是笈多王朝和后来印度佛教艺术发展的主要来源。*A. K. Coomaraswamy,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6, 1926, pp.165-170.支持这一观点的是荷兰学者范·洛惠岑·德黎乌(J. E. Van Lohuizen Deleeuw),她于1949年和1981年先后发表著作《“斯基泰”时代——一种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印度北部的历史、艺术、铭文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和文章《关于佛像起源的新证据》,明确提出犍陀罗艺术在观念上的确源于印度本土艺术,犍陀罗初期的佛像的出现是受秣菟罗艺术的影响。*可分别参见J·E·范·洛惠泽恩-德·黎乌:《斯基泰时期》,许建英、贾建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J. E. Van LohuizenDeleeuw, “New Evidence with Regard to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in Western Europe, Berlin: Museum of Indian Art, 1981, pp.377-400.此外,支持印度本土说的学者还有巴基斯坦的达尼教授(A. H. Dani),不过他的观点较为折中,他认为西方对于犍陀罗艺术的判断实际上是以西方古典艺术作为标准,这一做法忽视了艺术背后的历史事实,确切地说,应该是外来民族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犍陀罗艺术和文化。*A. H. Dani, Gandhāra Art in Pakistan, Islamabad: Department of Films & Publications, 195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英国学者克里布(J. Cribb),他认为是由于迦腻色伽一世将国土扩张到恒河流域,使得秣菟罗造型艺术北传,最终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J. Cribb,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p.231-244.
最后,虽然“希腊起源说”“罗马起源说”和“印度起源说”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新的观点对此提出过挑战。
一种说法认为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和塞人有关,代表学者是纳拉因(A. K. Narain)和达尼。纳拉因通过分析斯瓦特的布特卡拉I号佛塔(Butkara I)的发掘成果以及相关铭文,认为塞人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再由喀喇昆仑山南麓的支脉进入斯瓦特,他们在国王毛厄斯(Maues)统治期间控制着犍陀罗北部,并逐渐受到当地佛教的影响。在印度—塞人毛厄斯的钱币上就有与后来佛陀的坐姿几乎一致的人物坐像,这很可能就是佛像的最初起源。*A. K. Narain, “First Images of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Ideology and Chronology,” Studies in Buddhist Art of South Asia, edited by A. K. Narain, New Delhi: Kanak Publications, 1985, pp.88-95.另一个支持者是达尼教授。前文就提到,他虽然比较倾向于“本土起源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外来因素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1987年,以中巴共建喀喇昆仑公路为契机,达尼教授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合作,对喀喇昆仑沿线诸遗址进行过考察。在其《佛像的起源:契拉斯一地的证据》一文中,他声称在喀喇昆仑山的岩画中发现了残存最早的与佛像比较相似的图案,并将之与途经该地的塞人相联系,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归于塞人名下。*A. H. Dani,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The Chilas Evidence,”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ol.26, 1987, pp.13-23.
另一种说法主要是将犍陀罗艺术的起源与波斯、帕提亚相联系。1968年,马德雷尼·哈拉德(Madeleine Hallade)出版了《犍陀罗风格和佛教艺术的演变》一书,力证犍陀罗艺术的诞生与演变与印度—伊朗的文化互动有重要的联系。他认为,长久以来伊朗和印度地区就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受此影响,佛教艺术逐渐借用了许多伊朗文化的因素。犍陀罗艺术能够在希腊化文化消失和贵霜帝国灭亡之后的公元4世纪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就是印度笈多王朝和萨珊波斯之间文化互动的结果。*M. Hallade, The Gandhāra Style and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t,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68.1987年,西班牙学者坎塔尔·法布雷加斯(Chantal Fabrègues)发表了《印度—帕提亚人与犍陀罗雕塑》一文,认为犍陀罗艺术的形成应该是在印度—帕提亚国王贡多法勒斯时期。*C. Fabrègues, “The Indo-Parthian Beginnings of Gandhāra Sculptur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1, Inaugural Issue, 1987, pp.33-43.虽然其观点并未完全脱离马歇尔的影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印度—帕提亚人对犍陀罗艺术诞生的贡献。1988年,日本学者田边胜见发表了论文《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他认为,受波斯文化影响的贵霜佛教徒将肖像的概念传入了毫无塑像传统的印度佛教中,从而为贵霜时期塑造石佛像铺平了道路。*田边胜见:《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台建群选译,《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就犍陀罗艺术起源的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争执不下的局面,恰恰证明了无论哪一种观点也无法独自解释犍陀罗艺术的起源。英国著名学者约翰·鲍德曼教授(John Boardman)曾在其新近出版的《亚洲的希腊人》一书中对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做出过这样一个解释:“有关犍陀罗艺术起源的‘希腊巴克特里亚说’‘直接罗马起源说’和‘伊朗—希腊起源说’并不存在矛盾,这些假设大体上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一种假设可以独自解释这些毫无争议的西方艺术风格,所有要素和影响的综合,才可能是这一艺术史上最特别的多元融合的唯一解释。”*J. Boardman, Greeks in As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5, p.167.结合公元1世纪前后的历史,这一时期统治印度西北部和中亚的是贵霜帝国,多元文化并存与融合是其最为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因此贵霜帝国在犍陀罗艺术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不能被忽视。
二、独尊佛教?——对贵霜时期佛教的再探讨
有关佛教在贵霜时期的发展,学界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迦腻色伽王(具体是迦腻色伽一世、二世还是三世,尚无定论)是继阿育王之后的另一位佛教护法明王,在他的统治下,佛教得到极大发展,成为贵霜帝国的国教,而他主持的“迦湿弥罗结集”(又称克什米尔结集)也被视为大乘佛教诞生的标志,但不少学者已经就此说提出了质疑。
在众多质疑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艾伦·拉文(Ellen Raven),他认为“佛像既没有出现在迦腻色伽一世之前的贵霜钱币之上,也没有在其后的贵霜钱币上发现,它仅仅是(贵霜人)从伊朗、希腊化世界、罗马和印度的万神殿中选定的一系列神祇之一,用以表示国王对物质财富、军事胜利、统治合法和王权神圣性的关注”。*E. Raven, “Design Diversity in Kanishka`s Buddha Coins,” in Gandhāra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and Texts, edited by Kurt Behrendt and Pia Brancaccio,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pp.286-302.而尼利斯(J. Neelis)则进一步认为,从钱币学和铭文学上看,迦腻色伽王支持的不仅仅是佛教,还包括其他宗教,而所谓的迦腻色伽王弘法一说实际上都出自汉文大乘佛教的记录。*J. Neelis, Early Buddhist Transmission and Trade Networks: Mobility and Exchange within and beyond the Northwestern Borderlands of South Asia, Leiden: Brill, 2011, pp.133-134.
结合相关文献,尼利斯的质疑无疑有一定的道理。季羡林在为《大唐西域记》作校释时曾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著名的阿育王结集的记载并未在《大唐西域记》中明确出现过。他对此的解释是,玄奘在记载“迦湿弥罗的五百罗汉僧传说”中已经隐约提到了第三次结集,主要体现在无忧王(阿育王)、五百罗汉僧等元素。*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5-336页。然而,阿育王弘法作为佛教发展史上的一次大事,高僧玄奘居然没有用较大的笔墨对其进行书写,显然是令人费解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南传佛教的《大史》(Mahāvasa)一书中,该书花费了较大的笔墨描写第一、第二、第三次结集,却漏掉了迦腻色伽所主持的迦湿弥罗结集。*The Mahāvasa or the Great Chronicle of Ceylon, trans. by Wilhelm Geiger and Mabel Haynes Bode,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12. 汉译本可参考摩诃那摩等:《大史——斯里兰卡佛教史(上)》,韩廷杰译,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30-53页。可见,南传和北传佛教在对待迦腻色伽王和迦湿弥罗结集的态度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从《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北传佛教出身的玄奘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迦腻色伽王和迦湿弥罗结集的地位,因为其将五百罗汉出走迦湿弥罗归咎于阿育王笃信外道,这明显是为了衬托迦腻色伽王的形象以及迦湿弥罗结集的合法性。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钱币学和铭文。马歇尔在塔克西拉的两处主要遗址(西尔卡普和斯尔苏克)中一共出土157枚迦腻色伽一世的钱币,其中有44枚的图案是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太阳神米特洛(Mithro,很可能就是密特拉)、28枚是命运女神安娜希塔/纳奈亚(Anahita/Nanaia)、21枚是月亮神玛奥(Mao)、20枚是大地神阿索(Athso)、19枚是风神(Oado)、14枚是四臂Oesho神,只有3枚印有佛陀。*J. Marshall, 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788.而从美国钱币学会收藏的迦腻色伽一世金币上看,除了上述提到的神灵以外,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的智慧神Manaobago、仁慈之神Mozdooano和战争与胜利之神Orlagno的图像。*D. Jongeward, Joe Cribb and Peter Donovan,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5, pp.57-64.此外,在著名的腊跋塔克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中,迦腻色伽一世还宣称自己的王权来自于娜娜女神。可见,琐罗亚斯德教神灵才是迦腻色伽一世时期最为常见的神灵,迦腻色伽王对待佛教的态度恐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另一个争议点出现在迦湿弥罗结集的参与者上。据《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结集主要得到了贵霜国王迦腻色伽的支持,其举行地在迦湿弥罗(当时的克什米尔),参加的高僧有胁尊者、世友和其他499位高僧,结集的成果主要包括《邬波第铄论》《毗奈耶毗婆沙论》《阿毘达摩毘婆沙论》等共30万颂。*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31-334页。目前,此次结集的大部分经文已经失传,唯有《大毗婆沙论》等还有流传。从留存的比较完整的《大毗婆沙论》来看,这次结集显然还是以说一切有部的经典为主。吕澂先生对此有过十分精彩的解释,即《大毗婆沙论》实际上源自说一切有部中的迦湿弥罗派,该派的代表是迦旃延尼子,他曾著有《发智论》一经,其弟子后来主要在克什米尔一带传教,《大毗婆沙论》正是以《发智论》为基础而创作的。*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56页。因此,参加克什米尔结集的高僧很可能出自说一切有部,而并非大乘佛教一派。
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出土于白沙瓦附近的迦腻色伽一世的舍利盒上就有“这一虔诚的供奉物是为了一切众生的繁荣和幸福,由建筑师Agiala,在迦腻色迦普拉城,伟大君主的佛塔,为接纳一切有部的传教者而供奉”的铭文。*H. Loeschner, “The Stūpa of the Kushan Emper or Kanishka the Great, with Comments on the Azes Era and Kushan Chronology,” in Victor H. Mair, ed., Sino-Platonic Paper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Number 227, July, 2012.这就表明说一切有部在迦腻色伽时期依然占据着较高的地位,克什米尔结集很可能也是由这派僧侣所主导,把克什米尔结集作为大乘佛教诞生的标志显然也不是十分合适。
那么,大乘佛教是如何传入贵霜帝国的呢?笔者认为,大乘佛教在贵霜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事实还是可以成立的。据《高僧传》,月氏人支娄迦谶曾于东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主持翻译了《道行般若经》《楞严经》和《阿阇世王宝积经》等十余部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1页。可见,最迟在公元168年之前,大乘佛教的相关典籍就已经出现并传播到了中国。不过,大乘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很可能是得益于贵霜帝国的建立与扩张,而并非迦腻色伽一人或克什米尔结集一事之功。
一般认为,大乘的意思就是“大车”“大道”,它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解脱,更宣扬普度众生,让众生也得到解脱,其理想的个体就是菩萨。在大乘佛教看来,证得小乘佛教的阿罗汉果并非修行的最高成就,它只不过是修行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修菩萨行,普度众生,从而证得最高的佛果,达到成佛。*A. L. Basham: A Culture History of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93-95.由于是从大众部演化而来,大乘佛教最初主要流行于印度中南部地区,仅有部分的大乘佛教徒在印度西北部传教。贵霜帝国的扩张改变了这一现状,尤其是迦腻色伽一世将疆域扩展到恒河中上游地区时,大乘佛教徒开始有机会大规模进入印度西北部。
在众多北进的僧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鸣,他是大乘佛教的奠基人之一。在《付法藏因缘经》和鸠摩罗什翻译的《马鸣菩萨传》中都有马鸣作为人质被带到印度北部,后来其佛法折服当地国王的故事。*可参见《付法藏因缘经》《马鸣菩萨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东京: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第297-322、183-184页。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相对于南部的案达罗王朝和其他小国,尊崇佛教的贵霜帝国对于佛教徒而言更具吸引力,印度中南部的大乘佛教徒借此大批进入贵霜帝国并非没有可能。真正的情况可能是大乘佛教最早诞生于印度中南部,借贵霜帝国向恒河流域扩张之机,向贵霜帝国境内渗透,再加上贵霜帝国国土广大,境内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民族,相对于繁琐的上座部,大乘佛教源自大众部,教义比较宽容,善于吸收其他部派的合理成分,更容易争取到信众,自然也就得到了贵霜帝国境内不同民族的支持,得到了广泛扩散,并最终传入了中国。
不过,迦腻色伽王对佛教的弘扬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因为从印度—希腊人、印度—塞人和印度—帕提亚人时期开始,佛教就逐渐被统治者用作政治目的。这势必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后继者贵霜人。从斯拉瓦所收集的铭文看,以迦腻色伽名字为标记的铭文一共有67篇,其中,有近40篇涉及到佛教活动,*S. Shrava, Dated Kushana Inscriptions, New Delhi: Pranava Prakashan, 1993, pp.4-50, 139-148.显示出佛教在贵霜帝国的重要地位,迦腻色伽对佛教的支持应该可以成立。不过,迦腻色伽王对佛教的尊崇并不代表他要皈依佛教,其目的是为了安抚国内的佛教徒,巩固自身的统治。从40多篇涉及佛教的铭文的出土地点来看,它们主要集中于秣菟罗、憍赏弥等重要的佛教遗址,其他贵霜城市出现较少。可见,贵霜国王的这些佛教活动主要还是面向佛教徒,争取他们对贵霜帝国的支持,而不是有意识地向整个帝国宣扬佛教。
三、多元融合:佛教和佛教艺术在贵霜帝国迅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前文基本上否认了佛教曾作为贵霜帝国国教的观点,那么,推动佛教和犍陀罗艺术在贵霜帝国时期迅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佛教与其他文化因素在贵霜帝国时期的互动做进一步的分析。
除佛教之外,贵霜帝国境内流行最广的当属琐罗亚斯德教。就在佛教由南向北逐渐扩散的时候,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的波斯文化也逐渐向南亚次大陆传播。犍陀罗语的出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按照马歇尔的考证,犍陀罗一地曾是阿黑门尼德波斯帝国的一部分,阿黑门尼德波斯帝国官方语言阿拉米文通过公文的形式,逐渐传入印度西北部,并与当地方言(Prakrit,又叫犍陀罗语)进行融合,逐渐演化出了后来贵霜帝国铭文中常见的佉卢文。*Marshall, Taxila, Vol.1, p.15.不过,由于阿育王弘扬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在孔雀王朝时期的发展相对缓慢,直到印度—希腊人统治时期,它才在犍陀罗地区逐渐站稳脚跟。
随着贵霜帝国的建立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兴都库什山南北的联系逐渐增强,贵霜帝国境内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数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也使得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与佛教几乎并驾齐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越了佛教。依据美国钱币学会2015年出版的最新钱币图录,贵霜钱币上的琐罗亚斯德教神祇形象种类繁多且最为常见。以神灵形象最为多样的胡韦色迦一世钱币为例,在其钱币上共出现过30多种神灵形象,其中有15种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神灵。*Jongeward, Cribb and Donovan,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coins, p.268.
贵霜帝国时期最重要的琐罗亚斯德教遗址当属苏尔赫·科塔尔遗址。该遗址由两座神庙组成,较大的一座为长方形,南北横长35米,宽27米,大门朝东。中间为方形正殿,正殿中心有方形石坛,两侧及背后建有配殿。大庙外围北、西、南三面,用土坯和石块筑起院墙。墙上建有方形望楼,墙身建有壁龛,龛内置彩色塑像和石灰岩制作的雕像。较小的一座神庙位于较大神庙的左侧,其结构与大庙相同。由于两座神庙石坛的凹槽里都遗留了大量燃烧后的灰烬残余,所以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些庙宇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火神庙。*D. Schlumberger, “The Excavations at Surkh Kotal and the Problem of Hellenism in Bactria and India,” Albert Reckitt Archaeological Lec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77-95.结合相关的雕塑和铭文可以判断,苏尔赫·科塔尔神庙群的主要建筑时间是在迦腻色伽一世初期。*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333-334页。对于这些神庙,沃尔维克·保尔(Warwick Ball)曾提出过一个猜想,他认为,苏尔赫·科塔尔神庙的装饰中存在大量的佛教主题,很可能这些神庙是一庙多用,既作火神庙使用,也对佛教等其他宗教开放。*W. Ball, The Monuments of Afghanistan: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Co Ltd, 2008, p.266.
类似的混用也出现在中亚的铁尔梅兹遗址,只不过形式上略有不同。斯塔维斯基(B. Y. Stavisky)就曾经在卡拉·捷佩的佛寺遗址中发现过琐罗亚斯德教圣火坛的遗存。*J. Harmata, Fom Hecateus to Al-huwarizmi, Hungary: Union Acacenque International, 1984, pp.112-114.而据2011年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组织的实地考察,在铁尔梅兹的法雅津捷佩的佛寺遗迹中,也同样发现过琐罗亚斯德教火坛的遗迹。*任萌:《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考古调查:前贵霜时代至后贵霜时代》,《文物》2015年第6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猜想可能是受丝路经济特点和贵霜帝国政策的影响。哈尔马塔在《中亚文明史》中曾大致提到过,中亚绿洲中有相当一部分灌溉农田属于宗教寺院,特殊的僧侣阶级还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224页。由于佛教本身比较宽容,这些相对富裕的寺庙必然会成为丝路商人、旅行家们重要的庇护所之一。再加之贵霜帝国也鼓励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为了方便前来投宿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贵霜僧人在寺内单独开放一处琐罗亚斯德教圣火坛,供这些人来祭拜,也合情合理。
伴随着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庙宇的并存与混合,两种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逐渐出现。融合了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特色的“未来佛”——弥勒佛就是最好的例子。依据亚历山大·索普的研究,弥勒信仰很可能来自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密特拉崇拜,因为弥勒的发音与密特拉的发音基本一致,而且弥勒佛所带的救助思想也是早期佛教没有的,很可能是佛教受到其他宗教影响后的新变化。*A. Soper, “Aspects of Light Symbolism in Gandhāran Sculpture,” Artbus Asiae, Vol.12, No.4, 1949, pp.265-266.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弥勒佛并非起源于伊朗的密特拉神,而是来源于吠陀经中的一个叫Maitri的神,它和伊朗的Mithra有一定的联系,他们虽然都是沿袭自远古雅利安人的宗教神灵,但两者在功能上并没有任何交集。*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H.D. Thesis, Ohio State Univercity, 1983, pp.358-394.
虽然有关弥勒形象的起源与发展,学界未有定论,但笔者更倾向认为,不管其背后的佛理如何,弥勒佛形象能够在贵霜时期广泛出现,必须放入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量。从考古发掘上看,早在月氏人进入巴克特里亚之时,密特拉的信仰就被大月氏人所熟知。在著名的卡尔恰扬遗址的雕塑上出现的就可能是密特拉的形象。*V. P. Nikonorov, The Armies of Bactria 700B.C.-450A.D., Vol.2, Storkport:Montvert Publications, 1997, p.64.由于卡尔恰扬遗址并未出现佛教的图像,月氏人应该是先接受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密特拉神,然后才接触到佛教。因此,贵霜人很可能是在接触到原始佛教中的弥勒佛之后,才自然而然地将之与他们所熟悉的密特拉神相联系,再加上贵霜帝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说一切有部本身就主张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法,作为未来佛的弥勒佛广泛出现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琐罗亚斯德教之外,得益于贵霜帝国时期不断发展的海上贸易,来自东地中海的希腊化艺术和罗马艺术也持续影响着贵霜帝国内的佛教艺术。不过,由于贵霜帝国文化宽容政策的支持,有关犍陀罗艺术的“希腊起源说”和“罗马起源说”在贵霜时期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矛盾。主张“罗马起源说”的本杰明·罗兰德曾专门撰文分析过中亚各遗址(卡尔恰扬遗址、达尔弗津捷佩遗址等)的人物造像,认为流传于这些地区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风格的造型艺术曾对佛教产生过深远的影响。*B. Rowland, “Graeco-Bactrian Art and Gandhāra: Khalchayan and the Gandhāra Bodhisattva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25, 1971, pp.29-35.虽然,罗兰德在文章的最后一再强调其观点并未与自己先前主张的“罗马起源说”相矛盾,但从当时的历史来看,罗马艺术在中亚的传播虽只是借助于舶来的作为商品的艺术品,但也难排除一些希腊化的罗马艺术家或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希腊艺术家这时来到贵霜帝国的控制区域,这些人带来的恰恰是希腊化的罗马艺术或罗马艺术品,因此,佛教艺术应该主要还是受到原来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持类似观点的是雷卡·莫里斯(R. Morris),他梳理了苏联学者在中亚佛教遗址的考古活动,虽然其结论并没有明确指明希腊巴克特里亚艺术和犍陀罗艺术的关系如何,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希腊巴克特里亚艺术对佛教艺术的影响。参见R. Morris, “Some Observations on Recent Soviet Excavation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the Problem of Gandhāra Ar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03, No.3, 1983, pp.557-567.犍陀罗艺术在贵霜时期能够走向繁荣,其背后肯定有贵霜人对希腊化文化的吸收与融汇。*正如杨巨平教授所说:“如果我们承认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古典因素,事实上就等于承认了希腊文化的作用,因为这些古典艺术因素本质上源于希腊文明,罗马人不过是它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而已,而且罗马帝国东部(埃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人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希腊人或其后裔,政治上他们是罗马帝国的臣民,但在血缘上尤其在文化上他们还是希腊人。他们可能是最早来到印度的所谓‘罗马人’。”参见杨巨平:《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对于贵霜人而言,希腊风格和罗马风格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他们根本不会去区分哪些艺术风格属于希腊,哪些艺术风格属于罗马。尤其是贵霜帝国控制印度河河口附近的港口与罗马帝国建立起联系之后,大量罗马风格的艺术品和罗马东方带有浓郁希腊风格的艺术品同时涌入贵霜帝国境内,贵霜人肯定无法分清它们与原来希腊艺术品之间细微的区别,所以,贵霜的工匠很可能是根据各地不同的艺术风格并结合本地传统的制作工艺制造了当地的佛像,无论其所仿效的风格是来自希腊还是罗马。
最后,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形成很可能也受到了贵霜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犍陀罗艺术中的布施者形象。从“黄金之丘”出土的大量黄金陪葬品来看,贵霜人的前身大月氏人很可能比较讲究来生或者死后的享受。贵霜帝国建立后,尤其是迦腻色伽王接受佛教以后,部分贵霜佛教徒自然也要为自己的来生做打算,他们向佛寺大量捐赠财物以祈求福祉,前文提到的迦腻色伽舍利盒上的铭文就是最好的例子,受此影响,佛教供养人的形象逐渐出现,并成为日后佛教壁画和造像的重要主题之一。
此外,日本学者田边胜见曾提出,崇拜佛像的做法很可能是由贵霜人带到了犍陀罗地区。因为大月氏人在中亚时已经接触到了波斯文化中对宗教神灵和死去国王的崇拜,受此影响他们才创造了用于崇拜的佛像。*田边胜见:《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这一说法显然过于片面,崇拜偶像和英雄人物的显然并非只有波斯人,希腊人和贵霜人同样也有类似崇拜神灵和英雄人物的做法。希腊人自不必说,卡尔恰扬遗址中发现的早期月氏王族雕像群、苏尔赫·科塔尔遗址出土的迦腻色伽王半身像以及秣菟罗附近的马特王家神庙遗址都明确地证明了贵霜人确有崇拜偶像和先贤的传统。所以,与其说是贵霜人将偶像崇拜带到了犍陀罗,不如说是有偶像崇拜传统的贵霜人的扩张强化了当地已经流行的偶像崇拜行为,这才对后来佛像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同时,贵霜人并不是随意地选择偶像,而是有自己的考虑。在贵霜人看来,其境内民族众多,文化元素复杂,原来的法轮和圣树等形象已经无法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众的需要,而“强调神人同形同性”的希腊宗教,不但神灵形象众多,而且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已经被中亚和西北印度的不同民族所熟知。无论是印度—希腊人钱币、印度—塞人钱币、印度—帕提亚人钱币还是早期贵霜钱币,其上都有希腊神灵的形象出现。所以,贵霜人实际上是有目的地选择了希腊神祇形象作为佛像的基础。以佛教艺术中常见的护法金刚为例,据邢义田考证,这一形象实际上源自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其形象起初主要出现在远东希腊化王国的钱币和雕塑之上,后来,这一形象被佛教所吸收,演变为了佛教的护法金刚。*邢义田:《赫拉克利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传播与演变》,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7页。
四、结 语
总的来说,犍陀罗艺术能够产生并繁荣于贵霜时期,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迦腻色伽一世对佛教的推动,而是在于贵霜帝国本身对丝路不同文化的宽容。综观整个贵霜帝国的发展史,虽然其领土从中亚一直延伸到了恒河中上游,但贵霜人并没有独尊任何一种宗教,迦腻色迦王皈依佛教一说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贵霜人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给予其他文化必要的尊重,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但在客观上却造就了多元文化并存和融合的局面。以此为契机,佛教艺术吸收了希腊化文化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和贵霜本民族文化等因素,最终形成了具有浓郁多元文化特点的犍陀罗艺术。从现实意义上讲,贵霜帝国所在的中亚和印度西北部正是目前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地区,这些地区文化上虽以伊斯兰教为主,但民族成份复杂,各地传统也各有差异,贵霜人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对于我们发展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往来,不无借鉴意义。
(本文写作得到导师杨巨平教授的悉心指导,特致谢意)
(责任编辑:史云鹏)
Multi-culturesandtheGandhāraArt:aFurtherDiscussionontheDevelopmentoftheBuddhismandBuddhistartintheKushanEmpire
Pang Xiaoxiao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Gandhāraart originated from Greece, Rome, India, Iran or Sakas, Scholars have argued for a long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at it from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Kushan Empi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Gandhāra art. As nomads, Kushanas were always absorbing and integr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other cultures. Although the purpose of them was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they also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Buddhist art to absorb the Hellenistic culture, Zoroastrian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Kushanas. All these provide the basis of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origin of Gandhāra art.
multi-culture, the Gandhāraart, the Kushan Empire
K351.2
A
1006-0766(2017)06-0074-08
庞霄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15ZDB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