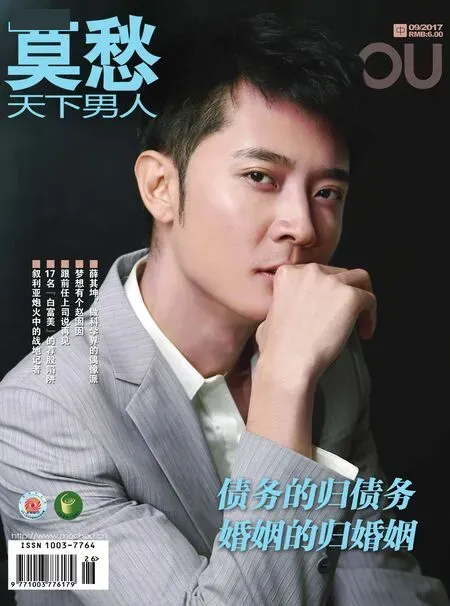叔公陈寅恪笃定务实,安心治学
□强江海
叔公陈寅恪笃定务实,安心治学
□强江海
陈寅恪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的侄孙陈贻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和叔公相处的时间很短,那时叔公的双眼已经失明了,但是在我心里,他却是独立与自由最好的践行者。”
只为读书而读书
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陈家祖孙三代居住在湘江东岸城北的“蜕园”。在那里,陈寅恪和七个兄弟姐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3岁时,陈寅恪便跟随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的生活是贫苦的,陈寅恪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而已。即便如此,陈寅恪仍苦读不辍。
此后,陈寅恪又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求学。前后十四年的时间里,陈寅恪游学日、欧、美,精通英、法、德、日等二十余种语言。
哪里有好大学,陈寅恪就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一生读过十多所大学。初到美国留学时,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人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有一天,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
陈寅恪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但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陈寅恪多次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然而却未怀揣一张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时,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寅恪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便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有何著作?”梁启超摇了摇头说:“他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
听完此言,曹云祥皱紧眉头,为难道:“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清华不请他,国外的大学也会请他的。”接着,梁启超向曹云祥介绍了柏林、巴黎几位大学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一听,觉得陈寅恪确实是个人才,急忙登门礼聘。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向陈寅恪请教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他被大家称为“活字典”“活辞书”,这与陈寅恪多年来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这样的习惯贯穿他的一生,也带入了他对子女的教育中。
陈寅恪一生育有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个孩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对读书的理解也是为了增长知识,从没有想过利用所学去谋求什么名利。

陈寅恪一家
我的活计就是教书
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大学,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兼课,教授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陈寅恪上课时,常用一块黄色包袱,包上几本参考书籍夹在腋下,不修边幅的他被清华学子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
正因为爱书、喜书,所以陈寅恪一生治学严谨,他对学生说:“书本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然而,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陈寅恪的眼疾得不到及时医治,右眼因视网膜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即使如此,陈寅恪也没有落下一节课,他备课与写作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陈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然而就在目光蒙眬之中,他竟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
眼部手术失败,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成了盲人教授。后来的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倔强道:“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清华为了方便他,干脆把课堂设在他家中最西边狭长的大房间内,陈寅恪就坐在家里一张椅子上讲授《元白诗笺证稿》,每次讲两个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
这个教室只能容纳二十多个学生,听课的有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研究生、讲师、副教授等。此时的陈寅恪体弱不能板书,只能由助手王永兴帮忙把引文、关键词和学生听不清的字句等写在黑板上。
陈寅恪对教学的严谨,让大女儿陈流求记忆深刻。陈寅恪双目失明后,很多研究工作都要在助手的帮助下才能进行。有一次,他已经上床睡下了,突然想起自己的作品里有一处需要修改,便念叨着,家人说要帮忙记下,可他怕记错位置,只有助手才知道确切位置,便没有应允。那一夜,害怕忘记修改的地方,陈寅恪一夜无眠。本就体弱的陈寅恪,为了教学,时常睡不好觉,每次看到父亲早起憔悴的神情,陈流求就很心疼,但陈寅恪的行为却让她一生受益。多年后,陈流求成了一名医生,不论多累,只要在工作岗位上,她时刻记着要对病人负责,不敢有丝毫松懈。
陈寅恪的认真严谨不仅让自家孩子受益匪浅,侄孙陈贻竹也是感触颇深。第一次见到叔公,是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上学时。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当时住在中山大学康乐园东南区1号楼,有时休息日,陈贻竹便会去看望叔公,扶着他到楼下门外的白色小路上散散步。在陈贻竹眼中,叔公是一位安静的长辈。让陈贻竹记忆深刻的是,在叔公家二楼西面有个大阳台,里面密密麻麻地排了十几把扶手上带小桌板的椅子,墙上挂着小黑板,旁边放着藤椅,这就是陈寅恪授课的教室。有时临走,陈贻竹会到教室里坐一坐,想象叔公坐在藤椅上讲课的样子,想着学长们说的叔公双目失明,上课每每都有新内容的话,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
双目失明却心如明镜
在抗战时期,陈寅恪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硬骨气,更让陈贻竹肃然起敬。
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聘书,决定举家赴英国。陈寅恪一家到香港准备护照,但由于欧战爆发最终困居港岛。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数万日军进攻香港,香港沦陷。陈寅恪挤不上逃难的飞机,以致滞留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离开暂时任教的港大,在家闲居。因为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全家生活陷入困顿之中。陈美延曾回忆道:“孤岛上生活艰苦,交通阻断,学校停课,商店闭门。百姓终日惶惶不安,家家没有存米,口粮更是紧张。”
眼看春节来临,陈寅恪一家生活无着。恰在此时,一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日军军部遂行文给香港司令部,要他们不可烦扰陈教授。驻港日本宪兵得知陈寅恪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便极力笼络他。司令部派宪兵给断粮多日的陈家送来了面粉,但陈寅恪断然拒绝。于是,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便往外拖,坚决不吃敌人的面粉。后来,日本人强付陈寅恪40万日元,让他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拒之。
那年除夕夜,困居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没有收纳日本宪兵送来的面粉,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算是过了一个春节。
没事的时候,陈贻竹喜欢翻看叔公的作品,书里流淌的不仅有陈寅恪安心治学的气魄,还有对家人的殷殷期盼,更有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的情意绵绵,是国事家事,更是一种情怀。他说:“在外人眼中,叔公是一代大师,爱国爱家,尽显男儿气概。但在我眼中,他就是那个静静地在白色小路上散步的老人,平静、淡然。”(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编辑吴忞忞mwumi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