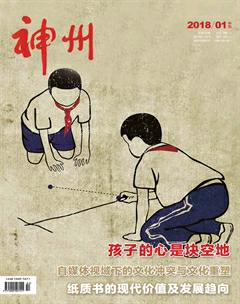浅析古代诗歌中“诗瓢”的文化意涵和表现
摘要:唐朝诗人唐求的事迹,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逐渐演变为了“诗瓢”的典故和意象,被赋予了具体详细的文学内涵。这种文学意涵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充实,到了明朝,“诗瓢”典故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新的转折,即与“酒瓢”等其他“葫芦”意象产生了融合,形成了丰富的“诗瓢”文化。
关键词:诗瓢;文化;葫芦;隐逸
“诗瓢”作为一个文化典故,产生于晚唐时期,但在当时并未发展成为有固定意涵的诗歌意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后,“诗瓢”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意涵,除了有对于“诗瓢”原始意涵的继承和补充外,还一部分是通过和其他“瓢”典故的融合,实现了内涵的升华,增加了“诗瓢”意象在诗歌中的表现力。
一、“诗瓢”的产生和内涵
“诗瓢”的故事发生在唐朝,但最早的记载却是在宋朝。朱胜非的《绀珠集》、曾慥的《类说》都提到过这个故事,但内容简略。黄休复所撰《茅亭客话》卷三中,有条目名为“味江山人”,对于这个故事的记载较为详细:
唐末蜀州青城县,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纯悫,笃好雅道,放旷疎逸,几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醺酣而归。非其类不与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内于大瓢中。二十余年莫知其数,亦不复吟咏。其赠送寄别之诗,布于人口。暮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识者云:唐山人诗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润损坏,十得其二三。凡三十余篇行于世。……有隐逸得志者,以经籍自娱,诗酒怡情,不耀文彩,不扬姓名。其趋附苟且得无愧赧唐山人乎。[1](《茅亭客话》卷三)
所以“诗瓢”其实是唐朝诗人唐求保存并传播自己诗作的一个方式。
唐求,《唐诗纪事》又称唐球,生卒年不详。唐求为何会选择“诗瓢”这种转播方式?先从唐求本人性格来说,至性纯悫。他至真至纯,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行为方式不会受到世俗的约束。而历代对于唐求的评价中,“放旷疎逸”的形容出现频率也非常高,所以在文献中的唐求都更偏向于是一个方外之士的形象,并称其为“唐山人”。唐求生活在青城,结交的人物本来就以和尚、道士、居士、隐士这类出世之人居多,加之这样的性格,就难免受青城道家影响,行为更加放荡不羁,也就能理解“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醺酣而归”的行为,和“非其类不与之交”这种非常主观的交友准则了。但是,从“诗瓢”典故有记载以来,所有的文献中都提到了唐求的一句话,即“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其中的“苦心”将作何解释,是了解唐求为人的一个切入点。有关唐求的记载,都只说他是一位超然脱俗之人,这样的一位方外之人,会存有什么样的苦心。元朝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为唐求立传,曰:“值三灵改卜,绝念鼎钟。”[2]唐朝末年是一个动荡不安、改朝换代的时期,辛文房认为唐求并非没有建功立业之心,但是随着唐朝的衰亡,唐求又处于山高皇帝远的蜀地,在现实中能实现功名事业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在这样的时代现实背景之下,唐求也不得不放弃。《山居偶作》中的“趋名逐利身,终日走风尘”,虽表现了他对于世俗权力的不屑一顾,但《唐才子传》中“(诗作)无秋毫世俗之想”[3]的评价并不符合事实。或者说,唐求将自己对于名利的追求深埋心底,停止了进入仕途的行为,转而将这些情感寄托于诗歌之中。唐求还留有几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所以当他大志未报之时,如果想将他的诗作、他的思想传达出去,自然是要寻求一种方法。元朝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提到唐求的诗作,认为他的作品“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4],有着较明显的个人风格,但是唐求本人却“人多不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求“诗瓢”的选择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博取人们的眼球,自然就受到更多的关注。
另一个方面,唐求在诗歌创作上,有着较高的追求。但自古以来,诗歌的创作与构思,都很难达到完美。如潘大林,虽日日有诗思,已经构思出“满城风雨近重阳”句,但却被催租之人打断,且再无后续。所以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告诫后人:“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明胡震亨所撰《唐音癸签》载:“唐山人(球),一生苦吟,诗思游历不出二百里”,可见唐求对于诗词语言韵律要求较高。但唐求放入瓢内的诗歌,“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内于大瓢中”,是他随时想到的句子,并不一定都是完整的诗歌。现存的唐求诗作,留在瓢中被后人发现的,不足其全部诗作的十之一二,流传至今的数量更少。但有如此数量已属不易,这是因为在遇水时,可将重要物品放入瓢内,保证其干燥洁净,瓢的这种储物特性,可以使唐求的诗作传播到较远的地方,他吟咏而得的佳句也就能被更多人读到。这也就能解释唐求所说“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中的“苦心”究竟为何了。除了他不得已而“绝念鼎钟”的选择外,还有对于诗思、诗句的追求。
二、“诗瓢”与“弃瓢”的融合
在古代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与“瓢”有关的意象或典故,并不只有“诗瓢”一个。接受范围更广、使用频率更高的,是“弃瓢”意象,即“许由弃瓢”典故。《庄子》记载: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汉代蔡邕在其《琴操》中对后面的内容进行了补充:许由认为“尧让天下”是对他的侮辱,于是在颍水之滨临河洗耳。后代多称赞这种行为,认为这是许由品行高洁、不为世俗所扰的表现。
在“弃瓢”和“诗瓢”典故出现之始,二者是有明确区分的。但鉴于唐求和许由二者极为相似的隐士身份,在后世的引经据典中,二者的形象也就发生了混淆。在诗歌方面,最早南宋末年,方凤就在《(附)方梓和诗》中提到过:endprint
新楼招乐偶今朝,与客登临四望遥。竹日晖晖侵酒斚,松风沥沥响诗瓢。
横烟曲径樵初过,落鹜空江叶正飘。看取他年欹醉帽,还思簪菊旧垂髫。
方凤作为南宋遗民,在宋朝灭亡后,遁归隐于仙华山。在这首诗中,方凤营造了一个松竹交映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其中的诗瓢,以在松竹林中,悬挂在高处,迎风作响的形象出现。元代诗人袁桷借用此典故,写出了“诗瓢淅沥风前树,雪在深村月在梅”。袁桷在《王秋山》中的“苔荒琴荐春无迹,风搅诗瓢树有灵”句,除了诗作中提到的是“诗瓢”,结合诗歌意境和上下文意思来看,尤其是“风搅”二字,完全是“弃瓢”典故。可见此时的诗作中,对于“诗瓢”“弃瓢”二意象的区分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三、“诗瓢”形象的补充和拓展
到了明清时期,“诗瓢”“弃瓢”二意象的融合也在诗歌中得到了继承。如区大任《游铁泉精舍》:
岩前旧是子云家,门掩飞泉一道斜。石室竟藏《高士传》,山园犹种故侯瓜。
虎看丹灶多年火,树挂诗瓢几度花。小草尚惭曾出洞,至今猿鸟怅烟霞。
诗人用皇甫谧《高士传》、故侯瓜、丹灶意象,结合诗瓢,营造了一个隐居者的生活环境。读的书是记录了从上古时期道魏晋时期诸多隐逸高士生平事迹的《高师传》,种植的是布衣种植的故侯瓜,看的是烧制弹药的丹灶,在树上悬挂的是寄托内心无法言说情怀的诗瓢。这些意象的罗列,是从侧面展现铁泉精舍及其主人的审美倾向,即对隐逸之士的赞叹和敬仰。“石室竟藏《高士传》”中的一个“竟”字,也反映了游览者,即诗人本人的惊讶之情。朱淛的《和韵奉招方岩兼呈马师山》“石掌横撑当酒案,松枝低亚任诗瓢”句也是两种意象的结合。
但是在这一时期,包含了“诗瓢”意象诗歌的特点,并不是多重意向的使用,而是丰富了诗瓢出现的环境背景,使“诗瓢”这一意象更加生动。其中较为突出了一点就是诗与酒的结合。如陈献章的《袁晖久在白沙候容贯不至以诗来和之》:“冷雨凄风寄我台,香林草屋梦空回。山中酒伴何曾见,水上诗瓢只谩来。”此诗中诗瓢的形象和唐求时没有太大区别,却和酒这一意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诗与酒是山中孤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明清的诗歌中,诗瓢依有了“酒”的加持,也就不再是唐宋时高洁出尘的形象了。它更多的是代表诸多文人的生活态度,而非确切的精神追求。如唐文凤《谢平川耆民钟尚义寄鲊(其四)》:“瓮潭昔有铜环鲤,何事而今碎雪鳞。慰我老饕尚能赋,诗瓢酒杓细分春。”唐求时的诗瓢是一个可以贮物的完整葫芦,此诗中的诗瓢放佛从云端跌落人间,褪去一身孤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破瓢,还成为了酒杓,充满了烟火气息。又如明蓝仁《次韵云松西山送别张兼善》:
西山一径绿阴稠,梅雨晴时送客游。对榻更期何夕再,抱琴深入白云幽。
微风药草熏衣袖,尽日诗瓢挂杖头。闲说道人犹惜别,呼尊剪韭夜相留。
张兼善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医生,人物生平无明确记载,从诗中的“微风药草熏衣袖”句也能看出,张兼善是一位整日与草药打交道的人。但诗中却未明确提出,作为一位医者,他的草药都贮存在何处,反而以一句“尽日诗瓢挂杖头”表明诗瓢是随身之物。这样的描写与张兼善的形象明显不符。在我国的历史上,瓢或者是葫芦,都有许多的实用功能。早在诗瓢出现之前,葫芦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密闭和防水的特点,而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贮存器皿,如酒葫芦、药瓢等。陆游就在诗中写到过“药瓢藤杖伴清闲”,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牋》卷八中也提到“若用杖头挂带乘药者,二三寸葫芦亦妙”。可见瓢若用做药瓢之时,通常也是挂在杖头之上的。修道或远行之人,杖头挂几个葫芦也是常见的装扮。但此时的“诗瓢”,它在这首诗歌中,就是一个随行路上存放诗句的工具,就像药瓢用来存放草药,酒葫芦用来沽酒一般。蓝仁特别指明“诗瓢”,一方面是塑造张兼善的医者形象所需,明髙启诗《送医士宋君之江上》中亦有“诗瓢与药囊,此去即行装”句,来描述医者的行囊装备;另一方面,是站在一位送别者的视角,希望张兼善这位即将远行的游子,多多写诗作文,记录路途事迹,保存在诗瓢之中,作为二人书信往來的内容,也是从侧面表达他送别诗的不舍之情。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诗瓢”在明代,已经没有在唐求手中的方外之人的脱俗气质了。
同样是明代诗人黄仲昭的“六年守岁宦途遥,何幸乡园度此宵。老至生涯惟药裹,春来心事付诗瓢”似乎还和“诗瓢”的原始意涵有些关系,但童轩的“密雨随风急,虚斋日晏眠。诗瓢髙挂壁,茶灶冷炊烟”就不是了。童轩的时写于他卧病在床之时,诗瓢高挂于墙,是因为他身体虚弱,无暇吟诗作对,与后面的“茶灶冷炊烟”的原因是一样的。从这首诗歌中,我们看不出作者是否有归隐之心,只能看出一个被荒废的器物。所以这时的“诗瓢”似乎已融入了寻常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到了清朝,朱彝尊所撰《王鹤尹诗序》中,提到王鹤尹“君独澹然于荣利,好为山水,游诗瓢酒榼,肆志娱衍,与海内名流继和,间倚声度曲”,此时的诗瓢已经是文人们举办活动、相互唱合娱乐时的玩物了。不仅其内涵发生了变化,连材质都在与时俱进。吏部尚书宋荦有诗名为《?子》,他在诗中提到,可将其留作诗瓢挂在房间中。但在明朝王绂的五言律诗《赋椰瓢》中,椰瓢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清朝时。诗曰:“炎方充贡物,颁赐出金门。外表匏瓜质,中涵雨露恩。香甘宜作果,坚确可刳尊。铭刻须珍袭,留荣及子孙。”这是南方上贡的贡品,也是用来赏赐臣子的珍品。
“诗瓢”典故源于唐末唐求,在后世的文学中,演变成隐逸之士的代名词,成为一个包含远离世俗含义的文学典故和诗歌意象。但瓢终究是世俗之物,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唐求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消失后,“诗瓢”超然脱俗的形象也就不复存在。但“诗瓢”尚存,还与其他的意象实现了融合,如“弃瓢”“药瓢”“酒瓢”等,还成为了文人雅士、吟诗作赋之人的随身之物,在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最终成为了一个被一般读者都能接受并理解的诗歌意象,而且在诗歌的创作中流传了下来。
参考文献:
[1]陈伯海主编;孙菊园,刘初棠副主编;陈伯海书系主编;朱易安,查清华副主编,唐诗汇评 增订本 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第4514页
[2](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京华出版社,2000.05,第215页
[3](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京华出版社,2000.05,第215页
[4](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京华出版社,2000.05,第215页
作者简介:王淼(1993—)女,汉族,山东济宁人,文学硕士在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明代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