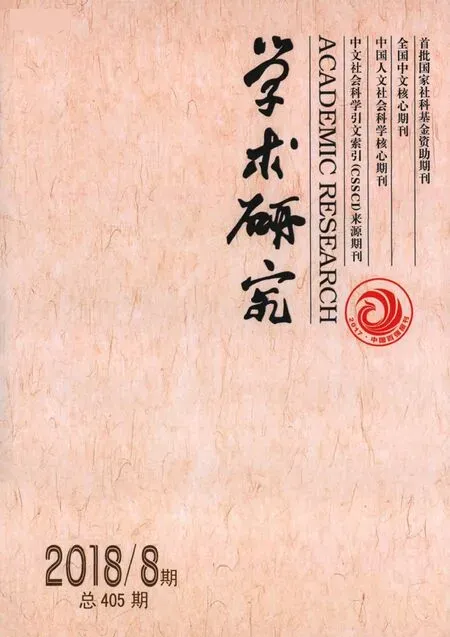公共服务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考察*
张 琦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后,a《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学术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重新变得热烈起来。这些讨论或侧重于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或侧重于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的来讲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最大限度地增进共识。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例如有人认为“市场决定”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传统上认为非经济的领域也应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b迟福林:《落实“市场决定”还需要解放思想》,《经济参考报》2014年8月11日。而有人则认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c洪银兴:《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说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10期。再如,有人主张市场配置资源只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应是由政府决定或主导;d卫兴华、闫盼:《论宏观资源配置与微观资源配置的不同性质——兼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含义和范围》,《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而有人则提出即便是宏观经济领域的调控也应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慎行。e周为民:《把握市场经济的实质,厘清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而2016年爆发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产业政策大辩论”,双方争论的核心正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a“产业政策大辩论”主要指2016年爆发于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关于产业政策的多次直接和间接争论,同时也包括其他著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田国强、李稻葵等关于产业政策的看法和观点。这场争论由于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张、林二人公开辩论即“产业政策思辨会”而广为人知。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专注于公共服务领域,对该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尝试给出我国当前处理公共服务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
公共服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以及供水、供电、公共交通、消防等公用事业,而广义的公共服务则包括所有具有公共性的商品和服务,除民生事业及公用事业外,还包括外交、环保、安全、国防等。主流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公共服务的有力武器,但公共服务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物品,因为现实中的某些公共服务属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范畴。此外,无论是公共物品还是公共服务,其提供主体都不仅仅是政府,虽然政府是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提供者。按照地理空间范围来划分,公共服务可以分为地方公共服务、全国公共服务乃至跨国公共服务。本文主要讨论地方公共服务,即主要以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为提供主体,以民生事业和公用事业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性公共服务。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脉络
政府与市场是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性,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西欧国家的封建领主制社会,还是东方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最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是封建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官府和百姓的关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等。在自然经济或封建经济模式下,市场是不重要的,只有在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技术诞生之后,市场才真正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在历史上第一次凸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b[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徐庆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年,第148-150页。
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并给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典表述。在《国富论》当中,亚当·斯密明确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限定在三个领域:(1)保护本国国民不受外国国民的侵略,即国防;(2)保护国民不受另一部分国民的压迫,即司法;(3)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c[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陈叶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85、803、815页。除此以外的领域,均应交由市场来负责。在斯密的体系里,作为“守夜人”的政府和“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是导致一国财富增长的绝佳搭配。
整个19世纪,盛行于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想是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很少,绝大部分都交给市场。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名言“供给创造需求”明确地道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理念。直到20世纪上半期,“自由放任”仍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奉行的圭臬。即便在1929年爆发于美国、随后横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也仍然坚信市场的自发调整,并不认为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大萧条”。货币主义学派掌门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美联储未能及时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是导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d[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 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巴曙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248页。不过,近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美联储并不认为增加货币供给是自己的责任。eMeltzer A. H.,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Vol.1:1913-1951, Chicagο: The University οf Chicagο Press, 2003,pp.263-264.
1936年,以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使得政府的作用在亚当·斯密给出的三个领域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防止通货膨胀、熨平经济波动,统称为宏观调控。
于是,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直到“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开始有两大转变,一是转而信奉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二是政府开始介入传统上由市场负责的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甚至走向“福利国家”。应当说,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后者的理论基础则有二:其一为“市场失灵”理论,即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统称为“市场失灵”的情形,需要政府介入;其二为社会福利思想,即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来促进社会公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之所以在“二战”之后发生重大变动,固然可归因于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和鼓噪,更是为现实的形势所迫。走出“大萧条”的泥淖和欧洲的战后重建,都需要政府挣脱“守夜人”的枷锁,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a关于西方各国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的影响因素,维托·坦茨曾有出色的归纳和论述。参见 [美]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1-100页。可以说,“大萧条”和“二战”,改变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至此,现代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已经基本成型,即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负责解决包括公共服务提供在内的“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实行宏观调控。
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各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又出现新的变化。宏观经济的“滞涨”现象与日益沉重的福利支出负担,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和福利国家的实践产生了新的质疑。在此背景下,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内阁开始掀起再私有化、去福利化改革,标志着自由放任思想的回归。不过,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归到“二战”前的状态了。
当然,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政府与市场边界,就有很大不同。以医疗保障制度为例,欧洲各国特别是北欧各国,“福利国家”的色彩更浓一些,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为人们提供医疗保障,被视为是政府的义务;而美国民众则主要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来解决,奥巴马政府旨在实现医疗保险全民覆盖的医改法案,虽历经坎坷最终于2010年获得通过,但由于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一直致力于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因而其前景十分堪忧。b杨洲:《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实施过程及其黯淡前景》,《比较》第87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86-96页。
通过“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可以看出西方各国政府自19世纪末以来的扩张趋势。如美国这一比重在1870年为7.3%,1960年为27%,至1996年则上升到32.4%;英国这一比重在1870年为9.4%,1960年为32.2%,1996年则为43%;法国这一比重在1870年为12.6%,1960年为34.6%,1996年则为55%;瑞典这一比重在1870年为5.7%,1960年为31%,1996年则高达64.2%。c[美] 维托·坦齐、 [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11页。因此,若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大政府”或“小政府”的话,可以说西方各国早已不存在“小政府”了。
二、公共服务的提供:政府还是市场?
公共服务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公共服务应由政府来提供,还是由市场来提供?由于公共服务和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涉及公共物品理论。
主流经济学对公共物品的定义主要通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条标准。非排他性是指该物品或服务无法排除那些不付费的使用者;非竞争性是指该物品或服务一旦产生就能以零边际成本向更多的消费者提供。由于这两点性质特别是非排他性的存在,使得这些物品或服务无法由市场自发提供或提供不足,因此市场失灵了。或者,即便某些物品和服务可以“排他”,但由于其非竞争性,额外增加一名消费者导致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也“不该”排他,否则就是无效率的。d哈尔·R.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八版)》,费方域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565-566页。不论是市场“不能”提供,还是市场“不该”提供,都指向同一结论: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提供。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公共物品理论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泾渭分明的:私人物品由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现状,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批评认为,医疗、教育、住房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了,a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9-44页。其理论依据正是上述新古典公共物品理论。
然而,这样的批评十分粗糙而武断,不仅因为这种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非黑即白”的选择本身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其理论基础新古典范式公共物品理论本身也存在很多缺陷。b笔者对新古典公共物品理论的缺陷曾有专文讨论,此处不赘。参见张琦:《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歧与融合》,《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1期。一般认为,新古典范式公共物品理论肇始于萨缪尔森于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在该文中,萨缪尔森第一次将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帕累托效率联系起来,并给出了公共物品有效提供(帕累托意义上的)的边际条件。cSamuelsοn P. A.,“The Pure Theοry ο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οl.36, 1954, pp.387-389.自此之后,主流经济学所谓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指的就是公共物品数量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然而这只考虑了公共物品的数量即需求方面,却并未考虑供给方面即为公共物品筹资的税费环节。除非在公共物品集体决策过程中,将数量和税费同时加以考虑,并满足维克塞尔提出的“一致同意原则”,d[瑞典]奈特·维克塞尔:《正义税收的新原则》, [美]理查德·A. 马斯格雷夫、艾伦·T. 皮考克编:《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刘守刚、王晓丹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145页。否则任何“不足一致同意原则”的集体决策,都将导致融资环节的扭曲和效率损失。也就是说,为公共物品融资的税费环节往往伴随着再分配这一导致效率损失的因素。这样的话,即便通过政府来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达到了“帕累托效率”,解决了“市场无法提供或提供不足”,但又何以保证这种效率改进一定大于税费融资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损失呢?因此,新古典范式公共物品理论就陷入了“双重标准”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来衡量公共物品的“最优”数量,另一方面却不以“一致同意规则”来衡量公共物品的税费分担安排。换言之,新古典公共物品理论只考虑了公共物品数量的“配置效率”,却忽略了在此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税费“分配非效率”;但是,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认为人们只在乎前者,而不在乎后者。
可以说,只考虑需求(公共物品数量)、不考虑供给(税费分担)这种“顾头不顾尾”的特征,正是新古典公共物品理论最大的缺陷所在。这也正是以布坎南为主要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新古典公共物品理论提出的最有力的批评。与新古典范式公共物品理论相对应,布坎南提出的公共物品理论可称之为交易范式公共物品理论。其核心就在于,分析公共物品集体决策过程时,同时考虑公共物品的需求(即公共物品数量)和供给(税费分担安排),因为参与公共物品决策的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供给者,供给(税费分担安排)将直接影响需求(公共物品数量)。如果我们把公共服务简单地比作聚餐,那么人们不可能只关心聚餐本身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必然关心餐费的分摊安排;餐费分摊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人们是否愿意参加聚餐、参加什么水平的聚餐。布坎南指出,人们在公共物品数量决策过程中关于税费分担的互动或相互依赖,才是公共物品决策区别于私人物品的本质特征。e[美]詹姆斯·M. 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马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4-136页。
当然,现实中公共服务的提供,并非每一项集体决策都要通过“纳税人—消费者”进行投票表决;特别是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兼具“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在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时,通常想不到这会使自己缴纳更多的税费。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影响,也涉及我国公共服务的决策机制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不考虑税费分担安排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并非总是处于完全的“财政幻觉”状态。f简言之,财政幻觉指的是人们通常觉得自己承担的税负比实际承担的要轻,而自己得到的公共服务的价值比实际价值要大。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意识不到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总额与其中涉及的个人份额之间的联系。财政幻觉有很多类型,除了包括笔者在此提到的人们感受不到公共服务的税费分担之外,还包括感受不到消费税的“寓税于价”等等。关于财政幻觉的详细讨论,参见 [美]詹姆斯·M. 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7-152页。现实中,人们会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公共服务税费分担安排的满意或不满意。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终止社保缴费、人们蜂拥至三甲医院求医、天价“学区房”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不足”或“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够”,人们感到缴纳的税费与得到的公共服务不匹配,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简单地主张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或由市场提供,是远远不够的。
三、公共服务非政府提供的可能性
与主流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的逻辑推论不同,现实中有大量的公共服务是由市场上的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自发提供的。在古代中国,虽然自秦代“废封建、置郡县”以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也时有变动,但国家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一级,“皇权不下县”是这一状态的通俗说法。在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地方公共服务无疑在广大乡村,而乡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则是乡绅与宗族,而非县级政府。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仅限于司法、治安、赈灾,甚至这些公共服务也是县级政府和乡绅、宗族共同提供的,而非政府单独承担。a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2-156页。亦可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修订译本)》,范忠信、何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45-259页。尽管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通过户籍制度、保甲制度等“编户齐民”,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控制,远非“皇权不下县”,b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128页。亦可参见张新光:《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4期。但至少就提供地方公共服务而非对乡村地区的控制而言,“皇权不下县”是基本成立的。而在西方国家,即便现在也仍有大量的公共服务由市场、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自发提供。那么问题就是,如何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围绕着“公共物品自发提供”这一主题,已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博弈论的相关文献,另一类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οr Ostrοm)为主要贡献者的“公共治理”理论相关文献,关于公共物品问题的实验经济学文献也可归入这一类。传统上,论证公共物品自发提供的实现,通常诉诸无限次囚徒困境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即参与人采取“冷酷触发”策略或“针锋相对”策略能够确保合作解的出现。c关于无名氏定理,可参见 [美]艾里克·拉斯穆森:《博弈与信息:博弈论概论(第四版)》,韩松、张倩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4-161页。此外,演化稳定策略(ESS)的概念,也为公共物品合作解的实现提供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思路。d演化稳定策略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生物学家史密斯提出,参见 [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演化与博弈论》,潘春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15页。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池塘资源”(Cοmmοn Pοοl Resοurces,CPRs)治理机制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公共服务的非政府提供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方法并非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而是更接近公共选择学派的交易范式。简言之,奥斯特罗姆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公共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情境”,而不是取决于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二选一”。所谓制度情境,是指包括人群规模、交流机制、个体异质性、惩罚和规则等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复杂的“制度—组织”结构。大量的实地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资源自发治理的结果并不像“囚徒困境”预言的那样悲惨,而简单地诉诸资源公有化或私有化的思路也并非一定有效。e[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1-34页。可以说,就公共治理或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言,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发现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除了政府和市场上的私人企业之外,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群也可以自发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治理。
经济学家当中,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科斯。1974年,科斯发表《经济学中的灯塔》(以下简称《灯塔》)一文。b中译本载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第181-205页。由于“灯塔”在经济学中一直被当作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反复出现,因此科斯撰写此文的初衷在于从史实上澄清这一谬误。在该文中,科斯梳理了英国历史上的灯塔制度后发现,英国最初的灯塔是由私人和私人组织建造并管理的,后来才逐渐被具有“公共性质”或“政府性质”的领港公会所购买并管理;也就是说,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早期历史上的灯塔是由私人提供的。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并没有据此否认灯塔是一种公共物品,也并非认为灯塔这样的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更有效率。不过,《灯塔》一文却梳理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收费模式。文中指出,私人建造灯塔的收费模式是通过港口代理,即港口收取灯塔使用费。换言之,通过将“灯塔服务”和“港口服务”这两种商品捆绑在一起,一并出售给灯塔使用者,以此来为灯塔的建造和维护融资。“灯塔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很难做到排他,但“港口服务”即船只到港停泊服务,却很容易做到排他,不付费者不得停泊,且根据船只吨位不同收费(类似于现在的停车场收费机制)。通过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捆绑在一起出售的做法,成功地实现了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
在互联网时代,私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可能性更是大大增加了,甚至屡屡超出人们的想象。例如,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地图,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政府部门提供的,但近年来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电子地图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纸质版地图。对于电脑终端或移动终端的用户来说,电子地图是免费的,那么它靠什么盈利?电子地图早期的盈利模式是通过对车载导航服务收费,而目前在导航服务免费之后,又可以通过在电子地图上产生的增值服务来盈利,如对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的移动定位服务收费,对地图上产生的酒店预订、订餐、团购等交易抽取佣金等等。甚至包括传统上认为需要面对面服务的教育、医疗等等,在互联网时代也面临着颠覆式创新的挑战。
当然,无论是奥斯特罗姆的贡献,还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盈利模式的出现,虽然证明了公共服务的自发提供并非像主流经济学预言的那样悲观,但也并未证明自发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效率的数量。简单地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最不足取的做法。真正重要的是,应当对现实中各种公共服务提供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论提供者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民间社群及私人企业。
四、公共服务中的公平与正义
除了公共物品理论之外,主张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的论者,有时还诉诸所谓“公益性”的理由。这种观点认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具有“公益性”,而公益性与市场机制是矛盾的,因此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类说法虽然承认市场能够提供公共服务,但却认为“市场化”会妨碍 “公益性”,因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前面提到的所谓“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的观点,暗含的理由其实就是“市场化妨碍公益性”。那么,什么是“公益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否就能保证“公益性”?
所谓公共服务具有“公益性”的提法,实际上指的是公共服务需要具有某种公平性,或符合某种正义。遗憾的是,“公平”、“正义”的含义并不比“公益性”更清晰。不过,如果我们不在纯粹抽象的意义上讨论公平和正义,仅专注于公共服务这一具体领域的“公平性”,还是能够得出一些基本的公平原则。这就涉及公共服务本身的特征。前面已经提到,除非采取“一致同意原则”,否则任何公共服务都必然涉及再分配因素,也就是说,每个人缴纳的税费数量,与他得到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a在某种意义上,“税费”与公共服务“数量”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恰是公共物品的特征之一。而在私人物品的情况下,每个人支付的费用或出价,与他得到的物品或服务的数量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布坎南提出私人物品的完全竞争市场制度体现的是“隐性一致同意规则”,因为在达成一项交易时,不仅交易双方表示了“同意”,其他人对这项交易也表示了“默许”(否则他可以出高价表示“反对”)。参见 [美]詹姆斯·M. 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马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80页。这一点无论对于政府提供还是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是成立的。既然公共服务必然涉及再分配因素,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再分配是更接近于“公平”或“正义”的?换言之,什么样的再分配更有可能在确保配置效率的同时尽可能使分配效率的损失最小化?基于这一考量,笔者提出公共服务的公平原则:公共服务可以存在且应当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再分配,但至少要避免反向再分配。
如果公共服务中存在反向再分配,那么公共服务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加入公共服务体系相比,穷人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反而可以获得改善,为什么还要强迫他们加入公共服务体系?也就是说,公共服务至少不应该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机制。而公共服务之所以应当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再分配,是因为既然再分配总是不可避免,那么有理由认为正向再分配比反向再分配更可取;而且,正向再分配也是现代财政学的一项基本原则。b被誉为“现代财政学之父”的马斯格雷夫明确主张财政职能当中应该包含“分配职能”,即正向再分配。可参见 [美]理查德·A. 马斯格雷夫、佩吉·B. 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子基、邓力平译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9-11页。当然,正向再分配的程度究竟需要多大,本质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公共选择,即人们愿意付出多大的“效率代价”来进行正向再分配。此外,笔者在此提出的公平原则,并不属于主张大规模正向再分配的强伦理标准,而是接近于罗尔斯“差别原则”这一较弱的伦理标准。c[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37-243页。
在这一公平原则的框架下,要讨论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就必须同时考虑公共服务的“税费分担”和“数量”。按照这一思路,下面主要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为例,来考察其公平性。
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三个板块,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从筹资方式来看,城职保的医保基金主要来自于参保人员缴费,而城居保和新农合的基金则主要来自于各级财政投入,个人缴费仅占基金总额的25%左右。d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当下,网购量呈爆发式增长,“三通一达”等快递高速发展,但一系列问题亦随之而来。就企业而言,竞争无可厚非,然而,对于同一家快递企业,不同的网点之间,出现诸如“跨区域取件”的恶意“竞争”,却是致命的。
按照我国现行的社保缴费制度,城职保的缴费主要以劳动雇佣关系为依据,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总费率大约为8%—10%,即工资的8%—10%用于缴纳医疗保险。从形式上看,医疗保险费率类似于比例税制,即所有参保人都按照同样的比例缴纳保费。然而,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类似于税基)存在一个上下限,即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60%的,按照60%计算;高于300%的,按照300%封顶,超出部分不再缴费。这就意味着,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事实上是累退的,即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超过社会平均工资300%),医保缴费占工资的比重最终是下降的。更重要的是,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都按照最低缴费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费,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并非按照员工的实际工资进行缴费,而是低报、瞒报了工资水平。粗略估算,目前我国平均实际缴费基数大约只有实际工资水平的65%。e李唐宁:《目前平均实缴基数不足工资七成》,《经济参考报》2016年3月28日。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3的应缴费工资总额并未缴费。若考虑到这些事实,那么城职保缴费环节的累退性就大大增强了。因此,从“税费分担”来看,参保人当中的低收入人群承担的比重较高,而高收入人群承担的比重较轻。
从参保人获得的医疗服务“数量”来看,同样也存在反向再分配。原因在于,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规则即“起付线”和“报销比例”都会导致高收入人群总体上可以获得更多医疗服务。首先,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更容易被“起付线”这一门槛挡在外面;其次,超过起付线的部分,高收入人群有能力负担更高的自费部分。
综合考虑医疗保险的“税费分担”和“数量”(俗称筹资和待遇)两个环节,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城职保”板块,存在系统性的反向再分配,总体上穷人“补贴”了富人。
基本医疗保险的另外两个板块城居保和新农合,从“税费分担”环节来看,大体上不存在反向再分配。这是因为,虽然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总体上具有累退性,a岳希明、张斌、徐静:《中国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测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但这两个板块的参保人群即农民、学生和城镇无业居民基本属于低收入人群,那么主要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收入为这两个板块筹资,大体上属于“低收入人群补贴低收入人群”,也就是说基本不存在反向再分配。但是,从获得医疗服务即“数量”环节来看,则与城职保板块类似,仍然是参保人中的高收入人群获得了更多的医疗服务。因此,综合“税费分担”和“数量”来看,城居保和新农合也存在一定的反向再分配,只是其程度要比城职保板块为轻。
事实上,由医疗保险保费构成的资金池类似于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公共池塘资源”(CPRs),这一公共资源仍具有竞争性,即任一投保人对该资源的使用都会减少其他投保人能够使用的数量;但由于每一位投保人都获得了“权益资格”,因此排他性大大减弱了。不过,城职保的医保资金池具有“专款专用”的特征,其中的扭曲和效率损失,要比通过一般税收融资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小一些。但我们仍然发现,城职保资金及其对应的医疗服务,总体上具有反向再分配的特点。其中的关键在于缴费制度本身并不具有累进性,并且现实中的缴费行为又通过低报、瞒报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加大了累退性。
此外,我国目前以公立医院为主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b截至2015年底,我国民营医院数量已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2.7%,但床位数只占全国床位总数的19.4%,因此公立医院仍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主体。参见李丹丹:《国家卫计委:民营医院占全国医院总数过半》,新京报网:http://www.bjnews.cοm.cn/news/2016/06/08/406095.html,2016年 6月 8日。又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医疗服务的反向再分配特征。总体上,公立医院获得的资金包括两部分:各级财政投入和医保资金,前者被称为“补供方”,后者则称为“补需方”。考虑到我国税制结构的累退性,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越大,则累退性就越强,反向再分配也就越严重。因此,在我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下,简单地对医疗卫生这一公共服务“加大财政投入”,尤其是对公立医院“加大财政投入”,不仅无从保证“公益性”,反而会进一步拉大而不是缩小贫富差距。
以上通过对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仅限于医疗这一公共服务,而是具有一般性。例如以同样的思路对基础教育领域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我国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办学,而财政资金同样来自具有累退性的一般税收收入;而在优质教育资源的享有方面,却通过“划片就近入学”的学区制,导致“买得起学区房的人,其子女上重点学校;买不起学区房的人,其子女上普通学校”;也就是说,优质教育资源更多地为高收入人群享有。更重要的是,购买学区房的人其实并没有对其子女就读的学校投入任何额外的资源,而且在房价预期上涨的情况下,买到的学区房可以在子女上学结束后再次出售,甚至还能赚取房屋总价上涨的收入。这就意味着,学区房已经变成了一种上名校的财富门槛和投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税费”付出。而关于学区房制度的改进措施如“多校划片”、以及2017年7月广州市政府率先推出的“租购同权”等,c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国广州政府:http://www.gz.gοv.cn/gzgοv/s2812/201707/3cec198881d44d33a80a145ff024a164.shtml,2017年7月17日。充其量或可使优质教育资源的可得性稍微公平一些,如“租购同权”可能会降低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财富门槛,但是,只要重点学校仍然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办学,那么基础教育这一公共服务的反向再分配特征就不会改变。
总之,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非天然具有“公益性”,因为这并不足以保证公平或正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几乎总是涉及一般税收融资,而税制结构是否具有累进性,是决定公共服务更加公平的必要条件。即便税制结构或缴费结构具有累进性,由该税收或缴费融资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同样也是公共服务是否能够更加公平的必要条件。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以具有累退性的税收收入融资,同时服务对象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那么这样的公共服务就具有正向再分配的特征,从而也就更加公平或符合“公益性”的本意。然而我国目前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极大程度上以累退性的税收收入融资,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却主要由高收入人群享有,从而具有强烈的反向再分配特征,可谓与“公益性”背道而驰。
五、结论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突出特点不仅表现为政府开始对宏观经济领域进行干预,更表现为政府支配的经济资源规模的扩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即便是西方各国,目前也早就不存在“小政府”了。而在政府支配的经济资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教育、医疗、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领域。主流经济学论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必要性,通常诉诸公共物品理论。然而,主流经济学的公共物品理论本身具有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将公共物品的需求(数量)与供给(税费分担)割裂开来,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而且也不能很好地用于分析公共服务的效率与公平。事实上,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群以及私人企业,在现实中都扮演着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由于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私人企业通过新的盈利模式提供公共服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就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言,应当对各种公共服务提供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论提供者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民间社群及私人企业。而那种认为只有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才能确保“公益性”的说法,既缺乏理论依据,也与我国当前的现实不符。由于我国税制结构总体上具有累退性,因此以一般税收融资的公共服务,具有反向再分配的特征。而目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受益机制,总体上更有利于高收入人群享有,进而进一步加剧了“劫贫济富”的反向再分配。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共服务由市场提供就更具有“公益性”,而是说“政府提供”并非“公益性”的充分条件。如果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改变,那么若要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就必须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向中低收入人群,而高收入人群的公共服务则由市场提供。也就是说,政府只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如基本医疗服务、普通基础教育服务等;而高收入人群更愿意享受的高端医疗、优质教育资源等等,则尽量交给市场。而从长效机制来看,加快开征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等具有累进性的直接税税种,将我国税制结构从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才是确保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更加符合公平正义,从而真正具有“公益性”的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