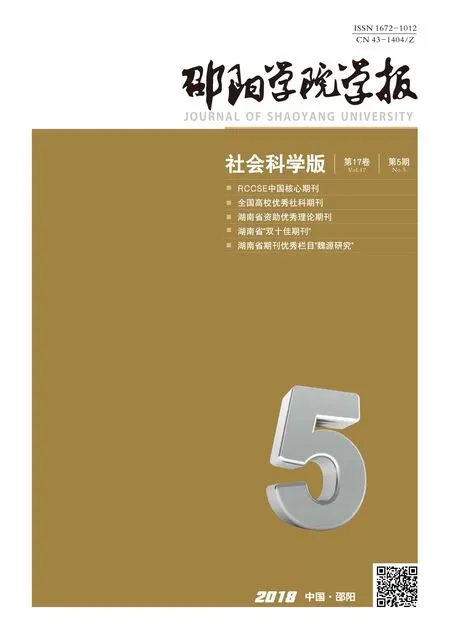生态美学观照下的六朝山水画论
郝 玲, 卫 欣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从广义上讲,生态美学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的研究,是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当代存在主义美学。从学科的角度看,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具体来说,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包括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自然科学,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哲学学科。然而这两门学科却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发现了特殊的契合点。因此,生态美学便在这个契合点上应运而生了。
六朝时期[注]吴黄龙元年(222年)秋九月,吴大帝孙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南京第一次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此后,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从东吴到陈朝,中国历史上称为“六朝”或“六代”。,南方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就巨大。在中国历史上,六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呈现出汉唐两大盛世间的过渡风貌,创造了极其辉煌灿烂的“六朝文明”,在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因而是一个风采独具的时代。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能够超越某一个体以及时代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从而表现为一种共同、普遍的集体审美追求。六朝作为古典山水画的萌芽时期,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用生态美学来观照六朝山水画论,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
一、生态美学的基本涵义
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的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来的,他给生态学下的定义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生态学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任何生命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此处的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随后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的学说,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探索的结合,从而形成了生态存在论哲学。这种新哲学理论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系统的整体性世界观,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生态学已经由自然科学转向了社会、伦理的领域。
在我国古老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人类的生态意识早就开始萌芽了。孔子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与代表人物,其代表的儒家学说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思想就是“天人合一”[1]10-13,实际上说的就是人的一种在世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关的、一体的、交融的,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东方存在论生态智慧。同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倡导“道法自然”,讲的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根源、趋势,这里的“道”就是宇宙万物和人类最根本的存在。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道的存在论的角度来看,道家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生成的共同本源都归因于“道”。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它们都旨在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换言之,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便可归纳总结为包涵人、自然、社会等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
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论哲学对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与存在是等同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种实践观一方面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力求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普遍平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证实了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54。马克思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它只强调自然对人的改造作用,而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也具有改造作用。生态美学是一种基于实践活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理论,它不仅能够体现人的“按照美的规律”来生活的本质,还可以构建人与被改造对象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存在论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革命精神的生态人文主义,是生态美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生态美学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美学观,并区别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美学形态。这里的“生态维度”与绝对“生态中心主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它是一种宇宙万物融为“生态整体”的新的生态人文主义,是一种生态存在论、哲学观与美学观,这种生态存在论的观念成为生态美学最基本的范畴。研究得知,认识论是一种人与世界“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关系,人与自然在这种关系中无法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而存在论哲学则是一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只有这种在世关系才能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提供可能与前提。海德格尔对此说:“主体和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3]70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在宇宙世界中是相互关联的,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自然存在在“此在”之中,与“此在”构成一个“生态整体”。生态美学所赖以建立的“生态论存在观”恰巧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东方古典智慧不谋而合。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总体上是一种人在“天人之际”的世界中获得吉庆安康的价值论关系,而不是一种认识和反映的认识论关系。[4]288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开始更理性地看待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导致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与污染。美国当代著名的生物海洋学家蕾切尔·卡逊以自己的笔触唤起了民众对当下生态问题的高度关注,在《寂静的春天》中她写道:“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5]203这里“一直行驶的路”实际上指的是污染自然环境的人类自我毁灭之路,而另一条人类很少走的“岔路”则是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美学以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提出了自然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观念,以自然与人共生共存的关系为出发点来探究美的本质。既重视人的主体性,也重视自然的主体性,并通过对自然的审美观照,力求重建人、自然、社会彼此之间的亲和关系。
二、生态美与自然美的解读
生态美与自然美在概念上都属于美学的范畴,具体来说,生态美包涵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大美,也包涵了人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之大美。人若想通达这种大美之境,则必须将自己融入天地万物之中,与自然生命同呼吸共命运,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崇高审美境界。当然,生态美的体验本质不应被理解为彻底消除自然环境中的个体差异,从混沌到虚无,追求无差别的绝对同一。相反,它既包含了所有生命的差别,但又不拘泥于这种差别。要努力打破由于自己与万物的差异性而产生的隔膜,消除主客二元对立的物我认识论,冲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以达到主体沉浸于自然变化的奥秘之中却又难以表达这种绝妙感受的审美境界。而自然美是指生命万物所呈现出来的美,它具有社会性与自然性。其社会性是指自然美的重要特征是具有实践性,自然性则是指自然美生成的必要条件是自然景物的属性和特征,如线条、形状、色彩、声音等。自然美包括日月星辰、花鸟鱼虫、山水园林等天地万物,内容非常广阔多样。它既与自然属性密切相关,也与人类的社会历史息息相关,当人将自己的感官体验与精神想象作用于自然之时,自然便被赋予了美的特质。因此,自然美是一种人们可以经常欣赏和感受到的经验现象。
那么这两者究竟有什么联系呢?首先,生态美和自然美的审美对象都离不开自然,两者都属于一种客观存在,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自然美侧重于对人的感官产生愉悦,而生态美则注重人的整体生活质量。显然,自然美是以人类为中心,而生态美则是以自然和谐为中心。相同的是生态美和自然美都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主观参与意识,不同的是,自然美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为人所用的对象化的自然,人在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中证实了自己的本质力量,自然被烙印上人的痕迹,成了附属于人的客观存在,自然界变成人肆意索取和破坏的对象。而生态美涤荡了人对自然的私欲,以和谐审美的态度观照人和自然万物,人对自然环境的依存促进了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彰显出一种包涵自然万物的宏观大气的美。因此,生态美对自然万物的生存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从宇宙万物(包括人)的视角来观照自然万物,而自然美只对人类个体的发展产生意义,它仅仅从人的独立视角来看待天地万物。也就是说,生态美是以道德伦理的情感来关怀自然万物,而自然美只对人具有道德伦理关怀。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万物不具有美丑之别,而生态则从始至终都对自然万物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次,生态美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还拥有着某种语境上的关联。古人对“自然”的领悟大多遵循了老庄道家的观点,老庄理念中的“自然”是指宇宙万物自然而然的本原。魏晋六朝时期,由于老庄道家中的自然观的影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从儒家的“比德”作用中升华出来,摆脱了抽象且形而上的客观存在形态,逐渐拥有了丰富且形而下的审美价值内涵,山水飞云,花鸟草木等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越来越频繁地显现在艺术作品之中。黑格尔曾经说过,“人必须在周围世界里自由自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个性必须能与自然和一切外在关系相安,才显得是自由的”[6]322。因此,中国古典自然观中的这种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审美关系,就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美。
再者,生态美中的“生”字表达了它和“生命”的联系是无法隔断的,天地万物皆有其独立的主体性生命特征,人与自然万物彼此依存,人是不僭越其他生命权利的生态存在物,这是生态美学所主张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古典艺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神化”“人化”和“情化”三个阶段。原始社会时由于对自然缺乏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在人们眼里都披上了神秘恐惧的色彩。封建社会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人对自然的认识从“神化”转变为“人化”,社会文艺作品中逐渐出现了山水林木的描写,然而自然尚未从儒家的“比德观”中走出来。只有当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互相融合作用时,作为客体的自然美才能独立成为审美对象。六朝时期,由于时代与文化的作用,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和主观审美意识开始升华,人对自然的认识由“人化”进入了“情化”,大自然开始真正独立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显示了一种生态美学的境界。用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说,魏晋“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它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情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7]151。
总而言之,生态美与自然美之间是辩证的关系,自然美的破坏会威胁生态美的存在。当自然变得不再怡情畅神的时候,人类开始意识到自然美的重要性,呼唤自然美的回归。丧失生态美的自然是毫无生机、蛮荒溃败的自然,它不再具有自然美,唯有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才可以重新恢复自然的美。因此,生态美决定自然美,生态美是自然美的前提,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生态美,自然美就会失去客观的审美对象,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导致自然美的缺失。
三、六朝山水画论与生态美学对话的可能性
六朝时期的山水画论是中国山水画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里面包涵了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这些生态美学思想,既包涵了“体证生生以宇宙生命为依归”的生态审美观念,也包含了“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生态价值观念,还包含了“亲亲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念。这些生态智慧可以促进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统一,也可以促进自然、社会、精神之间的生态平衡。
“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一种重建。”[8]11-18由此可见,生态美学中所包涵的这种绿色的生态审美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与六朝时期山水画论中的生态美学思想是同一的,它们共同的绿色思维和精神旨趣使二者的对话成为可能。
(一)走进自然:生态审美观的相通性
儒学思想长时间以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审美感受,“比德”是把自然美同人的精神道德联系起来,是当时人们对自然一直主张的观念。直到魏晋六朝时期,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玄学之风唤起了“人的觉醒”,人与自然的关系随之发生了改变,自然山水对人而言不再是认知关系,而是一种审美体验的关系。自然山水不仅体现了景物的外在美,还体现了与世人精神境界相同的内在美。中国的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而不是对纯客观自然景物的再现。士人在欣赏自然的无限风光时对自然采用审美的态度,人的身心在自然山水之中获得愉悦,从而进入物我合一、两两相忘的生态艺术境界。自然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对自然的这种客观美应保持一种追求与向往。因此,六朝的山水画家栖身于山川林泉之中,秉承对自然的生态审美的态度,在和谐共生的天人关系中通达自由玄妙的情境。
佘正荣在《生态智慧论》中主张:“体验和欣赏生态美要求不以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而是以个人的宽广胸怀去包融自然之美,这是对净化灵魂和丰满品格的高尚要求,也是我国古代许多贤人志士的崇高生活方向。”[9]266六朝时期,自然山水之美不在于自然山水本身,而在于它所蕴涵的“道”。南朝画家宗炳一生遍游山水,他对山水自然十分眷恋和痴迷,不知老之将至,即“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他将所画山水挂在卧室的墙壁上,每日凝神赏观,即所谓“卧游”。宗炳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追忆体悟着他曾经游历过的、给他清寒生活带来莫大愉悦的山水风光,藉此抚慰自己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无限热恋之情。其在《画山水序》中写道:“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他认为圣人运用“道”应对事物,贤者以高洁的情怀玩味物像,山水与“道”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山水画已经成为人们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简而言之,热爱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六朝时期山水画的主要内容。从山水画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宁静悠远、生动祥和的氛围,画面中的人物总是面色喜悦,姿态舒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切合着大自然的韵律,一切呈现出和谐而美好的景象,六朝山水画论里充满了强烈的生态意识。
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物质家园,同时也是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归宿。徐悲鸿先生说:“艺术家沉浸于这样的自然环境,故其所产生的作品,不限于人群自我,而以宇宙万物为题材。大气磅礴,和谐生动,成为十足的自然主义者。”[10]10这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因为文人画家能寄情于自然山水的审美境界中流连忘返,并让自己的身心在山水美中得到激荡,这便全面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的生态意境。生态美学要求人对宇宙万物应保持一种“亲和”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实现人与宇宙万物(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的“亲和”关系。因为生态美学的主旨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人类要想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则必须要与自然的发展节律保持协调一致,如此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而山水画论则是引导人们用生态审美观的思想多层次、多角度地去感受自然,享受山水美,并积极倡导人应当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拉近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在这一观点上,生态美学与六朝山水画论的审美主旨达成一致,也为二者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二)肯定自然:生态价值观的同一性
六朝山水画家以崇尚自然为基本精神,很重视自然生态,这与生态美学所肯定自然的生态价值观有很多的相同之处,这也正是生态价值精神的一种体现。六朝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士人为了躲避乱世,纷纷归隐于山林之间。栖居自然使士人发现了山水之美,他们对自然山水怀着一种亲和的态度,有了“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新发现,并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士人将自己疲惫的身心安放在青山绿水之中,在大自然的怡情悦色里放空自己的思绪,让整个身心得到舒缓和轻松,灵魂获得升华和自由。只有肯定自然价值、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自然山水的诗情画意与盎然生机才能在画家的笔下出现。山水画论中这种肯定自然价值、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为我们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生活模式。
自然界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在生态环境中,“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点都成为一个‘位’,而每一个‘位’则与周边的其他‘位’形成呼应、延伸、交流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生态位与外部所发生的关系,多向往复的联系,形成了系统的开放的姿态,既有与周边系统协同、协调的融洽性,又有各自本体与大环境之间的相独立的个体性;既有相生的平衡,又有相克的矛盾张力,形成动态性、稳定性、有序性的生态大系统”[11]6。王微[注]王微,(415—453),字景玄,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所著的《叙画》与宗炳的《画山水序》被后人所并称为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山水画论,与宗炳《画山水序》而言,更是理论愈加成熟。他提出“明神”的自然审美观,一方面表达了审美自然就是要让人完全沉浸于宇宙万物之中,不糅杂对尘世利害得失的计较,使人在自然整体中去感受与物俱化、万物合一的境界。这种生态审美思想对于我们现代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今频频爆发的生态危机,究其原因就是人对自然的感情发生了异化,人类只看到了自然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原有的审美价值。因此,“明神”的这种自然审美观表明了人只有在摒除一切欲望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恢复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人将自我生命融入自然万物之中,以明净自由的心灵去追寻自然山水,人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诗意与安宁,这是一种人性的自由表现。
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索取,以及对自然“人定胜天”的征服欲,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自然之美和生态之美皆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频发的生态问题正将人类置于一个自我毁灭的境地。要从根本上缓解人与自然的这种紧张局面,我们就必须以生态美学为依托,改变对自然的主客二分关系,走进自然,回归自然,重新肯定自然的价值,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这种理念恰好是六朝山水画中所提倡的。作为人对自然山水审美的把握,六朝山水画论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使人们意识到自然本身具有价值,这有助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培养人对自然的亲近意识,这些理论思想与生态美学中对自然价值的肯定和对自然整体生命的关爱不谋而合。因此六朝山水画论与生态美学在这一观念上也达到了契合,为二者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三)融入自然:生态伦理观的契合性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就是说在古人眼里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在老庄的世界中,世间万物在自然中天然地生成,和谐地统一于这个世界中。因此六朝时期,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文人画家眼里,自然万物都具有其伦理价值。大自然的每一处都充满了生命的灵性。它们一起构成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滋养着人们的精神情趣。山水画里展现了人贴近自然,亲和自然的情感,表现出人对自然环境的殷切关怀与深沉爱恋,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融的生态伦理观。尽管有时候六朝山水画论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理想化的表达,它仍为人们提供了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模型。
南齐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气韵”中蕴涵了浓郁的生生之美的生态思想。谢赫主张宇宙是一气流转、生生不息的生态整体,一切的物质存在都是有生命联系的,表现出宇宙生命整体的无限生机。这就要求画家要将自然生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山水景物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气韵”要求人对自然要有泛爱生生的仁者之心,将自然作为生命之气,与自然共生共荣,充满浓厚的生态韵味。六朝山水画的这种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了士人用生态审美观和价值观来体悟自然山水,体现了文人画家热爱自然,将仁爱之心推及自然万物的情意。大自然里每一个生物都是富有生命力的,世间的云舒云卷、花开花落、高山流水等富有灵性的存在全部在文人画家的笔下化为传神的“画魂”。这不仅代表了士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也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表现了寄寓山林的融入自然情怀。
“在魏晋以前,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的对象,也不一定是为了满足美的要求。但到魏晋时代,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美的要求。”[12]197由此可见,魏晋士人不仅强调人物之美与自然之美,更追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亲相乐。玄风盛行使世人更乐于归隐山林,他们以与自然山水相处为乐,以与飞鸟走兽相伴为欢,或栖居于田园美墅,或雅聚于竹林幽谷,或畅游于名山大川,他们对大自然的热恋已达到“何可一日无此君”的至高境地。他们这种把自然当良师益友和“自来亲人”的情感,切合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代生态美学精神。六朝画家的那种“万物齐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以往那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错误思想,人类逐渐改变了对自然的态度,并将自己与自然置于平等的位置。山水画中所蕴涵的这种“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态美学视阈下的“与物同游”“天人合一”的绿色内涵是一致的,都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亲密融合的关系,这也奠定了六朝山水画论与生态美学二者对话的基础。
四、结语
在生态美学的角度下发掘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理论和生态资源,融合中西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的生态智慧,这虽是还没系统成型的研究,但是却有着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生态艺术理论是美学在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视角和新突破,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六朝山水画论只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小部分,自然滋养了人和艺术,人应该对自然保持敬畏与尊重,不要再对大自然肆意破坏。在我国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艺术也应该发挥它的光和热。中国古代诸如六朝时期的艺术理论中都蕴藏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等待着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