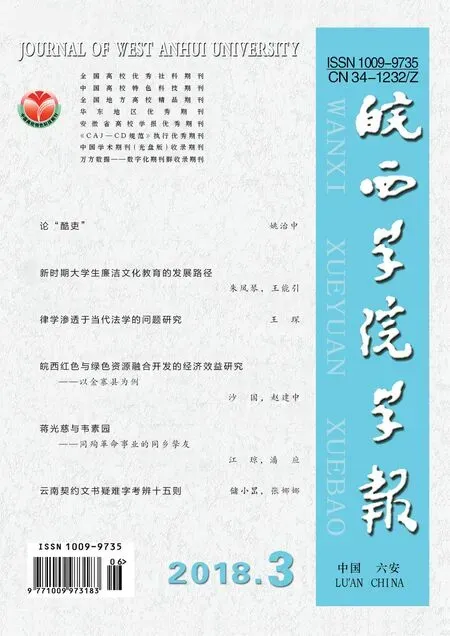舒城七门堰水利秩序与地方社会
关传友
(皖西学院 皖西文化艺术中心,安徽 六安 237012)
七门堰,又称三刘堰,是位于安徽舒城县境内杭埠河(古称龙舒水、巴洋河)中段的引水灌溉工程,是汉高祖刘邦伯兄之子、羹颉侯刘信创建,距今2200余年,是皖西地区至今仍发挥着农田灌溉效应的三大著名古水利工程之一(另两处是寿县的安丰塘和霍邱县的水门塘)。但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专门研究较少,且深度不足①。本文从水利社会史角度,对历史上七门堰水利秩序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展开讨论,以此展示七门堰水利社会不同阶层的作用。敬请诸方家批评指正。
一、七门堰历史概述
舒城县位于大别山东麓、巢湖之滨的江淮地区,地形地貌复杂,有山地、丘陵、岗地、平原,西南山区峰峦秀丽,中部丘陵起伏,东北为冲积平原。有舒城人母亲河之称的杭埠河发源于西南大别山区的孤井原、主薄原,贯穿全境,汇入巢湖,呈现出山区易发山洪、岗丘地区易旱、平畈易涝的特点。因此,旱涝灾害是制约舒城县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刘信根据舒城县地貌山川水文特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选择邑境西南三十五里之处七门岭东的杭埠河阻河筑堰,创建七门堰。故地方志书称“舒为江流要道,庐郡塞邑也。西去层峰萃起,巑峦秀拔,绮绾绣错,联岚四匝,若为境保障,而水利源头出是西山峻岭之下,势若建瓴,奔腾崩溃,汪洋浩荡,而民告病。羹颉侯分封是邑,直走西南,见山滨大溪下,有石洞如门者七,乃分为三堰,别为九陂,潴为十塘,而垱、而沟、而冲也,灌田二千余顷,而民赖以不病”[1](卷之八艺文志,明盛汝谦《舒城县重修水利记》)。其灌溉用水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由河入堰,由堰入陂,由陂入塘,由塘入沟入田的陂、塘、垱、沟相结合的“长藤结瓜”式自流灌溉系统。
自刘信之后,历代均有修治。如东汉末年扬州刺史(治所时在合肥)刘馥“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2](卷十五,《魏书》《刘馥传》)。魏晋至北宋时期,史未确载,但不能排除其曾得到修治,否则其不可能保持近千年而不淤废。南宋绍兴末年出任庐州太守的宋宗室赵善俊“复芍陂、七门堰,农政用修”[3](卷二百四十七,《列传第六》《宗室四》)。元末曾任舒城统兵元帅的舒城人许荣“按地形,修七门、、乌羊诸堰,以供灌溉之利,教民筑陂塘,垦荒芜,植桑麻。故虽兵旱相仍,而免流离转徙之患也”[1](卷之九艺文志,元杨淞《庐州许同知传》)。明洪武年间任舒城县学教谕的芒文缜《三堰余泽》诗:“泉流滚滚岂无源,三堰由来出七门。灌溉千畴资厚利,涵濡百世沐深恩。潜藏神物沦波冥,湿润嘉禾绿颍蕃。每向城东颙望处,故侯庙祀至今存”[4](卷之三十三,《艺文》《诗》)。当是对许荣修治七门堰后发挥灌溉之利的高度赞许。

图1 舒城县古七门三堰示意图(选自《舒城县水利志》)
明清时期修治七门三堰多有记载。明宣德年间,舒城县令刘显“细增疏导”,重修七门三堰,为荡十五,民“赖以不病”[1](卷之八艺文志,明盛汝谦《舒城县重修水利记》)。舒城人世代因感刘信、刘馥、刘显兴修七门堰之功,“蒙受其利,不忘其恩”,分别在七门堰口及县城隍庙旁建祠立碑,名“三刘祠”。七门堰又名“三刘堰”即源于此。明弘治癸亥年(1503),庐州知府马汝砺、知县张维善令义官濮钝之率民整修龙王、三门等荡,邑人、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秦民悦为之记。万历乙亥年(1575),知县姚时邻和治农主簿赵应卿“由七门岭以至十丈等陂,则为修理。由杨柳、鹿角以至黄泥等垱,则为疏通”[1](卷之八艺文志,明盛汝谦《舒城县重修水利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冬,舒城知县朱振“开坝濬沟”,重修七门堰,“俾山水盈科而进,溉数千顷,十荡九陂,咸食其德”;针对乌羊堰故道久湮,重开包家堰,使舒城东南乡“遂为腴田”[4](卷之十九,名宦)。康熙六十一年(1722),江淮秋旱,时任舒城知县蒋鹤鸣,“以灾告者一十八州县”,劝民乐输,以工代赈,募饥民、疏浚整治七门三堰[4](卷之三十四,朱轼《舒城县开复县河记》)。雍正八年(1730)二月,舒城县令陈守仁针对堰淤塞湮废之况,重开堰,使一万二千四百亩农田获得灌溉之利[4](卷之三十四,佘汝霖《重开堰记》)。嘉庆初年,邑人高珍开引水渠,“北通七门堰,以资下十荡忙水之利”[5](卷十一,《沟渠志》《水利》)。由于七门堰得到了多次的修治,使其充分发挥了灌溉之利,起到了抗旱保收的作用,地方志载舒城县“蓄水之利,昔称三堰,今以七门为最”[5](卷十一,《沟渠志》《水利》)。故舒城人尽享七门三堰之恩泽,将“三堰余泽”视为明清时期舒城县的“八景”之一。清邑人高华在《三堰余泽赋》中所赋:“山庄日丽,葭屋云兰,田分上下,亩尽东南。谛郭公之宛转,闻燕子之呢喃。一犁碧浪,叱乌犍处处,畦卦布;千顷青畴,飞白鸟村村,水护烟含,伫看秧马行来行行队队,却听田歌唱去两两三三。盖由源泉不竭,涵濡有余;惠泽灌千区恍接巢湖之水,恩波流万世若随仙令之车。白苹卧鹿之郊,咸肩耒耜;红蓼印龟之岸,齐力耘锄。惟导源夫一脉,实利赖乎三渠”[4](卷之三十三,《艺文》《赋》)。其正是舒城人尽享其灌溉之利的写照。
民国时期七门堰也“有整修的记载,但因受连年战乱影响,工程荒于修治”。至20世纪40年代末,七门堰渠首严重淤塞,灌区渠道几为荒废,水利效益锐减,“上五荡灌田仅万余亩,下十荡引冬闲水灌田也不到四万亩”[6](P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舒城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从1951年11月份开始动工,对七门堰进行了全面大修和扩建,至1953年底竣工。在二十六个月内,共开新干、支渠36000米,建涵闸、斗门、水坝等一百五十六处,计完成土石方230806方(其中石方18628方),实际用款356000余元,灌溉面积达97410亩。至1957年七门堰灌溉面积扩展到15万余亩,使这个古老的水利工程真正恢复了青春,发挥了它硕大的灌溉能力”。1958年始,在杭埠河“上游兴建了龙河口淠干渠,七门堰灌区纳入杭淠干渠的配套工程”,成为闻名中外的淠史杭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7](P18)。
二、维护七门堰水利秩序的制度
水利秩序就是“水利社会的群体(水利共同体)在获得水利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为民众普遍遵守的用水使水、修治和维护水利设施的若干规则”[8]。这些若干水利规则就称之为水利制度或水利规约。有史料可证舒城县建立维护七门堰水利秩序的制度是在明宣德年间,由当时知县刘显制订,其“分闲忙定引水例,董以堰长,民至今遵行之(上五荡引忙水,自四月朔起。下十荡引闲水,自八月朔起)”[5](卷十一,《沟渠志》《水利》),即“上五荡(苏家荡、洪家荡、蛇头荡、银珠荡、黄鼠荡)用忙水,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七月底接堰水灌田;下十荡(三门荡、戴家荡、洋萍荡、黄泥荡、新荡、鹿角荡、柳叶荡、马饮荡、蚂蟥荡、焦公荡)用闲水,每年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引堰水灌塘、陂、沟,蓄水灌田”[6](P61)。明弘治癸亥年,庐州知府马汝砺、知县张维善、义官濮钝之率民重修七门堰水利后,于“三门荡立为水则,画以尺寸,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至失望”[1](卷之八艺文志,明秦民悦《重修七门堰记》)。此用水制度一直至民国时期仍得到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七门堰的水利秩序。
为了确保七门堰水利工程能够得到合理有效运行,还实行水费征收制度,即按照正伕水、挂伕水标准征收水费。“全使用堰水的田称为正伕水,每担田(5市亩)收稻谷一斗。塘水为主、堰水为辅的农田称为挂伕水,每担田收稻谷5升。上五荡每车水埠征收糙米5斗(50公斤)。各荡征收的水费只作荡长补贴,如有整修事例,另行摊派,每年清淤整治用工近2万个,皆由农民自行负担”[6](P61)。
三、地方社会各群体所扮演的角色
七门堰以人工开挖的引水渠为主体形成的堰、陂、塘、荡(垱)、沟相结合灌溉系统而产生的水利社会群体,其无疑是属于“流域型”的水利社会。因此,七门堰所实际承担农田灌溉系统产生的水利社会群体就是一个大型的水利社会群体,其每一个荡(垱)、陂、塘就是一个小型的水利社会群体。如果七门堰上下游水利群体的水利权利和义务均等,能够在使水用水及工程修治活动中相互支持、帮助和谅解,就形成了“水利共同体”。故在七门堰水利社会中,地方社会各群体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地方官府、管理组织是水利秩序的维护者,地方士绅即是水利秩序的维护者也是破坏者,豪民无疑是水利秩序的破坏者。
(一)地方官府
七门堰属舒城县域的“公共之水”,是受地方官府控制的公共资源。所以地方官府十分注重对七门堰水利秩序的干预,其主要涉及水利修治、管理制度、水利纠纷等方面。
1、主导水利修治
“食者民之天也,水者食之源也。而水利不兴,有司责也”[1](卷之八艺文志,明盛汝谦《舒城县重修水利记》)。所以水利修治乃是地方官府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体现了其治理地方的能力。前述舒城县历代地方官多次对七门堰进行修治,使之发挥灌溉效益。如明万历三年(1575),舒城县令姚时邻和治农主簿赵应卿针对舒城县出现“有陂塘为道路者,有荡堰为沙堤者,有民间侵占致妨水道者,有汹涌湍激而沦没故址者,有壅塞横涨漂流民舍十余里者,致使春秋两无禾麦,而民之病者不可数计,独岁凶使然”的严重局面,遂“条陈申府及抚部”诸当道,修复七门堰工程,“见高者平,浅者深,浸者复,泛滥者消除,淤填者濬沦,水由地中行”,实现了“大小灌溉,远近沾濡”[1](卷之八艺文志,明盛汝谦《舒城县重修水利记》)。清康熙二十七年冬,舒城县知县朱振发布《修复七门堰示》,要求“水口如有应修应濬工程,十三垱齐心公举,不得互相推诿”“着两边堰长从公妥议,禀覆以凭,择吉祀神兴工,时迫春耕,勿得迟延自悮”[9](卷之二十艺文志,清朱振《修复七门堰示》),使七门堰得到了及时修治。以上可见地方官府在七门堰工程修治方面的主导作用。
2、制定管理制度
舒城地方官对七门堰日常管理的介入主要是确认堰长、塘长等管理人员资格,建立维护七门堰水利秩序的管理制度。如明知县刘显首定七门堰引水规则,董以堰长。清雍正八年,知县陈守仁在重修堰后,“查编细册,设立规条,锓梓以颁农氓,使永相遵守”[10](卷之三十一艺文志,清佘汝霖《重开古堰记》)。
3、平息水利纠纷
良法美意,积久弊生。舒城县水利纠纷自明代弘治年间就已经发生。癸亥年,天旱不雨,“舒民以堰久不治,诣郡控诉”[1](卷之八艺文志,明秦民悦《重修七门堰记》)。清雍正年间,舒城县七门堰的“堰口淤泥日积月累,渐成高阜”,“以致控司控道批府批县”[10](卷之三十二艺文志,清陈守仁《復开堰通详各宪稿》)。所引二例是因工程淤塞、水利不兴而引起的争讼,地方官员及时修治使之平息。
“大旱望泽,民有同情,上若有余,下必不足,上下相争,每有械斗之时”[5](卷十一,《沟渠志》《水利》)。因天气干旱争水而引起纷争在舒城县极为普遍。明末,“舒遭寇乱,井里为墟,水道率多湮没。时十垱之人路远心散,不能协力襄事,惟苏、蛇、洪三垱,紧接七门堰为力甚易。故康熙初年,即行开濬故道使水。今苏、蛇、洪三垱之人竟将七门堰据为己有,堵塞下流,忍将用余之水撇入天河,不容下十垱沾其余沥,返令其取给龙王垱,舍却现成有益之膏,不肯益人,强令人行不可行之事”[9](卷之二十艺文志,清朱振《修复七门堰示》)。是因苏(家垱)、蛇(头垱)、洪(家垱)三垱民户据七门堰水利为私利,引起下十垱民户兴讼到县,知县朱振惩治“顽梗之徒”,并为此发布《修复七门堰示》。到民国时期,舒城县水利纷争尤甚,因争水而引发械斗时有发生。故舒城县知事鲍庚称该县“一至久旱为灾,挖沟争水,农民聚斗,动至千人,甚有辗转借用枪械凶器,互相搏击”[11](附录三,鲍庚《舒城县大概情形》)。民国八年(1919),舒城县民方瑞庭等人因争执水利殴斗而杀伤人命,经安徽省高等审判厅审理,杀伤人命者受到惩罚[12](P233)。民国十七年(1928),“乌羊堰下游向上游要水发生械斗,死伤9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大旱,“下十荡地主石鼎九与上五荡地主张省如各带武装煽动群众,在洪家荡发生武装械斗,当场死伤3人”[6](P61)。在官府的强力介入后,才得以平息。
(二)地方士绅
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地方士绅作为“四民”之首,凭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特权优势,在地方社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学家张仲礼先生对士绅的作用概况云:“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13](P32)。因此,他们是地方社会的灵魂,对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发挥着主导作用。作者曾结合皖西地方实际,从兴学教化、文化建设、社会公益、慈善救济、敦宗睦族、调解纷争、社会代言、保聚乡里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地方士绅在皖西地方社会的主导作用[14](P231-283)。
明清时期舒城县的地方士绅多次参与七门堰水利修治活动及工程管理,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明弘治癸亥年,舒城县亢旱不雨,庐州知府马汝砺、舒城知县张惟善修治七门堰,得到义官濮钝之的筹策谋划才功成[1](卷之八艺文志,明秦民悦《重修七门堰记》)。万历乙亥年,舒城知县姚时邻、治农主簿赵应卿修治七门堰水利,得“午峰武君、少泉杨君咸协力赞助,遹观厥成”[1](卷之八艺文志,明盛汝谦《舒城县重修水利记》)。清康熙庚子(1720年)任县令的浙江秀水人蒋鹤鸣体察民情,与县内“绅矜士庶商度费用,皆愿量力乐输”,报经上宪批准,复开河道,选择一“为一邑一乡之望者”的绅衿,“总理其事,以董其成”,修治七门堰水利[10](卷之三十二,清蒋鹤鸣《復开河道通详稿》)。自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开始至十二月止,历时三月而成。因“钱米出入繁杂,畏难者几欲避去”,太学生周朝聘“代之,持筹握算,日无宁晷,而宽裕自如,侪辈推之,令尤加礼匾旌焉”[4](卷之二十三卓行)。恩贡生祝云奇与附贡生、乡饮长者束三锡督工役,事竣之后,上宪奖曰“良员上选”[5](卷之四十一,人物、耆寿)。雍正八年二月,舒城知县陈守仁重开堰,同堰食水士绅生员李炽然等十数人担任首事之人[10](卷之三十二艺文志,清陈守仁《復开堰通详各宪稿》)。乾隆年间舒城县举人程溁,曾官内阁中书,去官后家居,“遇利人济物事,为之不稍让。舒邑七门堰水利最巨,久之沟淤塞,溁捐田二十亩为沟道,因势疏浚,利泽复兴”[5](卷之四十,人物志、义行)。绅耆石朱霞五世同堂,“里有大格荡者,西引七门堰水,东经戴家荡,又东至大格。而自戴家荡分流下注道民人杨正秋田中,每苦启放不便,朱霞捐百八十金,购田九亩,开沟通流,至今下六荡犹利赖之”[5](卷四十一,人物志、耆寿)。
地方士绅还直接参与七门堰水利工程事务的管理。乾隆间,卫守备高子珍,“因汉羹颉侯创制水利代远几废,屡清理原委,务令上下十三垱均沾水利泽。间有豪强阻占,珍独不避艰险,力寻旧例。至今上下田亩不失水利,珍力实多也”[4](卷之二十三,卓行)。他有效地确保了七门堰水利的灌溉秩序。
地方士绅在维护七门堰水利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地方水利,诚如著名历史学家萧公权先生指出:“乡绅对水利非常热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乡绅都是地主,他们很容易了解确保租种其土地的农民收获的重要性。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也懂得灌溉的重要性,但由于他们没有乡绅那样的威望、财富或知识,自然要让后者来扮演领导角色”[15](P337)。其所说正是如此。
但在涉及具体利益时,地方士绅并不完全是水利秩序的维护者,有时会利用自身的权势地位充当破坏者的角色。清后期合心垱士绅刘翰林买通官府委任其管家王士泰为垱长,霸占合心垱水利,农户使水一次,一石田(5市亩)要缴八斗大米作“桩草费”[16](P183)。
(三)堰(垱)长
七门堰日常水利事务是由官方支配下的堰长行使管理职责,最迟在明宣德年间就已经确立有堰长管理。自后,凡是属公共资源的水利设施都有官方委派一至数人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堰设堰长、塘设塘长、垱设垱长,都是由民间推举有威望、处事公正之人担任。其报酬是通过受益农户缴纳水费收益支给。其职责是使水季节按时按量放水灌溉,冬春季节组织受益农户出夫岁修。但董长非人,不图公益,极易引起纷争。
(四)豪民
七门堰水利秩序的维护都需要社会大众(使水农户)的参与才能够得以有效实现,因其处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一般都是被动参与。但还有一类争强斗胜、欺弱的人群,即人们常以豪强、豪恶、顽民、凶徒、地棍等称之。在七门堰水利社会里,这类人群常劫夺侵占七门堰的水利资源,破坏水利社会秩序,是地方官府打击的对象。明万历《舒城县志》对此该县水利评述称云:舒城县“有可虑者,愚民狃于小利而昧大体”“豪右循辄轻价欺侵,则争田争水旧事復作矣”[1](卷之三食货志、水利)。明季兵燹后,因“豪强占塞”七门堰水,造成县西北乡“田多苦旱”[4](卷十九,名宦)。清康熙二十七年左右,舒城知县朱振发布《修复七门堰示》告示,针对七门堰上三垱农户霸占水利称云:“如有顽梗之徒仍前霸佔阻扰,本县即按作凶徒张秀明供报姓名,通申各宪,请以大法重处,决不轻恕”[9](卷之二十艺文志,清朱振《修复七门堰示》)。其在《劝谕息争均泽示》中对下十垱“平日既悭吝不出人工,临事又恶劳却步,今突妄希使水”的豪民,“尔若恃势用强,垱有成规,官有三尺,徒自取咎,水终不与也”[9](卷之二十艺文志,清朱振《劝谕息争均泽示》)。
四、结语
综合以上的考察分析,舒城县七门堰上下游用水民众在地方官府的主导下,对其水利资源进行合理有序的共同管理,建立了以利益均沾、义务共享的相对较为合理的用水使水制度,形成了一种较为有效的水利秩序,保证了七门堰水利灌区农业的有序发展。但这种水利秩序深受“水利周期”的影响。所谓“水利周期”是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社会史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研究中国水利史时,曾经以16-19世纪湖北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例而提出了国家干预水利事务(主要是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国家强力推行鼓励、组织修治水利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第二阶段是国家“作为本地区各种矛盾的仲裁者”,处理各种类型的水利纠纷,发挥仲裁者的角色;第三阶段是“国家屈服于本地区的困难”,对水利事务的干预能力大幅度下降[17](P614—650)。这就是所谓“发展—危机—衰退”的水利周期现象。明清舒城县七门堰水利事业的发展无疑也表现出这种明显的周期性。明前期、清前期七门堰的大规模修治都是由官府(国家)强力干预之下完成的,水利秩序得到了有效维护,是水利周期第一阶段的“发展”现象;明中期、清中期的地方官府处理七门堰水利有关的矛盾纠纷,水利秩序受到挑战,是属水利周期第二阶段的“危机”现象;明后期、清后期七门堰水利设施因淤塞得不到及时修治而湮废,水利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是水利周期第三阶段的“衰退”现象。受这种水利周期现象的影响,七门堰上下游十五荡水利秩序也出现了“运转—危机—破坏”的循环现象。
舒城七门堰水利秩序还与舒城县杭埠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联。地方志书称:前河(即杭埠河)源自于县境内二百余里的西南山区,至七门山以东“河出平地,故转徙无常”。人们在龙王庙处筑“石坝障河”,使其向北,水“绕南关外,环保县治,故风气攸聚,人文鼎盛,连艟巨舰,直抵城闉,无往来输挽之苦,民称便焉”[5](卷五舆地志、山川)。故称之为县河。但因“生齿日繁,山民不足于食,垦荒渐多,树叶草根无以含水,浮沙细石随雨暴注,日积月累,河道遂塞”[5](卷十一沟渠志、水利)。自明万历以后,杭埠河多次因山洪暴发而发生改道南徙,使得杭埠河中下游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利设施因此湮废而失去灌溉之利。七门堰因“堰引河流,山水挟沙,倒灌入堰,岁时挑掘,积沙渐高。夹堰皆民田,不容淤垫,苟非别筹隙地积土,则水利半废矣”;乌羊堰则因“南徙七里,沟屡泛决,田尽淤,而堰遂废”,出现“堰水所灌之田尽皆淤垫,宜稻者什之一,余皆宜豆麦杂植”的局面;堰是因“堰初有,以时启闭,故曰。河淤堰废,遂荡然,猝遇大涨,河流倒灌,常为城郭、田庐之害。”[5](卷十一沟渠志、水利)虽经清康熙、雍正、乾隆及嘉庆年间的数次疏濬开复河道,但仅“一时之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注释:
①作者通过查阅,仅有卢茂村的《话说“七门堰”》,刊《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李晖的《万古恩同万古流——论“七门三堰”及“三堰余泽”》,刊《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两篇论文都是对七门堰创始者、修治历史及效益的考述。
参考文献:
[1](明)陈魁士.万历舒城县志[M].舒城:万历八年刻本.
[2](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元)脱脱,欧阳玄.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清)熊载升,杜茂才.嘉庆舒城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清)孙浤泽.续修舒城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9.
[6]李少白.舒城县水利志[M].舒城:舒城县水利电力局,1992.
[7]汤光升.汉代著名水利工程——七门堰[A].舒城文史资料(第一辑)[C].舒城:政协舒城县文史委,1986.
[8]关传友.明清民国时期安丰塘水利秩序与社会互动[J].古今农业,2014(1):92-103.
[9](清)沈以栻,褚磐.康熙舒城县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10](清)陈守仁,贾彬,郭维祺.雍正舒城县志[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
[11]舒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舒城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5.
[12]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4]关传友.明清民国时期皖西宗族与地方社会[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6.
[15]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M].张皓,张升,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
[16]李用言.来自杭埠河畔的报告[A].淠史杭报告文学集——胜天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
[17](法)魏丕信.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A].陈锋.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以舒城县开展精准扶贫为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