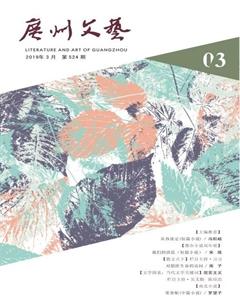论外视角
曾念长
一
2002年,乔伊斯基金会将悬念句子文学奖颁发给余华。在此之前,余华已在国际文坛获得卡佛文学奖,相比之下,悬念句子文学奖并无名声,显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这也不妨碍我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在颁奖词中发现一些有意味的细节。颁奖词声称,余华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我们注意到,这个奖项主要是肯定了余华的中短篇小说,唯有限定在这个范围内,余华的先锋写作才是与现代主义相匹配的。新千年之后,余华曾将自己的中短篇小说结集,以不同组合和不同书名在不同出版社出版。我无意中发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中短篇集里,余华重复使用了同一篇自序。序言开头说道,这是他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判断,余华这句话,多少含有某种总结意味,显示了时间赋予一个作家的特殊命运,也暗示了一种特定写作的有限性,和转向其他写作的无限可能。
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如果要贴上一张现代主义标签,理当落在一个特定时段的先锋作家身上,余华是最醒目人物之一。然而一个作家对某种写作信念的坚持,往往是不可靠的,恰如亲密伴侣,时过境迁,早已不能拾回初心。如果将颁奖词和余华自序联系起来看,余华的先锋写作始于1986年,一直延续至1998年。但是早在1990年代中前期,余华就已在下意识里弃暗投明,向现实主义投石问路了。这个秘密转向,以余华接连写出《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为标志,只是其中隐含的转型意义,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关注罢了。
1998年之后,余华陆续在国际上获得一些奖项,却在创作上陷入难产状态,一度被传江郎才尽。2005年,余华携长篇小说《兄弟》重返文坛,评论家和读者翘首以待,结果发现,那个曾经熟悉的余华已变得面目可疑,似乎再也回不到过去的余华味道了。2013年,余华又推出新长篇《第七天》,照例未能挽回许多老读者的心。豆瓣网显示,读者对《第七天》平均打分只有6.8分,在余华所有作品中可以说是最失民心的。用豆瓣数据来评判一部作品,可能极不严肃,但对余华这样的作家来说,每一部作品均有数万人在打分,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文学人口在交换意见,多少可以反映出某种复杂的真实。浏览一下豆瓣网上的简短评论,我们就会发现,读者对余华在新千年之后推出的两部长篇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读者依然迷恋旧时余华的先锋写作,认为复出之后的余华已大失水准,两部长篇配不上余华这个名字。一种读者则是余华的新增拥趸,接受余华转型之后的新写作,在两部长篇中看到了文学关照当代社会现实的强大力量,甚至感动到泪流满面。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并非只有一种标准,我们就应该对上述不同意见给予同样的重视。恰是这种意见分歧,以一种曲折形式显示了过去三十年来余华在写作道路上的渐行渐远。
下面我将举例不同时期的三部代表作,来说明余华是如何一路走远的。
第一部作品是余华出道之初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讲述一个青年刚满十八岁,在父亲嘱咐下出门远行,却遭遇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作品写于1986年,刊发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李陀当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是最先阅读余华这个作品的文坛中人之一。多年以后他回忆道,初读《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对文学的惯常理解受到了极大挑战,几致乱了套。他又接着说道,《十八岁出门远行》从根本上打破了我们对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惯性认识。后面这句话极为经济有效,可以帮助我们回到时代现场,重新理解余华这部作品的特殊价值。
就故事而言,《十八岁出门远行》并无复杂之处,其情节含量不比一篇中学生叙事文多多少,但是余华用一个简单故事表达了一个复杂的疑问——人与现实是如何相遇的。父亲让儿子出门远行,代表了那个时代曾经坚信不疑的现实观——深入生活,如镜子般忠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真相和全相。这个青年如马驹一般欢快,信心满满地上路了,但随后遭遇的一切是这般匪夷所思,世界有如躺在一面破碎的镜子里,线条逻辑不再连贯。我们大可不必追问,余华在创作时是如何想的。我们在乎的,是余华通过这个小说创造出了一种主观的现实,一个只被内心感受到的自我世界。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创造,颠覆了过去几十年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信条——世界是客观的,唯一的,无疑的,可以被作家一板一眼如实描绘出来,如镜鉴之物,明亮而清晰。余华则从客观世界里分离出另外一种现实来,它是主观的,多相的,可疑的,即便诉诸作家笔下也暧昧不清,如心波倒影,幽暗而晦涩。
第二部作品是长篇小说《活着》,创作于1992年,首次出版于1993年。迄今为止,在余华所有作品中,这是销量最大也是美誉度最高的一部。在1980年代,余华凭借先锋小说在文坛扬名立万,但在大众读者中影响有限。《活着》则两全其美,既得到主流文坛的高度评价,也获得普通读者的热烈追捧。这个现象不会是一种孤立的事实,而是与余华在写作路线上的转移有着密切联系。《活着》讲述了一个叫福贵的地主少爷,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遭遇各种命运的动荡,最后孑然一身活着的故事。与早期中短篇写作相比,余华在这个作品中恢复了现实书写的客观尺度,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道德世界,都是清晰可辨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恢复了时间的客观属性。余华曾经谈到对文学时间的理解。他借但丁《神曲》的诗句——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来说明时间是如何被诗人篡改了顺序,从而制造出一种不同于现实秩序的速度感。但在《活着》这部作品中,至少在宏观结构层面,余华没有开启文学时间,而是回归现实时间。他老实地叙述福贵一生的命运变化,有头有尾有过程,让故事回到现实秩序,也回到读者对客观时间的一般感受之中。
有人认为,这个时期余华向现实主义回归了。如果我们认可这个观点,也得补充一点,这个回归还没有最终完成。此时的余华,不过是披了一件现实主义的仿真外衣,内在的语言细节可以证明,骨子里的他还是个先锋作家。余华坦白,《活着》最初是以旁观者角度來写福贵一生,然而叙事受阻,难以为继,直至最后改为第一人称叙述,奇迹出现了,整个写作一气呵成。或许是因为有这样的写作经验打底,《活着》出版时,余华在自序中近乎大放厥词——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我们也可由此判断,余华依然未从主观的自我现实中走出来,他在1990年代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早期的先锋写作经验。具体来说,按照写作时间先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作品面向内心世界的自我意识在递减,面对外部世界的现实意识在递增。《活着》恰好处在中间状态,减一点自我,增一点现实,二者平衡得恰到好处。这就可以解释,《活着》为何两面讨好,通吃专业和大众两类读者。
第三部作品《第七天》进述一个叫杨飞的中年人,丧生于一场火灾,在冥界遭遇和寻访故人,由此追忆生者的世界和故事。在多数篇幅中,余华对故事的叙述采用了知音体,其间还反复植入各种早已被我们熟知的社会新闻,包括拆迁、贿赂、弃婴、车祸、豆腐渣工程、卖淫、自杀、凶杀、上访等等。我们发现,此时余华已经成为一个紧贴现实地面的作家了。这就不免让我想到了一个细节——余华当年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其原始素材也是来自报纸上一则有关苹果被抢的新闻,但是经过余华的二度叙述,这则新闻已被文学溶液彻底溶解,恰如米酿成酒,再无新闻痕迹了。而《第七天》则以新闻为补丁,大面积填补文学想象的裂缝,最后读者发现,这个作品成了一部无限接近当下现实的新闻串串烧。
余华曾说过,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文学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光。在新千年之前,余华大抵上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写作信念。他总是执着于记忆深处的事物,让往事转化成一种内心光谱,让肉眼可见的现实变成内心隐秘的现实。但是到了《第七天》这里,余华已离初心甚远,他对当下现实展开了正面强攻,必然无法再打动那些先锋派老读者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余华已成功回到现实主义传统——倘若如此,也是一个理想结局。1990年代,通过三部长篇写作,余华基本完成转型。在《许三观卖血记》这部作品里,余华已经能够用第三人称叙事轻松驾驭长篇写作,意味着他已走出自我世界,能以全知视角审视外部世界了。然而到了《第七天》,余华重启第一人称叙事,颇让人疑心他又回到了先锋写作状态。继续往下读,我们才发现,余华不过是披一件先锋派的外衣。前面说过,余华写作《活着》,披上了一件现实主义的外衣,显得相当得体,这一次却不成功,紊乱了气息,同时也让余华露了怯——他对当代现实主义写作是缺乏信心的。
余华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但我不是在说一个孤例。在余华身上,我隐约看到了当代文学的一段片面史——1980年代以来,由于一批先锋作家对新的现实经验的发现和开掘,传统现实主义发生了断崖式裂变,导致现代主义对峙而出,崎岖而立。到了1990年代,这批作家开始向现实主义写作转型,在两种现实经验中摆渡,由此开拓出新的文学境界,犹如两岸青山相对出,风景无限。进入新千年之后,当作家们纷纷着陆现实主义,却发现他们已在复杂的现实经验中迷失,抓不住世界,也找不回自己。问题就在这里,一批先锋作家回到现实世界,向现实主义投诚,却又为何在写作上不尽如人意了呢?
二
19世纪中叶,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走到了尽头,现实主义趁势兴起,成为主流,一时无两。然而好景不长,从19世纪后期开始,假以各种奇怪面目的现代主义冒了出来,成群结队,此起彼伏,在其冲击之下,传统现实主义几近崩盘。当然,在全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转移到20世纪的苏俄和中国,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相结合,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
通过简短回顾,我们发现,当代现实主义的最大冤家是现代主义,而不是早已过了气的浪漫主义。然而明眼人同样会发现,不管现代主义如何花里胡哨,其精神源头就在浪漫主义那儿。往简单里说,现代主义其实是浪漫主义的现代变种。当然变得相当厉害,面目全非,老祖宗也不认得子子孙孙了。可是有一点却是骨子里的,变不了。浪漫主义也罢,现代主义也罢,它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是内心感受法。世界是怎样的,并不重要,只有我感受到的,才是最重要的。它们通过文字建立起来的世界,以主观心灵为地基,以想象和幻想作为基本构架之法。它们看待世界有一个基本方向,我暂且称之为内视角。
现实主义恰好相反。它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依赖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摹拟、实证和整体把握,是一种外视角。借助发达的外视角,文学就具有了见证时代的功能。这就极大扩张了文学的史诗抱负——以诗性语言来记录历史的客观进程。现实主义作家也描写人物心理,但写的是他的心理,不是我的心理。他们要求自己像一台心电图测试仪一样,精细且客观地把人物心理过程描绘出来。
现实主义首先在欧洲成为主流,与当时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不无关系。孔德在183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实证主义哲学》六卷本,直至1844年出版《论实证精神》,一场思维革命在欧洲已深入人心了。实证主义主张回到客观事物中去,发动人的外部感官和经验理性,摒弃玄思、臆想和一切形而上学。通俗一点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睁眼说瞎话。这个准则在欧洲社会深度扎根,为19世纪的科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维地基。不仅自然科学飞跃进展,人类对社会领域的认知也向自然科学看齐了。孔德趁热打铁,创立了一门学科,叫社会物理学,意图明了,就是将社会过程当作物理过程来研究。
文学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变。欧洲本有史诗传统,以叙事诗来见证历史,具有古典时期的外视角特征。到了19世纪,史诗不再局限于一种文体,而是扩展为文学的基本认知功能。比如黑格尔就把长篇小说定义成现代市民史诗。他对比了长篇小说和传统史诗的相似结构,指出它们都是大容量文体,可以完整反映一个时代面貌。黑格尔提出这个观点,要比孔德提出实证主义略早几年,但属于同一个时代步伐,二者汇合,显示了文学扩展外视角、开放外部感官、见证大时代的必然趋势。
一切文学作品因细节而生动,但对现实主义来说,成功的文学作品还有两个重要指标——客观与宏阔。前者自不必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中说道,法国社会是个大历史家,而他只能当个书记员。他以时代记录员自谦,实则强调文学反映时代的客观属性。现实主义不仅反映时代,而且要有反映时代全貌的抱负。恩格斯对《人间喜剧》评价极高,称它汇聚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19世纪中期,以巴尔扎克为代表,法国长篇小说写作开创了一种重要体制,叫大河小说,其特点是多卷体,长时段,视野宏阔,一个时代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皆在作家法眼之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宏大叙事,虽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却是现实主义文学给予读者的最大承诺。
毕竟每个作家经验有限,要看清时代全相,就必須借助全局性视野,站在高处看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爬到高处呢?作家需要登上一座高山。这座高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人对历史和生活的最高认知。《三国演义》一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循环观,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本质的最高揭示了。有了这一句话,《三国演义》就建立了全局性视野,其叙事框架也就自然成立了。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之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高山供作家攀登。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座高山是人道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则是阶级主义。人道主义也罢,阶级主义也罢,都是人类对历史主流的判断,含有某种假定色彩。但这也不影响文学外视角的客观属性,正如一切科学研究,也都是从假设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