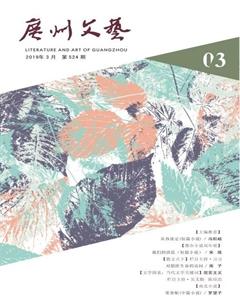对隐匿生命的访问
作者简介:
南子:上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南部地区,著有诗集《走散的人》,随笔集《洪荒之花》《西域的美人时代》《奎依巴格记忆》《精神病院——现代人的精神病历本》《蜂蜜猎人》等,著有长篇小说《楼兰》《惊玉记》。2012年获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2016年获西部文学西部诗歌奖。2017年获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提名奖。现居乌鲁木齐,为某报副刊编辑。
正 午
死亡和正午的太阳令人不可逼视。
——拉罗什力《箴言集》
我怕光,尤其怕正午的光。
正午的光有如一种生铁的坚硬质地。铁,既是一种结构也是一种质地,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生性敏感的我来说,是一个奇怪的词,在我的记忆中画出钢蓝色的弧线。
一想到这个词,周身便被一种灼热感覆盖,携带一种速度和力量在疾行,我在其中的形象生涩而模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少女时代的课堂支离破碎,而又广大无边,最后漫延到工厂。
那次经历与工厂有关。
高中毕业等待大学通知书的一小段日子里,我去了当地一家工厂做学徒工。工厂的机修车间是一个由生铁、机器、机油、光膀子的男人组成的内脏,厂房里机声轰鸣,弥散着腥甜的生铁气息。
车间里悬在头顶上的一种车——天车。
每一天,总有那么一些特殊时段,悬浮在头顶上的一辆机车从车间一头划向厂房的另一头,钢铁之躯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极像未来世界中的一个镜头,我吃惊地仰起头的样子可笑极了,因身躯过于渺小单薄,与庞大的机车构成了无与伦比的荒诞感。
机修车间里,生铁毛坯堆得到处都是。
白天,我穿着宽大难看的工作服,在空旷的厂房里吃力地搬运生铁毛坯。这些生铁毛坯呼吸着车间的噪音生长,在高速旋转的机器中转动,闪烁着钢蓝色坚硬锐利的光茫,它们每一分钟都被车床飞旋而出,交缠出一团团硕大无比的废铁皮,像热带植物般蓬勃生长。它们是工厂这特殊花盆里培植出来的奇怪的植物。叶片锋利,不是靠泥土、水分、空气生长起来的,而是相反。
最后,它们被堆在厂房外面,像科幻片里未来世界中硕大无比的南瓜和白菜,堆得比厂房还高,极具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质感。几场风、几场雨过后,它们的颜色由钢蓝色变成暗褐色,越来越陈旧。
它们总是堆得很高才被人运走。
在它们消失的地方,往往会有黄色粉末堆积,被风吹散在空气中,或者被雨水浸泡成一堆黄色的锈水,四处流淌,制造出工厂特有的气味,常年在这里盘桓。
它们造成的压抑感永远存在。让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正午炎热太阳的逼视下也变得不可思议。
南疆偏僻的小镇上,许多征兆是跟夏季躁热的正午连在一起的,某个夏日雨后的正午,毒烈的太阳迅速烧干地面上的湿气。一些掉落的叶子带着干草的气味和浓烈的日光气味混合在一起,迅速弥散、升腾。
南疆的正午,最难熬的是八月。
我很想描述一下南疆的正午时光,说被烧焦的中午,四边翘起;说炎热粘连的光线如何穿透了夏天的心脏。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表达这种内在的和谐。炎烈的风吹着,路上冷清清的,没有什么人在走动,道路两旁的树都僵住不动了。这是真的。
正午攜带着荒漠般的寂静,像一个人晦暗的生长期。太阳又大又白,人们都在午睡。老人、孩子、路边的狗。树叶儿耷拉下来,好像睡着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黏稠的梦魇的气息。热,白炎的光,虫的鸣噪,难以化解的一份艰涩。而我正躲在工厂正午的阴影中,于人于己在遮蔽中似乎后退了一步。
人是需要被阴影庇护的。
想到这里,我微微闭上了眼睛。
我时常失眠,正午的阴影来自于最炎热的夏日午后。那来自内心低潮的寒冷,时常在不设防的时刻向我袭来。
我在正午的某一个时辰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光亮犹如另外一种光明。梦中的景象变得时断时续,不置可否。正是在这种正午的光亮中,一些混乱的,灾难性的,彻底失败的景象,好像一个个确凿的证据出现在我面前。仿佛一切都已失去。
我又沉沉地睡去,当在夜晚醒来的时候,房间里是阴暗的,乳白色的窗帘透出的光亮半明半暗,让人误以为是早晨,天还没有全亮,很快便忆起了中午遍地的日光——还有整整一个晚上要度过呢。
不容多想,夜幕就降临了。
这一天正午,我吃过饭,带着慵懒而缓慢的步伐在镇机修车间的厂房里走着。
厂房里没有人,没有机器热烈的轰鸣声。其他人都去了别处。或在午睡,一切都像是在减速,制造出一种虚拟的寂静,与人隔离。
这个时候,我能够深刻体察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清冷、迟疑、僵硬和拒绝的因素。
我慢慢走着,脚步轻得像是悬浮在空中,周围的气温正在一点点地上升。我放慢脚步,带着担心碰破一些易碎东西的那种轻,穿过厂房里舒适的暗,各种属于工厂的味道在炎热空气中汩汩流淌。
厂房里,胡乱堆放的生铁毛坯散发出一股男人身上蛮横的气味儿。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它们,锃亮的车床像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突然,我的脚不小心碰到细铁管堆,一根铁管滚落在地,在空旷无比的厂房发出脆响,吓坏了我:“谁?”
这一声空洞怪异的叫喊像是从我的身体内部发出的,有一种耳膜被震荡的感觉,让人想到被打碎的玻璃和玻璃上的血迹。
我在这个喊声中一下子怔住了。想起同样的一天,因难以忍受正午炎热的逼视,我曾一个人慢慢向厂房外的树林走去——一小排白杨树林围成的走廊,树叶儿有疏有密,走过去是有亮光的,再走过去却是阴凉昏暗的,明暗交替间,却差点忽略了倚在厂房入口处的一位老人。
他是工厂厂房的门卫。五十多岁了,人称瘸腿老赵。
此刻,厂房大门及窗子敞开着,老赵正伏在桌子上午睡,微偏着头淌下汗珠,赤裸的胳膊上趴着一只绿头苍蝇,像睡着了似的静止不动,收敛起的翅膀,似乎带着某种隐喻。
那一刻,我明白了他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成了这个模样,就是这样,而非其他。让我明白:“生活永远无疑”是可怕的,而“永远如此”更是可怕的。
在这样一个个令人窒息的正午时分,是什么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刻就静止?
一个月后的初凉季节,我从工厂辞职去上大学,彻底离开了南疆这座令人窒息的绿洲小镇。
文疯子
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闹市街头一棵茂盛的梧桐树下冲我招手。一个疯女人。
现在是夏季,边城6月的夜气潮湿而闷热。夜,仍然是那种熟悉的味道,已然从白日蔽身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弥漫视野。纳凉的人流在霓虹灯闪烁的街头来来往往,梦一样。每一个路灯下出现一团伞状的黄晕,像舞台上的局部照明,使街景像是一个非现实中的场景 , 偶尔有人碰触到了我的肩头、胳膊,我也感觉不到。我看不见他们,我只顾往前走着,仿佛多年以前就这样走了。
就在我驻足闹市区一家旧书摊时,一抬头,我就看见了站在梧桐树下的她。
她的身体瘦削而单薄,干裂的嘴唇泛着白皮,狭长的脸像被谁故意狠狠地扯了一把,五官奇怪地擰在一起,此时她的长发早已剪短,灰中带白,像一丛枯竭的植物,在黑暗中飘散。
我吃惊地看着这个奇异的女人。
她却冲我笑了。
并不是所有人的笑,都使人心悦。一个单薄如纸片似的黑瘦女人蓬散头发,背景是昏暗的树影,她几近呆滞的目光盯着我看,还笑。我的指尖,一下子就凉了,血一下子往脑门上涌。
她扑哧一声又笑了一下,翻了翻眼白,笑声低缓、短促。
她向我靠近的身体散发出一股不洁净的味道。
她的年纪不轻,穿着十几年前款式老旧的衣裙,头发一缕一缕纠结在一起,上面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球,她左脚穿着一只鞋,右脚光着,就骇然地站在那里,使原本浓稠的夏夜变得突兀。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围着看热闹。
她见有人围观,便很造作地将斜披在身上的破残的旧床单摇来晃去的,故意让半只脏污的乳房露出来。我有些替她害羞。
她无邪地冲我笑着,那笑是给我也像是给所有过往的路人。
而她就那样慨然地站在那里,我有些替她害羞。
旧书摊的女老板似乎同她很熟络,向她招了招手,她便笑嘻嘻地向她走了过去,她拖着一只偌大的旧皮箱,似乎刚从很远的地方下车,欲往很远的地方去。
“嗳,你才下飞机?”
老板娘像在调侃——“衣服真多,又买新的啦? ”
“哎——”她受了夸奖,扭捏地笑着,显得很兴奋,又扯了扯裹在身上的旧床单,上半身几乎半裸,她的皮肤、乳房……
“咦,干吗呢干吗呢——”看围观的人有些小小的骚动,老板娘突然有些过意不去,赶忙替她扯了扯身上的布单。
昏黄的路灯下,我仔细地看着她的脸。我想我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这张脸。那张脸上有着被生活毁坏了的痕迹,哎,怎么说呢?就在她笑着的时候,那张留着昨夜残妆的脸上有一种被极度痛苦磨损过的冶荡和怆然,我的心被猛地刺痛了。
啊,我曾在哪里见到过这张脸?
“我走了,我不能再继续了,但是他们不让我走,说什么一会儿你就好些,一会儿就一切正常。一会儿你就可以回家了……身上太热了。去年春天他们就告诉过我,我可以回家,我走了,他知道我十二点一刻下飞机,他会着急的。”
她急促地表达着,身体不停地在抖动,眼睛看着所有的人,又像是谁也没看。当她说到“他”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抹温柔的笑意,使那张被生活毁坏了的脸一下子焕发出动人的光彩。但她的声音仿佛被夜间闪烁的绿叶截断,撒落在看不见的地方。
她抿了一下嘴角,转身走了。
后来有一次,我又在这个城市的闹市街角遇见过这个疯女人。
她仍然是一身“盛装”,顶着缀满彩色珠子的乱发,光着脚,只是披在身上残破的床单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了。
无从知晓她的一切。只记得第一次在旧书摊上看见她的时候,书摊的老板娘对旁人说:“这是个文疯子,没生病以前她可是新疆小有名气的舞蹈演员哪!那时她可是有家的。”
一个女人,要伤多大的心,才会变成她这个样子,而那个负心人,现在又在何处风流快活呢?
我想我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这张脸。
当她把脸转向马路,就在这一瞬,我看见她的额头一侧有一块伤疤,血痂已经黑紫。
那是被人用乱石砸的。
在如此乱而大的世界上,一个女疯子也不太好做了。危险到处都是,总有人想找个不顺眼的人来揍。她们那副样子,一定是有人看不惯,找着机会了,就捡些碎砖碎石照她们的脸投掷过来。
我看着她的背影,像看一张随时迎风起舞的落叶。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在翻看某天的《都市消费晨报》。当我翻到新闻版时,一行新闻标题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热心民警奋力营救跳楼女”。内容是:某天下午,当地某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有一女子站在格兰德歌舞厅14层的楼顶边缘徘徊。不吃不喝已有两天两夜。经民警颇费周折营救下来,发现该女年纪尚轻,不停地咿咿呀呀地唱歌。
该警察判断:“她的神经有问题。”该新闻还配了摄影照片,我看见这个年轻女子蹲在地上,长发遮面,微垂着头,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只见她的双手紧紧攥着铁栏杆······
这样的新闻在每天各地的生活小报上比比皆是。但谁会在意呢?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不过是人们公车里或餐桌上的谈资。
被生活毁坏的人无处不在。而人是多么的卑微,连痛苦都不能救赎。是的,我们曾为之付出的一切,得不到任何救赎。
现在我在看她。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她——这个文疯子。她正拖着那只偌大的棕色皮箱轻盈地走着。
夜风吹拂着她身后破残的旧床单,人群中几乎没有人能触碰到她,她的背影孤傲而又决绝。
孤独的人不说自己孤独
人的感觉是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如声、光、软、硬、轻、重、形状、颜色、气味等通过感官在人脑中的反映。一般正常情况下,人的感觉、知觉、印象与外界的客观事物是一致的,但幻听、幻觉、幻视等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
这些人,他们的幻听体验是十分生动而逼真的,但会给患者的思维、行动带来显著的影响。有的患者在幻听、幻觉的支配下做出违背本性、不合情理的举动来。
而这样的疾病是需要隔离的。好在,有专门针对他们的医院。为了治好病,这些患者不得不从她或者他的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封闭式场所。身体一旦被隔离,病人们也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
比如,住在精神病院的一位50多岁的女患者,她住院之前,有一天出门买菜,耳边有个声音对她讲:“老妖精又出门了。”这位患者听到之后十分生气,便掉头回家。可耳边的声音马上又说:“装蒜。”
这家精神医院里还有一位正上大二的男性患者,坚持认为自己也是互联网的一部分,身体的所有信息包括思想和生理指标能同步传到世界各地。还有的患者在幻听的支配下,辱罵或殴打亲人、同事和路人。
这些人,都是孤独的人。孤独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像空气一样,没有颜色和形状,但很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被其笼罩和淹没,注定无法逃脱。因为,他们丧失了与这个世界、与他人沟通的通道,他们被自己或被外界关闭,对外界没有热情,对他人没有关心,到后来,那种与他人的隔阂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发加重了。其实,这种与他人隔开的东西正是来自于他们的内心。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近40岁的男子,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他的皮肤黝黑粗糙,头发蓬乱。当他趿着拖鞋从病房懒洋洋地走了出来,像个布袋子一样把自己扔到了椅子上,再也不想动。坐下,意味着较长久的停留,身体的松垮程度仅次于躺下。
的确,当我在精神病院里遇到他时,他的身体及精神都极为松垮,是一种被“打摆子”纠缠过的人才有的那种松垮。他说话时,言语断断续续,思维混乱,目光空洞而不能与人长久相交。
病历卡上,他的名字叫马跃。他是5年前因继发性被害妄想症而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的。诊断结果为:“典型性精神分裂症。”
他说,自己总是听到耳边有另外的一个声音对他讲“水里有毒”。
为喝上干净的水,他跑了不少地方。有一次,他提着暖水瓶竟沿着黑细的公路,穿过大片荒凉戈壁,步行了20多公里的路,才在一个乡村里找到了他自以为的“干净水”。
为这一壶干净水,他往返竟花去了近一天时间。
在这之前,他经常出现幻听,怀疑别人给他的碗里下毒药,而拒绝吃任何食物,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饿了整整4天后已奄奄一息。我看着他,似乎体会到了他说的那种饥饿感。那是一种被火烧灼的感觉,从胃部漫延到全身,灼烧体内的每一个感官和每一寸肌肤。这是一个巨大的唯一的感觉,挤压着他全身的力气和水分,而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最后,他被人发现,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体发出一股难闻的馊腥气。
给他治疗的主治大夫说,马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边防某部,是个副营级干部,从小性格极为孤僻自闭,后来,入伍后,又在荒凉封闭而艰苦的自然环境下一待就是七八年,缺乏与人、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机会。生活中没有亲友探望,没有通信,少有进城或回家探亲的机会。他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并坚信自己是一个卑鄙的、让别人厌恶的、有害的人。
转业后回到乌鲁木齐,他更是难以适应多元复杂的城市生活,一天到晚担心自己以后找不到工作,会被饿死才产生了妄念——
我知道,他向我描述的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尽管,他从头到尾没有说到这两个字。但是,我听见了从他的体内发出的荒凉的叫喊声。
现在,他在我面前,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司务长)为什么要迫害我?要在我的碗里下毒?我好多天都没吃上饭了,饿得很——”
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脑袋也耷拉了下来。
画火车的人
有的人,比我更迷恋火车。
前些年,央视的《小崔说事》节目中,我记得有一位做客的主宾叫王忠良。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一辈子专以画火车为生,有着很深的火车情结。他因为对火车有说不出的喜爱,把工作都给弄丢了,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周围的人都说他神经有问题,是个疯子。
他说自己把中国的火车从1860年最早的“零号机车”直到今天最快的火车“中华之星”全部都画完了。
从电视上看,王忠良是比我年长得多的一茬人。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他的皮肤粗糙,黝黑,话不多,看起来十分沉默,敦厚。但他细小的眼睛里沉淀出我所不了解的东西:边缘者的气质,天然的感伤以及观望。
他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幅摄影:《铁路上的流浪者》。
忘记是谁拍的了,但它肯定比甜腻直观的风情照片更能打动人心:占据画面的是站在铁轨边上的一位少年,那是一张疲惫的面孔,脸上有着黑色油污,火车似乎刚刚离去,又好像即将到来,空气中似乎还留有铁轨与火车摩擦出来的铁腥味儿。不知哪个方向的大风正吹乱了他蓬乱的头发,眼睛里燃烧着一种迷惘的激情——好像火车狭长巨大的气流正准备将他单薄的身体带走。
他似乎天生就属于铁轨。现在,他正向我们张望。但他的眼睛看不见我们。
“钢铁的客人马上就要来到,它将要踏上天蓝的田间小路——”
现在,大雨将至,天阴沉沉的快要压下来,布满黄褐色锈斑的冰凉的铁轨在他的身后无尽地延伸着,像一把冰冷、锋利的刀子,把什么都搅碎了——
远方,流浪的少年,冰凉的铁轨——摄影者就这样毫不掩饰地把这种日常性的痛苦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喜欢那些没有名气的但是一直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无法实现的梦想,卑微的欲望,痛苦的抉择和勇气——这些,都是我一直渴望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