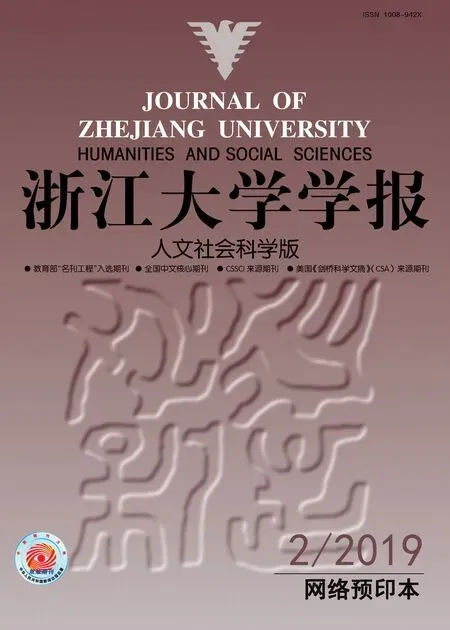论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与《神曲》的诗画融合
应宜文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是英国著名诗人兼画家,1789年他首创诗画共生的《天真之歌》(SongsofInnocence),又于1794年创作完成《经验之歌》(SongsofExperience),两部诗画集合为《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ofInnocenceandofExperience)。“前者描绘了世外桃源般的美景,赞美心灵的纯洁与善良,后者展现了惨绝人寰的场景,揭示了现实环境的世故与丑恶,两者诗文质朴,对比鲜明,爱憎分明,代表了英国工业时代来临时人们截然不同的两种精神状态。”[1]131《天真之歌》是他创作的第一部诗画合体、互文见义的诗集,合集《天真与经验之歌》是其诗学思想萌生的摇篮,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天真与经验之歌》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开始的标志。
布莱克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绘画同样被广泛认可,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家称布莱克是“大不列颠绝无仅有的最受欢迎的画家典范”[2]7。他为但丁《神曲》创作的插画是毕生最后一部长篇彩绘作品,也是其诗画艺术集大成之作。据考,当时的著名风景画家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1792—1882)煞费苦心地为布莱克的作品寻找收藏者,在林内尔的引荐下,布莱克有机会接受委托为《神曲》创作成套插画,他总共创作了102幅插画,其中7幅插画仅呈现雕刻轮廓线,并未上色。他不曾去过意大利,然而,他在接受委托后深受鼓舞,系统地解读《神曲》,全力以赴地投入精妙的艺术创作之中[3]38。因得到林内尔的赞助,1824年夏,布莱克开始为《神曲》创作插画直至逝世[4]110。他痴迷于以图像方式对原著进行再创作,是因为他的经历、观念、思想与这部史诗的主旨及内涵产生了共鸣,纯粹的诗画创作使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那般无忧无虑的创作状态之中。他正是借助但丁的《神曲》表达其艺术观念与审美意趣,通过独步一时的插画作品表现其诗学思想。
一、返璞归真与色彩写真
“布莱克是一位从不伪装、不戴任何面具的人,他的志向专一,沿着正直的道路前行,他索求甚微,故而表现得慷慨自若、高贵而快乐。”[5]2119世纪著名雕刻家兼画家塞缪尔·帕尔默(Samuel Palmer,1805—1881)在写给吉尔克里斯特(Alexander Gilchrist,1828—1861)的信中认为,布莱克为人真诚,举止稳重,心性纯真,人格高尚,才智超群且富有耐力。布莱克的老友本杰明·希思·马尔金(Benjamin Heath Malkin,1769—1842)认为,布莱克身上带有一种“古典主义的淳朴个性”,他的诗歌创作不同于18世纪英国奥古斯都时代的形式主义诗学风格,使其成为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先行者[5]7。
绘画讲“画如其人”,文学讲“文如其人”,诗歌创作亦是如此。布莱克的诗画作品演绎了一种率真质朴的风格,这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他的创作过程不是写完诗歌之后单纯为美化纸面而增加绘画,更不是先完成绘画后为了弥补画面空缺而创作诗歌,而是诗歌与绘画互为生发,创构而成。”[6]335他早年创作的《天真之歌》描绘了世界的自然本原,流露出孩子般的纯真无瑕,展现出人们心中渴望的美好。正如《羔羊》(“The Lamb”)一诗:“小羊羔我要告诉你:他的名字跟你一样,他也称他自己是羔羊;他又温柔又和蔼,他变成了一个小小孩,我是个小孩你是羔羊,咱俩的名字跟他一样。”[7]24这首诗的隐喻与韵律如同孩子们彼此坦诚的一问一答,“小孩”和“羔羊”代表新生,使读者自然感受到天真,诗意毫无世俗观念且明朗晓畅。诗歌画境中运用精心设计的青草地、绿树、枝叶、建筑等来阐释诗歌的象征意义,画面近处通过羔羊与小孩对视交流,展示一种真实自然的场景,探索自然、动物与人的真谛。此外,同诗集的《牧童》(“The Shepherd”)、《欢笑的歌》(“Laughing Song”)、《婴儿的欢乐》(“Infant Joy”)等诗篇,都呈现出自然写真的诗意与画境。
无论是布莱克的第一部诗画合集还是他暮年创作的《神曲》插画,他的诗画艺术打开了心灵深处最真实的一扇窗。“这些境地——不是如人设想的为灵感所激,也不是无师自通——就是使他天真的境地。”[7]2他的艺术创作个性鲜明、意趣悠长,他凭借自己的兴趣融入更多再创造的因素。青年时保留在作者心灵深处的天真梦幻景象似乎在暮年得以再现,如《神曲·天堂篇》第25章第15—102行插画,布莱克表现画面人物时运用环绕式的对称构图展现空灵飘逸之感,又突出了原著的诗意;《神曲·天堂篇》第26章第103—139行插画,布莱克采用环绕聚集的构图呈现欢腾鼓舞的场景,画面左右两侧各绘四颗星星预示着未来之星,又增添了一份孩童般的天真烂漫,人物的目光与姿态随兴而动,自如地遨游在宇宙之中。这种返璞归真的想象与超然物外的画境正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布莱克的诗歌多通过色彩来展现真实感。在其《天真与经验之歌》《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MarriageofHeavenandHell)、《美国:一个预言》(America:aProphecy)、《欧洲:一个预言》(Europe:aProphecy)、《尤里森之书》(TheFirstBookofUrizen)等作品以及《神曲》插画中,色彩表现成为布莱克诗画艺术的大布景,缤纷的色彩凸显了诗画特点与诗歌寓意,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的自然色彩表现,又有抽象、想象的色彩表现,每首诗都有相应的色彩作为背景,这种色彩背景衬托出诗歌耐人寻味的象征主题。如《经验之歌》的《序诗》(“Introduction”)配图为深蓝底色,隐喻阴沉昏暗的星空。又如同诗集的《扫烟囱的孩子》(“The Chimney Sweeper”)配图采用单一的深棕色描绘诗文、人物以及画面形象并配以大面积素淡的黑灰色作为底色,不仅渲染了煤烟污染四处弥漫的气氛,更能够相辅相成地表达诗歌的真实寓意。《神曲·地狱篇》第7章第128—134行插画同样运用了简率洗练的黑白单一色调,从近景的人物、建筑、船只到远景的水面、远山、天空,在黑色笼罩下显得格外阴森,这种色调恰恰与但丁原著诗意契合。布莱克诗画变幻不断的色彩自然流露出他真实的创作思想并有助于表现诗歌的真情实感。
二、爱憎分明与色彩镜像
在布莱克毕生创作中,《天真与经验之歌》与《神曲》插画是能够共通且前后呼应的作品。两者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对比强烈。由歌颂心灵纯真与善良的《天真之歌》到揭示现实世故与丑恶的《经验之歌》,是对善与恶的辩论;同样,他为《神曲》创作的插画表现从地狱、炼狱到天堂的升华,呈现了一幅幅迁想妙得的佳作,又是对如何弃恶扬善的探讨。鲜明对比的诗意在艺术表现上产生了绝佳效果,充分展现了布莱克精彩绝伦的创作能力。二是爱憎分明。布莱克为《神曲》创作的插画充满了对善与恶的审度,追求高尚人格的意义。《天真与经验之歌》深刻剖析了西方18世纪的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蕴涵了对真诚与虚伪、仁慈与冷酷、美与丑的辩证反思。从少年懵懂入世到中年经历人生沧桑,直至暮年返璞归真的诗画创作,他的诗学历程最后回归理想的境界,追求心灵的升华,崇尚美好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他创作的诗歌还是插画,都充满了思辨精神。三是具有伦理教化作用。他创作的在英国家喻户晓的名诗《老虎》(“The Tiger”)已选入教科书,成为青少年必读的范文。20世纪以来,他的诗画创作以各种形式被选用在动漫及海报设计、相册封套、书籍封面之中。这些诗画交融之作体现出他崇尚美好并始终怀有慈悲之心,这些创作始终充满想象力,始终留有一块“天真”的净土,表达他对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
布莱克的诗画作品富有色彩之美,色彩是他诗画思想的一面镜子,也是一种表达诗歌意象的重要语汇。生动多样的色彩不仅营造出与诗意相契合的视觉表征,而且也是对诗歌主题、内涵及意境的一种暗示。从诗歌文本的色彩配置具体分析,《天真之歌》的《序诗》配图构建了左右对称的布局,运用嫩绿色的植物藤蔓作为象征,栩栩如生,诗文以明快清新、由浅至深的钴蓝晕染作为底色,这种色调正可呈现诗歌开篇满怀希望的隐喻含义。同样的色彩表达方式在他暮年创作中再次出现,如《神曲·地狱篇》第3章第1—10行所绘的“地狱之门”,采用同样的画面构图作为序言的插画,其左右对称的大树与藤蔓运用突兀森郁的墨绿色来隐喻这一场景的特殊性,画面的背景由凝重而沉闷的深蓝色渲染,尤其是树干用色和背景色相互映衬,笼罩着一股“黑气”,一种默契神会的隐喻象征跃然画上。布莱克以色彩镜像揭示了诗歌主题,由表及里多层次地映射出诗境内涵。
综观分析,色彩镜像在布莱克的传世作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擅于运用透明纯净、清澈妍丽的色彩抒发诗意,表达他对善良、仁慈、和谐的赞美之情,如《天真之歌》的《飘荡着回声的草地》(“The Echoing Green”)一诗配图中高纯度的鲜绿草地与雅淡的青绿树叶交相辉映,加上浅蓝色与绯红色渲染布景,绘图妙于得意;又如《天真之歌》的《花朵》(“The Blossom”)一诗中轻施淡染着朱红与藤黄的布景色,意在互映互衬,构成一幅平淡天真的画境。他还运用各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以及灰暗、浓艳、浑浊、黑沉的深重色调,抽象地呈现诗歌所表达的隐喻及含义,这在《经验之歌》以及《神曲·地狱篇》插画中随处可见。色彩镜像可视为解读布莱克诗歌的一把金钥匙,能够开启其精妙入神的诗画艺术宝库。
三、纯美想象与宁静祥和的画境
布莱克的诗画创作充盈一种唯美意境,纯美的想象始终发挥着独到的作用。如《天真之歌》的《春天》(“The Spring”)一诗:“白天夜里,鸟儿欢喜;山谷之上,黄莺歌唱,天上云雀,欢喜雀跃,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来临。”[8]111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自然意象无处不体现出春天的蓬勃朝气。原作诗文与图像融于一体(图1),其图像上方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怀抱婴儿,婴儿天真活泼充满欢喜,伸出双手欲与羔羊“对语”,这一幕展现母爱的温暖与亲切、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间,歌咏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象;图像下方是与众不同的英文书法,这首诗歌的主题词“Spring”被诗化了,字母“S”尾部呈飘带状,字母“g”上下呈呼应状,书法字体飘逸灵动、轻盈欢快、热情奔放,英文字体与绘画融为一体,字体的组合使人们感受到春天的欢乐之情[9]148。这首赞美春天的诗从整体来看,留给人们对春天的纯美想象与无限憧憬。这种美的源泉一直延续到布莱克暮年的插画创作之中,如《神曲·天堂篇》第24章第20—31行:“这灵光,围着贝缇丽彩,一连三度在旋绕;并且唱了一首歌,歌曲神奇得连神思也无法向我复述。”[10]334原作画面旋绕的线(图2)与《春天》英文书法的线构成了极其相似的唯美旋律,有一种欢欣鼓舞的韵律,呈现了对爱心与希望的视觉想象。两幅不同时期的创作都以灵动飘逸的线条表达诗歌所蕴含的真挚情感和美好愿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1 《天真之歌》的《春天》

图2 《神曲·天堂篇》第24章插画
对纯美想象之神往使布莱克即便面对苦难、恐惧甚至悲壮的诗意,也仍然在画中表现出一种美。如《经验之歌》的《虻虫》(“The Fly”)一诗:“我难道不是一个像你一样的虻虫?你难道不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7]140布莱克将自己想象成一只虻虫,不知在何时会被偶然扑灭,隐喻了生命无常的悲惨命运。他不愧是一位想象力大师,如此的境遇在图文并茂的诗画中竟然表现得一派欢乐美好,充满生活情趣。诗画原作上方的诗文与大树的枯干相连,只见一只虻虫穿梭在字里行间,起到了平衡画面的作用;下方展现了一位身姿优雅的少女正在挥手,一位母亲正拉起孩子的双手尽情欢笑,在诗人笔下将面临湮灭的可怕险境变成了纯美的画境。同诗集的《老虎》一诗由强烈的问题构成:“是怎样的槌?怎样的链子?在怎样的熔炉中炼成你的脑筋?是怎样的铁砧?怎样的铁臂敢于捉着这可怖的凶神?”[11]1194-1195从诗意可以想象,画面将出现一只发怒时张牙舞爪的老虎,然而,布莱克的原作却展现了格外平静泰然之景象,老虎的眼睛炯炯有神,神情若定,悠然而行,丝毫没有让人感到恐惧,尤其是画面上的大树和树枝都呈平直之势,烘托出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气氛。诗人不仅巧妙地运用连续重复的提问以及诗句的节奏,而且通过描绘富有视觉寓意的动物形象来想象他心目中的“巨人”。
显然,诗人早年的诗画艺术对他一生具有重要影响。即使最为阴森恐怖、胆战心惊的场景,在布莱克的画境中也绝不会令人不堪入目,仍然唯美而充满想象,展现一种独特之美。如《神曲·地狱篇》第6章第12—35行:“守护冥府的三头狗——一只既可惊又凶残的三颈兽,声貌和凡犬相似,正居高临下,狂吠被淹的亡灵。它有垢腻的黑须、血红的眸子、庞大的巨腹,手上长着利爪,这时候正把亡魂剥撕抓……”[12]95-96这是多么惊心动魄、令人骨寒毛竖的情景,画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1832—1883)曾为这一幕创作插画,其画面忠实原著,如实地表现地狱第三层触目惊心、恶兽厉嚎、惊慌失色的情状。然而,布莱克的插画将凶险可怕的背景变成了浮光掠影的抽象布景,将凶神恶煞的怪兽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动物,维吉尔张开双臂正在帮助那些怪兽,犹如给宠物喂食一般慈祥博爱。布莱克那纯美的想象一直萦绕着他,对《神曲》原著所描述的丑恶可怖的场景他也不屑一顾,在他的想象中,仿佛一切都和风细雨、波澜不惊,他的心灵总是沉浸在美好而祥和之中。学者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1717—1768)称:“正如大海的深处经常是静止的,不管海面上波涛多么汹涌……”[13]5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显示一种“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14]72。布莱克没有将人生的坎坷、身体的病痛、心中的不满发泄于创作中,却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幅唯美宁静的画境。
四、结 语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布莱克从来没有直白地将求真、求善、求美当成写作目标,而是通过他毕生的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创作水到渠成地诠释了他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从《天真与经验之歌》到《神曲》,充分体现出他返璞归真、爱憎分明、崇尚美好的创作主旨,真善美可以说是布莱克创作思想的一条主线,将其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贯穿起来,凝练成诗画共生的审美意境。色彩因素实质是解读布莱克诗歌的一面明镜,通过镜像照射出布莱克诗歌的隐喻含义与空灵诗境,我们从其艺术作品可以品鉴到一种真诚、善良、正直的浩然之气。
诚然,布莱克从《天真与经验之歌》到《神曲》插画的创作前后呼应、一脉相通,他的《神曲》插画深受早期创作观念的影响,《天真与经验之歌》由诗歌艺术逐渐趋向绘画艺术,《神曲》则由绘画艺术最终回归诗歌艺术。布莱克选择了一条适合发挥其才华与玄思的创新之途,恰到好处地将两种视觉审美艺术完美融合。他的创作过程可谓“诗心入画”,诗歌艺术激发了其绘画艺术的活力,他将艺术观念与诗歌内在精神融会贯通,实现了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