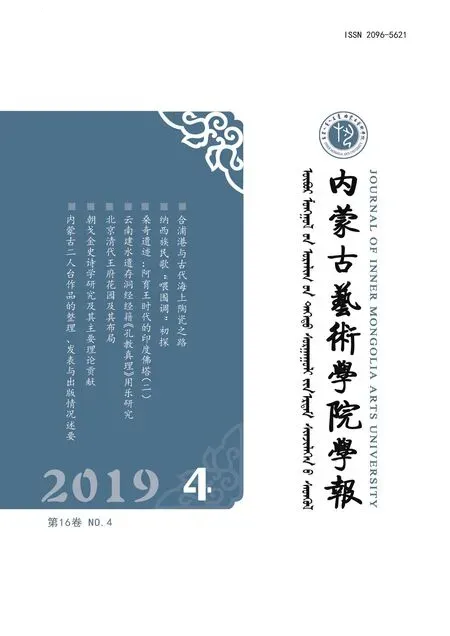表现与生成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中的宗教体现
宋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一、引言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其艺术主旨比较明确,每一件艺术作品似乎都有一个主题,如果要想此艺术作品的主题性能够发挥作用,需要极尽表现其艺术特色。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特色,似乎在艺术作品中能够窥见,当然,这也和艺术作品的风格、表现等有关。风格似乎与表现可以相媲美,这本身也涉及哲学的一些概念。本文,笔者试着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宗教表现进行一个交集式研究,或许对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能有更深入了解。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先民是信仰原始宗教的,他们会凭直觉感知世界带给他们的感觉,当面对生态环境或生活中的困难事件无法解决时,他们希望有神灵的护佑,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就是他们信奉的原始宗教。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无论艺术起源于何种理论,是游戏论亦或模仿论还是创造论,均不能整体概括艺术的起源。民间艺术中,宗教自然是民间艺术产生的根源。在原始宗教、民间信仰中产生的民间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生活中所用的一些物品,人们在最初的原始信仰仪式活动之中,通过“神人的沟通”,人作为主体参与进来,人的思想也参与进来,在仪式之中,人的精神得到了满足,人作为主体参与的宗教实践活动中使用的这些物品是能够体现出艺术审美思维,这种宗教实践活动就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些民间艺术特点。
其实关于宗教起源问题,“历史上已有无数哲人都谈到宗教起源于人的恐惧感与依赖感问题,休谟、费尔巴哈、罗素、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卡西尔等都对此有过论述。”[1](19)过去,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人们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会产生焦虑和恐惧,于是巫术和神话便产生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面对自然界的恶劣生态,他们会对其产生神性的崇拜与祈祷,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东西会以人格化的形式赋予他们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带有神性。马林诺夫斯基曾说:“在一方面有对于巫术效能的信仰,另一方面必有主观经验所产生的幻想之一与它相平行;这样的幻想,在文明的理性家是过而辄忘的,然也不是全不存在的,可是对于任何文化里的单纯人物,特别是对于原始文化的蛮野人,那就十分有力量,十分信而不可疑。”[2](100)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环境比较险恶,当他们面对环境的险恶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生,希望神灵护佑。比如面对高大巍峨的山脉,他们会对其以跪拜,用盛大的节日向山神跪拜,希望能得到山神的庇佑,在当时环境低下的时期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万物有灵”的观念不是没有来由,这是希求它们保护,逃避灾难的求生意识的一种表现。
二、民间艺术中的宗教观念表达
从北方民族的信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原始艺术中的审美心理、审美观念及艺术特征。世界上的很多民族关于信仰的来源,都有一些神话和传说。《圣经》中“创世纪”描写洪水泛滥了150天,所有的高山等都被淹没,所有的生灵都已死亡。中国这样的神话也很多,尤其是少数民族。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3](35)自然界的确千变万化,从而使原始先民心生一种恐惧和焦虑,这样的一种内在压力与生存环境的外在压力才是原始宗教生发的源泉。
游牧民族各种文化活动中,特别是在一些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中,人们在那种环境氛围产生的各种心理比如敬畏、恐惧等因为在仪式的氛围中从而显得更加神奇,这里面的艺术作品的审美特点也是依靠这些神巫意识或者原始宗教才可以解读。虽然说神巫意识和宗教还是有些微差别,神巫意识有点原始宗教表现的神秘心理,原始宗教有点人为宗教表现的神性心理,但是两者本质还是差不多的,都具有一种神秘色彩。有学者说:“神巫意识指的是人类早期表现出的一种原始神性心理,它是原始宗教观念所赋予的。它不同于人为宗教所表现的神性心理,主要在于把‘神’与‘巫’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神巫意识。神巫意识的核心是原始文化中所包含的灵魂观念。”[4](52)很多少数民族中这种神巫意识还是存在的,虽然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下,很多文明已然被现代文明掩盖了,但是有些已经长久地存留于民众心理和一些艺术活动中,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也从而使各民族文化放之光芒。
时间在推移,物质文化一直在进步,在进步的同时人们不难发现宗教意识还是人们的心理需求之一,因为对于人类来讲,宗教意识不仅是民众信仰的核心,它对人们的审美也起到一定作用,是人们审美文化中的核心元素之一。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中,宗教元素不可缺少,这也成为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具有支配或主导力量的因素之一,因此,宗教也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有着审美因素的显现。人们的审美活动中能够显现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的表达。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本身具有原始巫术的特点,也显示出了“神性”的表现。有些宗教仪式中,它的功能表现的并非只有一种。 “它是一种多职能的混融性结构,是一种若干社会需要借以同时见诸实现的形式。除了满足用幻想来弥补原始人在实践中的缺陷的需要(这种需要由于相信仪式具有超自然的巫术力量而见诸实现),仪式还满足他们在求知、教育、抒情和审美等方面的需要。”[5](52)在某些仪式之中,民众的审美需求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仪式之中本身就具有一些造型艺术,比如一些面具、服饰、图案等,这说明原始宗教的混融性特征是能够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也有这样的特征,即在宗教意识中有民族情感的表达也有审美的表现,这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很多艺术作品中均有体现,比如绘画、雕塑、岩等,虽然说可能和最初的原始宗教意识并不是很匹配,但是其宗教功能无法脱离。这些宗教艺术的表现形式应该说是艺术和宗教相结合的综合体现。
不同时期的艺术表达形式不一样,比如匈奴时期的岩画或是青铜器物上面的造型很多是以动物为主的形象,那些比较艺术的动物纹样源头我们可能拿捏不准,但是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巫师或是萨满的艺术作品,整个艺术作品应该是当时人为因素很多,是人在建构,人在设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作品比如一些图腾形象的创造,本身具有象征文化内涵,这些不一定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财产,但是却是他们全体游牧民族的艺术。这些艺术作品表现的艺术特征是通过游牧民族的思想与行为表现的一种艺术审美表现,表现了游牧民族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情感。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看,实际上那时的艺术审美并不强烈,这可能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关,当时人们只是需要一种心理慰藉,所以刻画的一些艺术形象只是起到一种祈愿和希望,人们希望能够通过祈愿达成自己的心愿,能够获取生活资源。而这时期的宗教的功能与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撼动的,艺术创作者们从宗教中吸取的灵感创作的艺术形象虽然不具备独立的欣赏审美功能,但是它们作为宗教观念的产物的象征性是不可被淹没的。当物质文明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期盼生活生产资源容易达到,人们需要更多的精神世界的东西支撑,他们所创作的艺术形象便更多的是从审美角度出发创作的艺术形象,宗教功能其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通过一些绘画、岩画、雕刻、刺绣、剪纸等艺术形式把一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或动植物形象创作出来,除了有宗教功能,重要的便是其审美功能了。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宗教最初是独立存在的,艺术性应该相对较小,直至后来才有艺术的审美存在,当艺术开始依附宗教存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想象色彩的,而艺术为艺术存在,其中的艺术形象中有宗教元素的显现。
原始宗教最初开始出现直至后来盛行,这期间的艺术作品的创造应该并不是全部的艺术为艺术而创作的,宗教功用性在其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艺术形式应该是为宗教服务的,所以它应该是艺术附属于宗教,但同时它是宗教和审美同时有功用性的,而宗教的功用肯定要大于审美的功用。客观地看,实际上它是具有艺术性又具有实际功用性的。到了后期阶段,当人类社会逐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虽然宗教依然是人们的精神信仰,但是当它不再是唯一的主要的生活重点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艺术也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艺术开始独立存在,艺术形象的创作也开始有独立的审美特点和意义,艺术可以独立表达审美思想和情感。所以,历史地看,艺术为艺术存在是在艺术依附宗教存在的基础上逐渐进展而来。漫长的事物演变过程中,通过生活生产或实践最终能有一种审美精神的独立存在,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才出现的。正如有的学者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实践中必要的表象因素越来越削弱,即它作为生产实践的一部分的地位越来越显得没有必要,图画的功能和作用便开始转移,如转移到“记事”等方面。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在“记事”的过程中,人的审美精神也不断积淀于记录下来的图画里。这样的图画除了记事的中心作用外,同时蕴含着使人愉悦的审美的成份了。但它还不是纯粹的艺术品。等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了,绘画的生产实践功能——如作为宗教仪式上的表象——几乎消解殆尽了,绘画的应用性功能——如作为记事的表象——弱化到可以被忽略不计,那时候,它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就明显地突显出来了。”[6](2-3)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就是如此,宗教地位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的一些面具、绘画等,当它们的宗教功能祛除后,它们才可以称之为独立的艺术,其艺术审美也是独立的,但并不是说有了宗教的功用的艺术就没有审美价值了。很多民间舞蹈就是最初由宗教信仰有关而创作的舞蹈,逐步过渡到独立的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宗教意识是这些艺术创作的原初,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需求是从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和宗教仪式活动中生发出来的。“不妨假设,原始人的已经萌生的审美需要是在两个基本方面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审美需要直接见于劳动活动,首先是见于制造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活动。在这里艺术活动同古老宗教没有联系。另一方面,审美需要见于原始仪式。其中,艺术胚芽同原始宗教信仰无疑具有联系。”[7](62-63)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作品有些是从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中生发出来的,有些是和宗教仪式有关的艺术作品,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宗教的作用,因为原始先民最初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宗教在他们生活中有着慰藉作用,对其生活有很大影响,这对他们审美思维及审美意识均有导向性作用。
从原始先民开始,他们信奉的是万物有灵观念,也就是灵魂观念,这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基础。也从而使原始时代开始的一切精神文化产品打上了灵魂的烙印。在一些巫术仪式或宗教活动中都是如此。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因为信奉的是萨满教,这本身就显示出灵魂观念,灵魂观念也成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宗教观念产生的自然根源。游牧民族对一些自然现象、各种灾难等都无法应对时,当他们生活出现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他们都把这些与灵魂观念联系起来。虽然现在游牧民族的文明也很发达,但在现时代,游牧民族还是信奉灵魂观念。对于万物有灵的观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说:“原始的万物有灵观以众所周知的观点,如此令人满意地阐明了事实,以致它甚至在高级文化阶段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虽然古典的和中世纪的哲学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它,现代哲学对待它则更为无情,但它仍然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原始性的痕迹,以致在现代文明世界的心理上,还清楚地透露着原始时代的余光。”[8](351)这说明,无论现代文明离原始文明有多远,但是其余光仍然照耀着现代文明,而现代人的心理则无法割舍原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思维观念里,万物都是有灵魂的,当出现各种灾难、疾病缠身等各种现象时,人们便会认为这是神灵所致,必须依靠仪式来解除。在他们的信仰中也是有这些观念存在的。他们有祖先崇拜的观念。《后汉书·乌桓传》中记载:汉昭帝时,乌桓曾挖掉匈奴单于的冢墓,匈奴大怒,发兵东击乌桓。《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送葬,有棺椁、金银、衣裘,而已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从随葬的物品看,说明匈奴人是相信灵魂不灭的,崇拜祖先就是灵魂不灭的一种表现。他们相信生者生前所穿什么,死后亦所穿什么。可以说,灵魂观念在游牧民族社会中一直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它成为原始先民们宗教观念意识的源泉,这些文化对他们审美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影响。
当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游牧民族的审美思维和审美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随着本民族活动的发展而在不断变化多元,改造自然的能力也逐步增强,也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游牧文化中的灵魂观念必然也会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从最初的万物有灵观念开始,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活着的,都是有灵魂的,在这个事物背后必然有一种支配它的‘魂’,他们对一切事物能够产生畏惧感也能产生崇拜感。
北方游牧民族社会中,宗教一直在起着重要作用,而由宗教衍生的审美关注的元素也是和宗教相关,在原始先民的世界观中,最初的审美应该是和宗教相联系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极大,所以他们的信仰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也就形成了原始宗教观念,从而宗教的仪式活动也备受重视,仪式也被重视,仪式之中的物品的审美自然也被重视,当宗教一旦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精神食粮时,那么表现在生活用品等物质层面里的东西,是能够看出宗教其中起着主线作用的。
我们说如果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文化和审美文化是交互的,两者之间应该并无实际界限的区隔。黑格尔说:“艺术却已实在不再能达到过去时代和过去民族在艺术中寻找的而且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寻找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至少是宗教和艺术联系得最密切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9](14)虽然黑格尔的时代和现在社会大环境已然大相径庭,但是他的看法却值得我们思考。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世界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和对在其中变化之中的认知。逐渐认知的过程其实就是审美逐渐清晰的过程,过程中的审美也是游牧民族的审美思想表现的过程。在游牧民族的认知哲学中,他们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意识和对世界的认知有关系的,当对世界认知逐渐清晰时,审美认知自然逐渐清晰明朗,对世界的认知构成了审美思维中的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也是艺术作品的构成元素。任何事物均有自己的构成法则,事物之间的要素是会相互制约和影响的,这些要素在相互和谐和相互制约的过程中,无论彼此间是和谐还是制约,这也是他们存在的方式之一。游牧民族的认知世界方法,也是他们审美形成的方式。游牧民族的审美哲学里,他们认为自然造就了万物,美也是其中一种,而游牧民族创造的美则是实践美学的一种。
三、结论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要满足生存。生存是第一位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是通过自然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他们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面对自然力不从心,于是想通过对自然环境以一种人格化的理解,在人格化面前,人与自然的沟通表现在精神方面。游牧民族的历史文献中,很多服饰、装饰、宗教仪式中的物品都是审美对象的一种。人与自然的沟通交流使得人对自然有感情的寄托,人自己创造的神灵形象也影响着人类自己,导致本来以物质为最终目的的产品最后成了精神产品。
游牧民族的原始艺术最初是始于原始宗教,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原始先民深感自己的无力和渺小,当他们不能驾驭外界他们就会希望能得到神灵的护佑,这表现在很多的巫术活动中,而仪式之中使用的一些物品的图案则是宗教的体现和审美的表现。总之,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活动实际上也是他们审美的表达,也是他们信仰的表现,这种彼此依托彼此依附的关系本身就造就了艺术作品的形成,是审美的表现,也是对宗教的依赖和信任的表达,由此可见宗教在其中的重要性。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的审美本身就是一种形态的表达,一种精神的表现,艺术作品通过一些具有设计感的图案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有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在其中,也深含着游牧民族的审美情感。艺术作品中,创作者的思想固然重要,但是创作者本身也是作为游牧民族中的一员,他的思想能体现游牧民族他们的独特审美表达,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民间艺术中,宗教的主题性是主要的,其和形式之间是彼此交融互通的。总之,民间艺术中宗教元素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