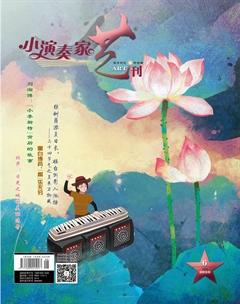陈嘉敏:将祖国小号之声奏响世界
申申 金音
与恩师卡普林斯基在一起
沐浴在大师怀抱中成长
有一次,我與单簧管教授赵增茂在琴房聊天,赵教授提及陈嘉敏教授就在琴房隔壁,早就闻其大名的我得此机会立刻前去拜访,从此便与陈嘉敏教授建立起常来常往的联系。
小号是一种古老的乐器,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古埃及和日尔曼部落的图画中就曾首次出现,根据埃及法老王图唐卡门的金字塔中发现的银质号角来推算,小号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可它进入中国或者说为国人知晓却是近些年的事情。
可以想象,当年陈嘉敏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期间,这门学科不论师资还是教材基本全是空白。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极为开明的夏之秋教授,至今他还记得夏先生用蒸馒头的步骤形象地比喻小号的学习:“拿两斤面揉成长条,二两一个,手指划,拿刀切,分开其中,揉成长条的两斤面就是长音,手按份分时就是很软的吐音,刀切开来的是顿音,分开的全部是吐音。此外,吹短的声音要用舌尖找感觉,吹柔和的音要用舌面找感觉。”
更可贵的是夏先生带着陈嘉敏遍访各学科大师,在陈嘉敏的记忆里至今清晰地记得跟随朱工一教授学音乐作品的处理,跟随沈湘教授学声乐发声的气息,跟随江文也教授学作品分析……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当年认识深陷“文革”囹圄的台湾籍“肖邦”江文也教授的情景,那时身为学生的陈嘉敏遇到衣衫不整的江文也教授在校园打扫厕所,攀谈后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居然颇有学问,后来才得知他便是大名鼎鼎的江文也教授,不禁敬佩至极。
“文革”开始时,陈嘉敏已成为中央乐团的一名演奏员,京城各大乐团所有重要的小号演出都能见到他熟悉的身影。尽管曾与奥曼迪、卡拉扬、小泽征尔合作过,也受到过大师的好评,可在那个年代,性格率真的他却难以受到重用,还常常遭到排挤和污蔑。
是金子总会发光,当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到中国演出舞剧《白毛女》时,伴奏乐队挑选的是上影乐团。在北京演出的那一场下午走台时,原来的小号演奏员嘴上起泡没办法吹,领导急得团团转,这时才想起找圈里赫赫有名的陈嘉敏来救场,没想到之前连总谱都没看过的他,前后两个小时的演出竟然毫无差错,令全场所有的上海演奏员目瞪口呆,从此在上海音乐圈美名远扬。因为在舞剧《白毛女》中的出色表现,陈嘉敏不仅在中国同行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还给日本同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1980年,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按捺不住求贤之情,力荐陈嘉敏前往美国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从此纽约爱乐来了第一位华人,世界管乐界也知道了中国优秀小号演奏家陈嘉敏的名字。
回国就是为了填补管乐空白
在海外,陈嘉敏的事业可谓如日中天,他说当年出国不仅仅是因为待遇,更多的是想开阔眼界。出国前,他觉得自己的演奏不错,但到了纽约,听到世界一流的铜管乐演奏家的演奏,瞬间发现差距很大,“做个比喻,搞音乐和盖房子不同,盖房子只需要打一次地基就行,而搞音乐需要打一次地基,盖两层,再打,再盖,永远不停地继续下去。其次,从曲目上讲,在中国多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唐吉诃德》等类似舞剧风格的演出,哪怕是在中央交响乐团,也多是柴可夫斯基等前苏联作品。而我到了纽约则是一星期两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仅有三次排练,许多作品更是我闻所未闻的。因为连听都没听过,我只有悄悄地学习,把乐谱带回家,再去图书馆借音像资料,一边看一边练习,虽说很辛苦,但学到了很多东西。”
1997年,在祖国的召唤下,已五十五岁的陈嘉敏想得最多的是祖国管乐事业的滞后,当年自己求学期间国家花巨资请来德国专家,也是希望中国管乐能早一天跻身世界前列,想到这里便毅然决定回国再干十年。
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服务?”他莞尔一笑,答道:“因为我太太的缘故,她是上海人,又是杨立青院长的同学。”
有一次我在他的琴房聊天,问及国内教出来的小号学生与国外最大的差距是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学生的所有通病我曾经都有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有口吃,学小号的学生大多没有吧,为了这个问题,我花了两年时间练节奏,现在才刚刚够用。还有,我们的学生不太重视基本功,太注重‘花腔,尤其是业余考进来的学生,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的学业都很紧张,根本没时间练习基本功,因此进了大学我得从头开始帮助这些学生练习基本功,尽管每天早晨七点开始我就陪着他们练,如此花时间花气力,但还是难出优秀学生。”
2000年,陈嘉敏教授刚刚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执教的第一个学生王逊,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担任小号首席,如今又回到家乡担任贵州民族大学小号教授。王逊告诉我:“在上音的四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小号入门的‘口径,痛苦极了,所幸在大学最后半年遇到了陈老师,让我顿时开了窍,一时间突飞猛进啊!”
凑巧今年有个学生要考小号专业,聊天时我向陈嘉敏教授请教了几个问题:
问:学习小号需要什么条件?
答:在初试时,我看考生往往会看他的嘴唇厚薄、肌肉方向是否正确、音色和吐音是否规范,当然还有在演奏时的嘴型、吐音和气息等的运用,即便是他的练习曲程度一般,我也会觉得比较规范。反观一个考生吐音不清晰,嘴动时又有倒勾的音色或者大肚子音,加上音色厚度不够,嘴型又是“地包天”,即使练习曲的程度很高,我以为从长远发展来看也会减分。
问:演奏海顿协奏曲用降E调还是降B调小号?
答:国际上有个别比赛规定要用降B调小号演奏此曲,但大部分演奏家都采用降E调小号演奏。在国内,音乐学院不会指定用什么调参加考试,况且降E调小号除了个别颤音相对好演奏外,其他的音准、音色以及气息的运用都比降B调小号难掌握。
问:小号的颤音怎么用?
答:小号的颤音在美国是用手,在俄罗斯则用嘴,它只能在独奏时使用,在乐队是万万不能使用的。
陈嘉敏教授认为教初学者正确的口型有两个原则:第一,越自然越好,也就是唇周肌肉要放松,上下唇形成相对平整的平面,嘴角不要向后拉;第二,口型虽然有一定的基本规范,但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他举例说:“如果学生的牙齿是下牙凸出,作为老师就不能勉强他上下唇是一个平面。同理,如果学生天生下颌向内收缩,也不能勉强他举号的角度呈九十度。”至于号嘴在嘴唇上的位置,只要保证气流是沿着号嘴方向进行就可以了。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学生,除了严重影响小号演奏发展的,陈嘉敏先生都不赞成改口型。
小号作为管乐乐器,需要很好的维护嘴唇的狀态,不能过度练习。一般演奏者每天最多练习八小时,如果想要很快攻克一首练习曲或一部乐曲,唱是高效率练号的不二法宝。该如何唱?陈嘉敏教授认为怎么吹就怎么唱,唱三遍吹一遍,也就是说边唱谱子,手指边按照谱面音符按键,唱不是随意地唱,要唱出强弱对比,歌唱的气息运用与吹号时应该是一致的。此外,针对耐力不是很好的学生,唱谱相当于休息,演奏与唱谱交替进行,既能让嘴唇休息,又不影响练习进度。
陈嘉敏教授有着极其丰富的乐队演奏经验,在教学中也很重视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他认为在乐团里音准、音量以及小号声部之间、小号声部和乐队之间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必备技能在重奏课中都能解决,所以他强调一定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上重奏课,重奏训练可以练习如何与各个声部保持平衡,也可以明确演奏标准。在乐队里所有的指挥对小号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指挥对于乐曲风格有不同的演绎,要适应每个指挥的风格,而这一点是许多乐队演奏员能做到但独奏家做不到的地方。此外,学生还应具备变奏能力,并且明确自己所在坐席的责任。
业余爱好还是摆弄乐器
陈嘉敏教授看上去是位不苟言笑的音乐家,却也是位热心又有爱心的教育家,每次在学校见到我,他聊得最多的总是学生的学习问题。他知道我这几年在帮助不发达地区做音乐教育,主动和我说他也愿意帮忙,因为落后地区的学生大多很刻苦,好苗子不少,还曾随我去淮阴师范学院兼职当教授,他一看到好学上进的学生就兴奋,教学不分时间,连学生都不好意思,劝他休息,他却对学生说:“我来一趟不容易,尽量多教你们点知识。”
作为小号演奏家的陈嘉敏居然还是国际乐器制造家协会的会员,这一点也让我很纳闷,他一语道破:“我从小就喜欢摆弄乐器,这是我的业余爱好呀!”
当年舞剧《红色娘子军》里陈嘉敏吹的小号是天津管乐器厂自己制造的708型,后来他还成了这家管乐器厂的董事长呢!陈嘉敏教授说:“好的乐器确实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也没必要太夸大其词,我用的一把小号还是二十七年前花六百美元买的,现在的学生用的小号很多都比我的好。”他接着说:“当年初到新加坡,为了生计,我曾从英国进了二十把破旧的小提琴,自己买了一本怎样制作小提琴的书,照葫芦画瓢地修缮一新出售,到现在我还经常给别人修琴呢。至于修小号,没有像车床这样的工具,有的话我也可以修。”
我见过加塞的小号,号手一手持号一手抓塞,在适当的时候用塞堵住号孔或把塞松出号孔,这样的塞在市场上要卖到八百块钱,可陈嘉敏教授为了帮学生减轻经济负担,花八块钱在南京西路的航模店买来梧桐木自己做,不但演奏起来声音很好,还刻上学生的名字作为奖励。
不事声张,默默耕耘,一心一意为了祖国的小号事业,这就是陈嘉敏教授。
我这个年龄多少都曾与样板戏结缘,一部舞剧《红色娘子军》令人如痴如狂,其中的小号独奏让我切身感受到小号的无穷魅力。后来从事音乐传媒工作,得知崔健也是小号演奏员出身,一次采访时我问他:“你小时候也会崇拜小号吹得好的人吧,当时国内有没有你崇拜的?”崔健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的陈老师——陈嘉敏,他吹得特别好,听他吹号真是一种享受,声音、技术都好,他曾在纽约爱乐乐团待过一年,现在在新加坡,我这辈子能吹成他那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