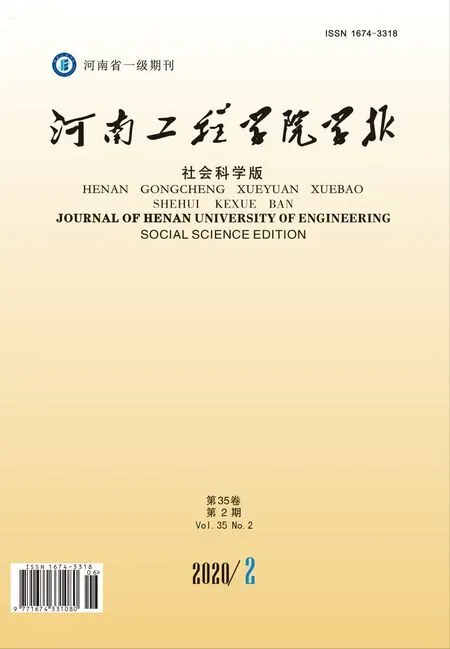虚构与非虚构之间
——论阎连科小说《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中的含混叙事
毕莉莉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小说写作对于阎连科来说一直都是一种称职的自我外在艺术,不仅是主体性得以独立的符号表征,也是人的思想与生命活力的物化存在,具有其他艺术难以取代的优越性、深刻性。但在阎连科最新小说《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以下简称《速求共眠》)中,这种对小说写作的自信转变成对自己及这一艺术行为深深的怀疑、对膨胀的欲望与异化人性的反思,而且阎连科在小说创作中从未停止对文体结构的探索和创新,如《日光流年》中的注释模式、《风雅颂》中诗经文本的挪用,而小说《速求共眠》在形式上更是极度自由,叙述者的叠合、文类跨界、文本抵牾等多重叙事手法的运用,打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界限,消解了真实,达到将对作家创作、小说叙事、文本虚构等所有的犹疑直接推向文本内的人物与外在的读者,接受更客观、直接的审判与拷问的目的。这样的含混叙事并不是语言和意义不清所造成的,而是阎连科在小说家身份与写作现实指引下的自觉书写策略。
一、叙述者的叠合
所谓叙述者,就是文本中那个“讲故事”的人,他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换身份,不断在文本中游移的,有时可能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有时隐身于文本之中。戏剧化的叙述与非戏剧化的叙述是布斯提出的一对重要叙述类型。[1]55阎连科在《速求共眠》中,正是通过两种叙述者话语的叠加,在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的同时,传达出他在探寻小说家当下到底以何姿态写作时的一种举棋不定的含混状态。
(一)戏剧化的叙述者
在叙述效果中,最重要的区别取决于叙述者的信仰和特征是否与作者一致,取决于叙述者本身是否被戏剧化。所谓戏剧化的叙述者,就是“把他们变成与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的生动的人物”[1]50。在《速求共眠》的大文本中,叙述者成为戏剧化的角色,一位与作者阎连科同名的具有野心的阴谋家。
在经济话语主导的时代下,写作与作家均陷入无以名状的精神焦虑与生存窘境。面对文学艺术纯正性与原创性日益遭受来自诸如影视艺术攻讦的现状,一方面,文本角色“阎连科”理性地思考着小说创作只有随同时代的需求完成自身的转型,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但这同时意味着小说对自身纯粹叙事的放弃,从此穿上名利的外套,“三十年的勤奋写作,把我从一个乡下孩子转变为一个所谓的作家,洋洋洒洒,泥沙俱下,毁誉参半的所有作品,都在那一刻变得轻如鸿毛,微不足道”[2]8,另一方面,文本角色“阎连科”按照经济权力话语和受众期待的导引,成为文学帝国中的欲望者,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写作或是小说具有的不可磨灭的文学魅力,“我要用自己所谓的名声,再次以李撞这个人物为原型,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集编剧、导演、主演于一身,让自己从贫穷而又自诩清高的文学队伍中,一跃跨界为电影艺术的大师,让那些苦苦在电影圈里为名声、票房、片酬和国内、国际的奖项而每日奋斗的导演和演员,完全折服于这部电影”[2]10。但这次实践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成为消费话语定制品的小说创作,脱离创作者与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制,从亨利·詹姆斯所说的“作者创造他的读者,正如他创造了他的人物”[1]69置换为“读者创造文本以至创造作家”[3],小说创作至此走向失去内省、独立与深度的自我毁灭的深渊。
成为文本角色的叙述者“阎连科”是理性与欲望的结合体,作者借助于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昭示出写作与知识分子现下的困境,寄予着对知识分子在消费文化下主体性丧失的警醒,实现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冷峻审视与深刻反省,而且这类戏剧化的叙述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真实效果,使读者产生某种“误解”,感到整个故事无中介地进入他的意识,这也是造成文本虚构与非虚构边界弱化的原因。
(二)非戏剧化的叙述者
非戏剧化的叙述者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也就是小说中具有明确承担叙述功能并直接以叙述者面目出现的人,他们未被戏剧化,与作品中的人物有明显的区别。阎连科在纪实小说、电影剧本、人物访谈录与案卷记录等小文本事件中,均以客观公正、无价值暗示、无道德倾向的立场[4],不断记叙文本发生与故事经过,是非戏剧化的叙述者。
在纪实小说与电影剧本中,作者呈现隐退的状态。纪实小说只是讲述了面对落榜青年李撞强奸乡村少女苗娟一事,李林、苗娟父亲、洪文鑫等人是如何以乡村伦理转悲剧为喜剧的。电影剧本向读者或观众呈现的则是一个农村建筑工人李撞与北大研究生李静如何结识、最终相互帮助的故事,对于其中隐藏更深的乡村伦理、乡土文化、绝望生活、心理乖戾的自救等,作为非戏剧化叙述者的阎连科没有做出带有任何个人情感的评价,始终秉持的是一种公正、客观的“显示”的立场。而人物访谈与案卷记录更是零度介入式的,在对农民工李撞与北大研究生李静之间是否存在感情、何以产生这种可能的原因追溯中,作者保持沉默,通过这种方式让人物自己设计自己的命运,讲述他们的故事。如对李撞、洪文鑫、罗麦子、李静、李社五个人的访谈,标明时间、地点、人物,并对环境背景进行说明,但五段采访中只有受访者的话语记录,没有采访者的声音,即叙述者“我”始终保持沉默,只能通过受访者“对你说吧连科弟”“我知道你想采访我”[2]186等才能发现叙述者的存在。同样的,在案卷记录一章中,只有完整的李撞、李静的审讯笔录,以及李撞案的证明信、保证书、结案书。人物访谈与案卷记录都将言说的权利交予被叙述人物自己,文本内外的读者都成为倾听者和裁定者,并不自觉被代入各个版本的叙述语境,显示出一种自然的状态。
阎连科的非戏剧化叙事,将人性、欲望、道德、阴暗、复仇等隐藏在生活表象下的个体内在真实在读者面前摊开,拆解了文本内外的界限,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做出价值判断,由此与作者共同完成对人文精神现状的反思。
因为叙述,意义才有了生产、生长的可能。从《速求共眠》的整体文本视野来看,一位时刻自嘲反讽并自我放逐的戏剧化叙述者阎连科,和一位认真进行文本创造和小说叙事经营的非戏剧化叙述者阎连科展现了一种“分裂”,这种“分裂”恰恰显示出作者阎连科内在的自省与矛盾进入一种焦灼的状态。面对消费文化对写作独立性的侵蚀,文学创作者该何去何从?
二、文本跨界下的多重叙事主题
阎连科在这部小说中设置了层层的文本世界,有六个显在与隐形版本:纪实小说、微信故事、电影剧本、案卷记录、人物访谈、整体小说。它们在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之下,每一个故事都包含其他故事中的基本元素,如主要人物(李撞、李社、李静)、人物身份(农民工、研究生)、人际关系(父子、师生)等,但每一个版本都有属于自己的显在主题指向,展现出某个生活的侧面,隐含着对乡土所代表的民间文化与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之间对峙的新一轮思考。然而指涉过多的层面,在有限的文本框架下似乎造成了对真正主题指示不清的含混状况。
(一)民间文化的多向度思考
综观阎连科长篇小说作品,可以发现作者一直致力于乡村题材的创作。在《速求共眠》中,阎连科始终还是没有放下对中国乡土世界的关注,他以极富现实责任感的态度、多向度的观察视角与主题,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乡土民间文化进行新的诘问。
纪实小说《速求共眠》讲述的是一个乡土民俗题材故事,李撞强奸苗娟一事,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但一方面由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另一方面碍于乡村民俗伦理的舆论和乡亲邻里之间的情面,李、苗两家最终选择结亲解决此事,从中可洞悉乡土人性的善良源于生存的无奈和现代法律意识的缺失。从村民对唯一说出强奸事实的洪家老大漠视的态度上,我们窥测到的是乡村道德宽容背后的虚伪麻木和冷漠残忍。微信故事《虫凰相爱缘何来,莲花盛开污泥香》通过农民工与北大研究生之间的爱情故事,揭示城市与农村深厚的文化隔阂,农村与城市似乎是两个对立的极端。爱上北大研究生的农民工李撞被贴上了“虫子”“蟑螂”的标签,每一个人都将这样的爱情故事当成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在电影剧本《速求共眠》中,五十多岁的河南老汉李撞,为了让儿子李社继续复读考大学,以三万元的价格卖掉了媳妇的骨灰,正好供应上儿子的学费。农村的贫穷、落后与封闭,使得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我们不得不驻足反思。
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乡土小说的书写不能够只囿于以往的书写方式与表现层面。因此,对于乡村当下真实的生活面貌,阎连科一直在寻找更适合时代变迁的叙写方式,《速求共眠》便是一次乡土书写的“再造”性实践,多重文本故事、多个观察视角和多种主题的呈现,使读者始终处于对民间文化无限丰富的考察中。
(二)现代文化的焦灼性窥探
与乡村世界相对照,对于城市,阎连科的书写态度处于一种不断的转变中,从向往、羡慕到嫉妒、仇恨及无情地批判揭露。阎连科对于他通过写作“逃离土地”来到的城市,保持着一种极端的、绝对化的书写立场,但在《速求共眠》中,阎连科笔下的城市除了带有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更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
小说开头一位叫阎连科的小说家想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叫《速求共眠》的电影,为了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他集结了身边的影视文学名流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等,但他曾发表的乡土题材纪实小说《速求共眠》没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而以农民工与北大研究生的爱情故事为噱头的微信故事却很快得到了顾长卫导演50万元的资助,这无疑映射出膨胀的名利欲望与当下文化消费过度追求猎奇感的现象。电影剧本《速求共眠》中,女主角李静被开除的原因竟是因为研究院院长老婆觉得李静过于年轻漂亮,职场生存的艰难与黑暗可见一斑,而李静选择放纵自己,“速求共眠”,以达到对抗现实与自救的目的,灼照与撕扯的是现代人混乱境遇下生存的绝望。在人物访谈中,李撞工友罗麦子的讲述,显露出人性的贪婪与恶;李撞的自述彰显着以李静为代表的城市人对农民的关爱与帮助;对李静的访谈透露出对民间朴素人情与道义伦理的赞美,以及对底层人民处境的同情。李静在学校遇到中午只吃两个冷馒头、喝自来水的李撞,当她去食堂吃新鲜热乎的饭菜时,便觉得欠了李撞什么。从整体小说着眼,阎连科通过对叙事实践本身的解构,反思在经济话语时代写作这一艺术行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深陷城市名利欲望包围圈的作家又应该如何去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去创作。多重的文本使作者有更多的机会展示现代文明的更多层面,打破原本对城市单一的批判叙述方式。
多版本多主题的形式,能够急速揭示在现代化的中国农村与城市隐藏的种种问题,如道德关怀、人性洞察、底层悲悯、社会批判等,提升了文本本身的可阅读性。但刻意讲求叙事技巧、故事里面套故事、多人叙事凑齐故事,可能会造成对真正硬核的内容浅尝辄止、浮于表面,降低小说的文学内涵与价值,甚至掩盖了阎连科对自身小说家身份及写作这一艺术行为进行文学反思的主线,而且不停变换文本模式也是阎连科对于写作行为“表意焦虑”的一种体现。
三、文类抵牾下的“真实”圈套
多个文本之间相互联系,之后文本的叙述不断地消解着前者叙述的真实性,形成一种叙述的圈套,对“真实”的不断抵进与叙述,成为文本叙事的动力,但虚构外延不断扩大,显示出作者对文学创作中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不确定,在虚构与非虚构的交叉地带隐藏着阎连科对“写作”这一艺术行为意义的深刻怀疑。
(一)局部真实与整体虚构
各个文本独自构成局部的真实,但在整体的视角下,局部的真实彼此颠覆,形成“互否”局面,在现实与艺术之真的追求中,使整体文本最终走向虚构。
在人物访谈中,从李撞口中得知,阎连科那篇名为《速求共眠》的小说写李撞强奸苗娟的情节是虚构的,“我和你嫂子是从小定亲,两相和好,这全村人有谁不知道!”[2]118即李撞的叙述颠覆了阎连科小说的真实性,而对洪文鑫的采访又颠覆了李撞叙述的真实性,“也许是李撞上辈子欠了人家苗家的,这辈子他该还人家。谁让他年轻时候在那村头泉边欺负人家娟子呢”[2]197。至此,李撞与苗娟的故事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无从验证。同样,在李撞与李静的故事中,对李撞的采访颠覆了微信故事的真实性,李撞的说法是邀请李静吃饭是与罗麦子打赌,罗麦子说“能和她约一下子,不吃饭,你们两个哪怕只是在路边一人喝一杯凉水,我都给你两千块”[2]227。之后李静保释他也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对罗麦子的采访又颠覆了李撞叙述的真实性,罗麦子说李撞贪图钱财刻意接近李静,“先和她谈朋友,勾引她,等她上钩了,然后再连色带财都拿走”[2]259。对李静的采访颠覆了上述所有人表述的真实性。李撞与李静的相遇是因为李撞捡到了李静的钱包并原封不动归还了,李静以五百元感谢李撞时被拒绝了,这对李静产生极大的震动,她觉得这个人实在、淳朴,两人一来二去有了感情……案卷记录又颠覆了人物访谈的真实性,故事发展为李静在学校了解到李撞家的困难,给了李撞八千元资助李撞儿子李社读书,李撞为了表示感谢想请李静吃一顿饭,追到李静小区拦截,由于行为过激造成误解,被带到了派出所。各个文本故事相互颠覆,使得在李撞与李静的故事中“什么是真实”成为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
阎连科通过这样一个对“真实”不断追寻的故事,表明他对作为文字操纵者和文学写作者存在困境的反思。真实无法探究,只存在于不断的“叙述”“转述”“他述”与“自述”中。阎连科在后记中更是直言说道:“越来越感到我自己的写作无意义。”“真的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觉得文学的无力和无趣。”[2]562
(二)内真实与外虚构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小说这一题材悄然地将阎连科试图用暧昧的体裁保证故事的可信性、使之成为可靠叙述、构建外在形式真实的尝试击碎,但对于作家阎连科而言,最终还是达到了洞悉、揭示事物的内在真实性这一目的。
从一开始小说的题目《速求共眠》,阎连科似乎就想用“非虚构”本身来保证叙述的真实性,给读者造成一种真实性的阅读期待,紧接着设置了一位与自己同名的小说家阎连科,并采用现实生活中大家相当熟悉的人物名字如蒋方舟、顾长卫来增强这种现实感,之后采用人物访谈、案卷记录等“非虚构”常用形式进行写作,由此进一步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但作者以小说方式呈现,读者以小说方式阅读,双方始终处于虚构的故事中,形式的真实始终笼罩在虚构的外衣之下。在《速求共眠》之前,阎连科曾将自己的创作观念称为“神实主义”[5],并解释为“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6]。他主张通过“神”的创作方式去抵达“实”的彼岸,虽然寓言、神话、传说、梦境这些实现“神”的方式在《速求共眠》中均无体现,但表现出更有力量的“实”是阎连科书写的唯一目的。一方面,阎连科将自己作为揶揄、讽刺的对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小说家角色”和小说本身,通过这种方式,抵达自我的内心,挖掘内在心灵的真实性反思:在目前这个现实中,小说写作对于现实是否还有意义与价值?小说家们又该如何书写?另一方面,虽然小说的形式最终决定故事的虚构,但是事实上小说中的某些故事绝对真实地发生过,即使小说中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其中揭示的种种现实问题蕴含深切的道德关怀和深邃的生命忧思,真切地触及当下社会的现实内核。
艺术源于生活,更应高于生活,但在真实不断自我“互否”的艺术场中,文学似乎已被生活击败,沦为生活的一种附庸,使如何处理小说艺术与生活真实陷入无可回答的圈套之中。随着“非虚构文学”概念引入中国,阎连科逐渐意识到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与越界问题,他自觉地用《速求共眠》做一次非虚构文学的相似性尝试,试图用这种更加贴合时代的方式去追问真实,即使最终没能突破小说写作的窠臼,但他依然站在现实的对面,书写他作为小说家的内在真实与良知。
四、结语
在《速求共眠》中,阎连科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下讲述几个相互关联的虚构故事。面对现实的丰富与小说内涵的空洞,在现实与虚构不断交融之间,始终贯穿的是阎连科对写作及“小说家角色”存在意义的反复探寻与反思。阎连科抛弃了以前在作品中扮演的将问题剖析再呈现的角色,而转向一种内在的自我剖析,从作家写作立场的“含混”到写作真实方式的“含混”,将“写作无意义”这一严峻现实问题通过不同的叙述策略抛出来,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传达的是一种含混的文化立场与态度。大多数读者可能因此觉得这是阎连科作为小说家对读者与文学的不负责任,但是这可能正是阎连科以作家的敏锐察觉到文学创作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后进行深刻思索的表现。没有将自我意识强加到其他人身上,不要求“速求共眠”,而须保持个体的清醒,将问题抛出,期待得到来自读者与社会更多的有力量的、现实性的反馈,这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文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