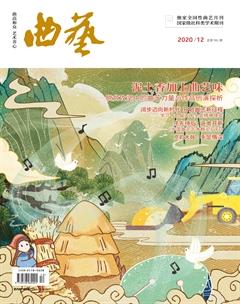发挥曲艺优势 文化扶贫助攻坚
马志飞
扶贫攻坚是党和政府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做出的重要战略举措,扶贫攻坚目标能否保质保量完成,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我国的扶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深耕细作”关键时期。曲艺人在决胜“扶贫攻坚”战役中承担着文化扶贫的光荣任务,需要在曲艺演出、创作和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思想,利用曲艺的独特优势,“丰富贫困地区文化活动,加强贫困地区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精神风貌”①。
一、顺大势而为之,拓宽艺术视野
所谓“大势”,是指一种事物演化的客观趋势。明代王夫之曾经在《宋论·卷七》中指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对待扶贫攻坚工作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将之放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高度来思考。“精准脱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在我国2020年重点经济工作中被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消除贫困是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有力支撑,对于全球贫困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示范意义。曲艺工作者一直秉承的“引领时代”“锐意创新”“使命担当”“弘扬中国精神”等理念,都是顺应国家形势和时代发展而自觉思考、积极践行的理论思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政府积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努力实现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成功跨越,这便是曲艺人面临的国之大势,更是当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生成语境。
曲艺人从来没有缺席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广大曲艺工作者在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带领下,开展了“文艺扶贫奔小康”“新时代曲艺星火扶贫工程成果巡礼展演”“送欢笑 到基层”“文艺小分队扶贫演出”等活动,出现了快板书《脱贫致富奔小康》、武乡琴书《扶贫队长张宏才》、相声《结穷亲》、快板说唱《陇原新貌》、单弦《梦想成真》、相声《扶贫扶出好日月》、河南坠子《冰泉梦》等曲艺佳作。但不可否认,扶贫题材的曲艺创作和表演在时代主题、创作理念、创作视野、表演风格、艺术水准、价值实现等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我们仍需要深刻理解扶贫攻坚的内涵要义,探索曲艺创作与表演的改革方向,助力扶贫攻坚工作开展。
要之,扶贫攻坚主题的曲艺创作与表演,关键在于顺大势而为之。也就是说,曲艺工作者需要站在全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思考扶贫攻坚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以局内人身份深入体验生活,投身扶贫攻坚一线,从中发现典型的扶贫人物和鲜活的扶贫故事。“文化扶贫”重在“扶智”和“治愚”,这是发挥曲艺优势的重要路径,通过优秀的曲艺作品和生动的曲艺表演让贫困群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达到转变观念、助推脱贫的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先决条件在于,曲艺人须具备全局视野和全球视野,据此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联系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看问题,从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紧贴时代发展抓创作,紧贴使命任务抓表演。
二、曲艺创作:突出固有的叙事方式
发挥曲艺独特优势开展“文化扶贫”,重在坚持曲艺固有的叙事方式。清嘉道年间的苏州评弹艺人沈沧洲曾经指出:“书与戏不同何也?盖现身中之说法,戏所以宜观也。说法中之现身,书所以宜听也。”②曲艺表演主要凭借曲折动人的故事来推进事物发展、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因此适合去“听”。不论是长篇大书,还是中短篇曲目,优秀的曲艺作品往往突出叙事性,具有“说”“唱”故事的基本要素:事件的起因以及发展的一环套一环,人物的性格特征,角色间的恩怨情仇,主题的多重交错,矛盾冲突的曲折多变等。民间说唱艺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了“四梁八柱”“提闸放水”“逢枝开花”“遇路转彎”等情节设计技巧,制造悬念则有“连环扣”“鸳鸯扣”“子母扣”“阴阳扣”等手法,还有程式化的书串条子“诗赋赞”等,在曲艺叙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说唱要素资源。
“曲艺是一门用口语说唱叙事的表演艺术”③,其本质是叙事艺术,说唱故事的曲艺作品构成了曲艺的主体部分,这与曲艺表演的接受对象有直接关系。曲艺表演主要面向基层老百姓,是一种民间艺术。在传统民俗社会,底层百姓大多不识字,文化程度较低,需要艺人用通俗的语言和优美的曲调,将复杂的故事简洁化,对人物的形象塑造讲究“抽丝剥茧”,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乡镇,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即使在各地的城镇码头,曲艺演出的对象也以市民、私塾先生、店铺老板、账房先生、学徒、苦工等底层百姓为主体,不太需要雅驯化的唱词道白去咬文嚼字,也不太需要雅致精细的音乐唱腔去描摹人物情感的细腻变化,他们需要的是畅快淋漓的说唱叙述和大开大合的情节推进。当然,也有很多体现文人雅趣的曲艺种类,如岔曲、八角鼓、鼓子曲、清曲等,以抒情性取胜的曲艺作品也数不胜数,但大多属于以曲会友的室内艺术类型,与江湖曲艺的纯粹娱乐大异其趣,在曲艺大家庭中所占比例有限。
反观当代的曲艺创作,有一部分作品淡化了,甚至丢失了曲艺的叙事性,转为抒情性为主的创作方向。突出表现为唱词诗歌化、格律雅致化、文辞戏曲化、叙述同质化、唱腔细腻化,一味向其他高雅艺术看齐,向城市观众靠近,希望通过舞台化表演来实现艺术风格的城市化和审美趣味的雅化。对接“文化大系统”的结果之一就是,作品的民俗气息淡了,自己的特色没有了,不接地气的作品出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笔者在这里并非否认曲艺向高雅化发展的现实合理性,不是说曲艺创作非得大老粗才行,反而认为曲艺的抒情性创作方向有助于其品位提高和格调提升。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曲艺主体是一种大众艺术,它的受众群体主要在广大农村和城镇基层,我们的曲艺创作首先要考虑基层老百姓的审美趣味,眼光向下,投向农村。须知,贫困群众大多数都在偏远山村,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有限,他们的意识和眼界与城市居民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需要曲艺创作突出叙事性创作风格,叙述与抒情相结合,适应他们的娱乐需求和精神追求,让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去影响他们的精神面貌。
還有一部分扶贫题材曲艺作品过于说教,没有处理好教育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故事情节明显脱离扶贫实际,一味将主人公塑造成“高大上”的完美角色,唱词和唱腔脱离原有生活环境,使得作品失去了人间烟火味,结尾都是大团圆的圆满结局,显得过于功利化。在歌颂型作品创作中,最大的问题便是脱离实际,全力以赴歌颂的同时,忽视了观众对故事情节合理性的怀疑,忽视了生活常识和现实逻辑性。因此,针对扶贫攻坚的曲艺创作一定要突出真实客观,力避直白说教,将以事动人、以情感人的艺术表现建立在坚实丰富的扶贫事迹之上,既不夸大客观情况,也不回避存在的矛盾和困惑,通过作品引发人们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达到了应有的社会效果。
三、曲艺表演:突出独有的幽默风格
曲艺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与众不同的幽默风格,据此成为我国喜剧艺术的突出代表,这是曲艺助推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基石。曲艺的形式十分丰富,既有散说体的评书、相声、故事、双簧等,也有韵诵体的快板、莲花落、数来宝等,还有曲唱体的鼓词、单弦、清音、渔鼓、坠子、琴书等,无论长篇大书还是短篇小段,几乎都是以轻松幽默的现场表演赢得观众的喜爱。这是由曲艺的群众性基础和娱乐性目的所决定的,“曲艺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是为满足群众消遣娱乐的目的而存在的。”④人需要欢笑,笑的艺术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西方有古希腊喜剧,如阿里斯托芬的《鸟》、克拉提诺斯的《酒瓶》、厄皮卡玛斯《跳舞的人们》等,还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莫里哀的《无病呻吟》《伪君子》《悭吝人》,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等;中国则有关汉卿的《救风尘》、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廷玉的《看钱奴》、李渔的《风筝误》等。曲艺界的喜剧风格作品更是多不胜数,如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姜昆的《虎口遐想》、评书《济公传》、独角戏《方言空城计》、杭州摊簧《卖草囤》、河南坠子《吹牛》、山东琴书《苦乐娘亲》等。
即使在大书表演中,也须有必不可少的幽默情节和喜剧人物,如民间说唱艺人口中的“四梁八柱”,其中的“书筋”就是指谐趣横生、憨态可掬或鲁莽可爱的人物,如《岳飞传》中的牛皋、《瓦岗寨》中的程咬金、《水浒传》中的时迁等,对于调节书场气氛、引发观众欢笑就有重要作用。“一部大书累月经年地在场上说,人们所以能谛听忘倦者,除了事吸人,情动人之外,还要有谐趣笑乐,调剂书中故事的气氛。”⑤一位优秀的曲艺演员,往往善于运用抖包袱、摆噱头、插书串等制造喜剧效果,迅速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借机阐发古今兴亡之变,劝喻世人弃恶从善,规劝民妇孝敬公婆,巧谏浪子回头是岸,起到正剧所无法替代的社会效果。
当前,曲艺演出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为了“笑”果而搞笑,忽视内容的丰富完整性而刻意制造笑料,甚至为了赢得掌声而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导致情节分裂、内容浅薄。还有一部分曲艺演员喜欢戳观众的“泪点”,节目的前半部分往往笑料百出,出尽人物的洋相,到了后半部分,开始解密人物背后的辛酸故事、难言之隐、坎坷身世或真情告白,弄得观众时不时地眼泪哗哗,喜剧结果变成了悲剧。这种手法偶尔为之尚可,就怕个别演员将之视为“金科宝典”,屡试不爽、频频得手,致使喜剧艺术走进死胡同。曲艺表演中的“喜”和“悲”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都是营造艺术效果的手段,揭示人性之善恶才是曲艺表演的精神内核所在,万不可本末倒置。
简言之,曲艺表演的幽默风格是其作为喜剧艺术的立根之本,“寓庄于谐”是曲艺表演有别于正剧表演的最大特点,其固有的市井风格体现为轻松风趣,主要目的是使观众获得快乐,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的感性体验。面向扶贫攻坚的曲艺表演实践,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幽默表演风格,通过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给贫困群众带来欢笑,使他们远离烦恼,精神愉悦,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力量。
四、价值取向:突出传统的讽谏功能
曲艺的另一核心特征是讽谏,通过讽刺黑暗现实与不良风气,或者揭露人性弱点与落后思想,反衬出正义和真理的现实紧迫性,从而间接传达正能量,进而确立曲艺自己的价值取向。有关作品繁不胜数,如相声《连升三级》《买猴》《如此照相》《巧立名目》,小品《如此包装》《卖拐》《不差钱》,道情《小姑贤》,二人台《卖碗》等,都是出于善意的目的而施以教育启发式的讽刺揭露,起到的效果是让人们向善向好。周扬同志认为:“不要以为艺术只能歌颂不能批评。艺术任何时候都是有歌颂,又有批评。曲艺中的相声等就要发挥它的批评作用,不要抹杀相声的这个作用。对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保守主义为什么不能讽刺?不要废除讽刺。我们不怕讽刺。”“社会上有一些矛盾现象、落后现象、可笑现象,需要讽刺。但要注意分寸,不要伤了人民,伤了朋友。毛主席讲过,有两种讽刺:对敌人的和对自己的。对社会主义一定要保护,要坚持。对错误的、消极的现象,要不要批评甚至讽刺?要的。不然,曲艺就失去一半作用。”⑥
不可否认,人性有弱点,自私、虚伪、吝啬、贪婪、欺骗、吹牛、耍威、懒惰等都是“人类通病”,针对此,说唱艺人大多采取“寓谏于谐”的方式进行讽刺性劝谏,借以达到教育、说理等目的。人们欣赏曲艺表演不仅仅在于娱乐享受,还乐意看到曲艺演员对社会不正之风的辛辣讽刺,听到曲艺演员对思想落后人物的无情嘲讽和对错误行为的有力谴责,抒尽胸中不平之气,获得心理平衡和精神满足。对被讽刺的对象来说,曲艺演员的讽刺批评可以极大地增强其耻感体验,知耻而后勇,知耻而奋进,从而改变个人的命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里,还需要把握好讽谏的度,注意讽谏与抹黑之间的根本区别,明确讽刺对象和目的,正如曲艺作家赵连甲所说:“相声小品没有讽刺,生命力就不强了。不要以为讽刺就是消极的,讽刺里有歌颂,歌颂里有讽刺。”
统观近些年的曲艺创作与表演,幽默的一面被大大发扬,但讽谏的一面却被大大减弱,面对不良现象不敢讽刺、不敢批评,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这便是当前曲艺创作与表演的突出问题之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结果,就是观众不接受这种“老和尚的帽子——平不拉塌”的曲艺表演。扶贫工作中,不乏工作负责、品行高尚的好干部,为了群众利益,他们抛家舍业,在扶贫第一线兢兢业业,做出了突出成绩。贫困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经过精准帮扶和自己的辛勤劳动,经济收入有了明显提高,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但也要看到,扶贫工作还面临“等靠要、慵懒散”现象,因病因懒返贫的情况也很突出,个别贫困群众甚至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和条件,扶贫攻坚“瓶颈”较为突出,也有个别扶贫工作人员存在消极应付、扶贫“走读”与“挂名”、玩忽职守的行为,甚至公然违抗党和政府规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曲艺工作者不能选择性忽视,而是要客观对待,利用曲艺进行揭露和批评,警醒他们深刻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帮助贫困群众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促进扶贫攻坚工作高质量开展。
当前,扶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时不我待。扶贫主题的曲艺创作和表演,必须要发挥曲艺自身优势,以艺术性为核心,其他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围绕之,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高度统一,才能真正让贫困群众乐意听、听得懂、愿意干,真正与贫困群众的精神诉求无缝对接。元初理学家胡祗遹曾经在《赠宋氏序》中说道:“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尚而变。”在扶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我们的曲艺创作与表演需要“变”,这个“变”是时代之变对我们的观念要求,同时也要坚持“不变”,坚持传统风格不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我国扶贫攻坚的伟大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文为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编号2020BYS02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
②马如飞:《出道录》。
③姜昆、戴宏森主编:《中国曲艺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薛宝琨:《论曲艺的本质和特征》,《薛宝琨曲艺文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⑤蒋敬生:《传奇大书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
⑥罗扬:《周扬与曲艺》,《中国艺术报》,2019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