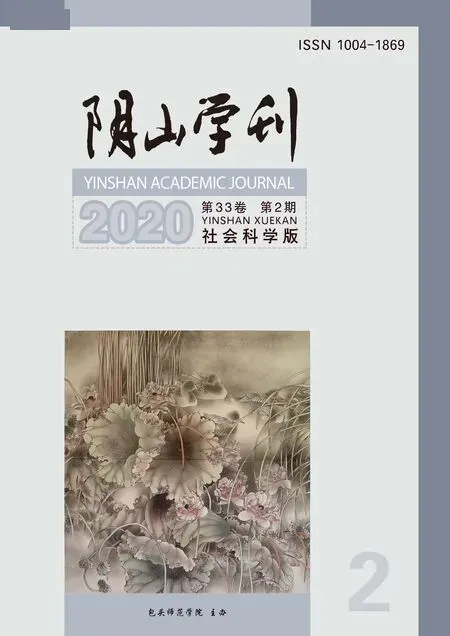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刘 家 书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教学部,西藏 拉萨 850007)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1]41。攻灭六国之后,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确立了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和地方国家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政体。郡县制全面推行之后,与之相对的分封制却并没有因秦始皇统一六国而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坚持分封制的思想和舆论依然广泛存在,分封制甚而在秦汉之际和西汉初年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复辟。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皇帝制度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历史纠葛
作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制,分封制和郡县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都广泛存在。谈及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历史纠葛,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大一统”,即统一国家的理想追求,它是维护国家政治统一稳定、维护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大一统”的思想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这里正式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则对“大一统”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发挥和总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1918
到了战国时期,“大一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社会普遍渴望结束诸侯国之间的战乱,实现国家统一。孟子和梁襄王的一段对话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情况。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4]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虽然“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已经被社会所普遍认同,但分封制仍然是政治体制的主流。分封制始于西周时期。在严密的宗法制、等级制前提下,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宗亲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周王室,即采取“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方法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春秋时期,郡县制开始出现。到了战国时期,为加强对新占领土地的控制,各诸侯国开始普遍在边地设立郡、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则彻底摒弃了分封制,采用郡县制。
西周时期施行的分封制,进一步强化了宗法制、井田制和等级制,巩固了新生的西周政权,为西周国祚的延续产生了积极意义。同时,也应看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分封的诸侯独立性较强,在周王实力衰弱的情况下,各诸侯国“藩屏周”的作用逐渐丧失,而且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导致中央王朝失去了对地方诸侯的有效管理和实际控制。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和战乱,就是分封制这一制度弊端的展现。分封制对“大一统”的国家统一极易产生隐患和威胁,破坏社会秩序的团结、稳定,导致国家社会秩序崩塌。
相较于分封制,郡县制则利于中央控制地方,更加符合“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从根本上说,郡、县出现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消除分封制的弊端。郡县制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官僚制度,使得中央直接管理地方成为现实,极大消除了地方的独立性,避免了地方的独立性和分裂倾向对中央的威胁。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5],清楚地阐释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之间的区别。对于封建皇帝来说,他们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其专在上”,令他们担忧并对其统治极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是“其专在下”。毫无疑问,秦始皇及之后的封建统治者都深刻认识到了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势,并从内心认同郡县制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皇权的统治。从历史发展来看,郡县制也更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和保证秩序,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正是在郡县制这一制度前提下,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官僚制度、察举制度、科举制度、税收制度等无不得益于郡县制度的发展。
二、秦汉时期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讨论
秦王朝之前的分封制下的地方诸侯普遍拥有巨大的权利和独立性,构成了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和挑战。相对而言,郡县制则更有利于推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无论秦朝还是西汉王朝的统治者,都追求至上的皇权和青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
在郡县制这个主流面前,秦汉时期社会舆论对于分封制的追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史记》中就记载了秦始皇时期两次对于完全郡县制的质疑和对一定程度的分封制的坚持: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1]41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1]44
两次的政策讨论虽然都以秦始皇赞成李斯的言论、决定继续实行郡县制而结束,但是这种思想的深刻影响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甚而这个制度在秦王朝灭亡之后还发生了两次短暂的复辟。
一次是项羽对六国各旧贵族和在推翻秦王朝统治过程中的功臣进行了分封,“诸侯罢戏下,各就国”[1]62。最后,刘邦、田荣等人认为分封不公平,起而反对之。虽然项羽的分封很快便瓦解,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导致项羽分封制失败的原因,不是有人反对分封制本身,而是反对分封结果的“不公平”。
另外一次分封制的复辟就是西汉建立过程中和之后,对韩信、彭越、黔布、吴芮等异姓诸侯和刘交、刘肥等同姓子弟的分封。西汉建立之后,在讨论为何刘邦能战胜项羽时,大臣们就直言因为刘邦的分封更公平、更得人心: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1]77
他们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使人攻占土地之后能“因以予之”,从而赢得了他们的普遍拥护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西汉时期这些大臣的言论可以看出,在郡县制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主流体制的时候,分封制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
为何分封制这个影响“大一统”的毒瘤制度依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无非是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一是拱卫政权的需要。秦朝时期,丞相绾、博士齐人淳于越都认为:“不为置王,毋以填之”,为巩固政权,应该“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全面实行郡县制,会导致“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的情况出现。刘邦建立西汉之后,也认为秦王朝的二世而亡,与“秦无尺寸之封,不立子弟为王”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些思想认识,无疑是看到了分封制的合理之处。当一个新生政权建立时,分封子弟作为枝辅,是必要的。班固就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总结:“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3]283在刘邦死后,平定诸吕之乱中,同姓诸侯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刘邦虽然认为分封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在政权巩固之后,就及时消灭了实力强大的异姓诸侯王,但仍然认为同姓子弟封王作为地方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因而也确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1]82的“白马之盟”。
二是争取支持的需要。刘邦要战胜项羽,韩信给的建议是“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1]793。在与项羽斗争的最严峻时刻,刘邦把分封作为争取支持的重要手段,刘邦曾真诚地问张良:“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1]625刘邦的重要谋士郦食其的一段话也说明了通过分封争取支持的重要作用:
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1]626
刘邦通过分封韩信、彭越、黔布等实力派为异姓诸侯王,争取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从而扭转了与项羽的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并一举在垓下将项羽彻底击溃。
三、西汉时期分封制的式微
西汉初建时,以刘邦君臣为代表,既认识到了郡县制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支撑,也认识到一定程度上的分封制的重要性,并设计构建了独特的“郡国并行制”,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巩固西汉王朝统治的问题。然而长远来看,分封制这一制度毕竟具有其内在的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隐患和威胁,并且愈发展下去,其弊端就愈加严重。分封制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矛盾具有内生性、根本性的冲突,并不随着血缘、个人情感等方面的因素而转移。
刘邦死后,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分封制下的地方诸侯对中央的威胁不断显现,其不仅占有土地广,而且财力丰厚、士人云集。如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万斤,他财物称是。”[1]639如江都王“好力气,治宫观,招四方豪杰,骄奢甚”[1]643。这些现象已经显现出地方诸侯王对中央集权潜在的威胁。在汉文帝以后,一些诸侯王蠢蠢欲动,后愈演愈烈直至发动大规模的叛乱:
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1]91
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1]639
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1]94
建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1]643
面对诸侯国的威胁,汉王朝内部有很多反对分封制的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分封的地方诸侯势力坐大的危险,特别是诸侯国势力强大之后发展成武装叛乱的倾向。他们提醒统治者要高度重视这种危险,建议提前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遏制地方诸侯国势力的发展。
起初,汉文帝、汉景帝面对诸侯国实力的日益膨胀,依然坚持刘邦分封诸侯时的信念,认为血缘、宗族关系依然重要,不肯听从“削藩”的建议,甚至淮南王刘长有僭越的行动时,也只是惩罚了其本人,并没有对诸侯国采取削弱的策略。当汉景帝真正认识到“削藩”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行动起来时,就发生了“七国之乱”。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开始规模削弱诸侯国的力量,并逐步收回对地方诸侯国内政的控制权,直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之后,才杜绝了地方诸侯国的威胁。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日渐式微,再也没有能力同中央相抗衡。
从西汉武帝彻底削弱地方诸侯国的力量之后,分封制虽然在名义上依然存在,但是后世封建各王朝进行的分封已经是荣誉性质大于实际权力,并且不再掌握能够同中央相抗衡的力量基础。后来的历史发展,大多王朝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分封制度,三国、晋朝、隋朝、唐朝、明朝、清朝等朝代也有分封王的举措,然而这些朝代分封的诸侯或者王与西汉初年的诸侯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四、关于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斗争的思考
秦汉时期的分封制与郡县制斗争及最终郡县制的胜出,清晰地表明中国历史向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迈进的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意志和信念是无可阻挡的。即使分封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复辟,也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家统一”而产生的后果。“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终极价值追求。
夏朝、商朝时期,限于王朝的实力,无法控制地方,采用了松散的“方国制度”来实现对地方的影响。然而,“方国制度”毕竟无法实现对地方的完全控制,导致地方叛乱频仍,夏朝、商朝君主疲于征讨地方方国。到了西周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实力的进一步强大和先进制度、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凝聚力,开始实行“分封制”,其初衷就是为了加强对边远地方的控制。西周王朝确实通过实施“分封制”达到了这个目标,昔日属于“蛮夷”之地的边远地方开始融入中央王朝管辖,并在文化上逐步实现了认同和融合。反观分封制产生发展的历史,分封制取代方国制,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西周中央王朝限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影响,无法实现对地方更加有力的控制,从而推行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分封制。因此,分封制也是为了“大一统”这个目标而诞生的,并且在推动早期民族大融合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战国时期,为了在诸国战争中取得优势,确立更加统一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成了必然,并且交通工具的进步、驿使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建立等因素也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提供了条件,郡县制应运而生。因此,各诸侯国纷纷在新占领地区和重要地方设置郡、县,秦国的“商鞅变法”更是在秦国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历史的发展是具有惯性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能够决定历史的进程。这突出表现在国家和民族在价值观、审美等意识形态方面仍然保留着从前历史的“痕迹”,并且在一定时期,这些“痕迹”表现特别明显,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虽然秦汉时期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一统”国家,确立了郡县制的主流地位,但是“历史的惯性”仍然决定了分封制并不会因为中央王朝努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和强力措施而退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反而会持续产生重要影响。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现实政治政策制定方面都是十分激烈的。当郡县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时,对分封制的“留恋”也绝不是某部分人或者少数人的想法,而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文化、潜在意志的体现。无论是秦朝时期提出恢复分封制,还是西汉初年实行一定程度的分封制,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团结、稳定——虽然提倡、推崇分封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由于地方分封所造成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混乱,他们一定也十分清楚分封制的弊端。这就造成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明知道分封制在全局上、长远方面会对国家的“大一统”造成严重破坏,为什么依然推崇分封制?
(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早期发展时期,就奠定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它包含着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敬鬼神而远之”“人与天地参”的人文传统。中华民族“天地君亲师”的理念深入人心,强调个人对宗族、对国家的义务构成了宗法集体主义的理念认同。
二是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的以伦理为中心的思想认识。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求善重德”的伦理性文化。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其中重要一环。
三是崇尚中庸的思维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种中庸之道施于政治,就是追求宗法社会的稳固。
中华民族这种文化传统提供了提倡分封制的充足理由:在重视伦常、重视人文、崇尚中庸的文化氛围里,相信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关系,这就导致他们会将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中的“忠诚”推广到政治生活中去,那么通过分封“同姓”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确保地方对中央的“忠诚”,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然而,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它不具有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中“温情脉脉”的特点。刘邦用“郡国并行制”进行了实验,检验的结果就是血缘关系、宗族关系在政治斗争中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幻想用“同姓”的力量来维持政治上的忠诚,这种想法是幼稚的。
(二)士阶层的影响
由于秦汉时期士阶层势力仍然强大,他们的影响也极为重要。春秋以降,士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具有以天下为己任、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特征,“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是他们的理想追求。孔子在《论语》中曾阐述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6]。“土”,即分封的领地,它不仅意味着财富,更是士作为一个阶层地位的象征,表明士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一席。
西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士阶层对刘邦集团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基于“付出应有回报”这一朴素的价值观,士阶层有理由相信,他们在“逐鹿中原”军事和政治斗争中为新生的西汉王朝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理应得到相应的“分疆裂土”的封赏。这也是秦汉时期分封制能够得到认可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于历史的原因,分封制在秦汉时期仍然有许多的拥护者,但是“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的选择,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分裂势力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就决定了分封制与郡县制斗争的结果,必然是郡县制的胜出。
五、结 语
分封制和郡县制均起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并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分封制无疑是占据主流地位的,郡县制仅仅相当于“特别行政区”般的存在。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体之后,分封制就不再适合历史的潮流,虽然还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以特殊的形式存在,然而已经不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关键的影响。
观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角逐,秦始皇选择郡县制作为中央和地方体制已经决定了郡县制的胜出。秦汉之交和西汉初年,虽然分封制出现了短暂复辟,但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是不符合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的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的。特别是西汉建立之初刘邦所构建的“郡国并行”制,其短期内有着巩固政权的作用,但从大局和长期利益出发,这个制度还是明显地展现了分封制的巨大弊端。经过西汉汉文帝及之后汉景帝、汉武帝的持续“削藩”,分封制彻底被郡县制所取代,更多地体现在名义上的分封制已经不再具备其原本的内涵和特征,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
这段历史也清晰地勾勒出了两种制度对国家、社会的影响。分封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对于团结王室成员、巩固新生政权的积极意义也成了其不断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郡县制也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进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促进民族融合、增强国家意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