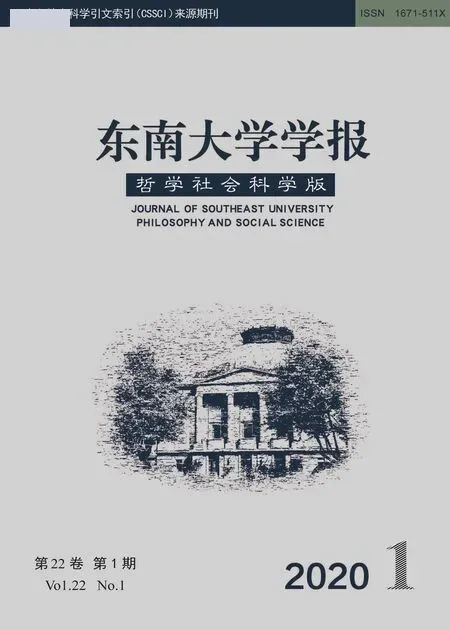法治社会的内在逻辑
杨 建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作为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近年来在政治实践层面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法治社会”得到了国内同仁越来越多持续且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围绕“法治社会”进行的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区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一般法理学的层面进行探讨,另一部分是在中国法理学的层面进行探讨。基于这一概念产生的实践背景与政治语境,目前的理论研究是以中国法理学层面的为主。不过,学界秉持着一个普遍共识,即一般法理学与中国法理学之间不是冲突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是一致的:一般法理学为中国法理学提供并确立一般议题、基础理论与分析框架,中国法理学对中国语境、中国实践、中国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反过来也可能推动一般法理学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发展。无论是一般法理学还是中国法理学,学者们普遍恪守着共通的学术准则。譬如就概念的研究来说,正如苏格拉底在界定正义的概念时指出的研究标准“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关系着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有相反的动作或受相反的动作”那样(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概念的研究也需要恪守逻辑与规范上的一致性。因此,当我们无论在一般法理学还是中国法理学的层面上研究“法治社会”时,判断一个法治社会的概念诠释是否成功,以这个概念的语义结构为限制,至少可以分离出三个基础的标准:(1)该诠释是否表述和运用了一个清晰、一致的“法治”概念观,并恪守了法治对形式规范与权力限制的要求;(2)是否表述和运用了一个清晰、一致的“社会”概念观,并在这个社会概念观之下准确呈现了现代社会的共同生活体系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与诉求,这种呈现能够增进我们对一个美好的共同生活的认知;(3)该诠释是否在“法治”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妥当、有效的关联。如上所述,目前针对法治社会的研究主要是中国法理学层面的,本文的工作主要是想在满足三个基础标准的前提之下,在中国的语境中,从一般法理学的层面勾勒出法治社会概念的内在逻辑,并尝试将之与中国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
这一议题的设定主要源自对实践以及理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困惑的澄清。传统上,人们将法治限定在政府公权力运作的领域,将社会主要视作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自治领域,因而对法治社会到底意指什么产生了疑问。一个自治的领域何以也产生了法治的问题?本文将主张和证明法治社会这一概念强调的不是某种“自治式”的社会法治,它指向的是一个自治、健康的现代社会能够存续和运行所必须依赖的组织性条件,是对作为现代社会的保障方与主导性治理力量的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规范性主张。
一、社会的继受与持续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先回到社会一词。传统中国无论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观念上,均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社会”。作为舶来品,“社会”一词及其实践有一个传入中国并逐渐在地化的过程。从“社会”一词在近代中国的继受与传播来看:最早是在1876年,日本著名学者——明治维新时代的精神导师——福泽谕吉首次借用日制汉语“社会”来翻译society(2)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制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62期。。随后,赴日留学的黄遵宪引入福泽谕吉的译法,在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将社会界定为“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3)黄遵宪:《日本国志》,第37卷第22页,转引自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这是学界第一次将西方现代的“社会”概念引入中国。不过,这样的做法一开始并不成功,它主要受到以严复为代表的学者们的集体反对。严复等学者认为,应当抵制日制汉语的引入,因此纷纷坚持使用“群”来指涉society(4)刘祥,周慧:《谭嗣同之“群学”、“社会学”辨析——兼论中国社会学一词的起点》,《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这一状况直到1895年才有了直观的改变。这一年,晚清在甲午战争中失利并签订《马关条约》,此消息甫一传开,朝野上下震惊不已,重新集结每个人的力量以改革、自强成为朝野共识,影响之深构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5)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在此背景之下,思想界与政界掀起了推进改革的浪潮,并在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之下开始频繁借助和使用“社会”一词,以冀推进前述的进程。当时的有识阶层意识到,西方舶来的“社会”似乎成了国人在政治上抵制专制、经济上振兴实业、文化上凝聚个体的“唯一”方案。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认知之下,严复在1903年也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接受了“社会”的译法。自此之后,中国学界便没有停止过对围绕“社会”一词所展开的“概念群”与“问题束”的追问与思考。
可以这样说,“社会”一词在近代中文世界的兴起,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概念本身即被视作现代性的体现。传统世界无论中西,人们一直生活在某类组织框架之中,但传统世界普遍对生活于其间的组织缺乏意识与反省。人们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反省生活,自发地组织起来,在个体之间自愿地联合形成公共空间,并最终用“社会”一词来概括这种新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这是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6)金观涛、刘青峰:《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第35期。。换言之,社会是对传统生活实现现代转型的表征和具象化。一个自然的、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传统生活基于怎样的原因需要实现这种现代转化,或者换一个稍微不同的表述,这个由社会所表征的现代生活与传统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或说特性?对这个追问的处理是重要的,因为它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如何理解中国语境中新近提倡的“法治社会”概念。
根据考据,法治社会的概念在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在1959年(7)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不过,它真正获得政治和学术生命力,则是源于近几年中国政治实践的发展和变化:2013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法治社会”的概念,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2页。;到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6页。;再到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在“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1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经由三次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层面创设了“法治社会”的概念,并使得“法治社会建设”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与法律议题,这个议题又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与细化(1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9页。。伴随着上述政治进程,学界对“法治社会”的概念与建设等议题的研究也越发集中、热烈和深入。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问题,将之提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予以规划。立基于这一事实,笔者主张,对新近提出并一再强调的法治社会概念,我们也可以提升它的论述梯度,在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层面上加以理解与把握。在这个层面上,本文力图指出,法治社会概念的提出,实质上继承和延续着近代中国致力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它是在为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如何培育、组织和运行中国的现代社会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案,这一方案为如何具体地推进我国的现代社会建设设定了规范的边界与要求。
二、传统生活现代转型的基本特性
对传统生活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理论工程。从本文立足的宏观的、结构性的维度来说,马克斯·韦伯的结构性把握是一个不错的论述起点。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开篇,韦伯指出,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不断实现普遍性与系统性的理性化的过程(1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在这个理性化的进程中,我们能看到技艺(科学)的理性化,政治(法律)的理性化,但对经济(社会)的理性化来说,仅有前述的两个核心要素还不够,由市民阶层组成并运转的社会还“取决于人们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样式的能力与性向”(13)[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这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样式将旧市民改造成新市民,迎来新社会。所以,本节追问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表达为:如何在社会结构转变这个全景视角中理解此种实用理性及其带来的改变?
相比于传统世界的意义结构,实用理性的兴起所传达的信息是,理性的角色和功能被限定了。它被剥离出意义目标设定的范畴,从实质理性变成实用理性,转而只能为目标的实现确定有效、可靠的手段。换言之,理性被实用化、工具化了。实用化、工具化的理性带来的是整个意义世界的“祛魅”——韦伯另一个核心的学术术语。用钱永祥的话来说:“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人逐渐把自身之外的事物和秩序平凡化、机械化、对象化、效益化。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的观点,这些事物和秩序似乎失去了内在的意义和目的,也不复具有本然的理性与价值。人不再依循一个有意义的宇宙大秩序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与价值,也不再按照传统的社会组织去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反之,上帝被赶到一个超越的‘彼岸’去,宇宙自然秩序不过是一套机械的运动,传统的社会政治权威,则被列为挑战的对象”(14)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6页。。人们不再向外去找寻价值的根据,转而向内诉诸主观的反思。这样的转变打上了鲜明的现代色彩,产生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结构性的特征。
第一,价值的去知识化(15)石元康:《历史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在以往,价值与意义客观地存在于世界之中,对世界的探寻也是对价值和意义的发现,这种发现所形成的认知,便是知识。这是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延续和传承的认知传统。随着实用理性主宰生活,世界逐渐祛魅,结果是,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聚焦在对组成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律的还原,对世界的客观知识只能来自于对事实的描述和说明,价值不再构成世界的一部分。也正是这样,进入现代社会,价值不再来源于世界,它只是人们的主观赋予,依赖于人们的论证和解释(16)这便涉及价值主观主义的问题。尽管下文还会提及这个问题,一个事先的厘清也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在规范层面上,价值来源于个体的主观赋予并不能推导出价值是主观化的,从个体认知的角度,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价值客观性的论证。价值的来源问题与价值的属性问题需要作逻辑的区分,价值来源于道德主体不代表价值是主观的、相对的、多元对立的。这与在社会结构(经验)的层面上,价值“必然”呈现出“主观化”“多元化”的特征并不冲突,它们之间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关系。第二,价值的主观主义议题背后的一个核心关切是政治权力,表达杜绝用政治权力背书某一种价值观、强行推进该种价值观的极权式做法的意思。但如果基于此认为,价值的客观论或一体论容易或者往往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这是一种逻辑和规范上均错误的解读。。这样,价值和意义的根据就变成了道德主体的选择和决定。知识本身要求具备普遍性与客观性,但依靠实用理性,已经无法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建立起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因此,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理性的实用化、工具化,另一方面是价值的去知识化。价值的去知识化,伴随的是在社会议题中,人——特别是在抽象的维度——作为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不断被拔高。
第二,价值的多元主义。价值的去知识化必然在社会结构的层面带来价值的多元主义,现代社会又被称之为多元社会,从根本上说即是肇因于此。甚至以赛亚·柏林和韦伯将价值多元主义视作现代社会的固有本质(17)[英]史蒂文·卢克斯:《以赛亚·伯林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之比较》,李红珍、曹文宏译,《江汉论坛》2012年第3期。。在传统的世界,基督教也好,儒家的教义也好,它们均代表了一个客观正确的一元方案,借着对客观宇宙的权威阐释,以某个特定的“善”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谋求社会的和谐与统一。但步入现代社会,随着价值的去知识化,原有的一元论述体系被打破(18)杨建:《刑罚规制个体自决事物的限度》,《学海》2018年第6期。,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元论”被以柏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犯了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19)刘擎:《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按照柏林等人新的理解,人的价值目标不仅多样,而且它们之间往往不可通约(20)这里需要为学界这一基础又经典的理论难题指出一个新的可能的思路。根据牛津大学新任法理学讲席教授张美露的理解,我们基于不可通约性作出的很多论述往往可以被证明是错的,是错误地理解了“不可比较性”的结果。她为此提出了一套新颖的比较理论。笔者想指出,她的理论贡献可以补强徳沃金的价值一体论,进而为相关基础议题在规范论层面的解决提出原创性的方案。参见Ruth Chang, Making Comparisons Count, Routledge, 2002。。价值的多元主义即是指,人们基于各自持有的整全理论,对何为美好的生活持有不同的认知和看法,这些经由人们自主选择和决定做出的认知和看法,往往相互冲突、不可调和,因为缺乏可以用来进行客观评定的标准,所以既无法有效分出高低,也注定长期共存,这种结构化了的对立表征着现代社会。当然,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本文所指的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主义特征是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说社会结构层面的意思是指——这样的判断搁置了在规范论上的争论——从观察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呈现出价值多元的核心特征。
第三,内嵌的合理分歧。价值的去知识化以及多元主义,必然使得现代社会内嵌着合理分歧。在传统的理解中,主体之间理性地沟通与交流一定会弥合分歧、达成共识,只有一方不讲道理或者非理性,认知上的对立才无法被消除。现代社会的出现也打破了这一信条。理性对于统合分歧来说无能为力,因为价值去知识化,根本的抉择没有办法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尽管理性会迫使各方尽力将观念陈述清晰、陈述合理,但理性无法消弭基于欲望和激情(性情)做出的根本抉择上的不一致。思考和交流越多,理性主体之间的分歧也就越多(尽管分歧也会随之明晰)。用韦伯的话来概括便是:“人们正可从最为不同的终极观点、循着相当歧异的方向来‘理性化’生活。”(21)[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页。罗尔斯更是列举了理性沟通中的六点困难来说明合理的分歧:(1)已有的经验的、科学的证据可能相互冲突或者太过复杂;(2)即使人们同意哪些考量是与议题相关的,但大家对各个考量的重要性也可能看法不同;(3)关键性的概念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合理理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4)我们评估证据和价值的方式受到我们的阅历、经验、人生阶段的影响;(5)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的规范性考量是不同的;(6)最后,根据我们在意的诸多价值进行选择,也很难设定和调整它们之间的优先关系(22)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6-57.。所以可见,现代社会内嵌的分歧不是由非理性造成的,而是理性本身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合理分歧在价值的去知识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之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第三个结构性特征。
不过,倘若现代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价值多元、分歧和冲突,传统社会中统一的价值准则又一去不复返,一个重要的追问便是:现代社会可以以什么为基础来将这些经常性对立的力量统一成一个整体呢?这个问题叩问的便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法治社会概念也应当被纳入到这一追问之下进行理解和诠释。
三、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社会所代表的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要成功落地、生根,如上所述需要寻求将经常性对立的力量协调在一起的力量与组织原则。现代社会中,政府惯常地以国家实际运行者的身份出场,往往被社会要求履行和扮演此种协调和统合社会力量的角色。但协调和统合的任务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它能否正确理解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以及采纳顺应这种特性的基本组织原则。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现代社会的上述特性提出了怎样的组织要求,我们再在这个要求的基础上考虑政府需要采纳何种组织原则才能兼容和胜任。
实用理性的兴起,世俗世界的祛魅,价值的去知识化使得被内嵌在社会分工合作体系之中的利益主体无法再依照统一的思想过同质化的共同生活。在传统社会中,定于一尊的一元道德体系(譬如基督教、儒家的教义)的存在,溶解了共同生活所必需的正当性需求,一元道德体系本身即是正当性的代表,成为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实质性的组织原则。如今,消解了传统依附关系的利益主体必须依靠自己,一方面直面弥散着的异见与分歧,另一方面承担起分工合作的职责,实践已经事实上多元化了的共同生活的宿命。很显然,现代性的背景之下,这种合作体系能够建立并得到维系有一个基线要求,即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各方需要自行约束在实质价值观上的分歧,并确保相互之间分工合作的结构是公正的。换言之,正义替代了一元道德体系成为社会统一和存续的新的世俗基础。只要社会各方的共同生活大体公正,现代社会就能确立并运转下去,反过来说,现代社会也一定会催生公正的法权诉求。也就是说,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正义构成了现代社会一个首要的组织要求。
当政府面对有着不同价值观念的利益主体,想有效又良好地凝聚和统合他们的时候,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呢?这就涉及了现代社会的第二个组织要求:中立性。政府要想在不同的社会主体面前维持正义,就必须平等地尊重和对待不同主体的不同价值观念。要想不有失偏颇地面对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及其实践抉择,就必须在各自不同的价值观面前保持中立。既不表达出倾向于某一类价值观而贬低、否定另一类价值观的意图,也不通过政策或行政行动促进某类价值观念或为其背书,这便是中立性的基本含义。立足于这个基本的要求,中立性还呈现出至少以下两个要点:(1)中立性要求中立,但中立性本身并非是道德上中立的(23)Steven Wall, George Klosko edited, Perfectionism and Neutralit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p. 6-11.中立性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规范议题,本文对此议题的补充说明是,在笔者看来,证立中立性的论证必须是中立的这类学术主张是不能成立的,中立性的证明应当基于实质的价值理念和承诺。,它是现代社会维系、运转的形式要求,只不过,这个形式要件的存在指向的是个体自主理性实践和美好生活的实现,保障的是道德主体的主体权利与价值;(2)中立性因此可以被称作现代社会的组织要求,但它不是对社会主体的规范和约束,而是对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政府的要求,指向的是权力运作的限制条件,表达的是对社会治理本身的正当性要求,定位在这种权力运作正当性的核心构成要件上。
此外,政府在有着合理分歧的价值主体面前,要维系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要秉持中立性的基本要求,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能够采纳的培育和治理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应当是一个形式原则而不是实质原则。因为只有形式原则才能在有着不同整全观念的价值主体面前恪守并维系公正、中立的治理要求。综合来看,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使得政府要想在公共领域成功地形成和维系一个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其赖以立基的组织原则必须至少满足公正性、中立性和形式性的组织要求。
面对现代社会价值去知识化、多元化、合理分歧长存的基本特性以及内在孕育的公正性、中立性、形式性的组织要求,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维系就必然需要依靠一个尊重社会规律、符合组织要求的组织原则,后发国家要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改造也必须采纳和遵循这一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提出“法治社会”的概念,要求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对此合理的、具有竞争性的学理解读应当是,执政党正确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及其组织要求,做出了将法治树立为培育和建设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的战略部署(24)类似的学术立场、思路和分析性的论证可参见杨建:《作为政治概念的法治文化:内在张力与规范诉求》,《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为什么这样的理解是一个好的解读,为什么法治可以也应当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以下是具体的理由:
第一,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其状态与属性决定了任何一元的实质价值准则都无法担当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打破原有的高度同质化的共同生活,就是要合理、有效地与多元的、相竞争的、整全的价值观念共存,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就是将原先的主导性伦理教义与世俗权力相剥离并重新确立世俗权力运行的基础和准则的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必然是包容性强的形式原则而非排他性强的实质原则。法治原则是当代主流国家公认的世俗权力运行的基础与准则,与传统但仍有重大影响的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原则相比,也是包容性强的形式原则。也就是说,法治作为相竞争的组织原则待选项之一,是较其他实质价值教义更具竞争力与生命力的方案。
第二,作为包容性强的形式原则,法治还指向并促进着社会统合、维系所必需的正义要求。法治作为更具竞争力与生命力的方案还不能充分证明它完全胜任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因为形式性只是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要件之一,形式原则并不必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的正义要求,所以还需说明法治何以是能够确保社会基本结构之公正的形式原则。有学者主张,存在着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且依照这个体系内的法律或者规则进行治理,就是法治(25)苏力:《法治中国何以可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苏力:《如何看待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红旗文稿》2016年第3期。。这显然是不准确的法治观,也没有全面描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界定和理解,这样的“法治”也确实不能胜任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26)杨建:《作为政治概念的法治文化:内在张力与规范诉求》,《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借鉴克雷默(Matthew Kramer)的理解,法治有大写与小写之分(27)See Matthew Kramer, H.L.A. Hart: The Nature of Law, Polity Press, 2018, pp. 159-160.。小写的法治存在于任何用法律体系来进行治理的地方,但这种小写的法治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一个社会的道德理想;大写的法治与前者不同,它指向的是一个自由、公正的现代社会,内嵌了这类现代社会在形式和程序上的特征与要求,因而必然构成一个社会的道德理想。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追求、捍卫和促进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保障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持续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执政党,其理解和实践的必然是大写的法治,必然承载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道德理想,因此也必然契合于并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的法权要求。也正是在这个面向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何以法治可以是也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第三,作为包容性强、契合于正义并追求其实现的形式原则,法治还能满足政府权力进行社会治理所需的中立性要求,能够有效地与中立性要求相兼容。面对有着不同的整全观念和价值诉求的社会主体,不仅权力运行的正当性而且权力运行的实践效果也都要求和取决于居中的政府不援引、不评价、不背书任何一方的价值观。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的道德理想,它的核心意涵便是要求政府守法,政府依据法律(而非某一方的价值观念)运行权力,同时政府依据的法律本身应当是公开的、清晰的、普遍的、明确的、一致的、稳定的、不溯及既往的等等(28)[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5-107页。,以确保多元共存的社会各主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的评价及其带来的经济与自由上的处分不会超出预先颁布的法律范围之外。通过以上的规范性主张,法治致力于保证政府公平地尊重和对待每一位社会主体,也即实现现代社会良好运行所必需的中立性要求。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决定了统合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必须满足形式性、公正性、中立性的要求。相比于诸多传统社会延续、发展至今的实质价值准则,在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法治因其内在的属性与规范力成为更具竞争力与生命力的方案,在社会现代化改造与转型的实践中脱颖而出,成为主流国家的奠基性准则。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尊重规律、顺应时势、立足长远,提出“法治社会”的概念,应该是正确地把握住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理解了现代社会的组织性要求,在结构性的层面上将法治确立为我国培育和运行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四、社会培育与治理的基本准则
法治作为统合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具有竞争力与生命力的方案,被中国共产党树立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基本组织原则。不过,这一正确的战略部署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法治作为宏观层面的组织原则不会自动落到实处(29)作为现代社会道德理想的法治,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等学者均指出,这一层面的法治原则在设定、评价、批判与矫正中观以及更为具体层面的政策、规则、手段、方法上的作用,反过来说,宏观层面的法治原则也需要中观层面的规则和具体实践层面的操作予以推进和落地。。说到具体的社会培育和治理工作,还需要真正体现法治原则的中观层面的基本准则对相关的实践予以规划、约束和指引。所以,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组织要求以及组织原则之后,必须了解在法治原则之下社会培育与治理所必须遵循的几个基本的实践准则。正是这几个基本准则紧扣了、推进和实践着法治要求形式规范、约束权力、恪守中立的规范意涵。
在传统生活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形成的是“两新一旧”的治理格局。“两新”一个指向政府,政府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逐步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议题设定和资源调配的能力,并向着全能、全责政府的方向一路挺进(30)杨建:《论开放式的弱者概念——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背景》,《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另一个指向个体,个体在生活的快速现代化,特别是新兴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的潮流推动之下,越来越活跃、积极,个体生活呈现出不可逆的开放性、互动性与自主性的趋势(31)杨建:《规范性论述兴起的实践背景与理论脉络》,《法律方法》2017年第22卷。。“一旧”是指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社会公共领域一如既往地孱弱、破碎,欠缺组织性和执行力。“一旧”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权能,持续加剧着“两新”之间的内在张力。法治社会概念的提出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期扭转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两新一旧”的格局,努力构建“三元共治”的新结构。在中国语境中,“三元共治”这个较为理想和规范的现代社会图景的最终实现,需要怎样调整原有的实践安排?面对现状,哪些基本准则正确体现了法治原则所保障的价值多元共存、合理分歧内嵌的现代社会特性?这些是本文接下来要去概括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结合上文已有的认知,现代社会的培育与治理至少需要明确和做到以下几个基本要求:
第一,从自然扩权转向有限扩权与为适度放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社会组织的组织程度不高,个体也呈现碎片化的原子状态时,政府责无旁贷地成为社会培育、社会分工与合作、社会治理等公共议题的主导者(32)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0页。。就像我们在面对和处理新兴问题中积累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获得了成长一样,政府在类似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也逐渐实现了专业化,并迅速扩大了自身的体量与能力。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政府权力的自然扩张,中西方主流国家均呈现出了这一特征,政府权力的扩张是近现代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显明事实。所以不难看到,在社会培育和治理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权力也借此过程实现着增长。但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主流领导力量都认识到,政府权力的自然扩张是无法完成这个扩张本来指向的培育一个健康、有活力、自行良性运转的现代社会的目标的。因此,如果我们将权力的自然扩张称为社会治理体系的1.0模式,这个自然扩张模式就必须转向政府对权力扩张的强大动力和便利进行自觉约束和限制的2.0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内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权力运作的政策,并运用各类内部评价和纠偏的手段,以确保法律对行政执法的约束力总体上越来越强。这个2.0模式在自觉约束权力扩张的同时客观上逐渐让渡出了二次赋权和放权的空间,将自我节制扩权与有意识地给社会放权结合在一起。从政府所处的情境来说,自我节制扩权很难,自我放任扩权却很容易,政府主导的2.0治理模式充分肯认其间的艰难,并努力形成和维持这一新格局,这种意识与前述大写的法治原则是高度一致的,也会为社会治理体系最终进展到完全切合法治原则的3.0治理模式打下很好的基础。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调试中,当务之急是确立和坚持2.0的治理模式,将有限扩权与适度放权的决定坚持到底,从而让社会及其各类组织逐渐获得自身的生命力,逐渐提升它们的组织能力和行动水准。也只有这样,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实践目标才能有效地实现(3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第二,改变原有做大做强壮大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与治理思路。社会及其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既离不开国家赋权、放权、给予其成长的独立空间,也离不开政府间接与直接的扶持与规范。不过,社会公共领域的组织程度、健康程度和活力并不取决于组成社会的单个组织的规模,甚至也不取决于单个组织的强健程度。社会公共领域的繁盛与否取决于它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程度。一个巨无霸式的环境保护组织比不上一千个规模小但各有专攻的环保组织;一个社区的象棋爱好协会更不需要它的象棋竞技水平达到很高的竞争水准;一个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慈善机构也完全不需要因为它的工作量逐年下降就要求它强制关闭。不同种类、不同方向、不同专业度和生命力的组织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将持不同价值观的个体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本身以及联合的过程就有其独特的和内在的意义,并不需要它们的实践结果来予以担保或作事后的证成。在消解了(政府身上对社会扶持和治理所持有的)这种有用性、功利性的定见和束缚之后,才能更好地孕育和呈现现代社会多元并存、兼容并蓄的现代特性。也恰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反而能够在基层社会组织中看到足球天才、象棋大师的诞生。换言之,社会及其组织机构的培育及延续并不需要遵循市场经济领域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因此政府扶持和引导的方向也不应该是追求社会组织的做大做强,扶持的范围和力度也不应当仅考虑社会组织的竞争力与生命力,对强健的社会组织予以扶持倾斜,对不具竞争力但对政府扶持有所期待和要求的组织却不管不顾。这并非是说,社会组织自身的理性化程度是一个不重要的可以被忽视的问题,但社会组织自身的理性化主要是也只能是通过其自身予以完善和提升,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应该是一个保护性、防御性、救济性的角色和作用。
第三,确立社会组织协作自治、互治的基本准则。国家放权给社会及其组织,是给予其有效生长的空间;政府对社会组织自身的运行意志、抉择和实践结果表达克制和尊重,是秉持政府在社会培育和治理上的中立性、公正性要求;此外,在社会培育和治理的整个事业中,还应当允许社会组织分担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和任务,与政府展开分工协作,推进社会组织自治、互治机制的落地和良性运转。对政府来说,这个社会自治的机制可以减轻它越积越重的负荷,提升它聚焦重点问题的能力和效率,也是进一步落实法治原则所要求的规范权力、约束权力的目标;对社会自身来说,这个自治、互治的机制就像游泳只能通过下水才能真正学会一样,可以确保社会的培育在社会实践中生根;此外,通过自治和互治才能更好地、真正地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的理性化程度,使得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行动策略的社会组织能够在法治原则的框架内将合理的分歧控制在形成与维系社会分工与合作并促进社会发展的程度之内。也是通过这个基本的治理准则,由私人联合而成的公共领域(社会)才会将社会培育和治理的过程从单方面强化、增进、扩大行政权力转向兼而保障和促进私主体的权利,也只有这样,才是对宏观层面作为社会组织原则的法治在实践层面的真正落地和推进。
五、结语
到此为止,我们经由对现代社会基本特性的说明,阐述了现代社会存续所内生的组织要求。面对公正性、中立性、形式性等社会现代化必须满足的组织要求,法治在与传统实质价值准则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更具正确性与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组织方案。中国共产党在正确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基本特性和组织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治社会的概念,法治社会核心的含义因此应当被理解为,将法治树立为中国(现代)社会培育和治理的基本组织原则。在法治原则的组织之下,社会培育和治理的具体工作框架应当转变为:树立有限扩权与适度放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改变原有的做大做强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与治理思路,以及确立社会组织协作自治、互治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