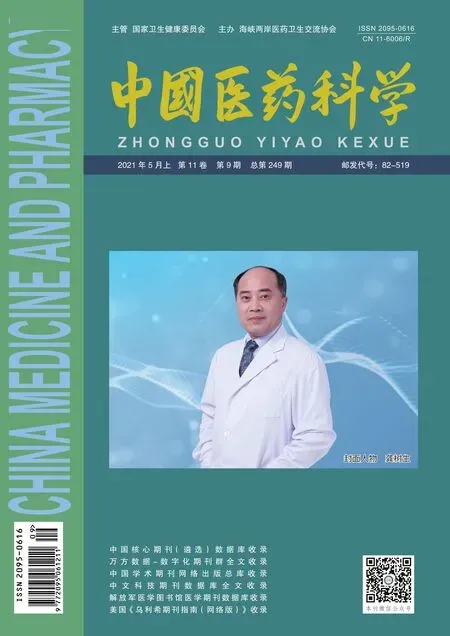杨小军教授治疗功能性烧心经验
范青峰 杨小军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长沙 410000;2.重庆市中医院,重庆 400020
有研究表明[1]根据所采用的诊断标准和所监测的地理区域,胃食管反流病(GERD)患病率为2.5%~25%。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逐步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日渐加大,加之饮食不节、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以及部分人伴有长期焦虑或抑郁状态,我国的GERD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功能性烧心(functional heartburn,FH)隶属于GERD。罗马Ⅱ中的“酸敏感性食管”首次被纳入FH的范畴,其定义发生了变化,在罗马Ⅲ中进一步修订为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疾病谱的一部分;在罗马Ⅳ里,FH的定义及诊断则更加清晰明了。而FH的治疗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经验性治疗,因此推荐个体化治疗。杨小军教授是重庆市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功能性胃肠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杨教授将中医运用至FH的治疗上,认为诊治其关键在于辨证论治,缓解患者症状治标是其一,重要的是找到根本病因,灵活的遣方用药加减便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1 FH
1.1 定义及诊断
最新罗马Ⅳ提出FH诊断标准[2-4]:FH是指发作性胸骨后烧灼样不适或疼痛,足量的抑酸治疗无效,无胃食管反流或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导致该症状的证据,无主要的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诊断前症状出现至少6个月,近3个月症状明显,且出现频度为至少每周2 d。糜烂性食管炎或Barrett食管的诊断并不困难,但功能性部分的诊断仍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反流高敏感(reflux hypersensitivity,RH)和FH方面[5]。最新罗马Ⅳ首次引入RH概念,并将其从NERD中分离出来的,RH及FH均隶属于GERD,24 h食管PH-阻抗监测是鉴别诊断RH与FH的重要检测方法。内镜和食管黏膜活检正常前提下,若不能诊断GERD,则需停用PPI进行24 h食管PH-阻抗监测,结果显示病理性酸反流则可考虑为NERD,而未发现病理性酸反流时,若反流症状指标(SI)≥50%,反流症状相关概率(SAP)≥95%,提示有反流相关症状,即可考虑为RH;若SI<50%,以及SAP<95%,则提示无反流相关症状,则可考虑为FH。即使诊断为GERD,在使用PPI进行PH-阻抗监测时,结果显示病理性酸反流时即可再次确诊为GERD,但在结果显示无病理性酸反流的前提下,有反流相关症状则考虑为RH,而无反流相关症状则可考虑为FH,对此诊断结果,RH和FH与GERD相重叠。NERD、RH和FH有1个共同症状即烧心,三者不同的临床特征主要体现在PPI治疗反应和是否重叠上腹痛综合征(EPS)两个方面,而FH重叠EPS发生率较高进一步强化了功能性胃肠病存在共同病理生理学机制的假说[6]。
1.2 治疗
首先教导患者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与良好的情绪,纠正患者不良饮食习惯和不合理生活习惯,可促进老年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较快恢复健康[7],同样亦适用于对FH患者的教导方案;其次对于肥胖者,鼓励其减重。药物治疗上西医应用质子泵抑制剂、黏膜保护剂和H2受体阻滞剂进行常规对症治疗,一方面帮助医生对GERD、NERD、FH及RH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同时可对FH合并NERD或反流高敏患者有一定治疗作用[8]。美国胃肠病学协会(AGA)关于FH的临床实践更新中指出:PPI对功能性胃灼热没有治疗价值,但被证明的GERD与功能性胃灼热重叠有例外[9]。FH患者除了烧心、胸骨后烧灼样不适或疼痛感症状外,大多数伴有焦虑或者抑郁症状。谷诺诺等[10]提出口服三环类抗抑郁药、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舍曲林、氟西汀、帕罗西汀、氟伏沙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西酞普兰、黛力新)调节中枢和外周痛觉过敏;并可进行认知行为治疗、行为矫正、放松治疗等精神心理治疗。一项安慰剂对照研究[11]结果显示,氟西汀对于反流性过敏和FH患者,能有效延长无烧心天数,且效果显著优于奥美拉唑。李业欢[12]用黛力新联合伊托必利治疗难治性GERD,得出两药物联合使用治疗难治性GERD可取得更好疗效且显著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结论。在对症支持治疗方面上选用消化酶、益生菌、益生元、粪菌移植、促胃肠动力药物等可改善FH患者的消化功能,并缓解其不良情绪。
2 中医对FH的认识
2.1 病名
中医学中尚无FH病名,认为其大多属于“吐酸”“吞酸”“嘈杂”“食管瘅”“噎膈”等范畴。
2.2 病因病机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曾有“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之记载,文中“心痛”是指胃脘痛,“烦心”与胃痛、欲呕、吐酸等症状同时出现,其意应属烧心之类的不适[13]。病机十九条:“诸呕吐酸,皆属于热。”辨明了吐酸的病机属热。汉代张仲景则有论述与烧心症状相关的条文与具体方剂,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76条:“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栀子豉汤主之。”第77条:“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173条:“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326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热稽留于内,上扰胸膈,可发为烧心,即类似栀子豉汤证;饮食不节,脾阳受损,积湿生热,气机阻滞而不得交通,少阳枢机不能正常运转而出现上热下寒,亦可发为烧心,即黄连汤证;饮食偏嗜,再加之平素焦虑或抑郁,肝经循胁贯胸中,肝木之气郁滞,失其条达,郁而化热,循经扰于胸中,可发为烧心,即乌梅汤证[14]。《伤寒论》对有关烧心的症状形成了方证对应的诊疗特色。
后世医家刘完素在病机十九条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伤寒三书·原病式》:“吐酸,酸者肝木之味也。由于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甚,故为酸也。”这说明吐酸与肝气相关[15]。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论述:“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时津液随上升之气郁积而成。郁积之久,湿中生热,故从火化,遂作酸味。”从论述中可知湿郁积日久生热是吐酸主要的病机。高鼓峰在《四明心法·吞酸》即云“反胃吞酸尽属肝木,曲直作酸也。”故吐酸一证,无论寒热虚实皆从肝论治。综上论述,古人的经典论述对现今的临床治疗具有很大的借鉴,以及从中总结出FH的病因属火、热;病变脏腑与脾、胃、肝等相关,病机多为脾胃气机升降失调、寒热错杂、湿郁久化热等,多从肝论治。
3 杨小军教授对FH的治疗经验
杨小军教授总结前人经验以及灵活运用经典方剂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FH的治疗特色。杨小军教授应用自拟柴胡苏黄降逆汤对肝胃郁热证型GERD伴焦虑状态或抑郁状态的患者进行临床观察与治疗,共纳入102例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西药组及联合组。总有效率、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积分差值、生活质量改善率,最佳均为联合组,最终得出柴胡苏黄降逆汤可以改善肝胃郁热型GERD伴焦虑状态或抑郁状态患者的症状结论[16]。同理,杨小军教授将柴胡苏黄降逆汤运用至肝胃郁热证型FH的治疗,并根据伴随症状灵活加减亦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3.1 辨证论治及用药特色
杨小军教授在诊断FH的患者时,认为FH患者多为实证,其中肝胃郁热证型是FH的主要证型;病因多为长期抑郁焦虑、饮食不节;病位主要在胃和食管,与肝、脾联系密切。肝主疏泄,调畅情志,肝失疏泄,机体气机失常,可进一步影响五脏之功能活动;其次肝气郁而不疏,郁久化热,肝木克脾土,脾失健运,胃失和降,病情常迁徙不愈,故FH病程多为6个月。肝胃郁热证型的FH患者,除了感烧心或者胸骨后灼热感外,还常见情绪抑郁或焦虑,善太息,嗳气频繁,咽喉部有异物感,甚至有咽喉至食管处感烧灼不适,口干、口苦,胸胁部时感胀痛,舌脉象常见舌边红,苔薄黄,脉弦滑;从经脉走势上看,肝经、胃经以及脾经都与膈肌、喉咙、咽喉等有密切关系。故杨小军教授亦用柴胡苏黄降逆汤加减,肝郁常导致机体气滞,不通则痛,故杨小军教授对于腹胀明显者加沉香、佛手、香橼,佛手主疏肝行气,香橼主疏肝理气,宽中;疼痛者加延胡索、瓦楞子,沉香、延胡索同主行气止痛,瓦楞子主制酸止痛;肝郁较重者,加玫瑰花、薄荷、郁金、合欢皮、菊花等加强疏肝解郁清肝之功,其中郁金、薄荷、菊花更擅长清泄肝郁之热。
脾胃湿热证型FH在临床上也属常见,其病因病机为湿邪阻滞脾胃中焦,湿邪易阻气机,故常见患者除烧心外,还感腹胀不适,大便黏稠,不尽感,舌苔白或黄腻,脉弦滑数。湿邪郁久化热,热邪蒸腾湿邪于口,则出现口苦、口黏、口干不多饮,郁热之邪趋上的特点,故将波及胃脘部以上的食管、咽喉。故患者常感胃脘部至咽喉处莫可名状的灼热不适感,杨小军教授常用香砂六君子汤合小半夏汤随证加减。中焦痰湿重者,加竹茹、半夏量加大,增强化痰除湿之功,加荷叶,升清气,同砂仁增强化湿和胃之功。
3.2 验案举隅
3.2.1 病例1 女,66岁,因“烧心、干呕5年余”于2020年8月24日就诊于我院消化内科门诊,辅助检查:2020年8月14日我院胃镜:慢性非萎缩性胃炎。24 h阻抗PH联合监测检查示:未见病理性酸反流,烧心、干呕等症状与反流无相关,考虑为FH。刻下症见:感烧心、干呕,偶有反酸、嗳气不适,胸骨后时发闷热痛,时有后背部酸胀,进食后有上腹部胀痛,纳一般,多梦,口干、口苦,自觉小便泡沫较多,夜尿2~3次,大便调,平素情绪急躁易怒,情绪不佳时烧心、干呕不适明显加重。既往病史: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肝炎、结核等慢性疾病。个人史: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药物过敏。查舌脉:舌两边红赤,苔黄腻,脉弦细滑。根据患者症状及舌脉四诊合参辨证为肝胃郁热证,予以疏肝和胃,清热降逆,方以柴胡苏黄降逆汤加减,具体处方如下:北柴胡10 g,陈皮10 g,酒川芎10 g,醋香附10 g,麸炒枳壳10 g,白芍10 g,瓜蒌皮10 g,大腹皮10 g,酒黄芩10 g,薄菏10 g(后下),酒黄连10 g,紫苏梗10 g,合欢皮10 g,山银花10 g,炒栀子10 g,川牛膝10 g,沉香5 g(后下),石榴皮15 g,茯神(木)10 g,菊花10 g,荷叶10 g,蛤壳20 g(先煎),水朝阳旋覆花20 g(包煎),醋延胡索15 g。共7剂,煎服,每日1剂,每次150 ml,每日3次。患者于2020年9月20日第一次复诊,刻下症见:烧心、干呕症状明显缓解,偶感反酸,嗳气消失,咽喉部时有异物不适感,胸骨后闷痛较前减轻,自觉有口臭,纳可,睡眠差,入睡困难,睡后易醒(需日服半粒舒乐安定),每晚睡眠3~4 h,大便正常,小便稍带泡沫,夜尿次数减少,1~2次/晚;舌边红,苔薄白稍腻,脉弦滑。前方减去荷叶,加蜜炙远志10 g,柏子仁15 g,酸枣仁15 g,龙骨20 g(先煎),牡蛎20 g(先煎),共7剂,煎服,用法用量同前。患者于2020年9月27日第2次来门诊复诊,刻下症见:偶有烧心、反酸症状,胸骨后闷痛感较前进一步好转,弯腰时胃脘部轻微感堵塞不适感,已无明显干呕,咽喉稍感干痛不适,服药时咽喉轻微有刺激感,咽喉异物感消失,偶有嗳气,纳可,睡眠较前明显好转,舒乐安定在服中药期间已停用,夜间醒后时有潮热感,大便正常,夜尿1次,小便偶有泡沫。舌淡红,苔薄黄稍腻。前方(第二次方药)上去龙骨、牡蛎、酸枣仁、柏子仁,加竹茹10 g,善后。
按:患者平素情绪不佳,急躁易怒,肝常失疏泄,肝气郁结,气郁久化热,木郁克土,肝气郁结产生的郁热多传至脾胃,热邪趋上,少阳枢机不利,疏泄失职,脾胃气机紊乱,导致胃气不降,胃与食管相连,故见患者烧心、干呕、胸骨后感闷热痛,舌脉均为肝胃郁热佐证;柴胡苏黄降逆汤为柴胡疏肝散与苏叶黄连汤合方而成,方中柴胡条达肝气而疏郁结,香附疏肝理气止痛,延胡索增强止痛之功,川芎助疏肝开郁、行气活血止痛,陈皮、枳壳、大腹皮理气行滞调中,加少量沉香助行气止痛,白芍养血柔肝,黄连清泻胃热,紫苏梗行气宽胸,疏畅中焦,瓜蒌皮清热化痰,黄芩、栀子、山银花、荷叶共清中焦之郁热,合欢皮、茯神助睡眠,菊花、薄荷清肝热,石榴皮酸涩收敛,蛤壳制酸止痛,水朝阳旋覆花降逆止呕。二诊时,患者症状有明显改善,但睡眠质量很差,故加蜜炙远志、柏子仁养心安神,酸枣仁宁心补肝,龙骨、牡蛎平肝潜阳,三诊患者睡眠明显改善,故去龙骨、牡蛎、酸枣仁、柏子仁,加竹茹增强清热化痰之功善后。
3.2.2 病例2 女,50岁,因“烧心、呃逆1年余”于2020年9月1日就诊于我院消化科门诊,辅助检查:2020-07-06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胃镜:慢性非萎缩性胃炎。24 h阻抗PH联合监测检查示:未见病理性酸反流,烧心、呃逆等症状与反流无相关,考虑为FH。刻下症见:烧心、呃逆频繁,偶有胃脘隐痛,时感食管处至咽喉部酸热感,无吐酸、恶心、呕吐等,稍有腹胀,感口中黏腻,纳眠可,大便前干后稀溏,2~3次/d,有大便不尽感,大便较黏稠,小便正常,偶有手足麻木。既往史有糖尿病,胆囊切除术后。舌红,舌边齿痕,苔黄白相间腻,脉细滑。四诊合参辨证为脾胃湿热证,予以健脾益气,清热化湿,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合小半夏汤加减,具体药物:太子参10 g,茯苓10 g,白术10 g,姜半夏15 g,陈皮10 g,木香10 g,砂仁10 g(后下),蛤壳(先煎)20 g,竹茹10 g,瓜蒌皮10 g,沉香5 g(后下),醋延胡索15 g,酒黄连5 g,紫苏梗10 g,地榆10 g,炒槐花10 g,山银花10 g,菊花10 g,玫瑰花10 g,薄荷10 g(后下);共7剂,煎服,每日1剂,每次150 ml,每日3次。患者于2020年9月8日复诊,症见:烧心明显缓解,呃逆轻微缓解,食管处至咽喉部轻微酸热感,偶有腹胀,现时有反胃,胃脘隐痛消失,口黏腻减轻,无恶心、呕吐,纳眠可,大便基本正常,1 d解1次,小便正常,未诉手足麻木感。舌淡红,苔薄白稍腻,舌边齿痕,脉细稍滑。前方减半夏量为10 g,加丁香10 g、旋覆花20 g(包煎),7剂善后。
按:患者舌边齿痕,为脾虚表现,脾虚运化水湿功能下降,水湿停聚易成痰饮湿邪,故见口中黏腻,大便前干后稀溏,大便黏稠,痰饮湿邪郁久化热,热邪蒸腾湿邪至食管、咽喉部,故患者常感食管处至咽喉部感酸热感,湿邪易阻脾胃气机,郁热扰动膈肌故出现呃逆频繁、腹胀,舌脉均为脾胃湿热之佐证;方中太子参、茯苓、白术健脾益气除湿,姜半夏燥湿化痰,陈皮化痰理气,木香、沉香理气行气止痛,延胡索增强止痛之功,砂仁醒脾和胃,蛤壳制酸止痛,竹茹、瓜蒌皮、山银花清热化痰,黄连清胃热,紫苏梗宽胸行气,地榆、槐花加强清热之功,玫瑰花行气解郁,二诊,患者无恶心、呕吐,痰湿之邪较前改善,仍有呃逆,故减半夏量,恐其辛燥,加丁香、旋覆花增强降逆下气之功。
4 小结
杨小军教授认为中医辨病辨证治疗始终坚持同病异治、整体观念的原则,辨证四诊合参,对患者的症状及病因病机要善于运用中医理论去分析、追本溯源。FH有别于反流性食管炎,以烧心或者胸骨后烧灼不适感为主要症状,伴或不伴有反酸、嗳气、呃逆、干呕等次要症状,而反酸症状多为患者的一个自我感觉症状,如食管处至咽喉部感酸热感,而患者却无吐出酸液等;且FH患者对PPI类药物的治疗症状无明显缓解或者缓解甚少,此时便要积极发挥中医药辨证论治的优势。认为FH之病因多为郁热,关键病机为郁热内蕴,临床上证型多为肝胃郁热证型及脾胃湿热证型,通过具体辨证及遣方用药,郁热得以消除,患者烧心不适等症状亦可随之消失或改善,故中医药的辨证论治有利于FH治疗方案的选择及临床疗效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