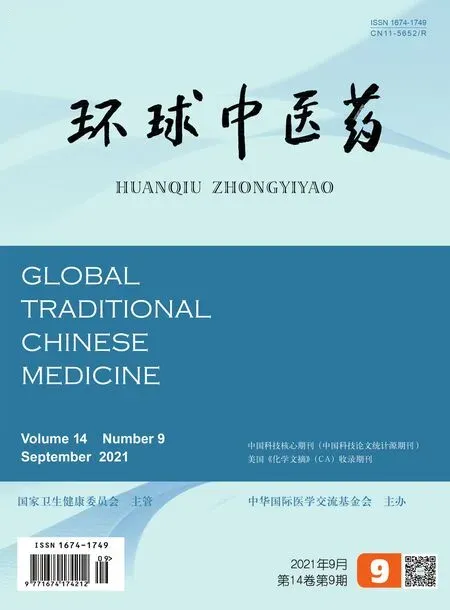从疏肝解郁论治甲状腺结节
陈金凤 温乔 严清萍 周围 娄锡恩
甲状腺结节(thyroid nodule,TN)是各种原因导致甲状腺内出现一个或多个组织结构异常的团块[1]。在古医籍中并没有专一对应的病名及明确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探析。目前,众多学者认为TN与瘿病表现相类似[2]。在其病因病机的认识上,大体归因于水土失宜、情志内伤、饮食失调三类。在治疗上重视调理肝脏,常以疏肝理气为首法治之[3]。虽然众多学者认识到从疏肝解郁论治TN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但有关从疏肝解郁论治TN的理论探析及具体治法的阐述仍不够详尽和细致。故本文以从疏肝解郁论治TN的中医理论基础和现代临床研究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从疏肝解郁论治TN的理论源流,并根据肝脏体阴用阳的生理特性提出以调肝用及护肝体为治疗原则的疏肝解郁新治法。
1 从脏腑角度而言,肝气郁滞是TN形成的关键病理基础
1.1 肝气郁滞可致瘿病的理论渊源
对于情志内伤致瘿的认识,早在隋代曹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即有“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的记载。至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中言:“瘿多着于肩项,瘤则随气凝结……随喜怒消长者,名气瘿。”又宋代申甫等在其所辑之《圣济总录》中云:“忧恚劳气,郁而不散……又此疾,妇人多有之,缘忧恚有甚于男子也。”首次提出了瘿病常以妇人多见,主要与情志不舒有关。明代朱橚在《普济方》中言:“夫瘿之初结者,由人忧虑,志气常逆,蕴蓄之所成也。”清代高思敬所著《外科问答》中亦有“瘿瘤……此症得自郁怒伤肝”之说。由此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了情志因素与瘿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后随着人们对瘿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肝气郁滞可致瘿病的观点逐渐形成。
1.2 肝气郁滞致瘿的病理机制
《明医指掌》中论瘿病时讲:“若人之元气循环周流,脉络清顺流通,焉有瘿瘤之患也?必因气滞痰凝,隧道中有所留止故也”,阐述了由于气机郁滞而致病理产物阻滞经络的瘿病病机。肝脏处于人体中焦,其气疏畅发泄,可上通下达旁及中州,疏畅内外,无所不至,是一身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其性调达,最恶抑郁。一有怫郁,则气郁为病。而肝气的正常疏泄是保证气机调畅的重要条件,气血津液的运行又以气机为主导。若肝气郁滞,失于疏泄,三焦气机阻滞,脾失运化,水液失布,则聚湿生痰;气为血帅,气滞无以推动,则血凝而为瘀,或气滞日久,郁而化火,炼液为痰,灼血为瘀。以致气血痰相互胶着,阻于脉络,循厥阴之脉上逆,循喉咙之后,搏结于颈,留而不去则成瘿病。
1.3 肝气郁滞致瘿的现代研究与应用
现代研究表明,TN的发生与焦虑、抑郁等情绪密切相关[4]。而疏肝解郁类中药确实可以通过改善人体的焦虑情绪,控制TN的增长[5]。在此基础上,以陈如泉教授为代表的当代医家重视从疏肝理气论治TN,认为本病气滞为先、痰瘀互结,肝气郁结是本病的重要致病环节[6]。治疗上提出以疏肝理气为基础的疏肝理气解郁、疏肝理气散结、疏肝理气化瘀、疏肝理气益气、疏肝理气化痰、疏肝理气清热、疏肝理气滋阴、疏肝理气温经等八个治法,临床收效甚佳。除此之外,不少医家以疏肝解郁类中药治疗TN,获得可观的临床效果[7-9],进一步证实了肝气郁滞是TN的关键病理基础。
2 从经络角度而言,肝经郁滞是TN的潜在发病机制
2.1 甲状腺虽系诸经而为肝经所主
根据经络学说“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原则指导,一般认为甲状腺与通过其所在部位循行的足阳明经、手足少阴经、足太阴经、足厥阴经等经脉均相关联。而《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中载“东风生于春, 病在肝, 俞在颈项”,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诸脏之中唯肝脏经气输注于颈项,而甲状腺正位于颈前喉结之下,故甲状腺虽系诸经而为肝经所主。同时,从现代医学角度而言,甲状腺的分泌功能直接受大脑调控,而足厥阴肝经不仅经过TN的发病部位,且“与督脉会于巅”,即与督脉相合而入络于脑。故肝经通过与脑的直接联系参与对甲状腺分泌功能的调控。这一点正好与西医理论中,肝脏在甲状腺激素代谢中有着重要作用的认识有所契合。
2.2 肝经郁滞以致瘿病的病理机制
《灵枢·经脉》载:“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与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且“其系上络于心络”“其脏在右胁右肾之前”,提示其与五脏关系密切;又交太阴、阳明、督脉而通于三阴、三阳、奇经八脉,其循行遍及周身,贯穿上下。故肝气的疏泄可以调节全身气机及气血津液的通畅。《灵枢·玉版》曰:“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正常情况下,甲状腺受肝脏疏泄功能的调控,随肝经经气的循行流通维持其正常的分泌功能。然受外邪、七情、饮食内伤、素体肝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肝经经气循行不利,肝气调控气血津液功能失常,产生痰瘀等病理产物内滞于络。又“厥阴主血”,为多血之经,势必导致肝经瘀甚,不得疏泄,形成TN产生的潜在机制。《灵枢·经脉》记载肝经是动病称:“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肝经经隧不利,其升发之气不得上行,津液不可随气布散,则咽干。这与现代医学阐述的TN压迫喉返神经时可引起咽干、咽部异物感等不适症状相符合。
2.3 肝经药物在TN中广泛有效应用
现代学者通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发现,在现有的能查阅到的治疗TN的药物中,肝经药物的使用频次位列第一[10-12]。多项研究的结果具有相对一致性,证实了肝经药物在古今的TN治疗中被广泛应用。再具体到单味中药,夏枯草常常作为消肿散结类药物应用于TN的治疗,《神农本草经》言其“散瘿结气”。现代药理证实,夏枯草确有针对TN的抗氧化、抗组织增生及抗肿瘤作用,据此研发出了夏枯草口服液及夏枯草膏等制剂广泛有效的应用于TN的治疗,而夏枯草亦归属于肝经。除此之外,柴胡、郁金、橘叶、王不留行、急性子、猫爪草等其他多种植物类药及蜣螂、土鳖虫、蜈蚣等善搜剔经络之虫类药作为治疗TN的常用有效药物,皆入肝经,直达病所。以方测证,肝经郁滞作为TN的潜在发病机制在治疗上得到广泛发挥及应用。
3 从病证相合的辨治角度而言,肝气郁结作为TN的核心病机贯穿病程始终
西医学认为TN是一种形态学概念,根据病因、病理类型分类繁多,关于病理机制的假说也不尽相同。而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但TN发病隐匿,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常由患者偶然触及或在体检时意外发现,其检出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测方法。临床上除了利用传统的四诊外,常借助超声等影像学资料作为望诊的延伸加以合参,以便明确其病理性质,区分良恶。因此在具体临证中,将西医的病理分型与中医证型相结合,达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论治TN,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1 囊性结节多为气郁
临床上所见囊性结节患者大多没有明显的全身症状,多由检查发现。触诊表面光滑,多数没有痛感,少部分患者会有肿胀不适感,结节可随吞咽动作上下移。查甲状腺功能多显示正常。甲状腺超声图像显示,结节有明显的液性暗区与实性结节相区别,结节有包膜,边界清晰,形态良好。西医认为纯囊性结节由多个小囊泡占据50%以上结节体积,呈海绵状改变的结节几乎全部为良性结节。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而言,此时患者一般没有颈部的局部压迫症状及明显的全身症状,部分患者可有乏力、胸闷、喜叹息及随情绪波动等症状,或是由自己发现颈部有可触及或肉眼可见之包块而就诊。观其舌脉,多舌红,苔薄白,脉弦。此时主要由肝气不疏,壅塞颈前而为病。但当囊性结节内液体增生或伴囊内出血时,颈部可见明显占位及胀痛感,此时应及时冷敷或采取穿刺抽液联合无水乙醇注射治疗;少数囊性结节也可合并甲状腺恶性肿瘤出现,应优先考虑手术治疗。
3.2 疼痛性结节、慢性无痛性炎症结节等多为气郁化火
炎症性结节可视为TN的急性发作期。由于个体先天禀赋及后天体质的不同,气郁日久有的人可进展为痰结血瘀,有的人则易气郁化火。化火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炎症反应,炎性结节急性期多表现为发热、局部疼痛、短暂性甲亢症状、超声可表现为片状低回声影像等。结节肿大及触痛是其主要的临床特征;慢性无痛性炎症结节仅有甲状腺肿大,无疼痛症状,可伴有甲状腺功能变化,超声下可见甲状腺弥漫性肿大,回声不均等征象。而郁火又可分为实火和虚火。二者无法从影像学上进行区分,必须依靠中医辨证加以鉴别。症见颈前结节、疼痛明显,烦躁多汗、性急易怒、眼球突出、手颤抖、口干、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等为肝火炽盛之实火;症见起病缓慢、颈部肿大、隐痛缠绵、心悸不宁、少寐、疲乏易出汗、舌红少苔,脉细数等,为心肝阴虚火旺之虚火。临症时将影像学资料和中医四诊合参辨证相结合,才能更准确的进行诊疗。
3.3 增生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良性腺瘤等多为气郁生痰成瘀
这一阶段可由以上两个阶段发展而成,也可直接发病。超声下甲状腺腺瘤呈椭圆形,有声晕,其内部为实性,边界清晰,包膜完整,以单发多见;增生性结节则常为多发,也有单个存在,单个的增生性结节与良性腺瘤常难以区分,必须依靠病理学确诊。结节早期多无明显边界,随着结节的增长,其周围逐渐形成薄的纤维组织包膜可视为中医病理产物“痰”的具象化表现。其周围的正常腺体组织则会轻度萎缩,在增生的结节边缘常可见扩张的血管,为维持增生细胞的营养而改变正常的血行方向,向结节的中心延展,随着结节的增长,可造成局部毛细血管破裂而形成结节内出血,这一现象与中医的“瘀滞”不谋而合。临床可见患者颈前肿块,按之较硬或有结节,日久难愈,纳差,咽部有异物感等,舌质紫暗,苔薄白,或有瘀点瘀斑,脉弦细涩。此时气郁痰凝,由气及血,以致气血结聚。
因此,在TN的常规诊疗中,以超声为代表的影像学检查作为中医望诊的延伸在该病的辨证论治中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不少现代学者致力于研究甲状腺超声特征与中医辨证分型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临床辨证论治提供参考[13-15]。在该病的治疗上,西医认为对于诊断为良性TN且未达手术指征的患者不需要进一步治疗,定期复查即可。而随着病程的深入,部分患者可出现结节进行性增大产生压迫症状或因出现咽部不适、异物感等加剧情绪焦虑,使得肝气郁滞—焦虑的病机形成闭环,逐渐加重。且西医在良性TN的消散上并无特效药物可用,使得中医在借助影像检查手段的情况下明确良性TN性质后结合病机进行论治的优势得以凸显。
4 以调肝用及护肝体为原则治疗TN新治法
4.1 调肝之用——治疗TN的首要治法
TN以肝气郁结为主要核心病机,木郁达之。纵观历代医家治肝之理法,唯清代王旭高所著《西溪书屋夜话录》论述最详,首提治肝三十法,其中治肝气法涵盖了疏肝理气、疏肝通络、柔肝、缓肝、培土泄木、泄肝和胃、泄肝、抑肝等八个治法。名目繁多,而多有名异实同之虞。近代医家秦伯未结合王氏治肝三十法总结提炼出治肝十六法,在治肝气上提出疏肝、散肝、化肝三个方面。岳美中治肝则以补、泻、和三法概之。具体到TN的治疗上,笔者认为,治病求本,肝用在气,肝气自郁则理气解郁,肝络郁滞则通络开郁,使气畅络通,为解除肝气郁滞之第一要务。
4.1.1 理气解郁,虚实兼顾 TN患者症见颈前肿大,弥漫对称,质软光滑,自觉颈胸及胁肋部胀满不适,情绪欠佳,超声多提示为囊性结节者,以气郁为主,治以疏肝理气。方宜四逆散、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为基础化裁,疏肝行气,解郁散结。具体用药以柴胡、枳壳、郁金、茯苓、香附等为基础。以柴胡之升,疏肝木而从其性;枳壳之降,利气机以散其滞;郁金、香附气血同调,解郁散结以行肝经之滞;茯苓善治结气而通利三焦,使全身气机之通路畅达。在这一时期,应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以党参、白术、茯苓、法半夏、化橘红等药取六君子汤之意,健运脾气,杜痰之源。气有余便是火,若见发热、颈部疼痛、烦躁多汗、性急易怒、舌红苔黄、脉弦数等症为气郁化火,可加丹皮、栀子、牛蒡子、生石膏、连翘、蒲公英、夏枯草等药清肝泻火,化痰散结。另外,《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若不见热象,而见患者情绪低迷,胆怯易惊、疲乏甚、有麻木感等症时,要兼顾其肝气虚损,补泻兼施。宜白术、人参、生姜、杜仲、天麻、细辛等药扶正益气以使肝用有源。而不可囿于“肝脏无补”之旧论。
4.1.2 通络开郁,痰瘀并除 吴鞠通论治肝病时言:“初病在肝郁,久病入络。” TN患者症见颈前肿块,按之较硬或有结节,舌见瘀斑,脉细涩时,超声提示结节多为囊实性或实性。此时气滞痰凝,痰瘀互结,肝经经络被痰瘀所阻,肝血郁滞。其治正如王氏“治肝三十法”中云:“如疏肝不应,营起痹窒,脉络瘀阻,宜兼通血络。”治宜活血通络,化痰散结。宜用当归、川芎、赤芍、丹参、鸡血藤、月季花等药活血行气,以通经络;王清任《医林改错》曰:“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故用红花、桃仁、泽兰、茺蔚子、莪术、王不留行等进一步去除其内瘀血。痰湿凝结,药以法半夏、天南星、白芥子、皂角刺、浙贝母、猫爪草、夏枯草等化痰散结。若痰瘀搏结,结节较硬者,可加玄参、鳖甲、牡蛎等软坚散结药物以增消散之功。唯有使肝气所行之道路通畅、内无物阻,方可达所调之肝气升降出入有序,肝用自如而郁开结散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现代数据挖掘的研究表明,古代医家多提倡以海藻、昆布类咸寒软坚类药物治疗瘿病[16]。海藻、昆布性味苦咸寒,软坚散结之功颇峻,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二者含有大量的碘。自1996年中国施行全民食盐含碘后,多项调查显示,过量的碘摄入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碘过量也是TN的诱发因素之一[17-19]。古代医家提倡咸寒软坚散结类药物治疗瘿病应与当时地区性碘缺乏不无相关。故在临床治疗上应斟酌慎用,必以疏肝理气通络为先。
4.2 护肝之体——体用结合,补泻兼施为治疗TN的次要治法
《临证指南医案·肝风篇》华岫云按:“故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首次提出肝脏体阴用阳之说。阐述了在正常生理下,肝藏血,血养肝,体得柔而用则刚;肝疏泄,血归肝,用行刚则体方柔的并济关系。肝之体用相辅相成,顾护肝体、刚柔并济对TN患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4.2.1 补养肝血,心肾同调 TN一病,缓起渐深,日久瘀血内阻于络,旧血日耗,新血难生,以致肝血亏虚,暗耗肾水,伤肝木之根。体无以养,则用更难伸。且该病初时在郁,多以芳香辛燥类药物调达木性,易伤肝血。TN患者症见面目、爪甲不荣,头晕目昏时,治宜补养肝血,充实肝体,以资肝用。论补肝,《金匮要略》中“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以调之”实为补肝理论之始祖。然至清代尤怡评其“后人不察肝病缓中之理,谬执肝先入脾之语,遂略酸与焦苦,而独于甘味曲穷其说”而提倡“肝虚直补本宫”之说。近代医家秦伯未[20]基于《金匮要略》中补肝理论及《内经》中“肝欲酸”“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泄之”等观点提出:“补肝用酸味,疏肝用辛味,清肝用苦味的基本治肝法则。”结合以上补肝理论及TN郁滞的病理特点,用药当以酸苦之味化生阴血,直补肝脏为主,而不可独用甘缓、黏腻之味,以防病邪胶着。以补血、和血通用之四物汤、逍遥散、酸枣仁汤为基础,去味甘滋腻之熟地,少用白芍,酌情加入牛膝、续断等调血和脉之品,补益肝血。取“有形之血不可速生,必赖以气而得生”之意,酌加黄芪、党参益气补血。另按五行生克,肾为肝母,心为肝子。肝血亏虚,当以母生子养。药宜山茱萸、五味子酸甘以滋肾水,远志、茯神苦甘以养心神,酸枣仁、柏子仁补血安神而达心肾同调之效。切不可见肝虚损则立即以厚味滋补肝阴,刘渡舟[21]曾在《肝病证治概要》中讲:“过去局限于将肝虚证指为肝阴不足,导致概念不全面,任何一脏都有阴阳气血不足的病症,肝脏也不例外。”肝血虚与肝阴虚当分而论之,以防过于滋补而使邪胶着。
4.2.2 滋润肝阴,阴阳并补 随着TN病情的迁延,肝血不足进一步发展为肝阴亏耗,肝之阴精不足,肝中所郁阳气失潜,亢而化火,虚火内扰。症见咽干口燥、心悸不宁、少寐烦躁、潮热盗汗、倦怠乏力、脉弦细数等。治宜滋养肝阴,去除虚火。王旭高补肝阴喜用地黄、白芍、乌梅;叶桂之师王子接在其所著的《降雪园古方选注》中载补肝汤言:“桃仁、柏子仁辛润,以补肝阴。”具体到TN一病,滋补之味多厚腻碍气,补肝阴之法应在疏肝理气的基础上酌情加用。以熟地、白芍、乌梅等药,酸甘化阴;桃仁、柏子仁辛以理气,润以滋阴。除此之外,清代名家叶天士在温病学勃兴的时代背景下,深受滋阴派大家朱丹溪的影响,提出了以肝脏体阴而用阳为核心的肝阴理论[22]。在治疗上强调乙癸同源,肝肾同补以滋水涵木,使肝体得护。在用药上常选用制首乌、生熟地、枸杞、肉苁蓉、石斛之类填补下焦肝肾之阴。对于虚损较深者,叶氏喜投血肉有情之品,化裁使用大补阴丸、复脉汤、地黄饮子等方以补肝肾之阴,留存阴液。在TN的治疗上,此法可用于TN放、化疗后或射频消融术后或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的患者。临床研究表明此类患者肝脏体用两伤,可见肝郁气滞、气阴两虚乃至阴损及阳而脾肾阳虚之证[23]。在上述滋阴药物的基础上,佐以鹿角胶、龟胶、鳖甲等血肉有情之品,填补肝肾之精,滋阴潜阳。然“阴药呆钝”,且临床上此类患者常阴损及阳,阴阳两虚。治宜阴阳兼顾,以达“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生而源泉不竭”之效。可予六味地黄丸化裁以求阴阳兼顾。如周岱翰教授以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甲状腺癌术后需长期服用甲状腺素片,或经放射性碘治疗后肝肾阴虚证患者,可获宏效[24]。另如,陈如泉教授[25]运用沙参麦冬汤合二至丸化裁治疗甲状腺癌术后气阴两虚患者收效良好;朱永康教授[26]以生脉散和右归丸加减治疗甲状腺癌术后患者颇有验效。其治则皆从此类思维出发,顾护肝体,重视养阴,而善于阴阳并调,以期恢复肝用,体用平衡,则其症可除。
5 分析与展望
综上所述,从疏肝解郁论治TN既具有中医传统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性,同时又符合现代临床研究的可行性。肝气郁结的病机贯穿了整个TN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以调肝用和护肝体为原则的治疗大法,确实能够为临床TN的治疗和研究提供新的科研思路和方法。虽然当前西医在手术治疗及甲状腺激素的使用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临床疗效,但对于不符合手术指征又有临床症状困扰及手术后甲状腺功能需要恢复的患者而言毫无裨益。并且其可能造成需要终身甲状腺激素代替治疗等副作用及复发率高等缺点不容忽视。结合本病有良恶性病理区分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医的优势更多的是在良性且未达手术指征的TN的消散、恶性结节术后缓解临床症状、防止复发以及甲状腺功能的恢复、减轻西药不良反应及增效等方面上。中医凭借其特有的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方法,通过动态全面的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旨在从根本上改善机体郁滞的内在环境,重视治本,在调畅肝脏的过程中使TN渐消缓散。未来中医药如何做到预防TN的发生、恶变及复发将会成为治疗的重中之重,而从疏肝解郁出发论治TN,防治结合或可成为新的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