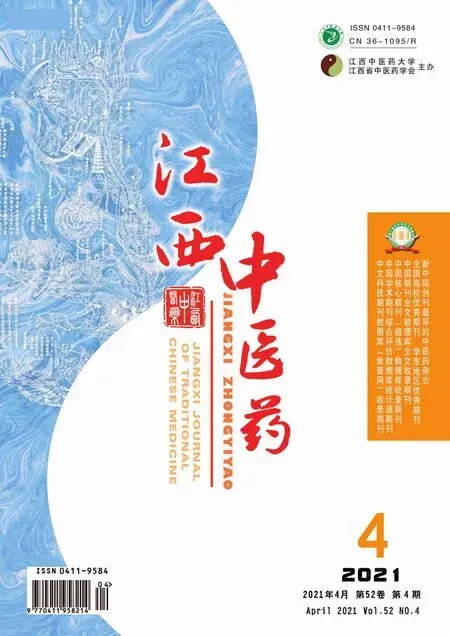李东垣“阴火”论观点临床运用浅析
★顾大伟(余姚市牟山镇卫生院 浙江 余姚 315456)
1 “阴火”的病因病机
《脾胃论》是李东垣的主要论著之一。李氏根据《黄帝内经》中“人以水谷为本”的观点,强调补益脾胃的重要性。人禀先天之精而生,赖后天水谷以养,人体脏腑精血来源于先天,滋生给养于后天,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张仲景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胃论》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详细论述了“阴火”。李氏认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提出益元阳与降阴火的辨证关系。“阴火”乃脾胃气衰,元气不足,得以乘其土位,创制了“甘温除大热”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阴火”的病因为饮食伤胃,劳倦伤脾,七情伤气。该火因热自内生故谓之“阴火”。《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云:“故夫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1]由此可见,元气与阴火是有矛盾关系的。元气升发温煦心肺,下济肝肾。五脏之中,肝主升发,肺主肃降,肝随脾升,胆随胃降;心居上焦,肾居下焦,肾水上承,心火下降,水火既济,心肾相交;气机运行,全凭升降,而脾胃为升降之枢纽,推动了脏腑精气的循环化生。东垣认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之气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他阐述了元气虽为“五脏六腑之本”,但有赖于后天脾胃的滋养。“阴火”一论,后世有医家理解为“阴虚火旺”之意,也有认为其是“虚阳上越”,可谓见仁见智。刘炳凡在其《脾胃论真铨》中提出,此火不是温煦机体新陈代谢的“少火”,“少火”与元气互相资生。而离位的“阴火”,实为“食气的壮火”,故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称其为“元气之贼”[2]。
2 “阴火”的临床表现、治则及代表方剂
《灵枢·五邪篇》云:“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胃为阳土,喜润,以通为用;脾为阴土,喜燥,以升为补。阳有余,则胃气有余,相对而言,则脾阴不足,阳有余化为热中,热主化谷,则善饥。清代医家叶天士,对脾胃学说进行发挥与创新,他提出“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治脾可宗东垣甘温升发,治胃则宜甘润通降”。李东垣指出:“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阴火上冲,则气高而喘,为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这里李氏认为下焦“阴火”上冲,侵害脾胃,脾胃虚不能护养肺气,而“阴火”刑金,所以表现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肺主表,肺气既伤,体表空虚,所以表现为头痛、口渴、脉洪。此处的发热症状,类似于白虎汤证,但李氏指出:“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这是白虎汤证所不能见到的。此处抓住了该病的本质“皆因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李氏从而得出:“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立补中益气汤治“脾证”始得之证,益气升阳,甘温除热则自愈。
补中益气汤治法是健脾升阳,以降阴火,既是甘温除热法,又是顺应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调畅之法。“脾证”辨证的重点在于脾胃气虚症状,如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倦怠嗜卧,四肢不收。同时兼顾“阴火”亢盛的症状,如火热上行,独燎其面,气高而喘,身热而烦。《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烦劳则张”,又如《灵枢·终始篇》云:“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可饮以至剂。”基于此,《黄帝内经》高度概括了脾胃气虚发生、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相应的治则。
3 临床应用
3.1 益气升阳治久病发热案 发热一症,产生的原因很多,大致而言,可分为外感、内伤。外感一类,有表热、表邪入里化热;内伤之中,有常见的气虚发热、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有痰、食、血、气等郁而发热;有阴盛格阳的假热。笔者根据李氏“阴火”论的启发,临证遇到脾胃气虚的发热患者,宗其要旨,灵活施治,常能应手获效,现举病案以证之。
余某,男,56岁,农民。2012年10月12日初诊。患者2011年5月经上海长征医院诊断为“胰腺癌”,术后致脾脓肿,后予脾脏引流,“泰能、奥硝唑”抗感染治疗,前后住院4次,但仍身热不退。每日中午前后发热,体温波动于38.5 ℃~39 ℃之间。现见患者面色少华,形体消瘦,神疲体倦,时有胃脘痞闷,纳差,动则气短,语声低弱,大便稍干,舌体胖大有齿痕,舌质淡,苔白,脉细数。分析此证,患者术后倦怠,言语声低,面色无华,舌质淡,是脾胃气衰所致,故而辨证为气虚发热,处方:生黄芪30 g,生晒参9 g,炒白术12 g,当归12 g,升麻6 g,柴胡15 g,陈皮6 g,甘草10 g,黄芩15 g,青蒿15 g,嘱家属自备红枣7枚,生姜3片入煎,5剂。二诊,患者告知药后3日,午后身热渐退,最高体温37.8 ℃,纳食有味,精神稍好,效不更方,5剂。后其子女欣喜告知患者发热已除,考虑患者脾虚内伤,继已归脾汤调养2周。患者此后近半年未出现发热症状。
按语:发热一症,特别是高热病人,首先考虑外感、实热证,对于久热不退的病证,临床中亦有养阴清热法。该医案属于“气虚发热”,此乃脾胃气虚,阴火上乘所致。《素问·调经论》诉:“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这是各种内伤导致发热的必要条件,经方大家刘渡舟先生认为“阴”在这里理解为“内”,此乃内伤气虚发热之症,李东垣将此病理机制高度概括为“阴火上乘土位”。他提出:“日高之后,阳气将旺,复热如火,乃阴阳气血俱不足,故或热厥而阴虚,或寒厥而气虚。”该案中患者发热正是日高之后,补中益气汤中“甘温”的药物为人参、黄芪、甘草,三者补益脾肺,白术燥湿健脾,陈皮理气畅脾,升麻、柴胡升举清阳,当归和阴养血,姜枣调和营卫,加强黄芪固表卫外的功能。诸药协和,补中益气,调补脾胃,并能益卫固表,体现《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治则。当然,对于虚实夹杂证,除可采用补中益气汤为基本方剂以外,还应根据中气虚弱之轻重,累及脏腑之多寡,兼夹证之有无而辨证论治。亦可选用当归补血汤、归脾汤、桂甘龙牡汤、四君子汤等进行治疗。
3.2 升脾阳、降阴火治内痔出血案 李氏在《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中提出:“脾胃既为阴火所乘,谷气闭塞而下流,即清气不升,九窍为之不利。”“九窍”:两眼、两耳、鼻两孔、口、前后二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脾胃元气充盈,升降有司,倘若脾胃功能活动相对的平衡遭到破坏,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人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病证。笔者在临床中治疗了多例脾虚下陷的便秘和痔疮患者,均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收功,今抛砖引玉,以医案证之。
李某,女,68岁,农民。2018年7月28日初诊。患者2年前因“内痔”手术治疗,术后总感肛门坠胀。3天前因劳累后出现肛门有物脱出,便纸染血,就诊市级医院肛肠科,西医诊断为“内痔Ⅱ期”,建议住院手术治疗。时值盛夏,恰逢水稻收割之际,患者因故就诊中医。病来坐卧不适,大便3日未解。面色少华,形体偏瘦,舌质淡,边有齿痕。苔薄黄腻,脉细弱。证属脾虚气陷。治法:补中益气,兼清内热。处方:生黄芪30 g,西党参15 g,炒白术12 g,当归12 g,升麻9 g,白桔梗9 g,柴胡9 g,陈皮6 g,甘草6 g,玄参12 g,黄柏10 g,黄芩10 g,制大黄10 g,川楝子10 g,大蓟15 g,小蓟15 g,仙鹤草30 g,侧柏炭12 g,5剂。嘱大便后予第三次药汁温水坐浴,1天2次;5天后患者复诊,欣喜告知服药后,大便每日1次,便纸少许染血,肛门脱出物不再出现,尚感乏力、肛门坠胀。原方去大、小蓟再服5剂,数月后患者因感冒就诊,得知服药10剂,诸症悉愈。随访1年余未见复发。
按语:《脾胃论》中补脾胃泻阴火的升阳汤、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以及清暑益气汤,都体现了在益元阳、升阳气的前提下注意了降阴火的问题。如补脾胃泻阴火的升阳汤,李氏组方中在辛甘升散中使用芩、连、石膏以泻阴火。笔者师其意而扩其用,临床中常常用其治疗脾虚兼有内热的患者。本案患者年老体弱,患痔疮后手术治疗,耗气伤血。暑伏天气炎热,加之忙于农务,故而旧疾再犯。知其中气亏虚,加之劳倦内伤重耗其气,气虚下陷,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湿热内生并乘虚下注肛门,局部气滞血瘀,脉络不通,故痔疮脱出肿痛。黄柏、黄芩清热泻火,黄柏又有解毒疗疮之功,长于清下焦湿热,制大黄泻火通便,佐以川楝子理气止痛,本方补中益气,兼清内热,药证合拍,故能药到病除。
4 总结
元气与阴火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两者更是升降相因的。上乘阳位的“阴火”是“食气”的,下安其位的“少火”是“生气”的。元气在生理的情况下是维持脏腑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它不断的靠后天脾胃的滋养而发挥功能,同时游走于各脏腑之中,在脾胃,则助其化为精微,上助于肺脉,化而为血,以奉生身。饮食、劳倦、七情等因素,致使脾气下陷,势必导致“阴火”上升而乘其土位。心为君主之官,心不主令,相火则代君行令,故而出现一系列阴火上冲的征象,然而此火非实火和阴虚之火,治疗上宜补益元阳,以降阴火。元阳复,则阴火自然潜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