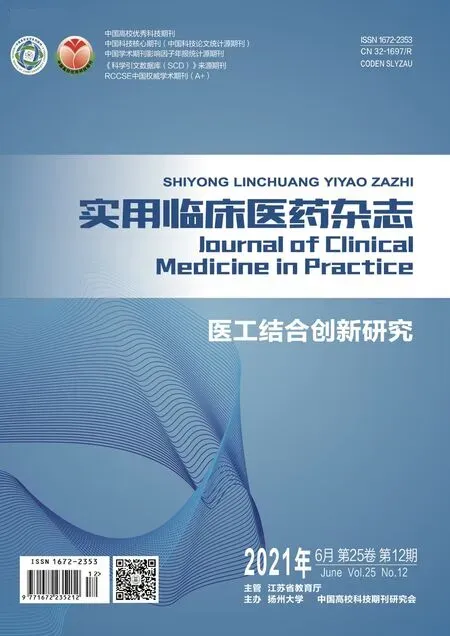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后不同时机应用唑来膦酸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疗效
杨海澔, 肖 睿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骨二科,四川 宜宾,644000)
骨质疏松(OP)常发生于绝经后女性和老年男性,特征为全身不同程度的骨密度降低及骨组织微结构改变,导致骨脆性增加,使非重力创伤下骨折风险增高[1]。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OVCFs)是指由OP引起的椎体骨密度(BMD)和骨强度降低,在轻微外力甚至没有明显外力的作用下即发生的骨折[2]。OVCFs患者多为胸腰段受累,可出现胸/腰背部疼痛及下肢神经症状等,并影响心、肺及胃肠功能,部分患者可致残[3-4]。椎体后凸成形术(PKP)是治疗OVCFs常用的微创手术方法[5]。唑来膦酸是第3代双膦酸盐(BPs)类药物,可有效抑制骨吸收,增加骨密度,有效降低椎体再发生骨折的风险[6], 但术后如何选择最佳用药时机,仍无定论。本研究探讨PKP后不同时机应用唑来膦酸治疗OVCFs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1月—2019年1月本院骨二科收治的80例老年OVCFs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年龄≥60岁; 被诊断为骨质疏松症者; 经双能X线骨密度仪测定BMD, T值≤-2.5者; 有明确病史,伴腰背部疼痛,活动后加重,并伴有肋间痛症状,相应椎体节段棘突有压痛或叩击痛,不伴脊髓及神经根受压症状和体征者; 经X线或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实为新鲜椎体压缩骨折者,且伤椎后壁完整,脊髓无明显受压; 既往未进行过抗骨质疏松治疗者。排除标准: 椎体爆裂性骨折者; 合并其他部位骨折者; 合并恶性肿瘤或骨转移瘤者; 合并肌酐清除率低于35 mL/min的肾功能不全者; 合并椎管内占位病变、代谢性骨病、强直性脊柱炎等者; 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者; 有抗骨质疏松治疗史或脊椎手术史者; 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或器官功能不全者。样本含量的估算: 采用成组设计两均数的样本含量估计的计算公式:n1=n2=2[(Zɑ/2+Zβ)σ/δ]2,δ为容许误差,σ为样本标准差。根据已报道实验结果,检验效能(1-β)取0.90,β=0.10, 取双侧检验α=0.05, 查表Zɑ/2=Z0.05/2=1.96,Zβ=Z0.10=1.28。本研究中2组样本例数相同,按公式计算,每组至少31例,共需要纳入62例,按15%的失访率估算需总共纳入72例,最终本研究将总样本量扩大为80例,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40例。所有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2组性别、年龄、病程、骨折部位、甲状旁腺素(PTH)、血清25-羟基维生素D(25OHD)、空腹血糖(FBG)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组术前一般资料比较
1.2 方法
1.2.1 PKP方法: 患者取俯卧位,在C形臂X线机透视下确定伤椎并进行体表定位,做好标记后,常规消毒铺巾。用2%利多卡因进行局部浸润麻醉后,在标记处做长约5 mm的纵向小切口,均为单侧穿刺,选择正位透视椎弓根影外上缘处作为进针点(正位10点钟或2点钟方向),置入穿刺针,在C形臂透视协助下,穿刺针针尖在侧位透视下达椎体前1/3, 正位透视下接近棘突中线。建立工作通道,置入工作套管后,置入球囊,适当加压使球囊撑起压缩椎体,透视见椎体骨折复位良好,取出球囊。调配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注入骨水泥推进器。在C形臂监测下,将2~5 mL骨水泥用骨水泥推进器注入椎体,待骨水泥凝固后,退出推进器及工作套管。术毕敷料覆盖伤口。术中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观察其双下肢感觉和运动情况。患者术后24 h佩戴支具保护后下床行走。
1.2.2 抗骨质疏松治疗:观察组在PKP后第3天静脉滴注唑来膦酸注射液(商品名: 依固; 生产厂家: 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113138)5 mg, 1次/年,静脉输注时间不少于15 min, 给药前充分补液。对照组在PKP后1月使用唑来膦酸,使用方法及剂量同观察组。2组均同时口服碳酸钙D3片(商品名: 钙尔奇; 生产厂家: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10950029)1片/次, 2次/d; 骨化三醇胶丸[商品名: 罗盖全; 生产厂家: R.P.Scherer GmbH & Co.KG(德国);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J20150011]口服, 0.25 μg/次, 2次/d, 均规律服药1年,用药过程中定期监测血钙、血磷及肝、肾功能。
1.3 观察指标
PKP前以及PKP后1(对照组使用唑来膦酸前)、3、6个月及术后1年各时点进行随访,并完善相关检查: ① 采用X线检查测量治疗前后伤椎椎体高度和局部椎体后凸Cobb角变化,评价压缩骨折椎体恢复情况; ②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胸腰背部疼痛情况; ③ 采用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评价日常功能情况; ④ 采用双能X线骨密度检测仪测定腰椎及髋部BMD; ⑤ 检测骨转换生化指标(BTMS): 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β-Ⅰ型胶原C-末端肽交联(β-CTX); ⑥ 记录2组椎体压缩骨折再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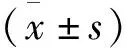
2 结 果
2.1 2组VAS评分比较
2组术前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组术后1、3、6个月及术后1年VAS评分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1、3个月,观察组VA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2组术前、术后 VAS 评分比较 分
2.2 2组ODI评分比较
2组术前OD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组术后1、3、6个月及术后1年ODI评分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1、3个月,观察组ODI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2组ODI评分比较 分
2.3 2组伤椎椎体高度比较
2组术前伤椎椎体高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组术后1、3、6个月及术后1年伤椎椎体高度均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1、3、6个月及术后1年,观察组伤椎椎体高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2组伤椎椎体高度比较 mm
2.4 2组局部椎体后凸Cobb角比较
2组术前局部椎体后凸Cobb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组术后1、3、6个月及术后1年局部椎体后凸Cobb角均小于术前(P<0.05); 术后1、3、6个月及术后1年,观察组局部椎体后凸Cobb角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5 2组局部椎体后凸Cobb角比较 °
2.5 2组腰椎及髋部BMD T值比较
2组术前腰椎及髋部BMD T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组术后6个月及术后1年腰椎及髋部BMD T值均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6个月及术后1年,观察组腰椎及髋部BMD T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6 2组腰椎及髋部BMD T值比较
2.6 2组BTMS比较
2组术前PINP及β-CTX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组术后6个月及术后1年PINP及β-CTX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6个月及术后1年,观察组PINP及β-CTX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7。

表7 2组术前、术后PINP、β-CTX比较 μg/L
2.7 2组不良反应及再骨折发生率比较
2组随访时间为12~19个月。2组均未出现症状性骨水泥渗漏、术后感染、脊髓神经损伤、肺栓塞等并发症。应用唑来膦酸注射液后,部分患者出现急性期反应(发热、恶心、头痛、肌痛和关节痛等流感样症状),观察组9例(22.5%)与对照组8例(20.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予以非甾体类抗炎药对症处理, 3 d左右均完全缓解。2组未发生下颌骨坏死、肾损害、巩膜炎、葡萄膜炎、视神经炎等并发症。1年随访期内,观察组1例(2.5%)出现椎体再骨折,与对照组2例(5.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例患者均要求药物保守治疗,未再行手术治疗。
3 讨 论
性别、高龄是OP的独立危险因素,据统计,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患有OP[7]。OP最严重的并发症是骨质疏松性骨折,其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且女性比男性的发病率高,骨质疏松性骨折最常见的类型为OVCFs。研究[8]表明,老年疼痛性OVCFs患者早期应用经皮椎体强化术(PVA)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且能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病死率。PKP属于PVA的一种,可通过球囊扩张复位部分骨折椎体,恢复压缩椎体的高度,并填充骨水泥加固椎体,改善脊柱后凸畸形。PKP能快速缓解疼痛并维持椎体稳定,较经皮椎体成形术骨水泥渗漏更低,成为治疗伴后凸畸形OVCFs微创手术的首选方案[8]。但有研究[9]认为, PKP后增加了相应椎体的刚度,会改变邻近节段椎体的力学传递方式及力学特性,导致邻近椎体载荷加重,增高邻近节段骨折的风险。相关报道[10]显示, PKP后邻近椎体新发骨折发生率可达12.5%~36.8%。因此, OVCFs的基础病因是OP, 手术并不能降低再骨折的风险,抗骨质疏松治疗是治疗OVCFs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目前, BPs类药物已成为临床防治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一线药物,可使脊柱骨折的发生率降低40%~70%[6]。唑来膦酸是第3代BPs, 可迅速分布于骨骼中,作用于骨矿化表面,通过与羟基磷灰石紧密结合阻断甲羟戊酸通路,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及合成,加速破骨细胞的凋亡,增加BMD, 从而起到抗骨质疏松的作用[11]。研究[12]证实,唑来膦酸联合PKP在提高BMD、降低椎体再骨折发生率、改善患者远期临床症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MORIWAKI K等[13]研究表明,治疗OP时,患者使用唑来膦酸比阿仑膦酸钠具有更高的依从性,而且更经济。骨折术后常规剂量的唑来膦酸不会影响骨的重建和矿化,不会导致骨折延迟愈合,还有利于增加骨折手术内固定物的稳定性,但如何选择最佳的用药时机,仍需进一步研究。
AMANAT N等[14]对建立的闭合性骨折大鼠模型于骨折后第0、1或2周使用单次剂量的唑来膦酸,均能显著增加骨折部位的BMD和愈合骨折的强度,但骨折后1或 2周给药比断裂时给药效果更佳。一项研究[15]显示,术后2~12周注射唑来膦酸可显著增加全髋BMD、减少再骨折的发生,并可降低伤后死亡率。但另一荟萃分析[16]显示,术后立即给予BPs的抗吸收效应会对随后的骨折发生率产生积极的影响。李季等[17]研究表明,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PVP)联合唑来膦酸治疗OVCFs, 可恢复椎体高度,缓解疼痛,显著提高骨密度,改善骨代谢,但术后第2天使用唑来膦酸与术后1个月使用唑来膦酸相比,改善效果更佳。但也有研究[18]显示,高龄患者肱骨骨折后使用BPs可能增高骨折不愈合风险。考虑唑来膦酸使用后可能出现发热、头痛、恶心、关节痛等症状,为避免与手术本身造成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相重合,故本研究观察组选在术后第3天使用唑来膦酸。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年OVCFs患者行PKP后使用唑来膦酸抗骨质疏松治疗,不仅可减轻疼痛,改善相关骨功能,恢复椎体高度及校正后凸角度,还能显著提高BMD, 改善骨代谢,降低椎体再骨折发生率,但术后早期使用唑来膦酸较术后1、6个月及术后1年的BMD更高, PINP及β-CTX更低。本研究结果提示,老年OVCFs患者行PKP后尽早使用唑来膦酸抗骨质疏松治疗,能更好地抑制破骨细胞活性、降低骨转换、减少骨吸收及增加骨量。
综上所述,老年OVCFs患者行PKP后尽早使用唑来膦酸抗骨质疏松治疗,可减轻患者疼痛,恢复椎体高度及校正后凸角度,且在提高BMD、改善骨代谢方面更具优势。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可能导致结果偏倚,还需展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