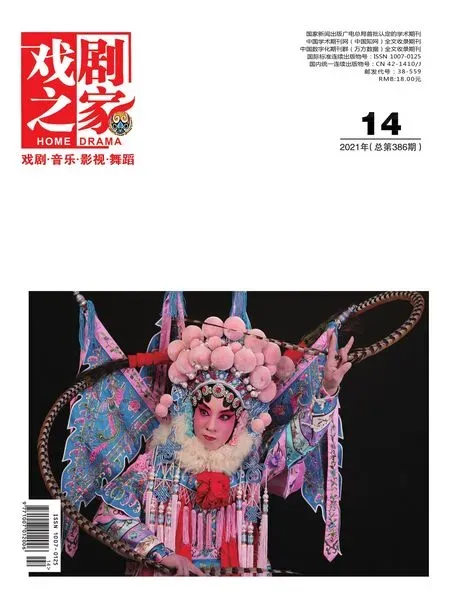浅析杂剧《苎萝梦》的主题承载
——用金批《西厢记》的叙事理论进行阐释
李国翠
(烟台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5)
【关键字】《苎萝梦》;陈栋;思想主题;“寄托笔墨”;“羯鼓解秽”
陈栋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戏曲作家,共留有杂剧《苎萝梦》《维扬梦》《紫姑神》三部,这为处于衰落期的清代杂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吴梅先生就曾指出杂剧《苎萝梦》“皆精心结撰,直入元人之室”,认为其是陈栋杂剧的代表之作,而且还评价道“因示梦补欢,其事亦新。四折皆旦唱,语语本色,其艳在骨”。除此之外,杂剧《苎萝梦》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思想情感,它并非是一般的才子佳人戏,而是以作家的人生经历为依据、寓有深意的有为之作。联系陈栋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年遭际、思想性格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苎萝梦》虽写西施与吴王转世者王轩梦结连理、了结前恨,以及郭凝素艳羡王轩并效仿其题诗浣纱石,以期遇西施却被东施之魂羞辱之事,但是在深层次却寄予了作家功业未就的补偿心理、理想的人格形象以及对社会现状的观照。
本文所依凭的叙事理论出自《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此书被视为“叙事理论体系”的代表。金圣叹在评点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情感意蕴的赏评,除此之外,还总结出了一系列戏剧叙事的技巧和方法,其中就包括本文所使用的“寄托笔墨”法和“羯鼓解秽”法。从杂剧《苎萝梦》中,我们就能看出陈栋对金批《西厢记》中的“寄托笔墨”法和“羯鼓解秽”法有着熟练的使用,本文主要是凭借这两种叙事方法,对杂剧《苎萝梦》的主题思想进行阐释和挖掘,来揭示杂剧《苎萝梦》之所以被众多戏曲家所称赞的原因,并对以后读者的阅读进行一个浅要的指导。
一、“寄托笔墨”法
在金评《西厢记》中,金圣叹认为叙事的动机是“如此,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彼岂不悟此一书中所撰为古人名色,如君瑞、莺莺、红娘、白马,皆是我一人心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无极,醉梦恐漏,而至是终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之人之事,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惊艳》总评),也就是要借剧中的历史人物和“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对于这种创作意图,尤侗也曾自言道:“古之人不得志于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既又变为词曲,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尽致而后已。”在杂剧《苎萝梦》中,陈栋借吴王转世者王轩的遭际自况,抒发了自己满腹才学的自信进取精神以及功业未就的慨叹,又通过与西施梦结连理的编织虚构,消解了一些自己在仕途追求上的遗憾。
陈栋弟子周之琦曾在《<北泾草堂集>序》中对恩师陈栋的人生经历有过这样的描述:“中间先生客怀、客许、客洛,又以试事往来南北……先生于学靡弗通,襟抱简远,有魏晋间意。然恒苦疢疾,朝芪暮术,饔飨俱为。制举文人不屑屑于有司之绳尺,以是屡困省试,卒赍志而没。”由此可知,陈栋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疾病缠身、功名之途不顺,怀抱着未遂的志愿而死。陈栋心中的郁郁情绪在杂剧《苎萝梦》中有着明显的体现,自己的个人境遇与内心感怀与剧中的王轩相似,便借王轩以自喻,将胸中的委屈与不得意倾吐出来。在杂剧《苎萝梦》中,东施评价王轩是“天边文星堕”,由楔子中王轩的出场自述便可看出他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真文士:“小生王轩是也,一生落拓,四壁萧条。若论起俺的才学,即如目下所重宏词、书判、帖括、明经这几科,俺那一件应付不来,只是时运未至,到了二十多岁,还把领青衿披在身上。”除此之外,我们从西施的唱词中也可以看到王轩气质非凡,有较高的气度:“则见他,拂青霄,气似虹,步苍苔,形似虎。依然是,江东伯主旧规模,怎眼乜斜盼不上捧心憔悴女。”王轩与作家陈栋都是落魄穷困、潦倒失意的,却依然有着真才实学之人的非凡气质与积极进取的情怀,此时作家是借王轩来“浇我块垒”,将其怀才不遇的苦闷都倾注到王轩身上。
除此之外,杂剧《苎萝梦》中的王轩是一个功名未就、旅途困顿的文士,在楔子中王轩自述道:“争奈家无长物、瓶少储粮,少不得就要拔剑出门、糊口四方。今日乃是寒食,别人家都要安排香车宝马,预备着踏青,我独自一个守着几本破书,也觉得气闷不过,特地叫了一只小舟,来这苎萝村里访访西施的遗迹。”作家陈栋也如王轩一般,在旅途寂寞之余,期盼与红颜美人相遇相爱,希冀能功成名就过上富贵生活,陈栋对情爱的渴望与对前途的担忧聚焦在王轩的梦中,遂生出王轩与西施在梦中相会、再续前缘,从而得以成就才子佳人的佳话。吴王转世者王轩与西施梦中相见,唱词里极写王轩昔日的富贵生活:“(末)那壁厢金壶玉碗、雁瑟鸾笙,好不富贵。(旦)莽兀兀金兼玉,玑琤琤笙共竽。(末)敢怕还有车如流水马如龙哩。(旦)扑剌剌马和车,都是你书生当年唾馀。”又如西施唱词里对吴宫生活的描绘:“【红绣鞋】这是采香径,烟光荡漾。这是玩月池,水色汪洋。这是琴台花,影夜芬芳。一丛那金戈凋玉树,谁还向绣榻问名香。您不见碧萋萋芳草长。”西施的唱词缠绵悱恻,不仅可见西施对吴王念念不忘之情,及西施感情的忠贞,而且用几乎白描的手法,细致地把当年吴宫的景色、吴宫奢侈的生活一一展现出来,其中也蕴含着作家对于功成名就、金榜题名后的理想生活的愿景。
在以下的唱词里,西施大胆地抒发自己对吴王的想念和爱慕,可见其“不更二夫”的忠贞:“【双雁儿】擘绛桃、滋甘露、进醍醐,可抵得劝金樽、捧玉壶,这些时,翠帐红茵怕孤处。妾有一诗与君听者,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昔日此心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此时的西施不仅用诗句来表达自己对吴王感情的忠贞,而且通过大胆而热烈的唱词来抒发自己对吴王的想念,对感情忠贞不二的西施是作家陈栋心目中的理想佳人形象。值得指出的是,“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是古代文人们最高的人生理想之二,然而当这些理想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时,就转而去幻想与梦境中寻求补偿,以倾泻自己内心的抑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显然作家陈栋就是在杂剧《苎萝梦》中寄予了在现实中寻求不到的仕途与佳人理想。
总而言之,杂剧《苎萝梦》中的王轩和西施是作家心目中理想的真文人和真佳人,他们身上寄予了作家陈栋的理想人格形象。《苎萝梦》一剧中的西施不只是“千古第一佳人”,而且还有着“烈女不更二夫”的贞洁,她才貌双全,虽位列仙班但仍然对吴王念念不忘,想尽办法在梦中与吴王转世者王轩再续前缘。而王轩更是作家陈栋的代言人,二人同样是时运未济,却仍有着真才实学和对高洁品性的坚守。
二、“羯鼓解秽”法
金圣叹用唐明皇听曲而不乐便自击羯鼓开怀的事例来引出“羯鼓解秽”之法,并将其用于文学创作:“忽悟文章旧有解秽之法,因而放死笔、捉活笔,斗然从他递书人身上凭空撰出一莽惠明,以一发泄其半日笔尖呜呜咽咽之积闷。”(《寺警》总评)作为叙事技法的“羯鼓解秽”,是指在叙述事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出人意料的“奇笔”,借突转的文势来扭转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改变作品的气氛,注意叙事节奏的“冷热相济”,从而使读者在郁闷、沉寂的精神状态下转向愉悦、轻快的心境,给其带来耳目一新甚至惊心动魄的感觉。在杂剧《苎萝梦》中,前三折西施的旦本戏整个基调是感伤的,属于“冷”,第四折以东施为主唱,整折呈现出欢快的气氛,属于“热”。除此之外,前三折是借王轩隐晦地寄托自己的情感,而第四折中陈栋则是巧妙地借东施之口,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假文士进行酣畅淋漓的讽刺,“以一发泄其半日笔尖呜呜咽咽之积闷”。
杂剧第一折写西施“仙籍虽登,情丝未断”,对当年与吴王欢爱的光景念念不忘,使得西施整日里郁郁寡欢,难享仙家之乐,在其唱词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对于吴王的殷殷思念和对于昔日生活的美好回忆,充满着闺怨之妇的哀愁,整个感情基调基本上是哀怨的,如:“【谒金门】春寂寂,小束榴裙独立。斜日栏杆何处笛,烟围芳草碧。若个久淹消息,怪煞翠鸾千百。绛阙佩环归未得,铜驼风雨黑。”“【么篇】巫岭知何地,桃源别有天。这朝朝暮暮无人见,竟生生死死将人怨。怎来来去去由人便,便做得潜英账内影朦胧。知他在蘼芜香畔情深浅。”
第二折写西施奉旨下凡暗配王轩却一直没有机会,见王轩题诗浣纱石便觉得王轩有意于自己,求助梦神约王轩于梦中相见。这一折中,西施的情感是多种交织的,既有重回人间故地的恍然如梦之感,又有再遇情郎的欢喜与急迫,也有不能泄露天机而怕王轩不认得自己的焦虑,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整体的基调是欢喜之中夹杂着淡淡的忧愁,如唱词:“【么篇】则见他,拂青霄,气似虹,步苍苔,形似虎。依然是,江东伯主旧规模,怎眼乜斜盼不上捧心憔悴女。想我这,容颜凋残非故,便不是,转胞胎,也难认,这幅换稿美人图。”
在第三折中,转眼间便到了离别之时,西施要重返仙班。此时的西施再也按捺不住心中对王轩的难以割舍之情,满腔离别的苦语便倾泻而出,西施用大段的唱词来表现内心的不舍与留恋:“【哨遍】遥指天风浩荡,歹云头不住的排空上。相对两彷徨,怎忍教顷刻分张,自思想,想当初钗分镜破,凤只鸾孤,倒守得出凄凉况,蓦忽回头凝望,见凄凄鉴水,黯黯金门,非是我今朝环佩去遥空,不情愿并头莲再产他方。恨杀这梦中随倡,把誓海填平,盟山销广。”场面充满了伤感气氛,如果故事按照这一路线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得杂剧更加悲凄,使人读来感到更加的郁闷和感伤。
前三折主要是西施为主唱,整个下来都是感伤低沉的,然而第四折中陈栋将故事情节安排得跌宕起伏,东施的唱词语言俗白、轻松活泼,就像一声惊雷扫清了前边剧里的哀伤和沉闷,使人能从这出乎意料的转变中获得轻松的快感。除此之外,陈栋还能够畅抒其胸怀,如果说前三折是作家借王轩之口抒发内心抑郁不得志之块垒,借西施与王轩来表现自己的理想人格,那么第四折则是与前三折的故事情节、人物设置以及主题承载都截然相反的,陈栋通过“羯鼓解秽”之法,借东施之口大胆而充满激情地来表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照。
陈栋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尾声中,在其生活的年代里,经过清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国家经济取得了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的膨胀。对于文人来讲,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考取功名的压力越来越大,上行的通道越来越拥塞。于是,文人之间竞争激烈,很多假文士们纷纷采取做假文章、衣钵相传、贿赂等手段去谋求官职;而坚持操守的文人则往往没有官做。有感于这种社会现状,陈栋便在杂剧《苎萝梦》第四折中借东施之口大胆讽刺了那些沽名钓誉的假文士。作家在这里的人物安排相当巧妙,东施在郭凝素眼中是“面貌像鬼一般的”丑妇形象,而借东施之口来讽刺社会上像郭凝素一般的“假文士”,讽刺效果更加强烈,如东施的唱词:“【阿纳忽】哎,酸倈儿应不的文科囚脸儿,说甚风魔井中蛙不知天大,癞蛤蟆妄想着天鹅。【慢金盖】慢张罗风流俏哥说,起波笑得人牙儿堕,小孩儿乱写得纸涴,瞎眼人强捏着笔搓,涂鸦手硬拿将墨磨,没字碑生敲得砚破,把别人把戏移来门前,做假文章乔功课。”非常辛辣老道、粗犷豪爽,丝毫不给人留脸面,大骂郭凝素是“衣钵相传一样喽啰”“酸倈儿应不的文科囚脸儿”“做假文章乔功课”“靠祖上官装不得门面”。通过东施之魂的讽刺嘲骂,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社会上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假文士”进行了辛辣的嘲弄与批判。杂剧最后,陈栋也借东施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希冀,即“永不许痴梦人到这小江中棹兰舸”。
陈栋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鼎盛时代,既带着“康乾盛世”的余晖,又交织潜藏着各种不公的社会现实;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更是历经坎坷,落魄而不得志。从杂剧《苎萝梦》的曲词和内容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作家是融社会现实、自身经历于杂剧中,可以窥见作家笔调中暗含的丰富而深厚的情感,正如傅惜华在《清代杂剧全目》中称陈栋“所作杂剧三种,皆寄慨之词”。
——以《螳螂捕蝉》为例,谈劝说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