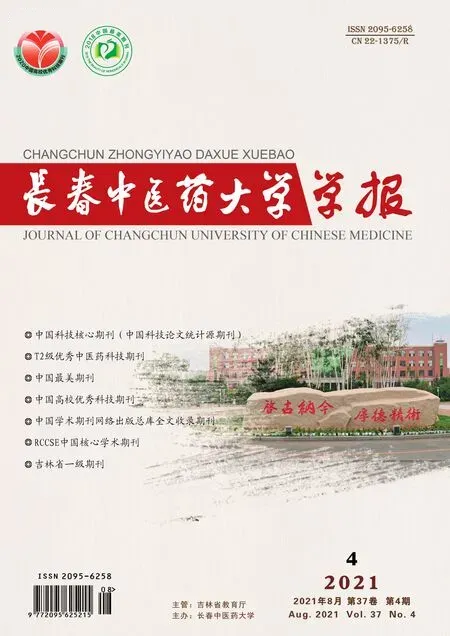齐秉慧辨治脾胃病证心法探析
李春苹,陈塑宇,汪 剑
(1.云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昆明 650500;2.云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昆明 650500)
清代医家齐秉慧,字有堂,叙州(今四川省宜宾市)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卒年不详。齐氏得喻、舒、黄三家之传,实为喻氏三传弟子。其上溯岐黄,下逮百家,深思熟虑,穷究医理,且医术达到了“治病迎刃而解,愈者十之八九”的水平。齐秉慧晚年将数十年寤寐诚求之心得,包括仲景、嘉言之蕴奥,立斋、养葵之秘旨等,阐发而成《齐氏医案》一书。《齐氏医案》卷四主要论述了后天脾胃学说及相关疾病的证治,然其辨治脾胃病的心法,则非局限于此卷,而是贯穿于全书,说理清晰,充分反映了齐氏在医学理论上独到的学术见解。本文拟从《齐氏医案》对脾胃病证的论治经验进行探析,以总结其辨治脾胃病证的心法。
1 太阴阳明,分治脾胃
齐氏推崇仲景,倡行六经辨证,认为“为病各不相同,然要不外乎六经,以六经之法按而治之。分经用药,乃千古指南,一定而不可易之法”[1]2。感慨于天宝年间,由于政乱,仲景之作湮没不传,加之《局方》盛行,致使医家鲜能分辨六经,按法治病的现状,遂在《齐氏医案》一书中将六经各绘一图,并注明某经系属某病,某病宜用某药。且齐氏得清代著名伤寒学者舒驰远先生真传,于六经定法中仿其分列经证、腑证,以用于分别病位表里与脏腑归属。其在脾胃病证的治疗过程中,重视从太阴阳明分治脾胃。
1.1 太阴经证,法当理中醒脾
舒驰远《伤寒集注·卷八》言“六经之证,未有能外太阴者,以脾为一身之主,脾气强健,何病不愈? 否则,诸法皆不验矣。”“太阴篇之法独略,非略也,散见于六经耳。”六经赖脾胃之气以斡旋,脾胃乃六经之根本。中焦如轴经气轮,气机旋转升降如常则诸证不起[2]。齐秉慧认为,人身后天水谷之精气生血,精气者,精微纯静之气,故属阴;水谷之悍气生津,悍气者,勇悍浮动之气,故属阳。血入于营,津行于卫,皆藉脾中之阳而为传布周流。若脾气不足,则其所生之血传布不尽,停蓄膈中,不能复行经络而为败浊,兼之胸中之阳不能宣布,痰血即上逆而吐也;其所生之津传布不尽者,不得复为津精,皆由胸中之阳不能宣布,则上逆胸中而为咳唾。痰血兼见,并五饮诸证,均宜大补中气,宣畅胸膈,醒脾逐饮,随饮加药,一定之法也[1]61。且齐秉慧于“足太阴脾经之图”中基于太阴病的提纲提出法主理中汤加砂仁、半夏。而由于脾失运化引起太阴见留饮、水饮、支饮、悬饮、溢饮等诸多饮证,则以温脾涤饮法治之。理脾涤饮方组成:黄芪、白术、砂仁、半夏、干姜、白蔻。此方乃理中汤化裁而来,为足太阴脾经之药,亦寓“脾居中州”之意,共奏理中醒脾之效。
1.2 阳明经病,首辨在经在腑
《黄帝内经》言:“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所以惟有下夺一法,夺其土而邪自不留耳。否则邪住腑中,漫无出路,迨耗尽津液而死也。”仲景《伤寒论》中阳明病篇提纲“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明确提出,夫阳明,胃也,阳明以胃实为证,胃实则皆下证也。然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源,多血多气之冲,乃吉凶生死之所攸关,治之尤难[3]52,不可简单地将“阳明以胃实为证,胃实则皆下证也”作为治疗原则。齐秉慧承喻嘉言伤寒心法,认为阳明病来路由太阳,去路趋少阳,必首辨其在经在腑,在经则递传,入腑则不传,腑证则当下,经证不可下也。故按照邪气所在部位之深浅将阳明病分为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和少阳阳明。外邪初入阳明,表邪有余者,法主葛根解阳明之表;邪气尽入胃腑,察其浅深,斟酌于白虎、承气诸法之中;邪气流溢少阳,未离阳明,参合少阳法于微荡胃实之方中。齐氏对此还有所发挥,于太阴转阳明一证中,以小便利否来判断太阴脾脉证主之黄是否可免,大便硬否来判别太阴是否复转阳明;于少阴转阳明一证中,持有少阴本气虚寒者多自利,此言六七日不大便,是必热邪内胁真阳矣,加以腹胀,邪转阳明,此少阴负而趺阳胜,肾水势在立尽,不可缓也,法宜急下以救之的观点[3]57;厥阴转阳明一证中,齐氏提出:此证为热结旁流,法宜附子汤合小承气汤,下利谵语者,亦须先辨其阴阳,且强调了虚寒纯阴之证不可妄用大黄。基于此,齐氏对三承气汤做出了明确的区分:承气者,承领一线未亡之阴气也;大实大满,法当急下者则用大承气,梢轻则宜调胃;而小承气之法,但心下痞,微烦而无实满,故不用芒硝,较轻调胃又可知矣[3]54。并于“足阳明胃经腑之图”中对三承气汤的运用作出更为具体的阐述。
2 明辨阴阳,脾胃证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景岳全书》亦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医道之大纲……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由此可见,辨识阴阳在诊病中具有重要性。齐秉慧对阴阳二证的分辨亦颇为重视,其赞同舒氏《伤寒集解·六经定法》所云:“病有阴阳之分辨,不得其法,无从分认。”为此,他吸纳了舒驰远关于阴阳辨证的经验,临证以阴阳十六字诀(辨阴病十六字: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辨阳病十六字诀: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4]作为判别标准。齐氏所持的凡病皆须辨清阴阳之后辨证论治的观点,在脾胃病的论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现举两个例子。
2.1 呃逆一证,当分虚寒实火
齐氏在治疗呃逆时,首据“张目不眠,身轻恶热”之症,判断其为阳证,即有实火,并认为此由于胃实闭结,阳火上冲而导致的打呃,乃真阴立尽之候,治疗上应遵循急下存阴之法;由“目瞑倦卧,身重恶寒”之症,断定其为阴证,即属虚寒,且持“此由于脾气虚寒,健运无权,气不调达而引起的打呃,其势缓,非死证”的观点,治疗上则宜人参、白术、干姜、附子、甘草、半夏、丁香、白蔻仁以温中而散逆[3]26。
2.2 凡遇泄泻,不可仅知分利
齐氏在诊治泄泻一类疾患时,首先批判了凡遇泄泻,仅知分利后因阴阳不分而致愈误愈深的医家行为。他认为一味分利的后果是气化愈伤,脾土日衰,阳气下陷,不能升举,津液不上腾,继而出现目中干涩,紧闭难开之症。然世医见此症后,竟又误诊为是由泄泻引动肝火,兼之肾水不足引起的,继而予以泻火滋水、佐金伐木之法,实则是益西损东,愈误愈深之举。齐氏主张法宜黄芪、白术、附子、桂枝补火殖土,回阳止泻,更加白蔻宣畅胸膈,补骨脂、益智仁收固肾气,则阳回而津自升,目开而障自落。若见泄泻而瞳仁散大见昏蒙者,乃为火败土衰,水邪泛滥,法当补火殖土,以御其水;若见泄泻而瞳仁缩小者,乃火土熬干肾水而致肾水不足,法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3]26。
3 脾胃调治,妙用升提
心肺在上,肝肾在下,脾胃居中州,为四脏之主气[3]140。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其在气机升降运动中起着斡旋一身之气机、转输的作用。齐氏对脾胃这一枢机尤为重视,其扬东垣先生补中益气之法,于因饥饱、劳役、饮食不调、劳力过度等引起的脾胃病证中,活用补中益气汤,对补中益气汤方组成药物分析论述完全赞同并继承。如运用中医五行理论中脾胃与肺之间的相生关系,考虑到脾胃一虚,肺气先绝,盖肺为土之子,先补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衰,故方中黄芪主要用来益皮毛而闭腠理,防止自汗损其元气,蕴补子之义;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炙甘草之甘可泻大热,补脾胃中之元气,继而调治心火乘脾之况;白术苦甘温,既可除胃中热,还能利腰脐间血;加升麻、柴胡以引在下之胃中清气;以陈皮理乱于胸中之气,使清升而浊降;用当归以调和气血。除此之外,齐氏还对补中益气汤灵活加减用药作出详细的阐述。
齐氏于补中益气汤调和脾胃中,亦遵循东垣之法,认为只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生机才能活跃,阴火才能敛藏,故其强调了升麻、柴胡的升提作用。岐伯曰:“升治者,乃气虚下陷不能升而升之也。”凡人饥饱劳役,内伤正气,以致气乃下陷于肝肾,清气不升,浊气不降,脾胃不能克化,饮食不能运动,往往变成痨瘵,故借人参、黄芪之功,用升麻使由右腋而上,柴胡使由左腋而上,以升提其至阳之气,不使其下陷于阴分之间[3]138。当然,这与陈皮、炙甘草二味于补中解纷,使补者不至呆,补而升者不致偏坠是密不可分的。
4 论治脾胃,推崇温补
齐秉慧为喻氏三传弟子,但也潜心考究薛氏、赵氏等书而会通之。其深受倡行温补风格的喻氏、舒氏、薛氏、赵氏、李氏等影响,自然推崇温补。
4.1 胃病责肾,注重温养
齐氏重视脾肾,提倡先后天并重的学术思想于其临证中常可窥见,认为先天之肾与后天脾胃之间存在着“先天之气为脾胃之主,后天脾胃为先天元气之宅”的关系。齐氏赞同赵献可《医贯》:“饮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赖少阳相火之无形者在下焦腐熟,始能运化也。”故其于后天论中强调:“饮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若用寒凉之药,饮食亦不运化矣。盖脾胃中之火,土中之火,纳音所谓丙丁之火,炉中火也。盖养炉中火者,必频频加炭,宜以热灰温养其火而火气自存,一经寒水,便成死灰,将以何者蒸腐水谷,以何者接引灯烛?举目皆地域光景,可不畏哉?故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正取温养之义也”的观点[3]141。即脾胃在蒸腐运化水谷之时,不仅需要脾气及脾阴脾阳的协同作用,还有赖于肾气及肾阴肾阳的资助和调节,须在肾气的蒸化及肾阳的温煦推动下共同完成。若肾中命火衰弱,则釜底无薪,无以蒸腐水谷,此肾寒而脾亦寒,脾寒不能化,故而导致饮食难以运化的情况[5]。故其在治疗脾胃病时,重视从肾论治,提出“胃病责肾”的观点。
齐氏“胃病责肾”的这一观点于治疗脾胃病中的反胃尤有体现,他提出了从肾论治反胃的两种方法:一为肾水不足,一为肾火不足。肾中阴水枯竭,则大肠必然细小,水不以润之,故肠细而干枯,物即细小,则饮食入胃,不能下行,必反而上吐,证见食下喉即吐,方用熟地黄、山萸肉、当归、玄参、麦冬、五味子。肾中命火衰弱,则釜底无薪,无以蒸腐水谷,此肾寒而脾亦寒,脾寒不能化,必上涌于胃,而不肯受,则涌而上吐,证见食久而始吐,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方用熟地黄、山萸肉、肉桂、茯苓[5]。齐氏“胃病责肾,注重温养”的学术思想具有警示后人在治疗脾胃病时不可妄投寒凉之药,而应注重温养脾肾的重要意义。
4.2 顾护脾胃,反对肆伐
齐氏提倡顾护脾胃,反对肆用克伐的思想实则源于仲景论治杂病注重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故其在治疗脾胃病证用药时喜用建中汤、理中汤、附子理中汤、黄芪汤等甘温建中之品以调补脾胃。另齐氏受李中梓影响,在诊疗脾胃病常见疾病时,考虑到脾胃多为饮食、劳倦及情志所伤,易发生脾胃虚弱、生湿凝痰,终致脾肾两虚,故选方用药时在辨证论治之外,还多用药性温和、药味甘辛的补益药物温补脾胃。
李中梓治疗脾胃病时从阴阳水火立论的思想于《齐氏医案》中多处体现,齐氏完全赞同并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后天脾土有阴土和阳土,随火寄生,即当随火而补。继而从阴阳、水火的角度,分别以归脾汤补少阴心火,以生胃土(足阳明胃土随手少阴心火而生);八味丸补少阳相火,以生脾土(足太阴脾土,随少阳相火而生);理中汤用干姜,所以制土中之水;建中汤用芍药,所以制土中之木;黄芪汤所以益土之子,使不食母之食;六味丸所以壮水之主举例,阐述出了“土无定位,寄旺于四时,能代天以成化,故四脏中兼用之。”的观点[3]148。基于此,齐氏提出“总以补土为主,不用克伐。”
还以“世之酿酒者,以米与水贮瓦缸中,必借曲糵而成,前人药味,犹曲糵也。”来类比举世所常用的具有较强破气消食之力的神曲、麦芽、山楂三味药治疗伤饮食脾胃病的现象,并痛念此弊。伤饮食脾胃病乃因食有所停积,脾弱不能转运,故而不能消化所导致,其主张脾胃在人身,非瓦缸比,脾胃强健,自有化食之能[3]147。其反复强调应补其虚,助其弱,使自能食而化矣,而非肆用克伐,最终贻害于人。除此之外,齐氏推崇洁古“养正积自除”的观点,并认为洁古枳术丸乃专为伤食者设。补药倍于消药,先补而后消,且白术之本意不取其食速化,但令人胃气强,不复伤正。
最后,由齐秉慧《齐氏医案》“伤饮食脾胃论”治验:“曾治亲友太学谭庭才,拔贡知县谭瀛公三子也,患腹痛俱急,命在须臾,来寓求治。余曰:此绞肠痧也。急用干马粪(马通)炒黑存性一两,干黄壁土块少许捣碎微炒,入黄酒(无黄酒,淡水酒亦可)一品碗煎好,布滤去渣,乘热服之,少顷即睡,醒来病去如失”[3]149。中可知,其遵循的是《素问·举痛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理论,故用出自仲景“治痞块腹痛方”,最能定痛,又不伤气,又能逐邪化物的马通,以黄酒佐之,无微不至,非吐则泻,以治腹痛。然笔者认为,此方中最独特之处在于黄土,用黄土者,因马通行之迅速,得土性而稍缓,且黄土与脾土同气相求,同性相亲,引之于痛处,使马通易于奏功也[3]149。齐氏寓补土于克伐之中,也体现出了其提倡顾护脾胃,补虚助弱,反对肆用克伐的思想。
5 小结
《齐氏医案》汇集了齐秉慧数十年寤寐诚求之心得,笔者认为,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并非盲目地上溯岐黄,下逮百家,照搬照抄,而是在广泛阅读古人理论与临证医案的基础上,懂得深思熟虑之后提炼出自身学术思想的精华,可谓遵古而不泥古。从笔者所撷取的《齐氏医案》中齐氏关于脾胃病的辨治心法可以看出其治疗脾胃病证,从六经、阴阳、先后天图说出发,主张太阴阳明,分治脾胃;明辨阴阳,脾胃证治;脾胃调治,妙用升提;论治脾胃,推崇温补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对后世很多医家产生了影响,对我们现代中医学者提高理论和临床水平仍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