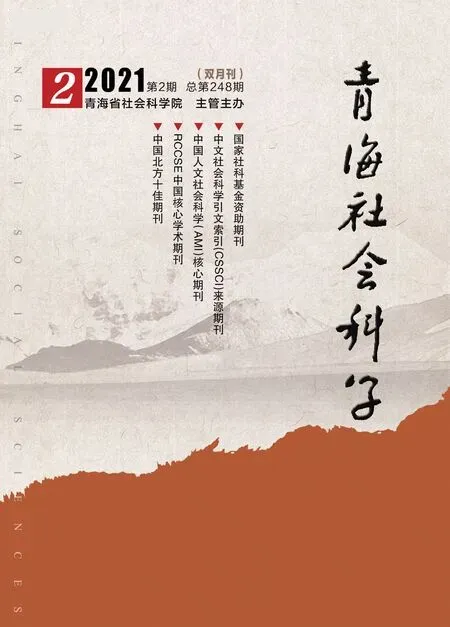生态系统脉络演进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村落开发
◇郑寿斌 蒋述卓
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特指形成时间较早并拥有丰富文化和自然资源的村落。[1]冯骥才认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沉淀在传统村落之中,少数民族文化和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在传统村落之中。[2]2012年9月,为突出文化传承价值,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决定将“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从生态学学科角度来看,传统村落是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相结合的复合生态系统。[3]中国传统村落在自然生境、历史脉络、文化肌理与物理空间格局等维度存在脉络独特性,且各维度脉络之间相互依存、联动演化,不能孤立存在,共同组成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需要立足系统、联动的视角对传统村落开发进行研究。本文以贵州屯堡为例,提出生态系统脉络演化视角下的传统村落开发。
一、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
由于生存区域多样性和历史复杂性,中国传统村落极具独特性和多样性,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具有多维性、演化动态性及演化联动性特征。
(一)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多维脉络
中国传统村落既与自然生境同构、共生,也烙印着中华民族在不同区域、历史时期形成的历史、文化脉络,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多样性。首先,自然生境肌理是传统村落发展的底色。就宏观地形而言,中国从西往东地势渐低,呈三级分布,海拔落差大,经纬范围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同时,境内温度带跨越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地形、温度的复杂多样,使国内气候表现出多样性特点。自然生境的多样差异使中国传统村落表现出多元适应。比如特定地区的光照决定了当地木材的种类和材质,影响建筑材料的可选择性,同时温度通过防寒、防热需要影响建筑格局、技艺等。这一点从北方与南方村落的房屋格局对温度的适应就能看出,北方房屋防寒特点显著,南方房屋散热效果强。微观上来看,传统村落生境还在水资源景观、山体微观形貌、岩层土质特点、本土动植物分布等方面存在细部差异。自然生境丰富性是中国传统村落的多样性基础。
其次,悠久的历史使中华民族各地区族群历史形成脉络极富多样性,即使在相对局限的地理空间内,也表现出细腻的脉络特征。藏羌夷民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武陵民族走廊、南岭民族通道等“走廊”“通道”的存在就是中华民族族群历史脉络丰富性的生动表现。[4]3单以福建为例,闽南、闽北、闽西、闽东、闽西南、闽中、莆仙等区域就表现出族群、文化、方言等方面极大的差异性。地处闽西的龙岩在历史上就经历过多次移民潮,汉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形成客家文化与福佬文化。历史的复杂性和族群形成脉络的丰富性是中国传统村落历史脉络多样性的基础。
再次,各地区差异化的自然生境、历史脉络又会极大地影响各地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型,包括经济成分、宗教、民俗习惯等,即使是小区域内同一族群村落也会出现差异。“百里不同音,千里不同俗”的说法就是中国区域文化多样性最真实的反映。[5]以贵州屯堡为例,该族群起源于六百多年前的“调北征南”明朝驻军,六百多年来顽强扎根在汉文化母源地之外并稳定传承明清汉族文化。[6]屯堡村落是由屯军后裔和后期迁入汉移民融合形成的村落,现今主要分布在安顺地区。漫长的历史演化路径使得其沉淀积累了多样的民俗文化遗存,包括每年农历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戏”,正月举办的“抬汪公”“迎城隍”,每年多次的“玩花灯”,十二年一次的“过河活动”等。各村落民俗文化表现形式多样,但不同村落民俗文化传承种类和传承状态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比如地戏是屯堡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因其奔放、粗犷的风格与内涵流行于屯堡地区。地戏的产生与发展与屯堡人息息相关,屯堡人保存、发展了地戏,而地戏又作为屯堡人文化基因外显强化的载体强化了他们的族群凝聚力。屯堡地戏的表演内容多是军事生活场景,表演人物多是封神人物、杨家将、薛家将、岳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等。由于每个屯堡村落具体历史情境和文化功能需求不同,地戏发展过程中会演化选择出不同的类型和话题。比如屯堡东部地区村落,处于当年“征南”大军的驻地,所以地戏演出的伴奏、道具、服饰乃至内容形式与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区别。[7]
最后,各具特色的自然生境、历史脉络、文化肌理等使传统村落形成各不相同的物理空间格局。与自然生境的功能性同构和村落历史脉络、文化肌理的深刻嵌入是村落物理空间格局独特性的基础。如果把传统村落视为统一的生命体,那么每个传统村落的自然生境、历史脉络、文化肌理、物理空间格局等要素均存在独特性,并且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承载、相互影响,不能孤立存在,形成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由于生存区域多样性和历史复杂性,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极具独特性和丰富性,单独村落系统脉络具有不可复制性。
(二)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演化的动态性
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经过一定时间跨度的动态演化而形成。首先,在时间的纵向上看,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间段表现出不同的肌理,村落自然生境、历史脉络、文化肌理、物理空间格局等伴随村落生存环境、历史进程的变化不断发生动态演化。
其次,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演化又存在差异化的演进速度。一方面,同一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速度存在差异,这与国家大环境的整体变化有关,也与具体村落不同时期的历史困境有关。另一方面,在同一历史阶段不同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演化速度也存在差异。比如清朝初期,贵州人口进入发展高峰,人均耕地下降,屯堡村落面对接近饱和的生存资源现状,开始排斥新移民进入村落。随后,新移民大多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屯堡村落附近建立新村落,并与屯堡族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生存竞争。近代以来,新移民由于耕地条件的限制,有更强的经商传统,加之更加接近主流汉文化,政治和经济能力渐渐凌驾屯堡人之上。这一时期,各个屯堡村落表现出联合抗衡新移民的趋势,五官屯、狗场屯、鸡场屯通过共同举办“汪公信仰”活动联合表达同一的文化身份和相对新移民的族群差异,表现出对新移民村落的防御心理,并形成防御式互利共生关系。[8]这一阶段,相对新移民村落与国家文化、经济紧密联动发展,屯堡村落文化上固守,经济上与国家大环境弱联系,屯堡村落生态系统脉络表现出极强的惰性,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和演化慢节奏。
(三)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各要素演化联动
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是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经过一定的时间跨度动态演化形成的。但生态系统脉络之中各要素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任何一部分要素的变化往往都牵动整个系统脉络的联动变化。以屯堡为例,由于军事移民背景,许多屯堡村落都带有一部分军事遗迹,或者部分村落整体就是军事堡垒。军事移民背景主导了屯堡村落建立时对生境的选择。移民背景和村落生境又决定了村落早期基本的物理空间分布格局。后期族群的文化适应促进村落空间功能的分化和完善。以云山屯为例,该村落是屯堡最具代表性的军事遗迹突出型村落之一,位于安顺西秀区云鹫山峡谷之中。云鹫山山体险峻异常,通往云山屯的古道只有一条。云山屯是一个封闭型的村落,蜷缩在40多米高的半山峡谷里,利用两侧陡峭的山体为屏障,村落入口设有箭楼,重要位点设有14处碉楼。云山屯的布局,充分表现了屯堡军事移民的背景,展示出村落军事防守的特点,村中民居都以石墙呼应,墙上满布枪眼、箭眼等机关。同时村落军事设施与民居高低错落,沿狭长山谷地势分布呈弯月形。地形与村落之间、军事设施与民居之间防御性能高度呼应、互为依托,村落与自然生境高度共生。村落内大部分防御性军事遗迹、商业遗迹以及其它文化空间遗迹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顺应村落需要变化产生的。村落中心腹部是最重要的文化空间戏台场坝,商铺、祠堂、财神庙等向两侧延展,形成主街,主街两侧民居通过小巷紧密连接。云山屯建屯时作为军事战略要地,以防御性功能为主。明末清初,随着屯田制的瓦解和军事意义的褪去,云山屯利用交通便利的优势吸引许多商户搬迁于此,此后该村落从以防御性为主的军屯逐渐转变为以商业为主的商屯。[10]这一演化过程也伴随着村内人口与文化肌理的变化,村落内戏台、商铺、祠堂、财神庙等物理空间元素也随着村民经济基础、文化精神需要的变化而改变。
从云山屯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历史脉络、自然生境、文化肌理、村落物理空间格局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们在演化上存在联动性。由于这样的系统联动性,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各要素之间往往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承载。村落物理空间格局与自然生境存在整体功能上的同构,同时物理空间承载了村落历史脉络、文化肌理的深刻嵌入。反过来看,族群历史脉络、文化基因在演进过程中又会改变村落物理空间格局乃至自然生境状态。传统村落历史演进是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整体演进,系统脉络各要素演进并不孤立进行。
二、国家经济发展浪潮下的中国传统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的变迁速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这与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外来文化对传统村落的冲击息息相关。本质上是作为村落生存背景的国家大系统在不同时期发展速度不同导致的对传统村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发展速度是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快速演化最重要的背景,其对传统村落改变的深度和广度是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屯堡村落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具独特性,其与国家大系统功能联动程度的变化和村落内聚型心理特征的瓦解、转向又是中国传统村落在这一时期的普遍性特点。
(一)国家大系统和村落小系统
工业化之前,中国传统村落的变迁速度相对缓慢,这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低生产力、科技发展水平相关,村落与国家经济运转关联弱,自给自足生产特点明显。费孝通在论述中国乡土社会时指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11]同时工业化之前的中国乡村与城市实际上是共生共长数千年的关系,经济、文化同根同源,不存在较大的能量势差。在这样的背景下,村民之间、村落之间,村落与城市之间较少发生财货、信息流通。伴随村落国家经济弱联系的是村落人口、物质、文化的低速流动。这与马克思对19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论述异曲同工,马克思认为当时法国的村庄就像马铃薯袋子,村民就像一个个互不相关的马铃薯,他们的生产方式使彼此间相互隔离。[12]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村落运转主要依靠村落小系统内循环,国家大系统对村落小系统产生的辐射拉力较小。
近代工业化为中国社会引入了新的科技、经济和资本运作方式,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结构、发展速度差异逐渐扩大。发展速度渐快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大系统,利用扩大的经济能量势差,吸纳乡村人口乃至生产要素,乡村变迁加速。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使中国传统村落的变迁进入加速度时期,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并实现经济腾飞,乡村和城市的经济错位、势差渐强,国家大系统对传统村落小系统的虹吸效应变大,城市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远远超过农村,城乡发展逐渐处于失衡状态。城市的兴起伴随着对乡村封闭和内循环的大力突破。[13]与此同时,农村面临人口结构、人地矛盾的问题,人口外流更严重,其根本动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发展。
以屯堡为例,改革开放后,国家大系统辐射力度与自身内循环产生的内聚力差距决定了村落的兴衰。经济快速发展时,大系统内能够得到更好的资源,包括经济利益、子代教育等社会服务,对小系统产生生存质量上的强大势差,村民就更有可能往大系统流动,小系统内资源要素不一定留在系统内完成内循环,而是流向能产生更高回报的地方。在对屯堡村落进行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村落人口是留在本地还是离开,是留在本村还是去邻村,是由村内工作机会、人均耕地水平与出外工作机会进行对比发生的,村落人口迁移流动与经济状况有直接联系。像岩上村等不发展旅游业,同时人均耕地少、经济类型单一的村落,青壮年外出务工和户籍转出的状况比较普遍,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相对明显。经济状况较好的二官村,外出务工村民较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不多。而像较早发展旅游业的天龙村,其人口流动与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基本同步。当旅游业稳定发展时,产生大量工作岗位,带动整个天龙镇片区的经济发展;当旅游业发展不顺利,对劳动力磁吸作用消失,人口外流与留守儿童等问题会重新显化。屯堡经济结构稳定性与社会结构稳定性是互构关系。[14]
(二)中国传统村落内聚型心理瓦解
工业化进程之前,中国传统村落在与国家大系统的弱联系中,保持了村落经济生产、治理能力、文化传承等相对稳固的内循环体系。工业化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村落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物理层面越发开放,村民、村落对国家大系统功能性吸附增强,资源联动越发紧密。与此同时,村落内聚型的心理特征伴随村落物理层面的变化也发生了瓦解、转向。以屯堡村落为例,明初之时,由于屯军进入贵州,打破了原有民族之间的生态平衡。当时,布依族、仡佬族、苗族三个主体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于安顺地区。屯军进入后,因为要占有更好的耕地,使得少数民族一再搬迁,并且屯军与其他少数民族是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明朝之后,屯堡人相对少数民族单极化的政治权利不复存在,并且人口数量极其弱势,族群保持了较长时期的防御式心理态势。[8]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消除带有民族歧视的历史遗留痕迹,保障每个民族的合法权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次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平等民族政策的实施,使得屯堡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缓和。但这一时期的屯堡村落与国家大系统经济联动性较弱,屯堡族群内聚式心理态势依旧占据主导。
在人体脂肪、心肌、骨骼肌以及巨噬细胞中,脂蛋白酯酶均有一定分解,也是TG水解中的关键。另外对于脂蛋白酯酶,一旦胰岛素抑制作用降低,不足以表达基因效果时,酶活性降低,造成TG水解速度降低,造成低密度脂蛋白形成。同时胰岛素降血糖能力有所干扰,机体得到的信号就是饥饿,所以一旦人体进入到脂肪动员状态,脂肪细胞的脂肪开始分解,指标开始释放。
改革开放后,屯堡村落与国家大系统功能联动越来越紧密,国家经济一体化力量打破了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城市、村落与国家甚至族群与族群的藩篱。屯堡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越加频繁,文化习俗渐具共同点,加上大众化的学校教育打通了语言上的障碍,跨民族的婚姻更加频繁。同时,科技的进步、大众传媒的普及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拓宽了屯堡人的文化视野,也逐渐影响和改变了屯堡人的生活。
三、中国传统村落开发困境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自信不断增强,传统村落的经济、文化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其开发广度和力度不断加大,但不成熟的开发环境和方式也导致中国传统村落出现一系列系统性开发问题。
(一)在原生态保护与商业化利用中徘徊
在原生态保护与商业化利用中徘徊是造成中国传统村落开发紊乱的主要原因,其背后是开发方式和理念呈现割裂化的现状,无法提供有效融合二者的视角和理论载体。
一部分传统村落在开发过程中侧重对村落的原生态保护,试图通过设定法规、政策保留村落的历史、文化遗迹。这一开发方式忽略了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演化特征,过分强调对村落现状的保持,疏于对村落文化空间的活化利用,欠缺内源性的生长活力支撑,最终往往在保护中筋疲力尽,效果也相对有限。如刘魁立所言:“当我们说保护一种传统文化,不让它受到市场经济的干扰是不大可能的。”[15]同时,片面强调对村落遗迹的原生态保护实际上也否定了传统村落现在和未来的流动性,割裂了村落遗迹与村民、村落整体空间格局、村落生境、村落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联系,不利于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整体功能的延续。
另一部分传统村落则在开发过程中强调对村落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利用,为村落生存发展找到经济支撑并保持活力。[16]但这一开发方式往往忽视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整体性,片面强调开发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文化元素,满足消费者猎奇心理。现今大量传统村落被地毯式开发、重建,原有村落物理、文化空间被深度破坏,为了突出民族性、地域性,修建各式仿古建筑,结果是同化现象扎堆出现,真正体现村落独特性样貌、内涵的村落生态系统脉络被严重破坏,村落文化整体性和功能联系被割裂乃至荡平。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延续是村落整体文化功能、村落独特性留存的载体。在关注点之外的隐性因子极易被无意识损毁甚至在开发中被剔除,这必然伴随着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不可逆消逝和村落系统功能的丧失。被过度关注、开发的文化元素失去了村落整体历史文化和功能联系,就失去其内涵依托,意义由活转死。另外,在商业思维主导下的传统村落开发方式也加深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冲突,注重对传统村落资源的碎片化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村落开发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内在脉络延续的合理性,将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独特性、多样性置于城市化、现代化乃至西方化洪流的冲刷之中。比如在屯堡村落的修缮过程中,部分村落在开发中所用的建筑材料不是同源性的自然材料,而是现代化的建筑材料或者看似接近但肌理有较大差异的材料,微小的材料差异也改变了村落沉淀下来的审美感受。这些村落在改造过程中生硬地嫁接现代化设计理念,突出光影、色彩、立体几何构型,但失去了中国文化中人与村落、自然共生合一的审美精神与质感,现代化设计理念很突兀地刺穿并肢解村落原文化场域。这本质上是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冲击与剥离,对异文化的引入欠缺深刻反省和有序借鉴。
在商业化思维的引导下,中国传统村落往往代表的是城市的附庸,其实现发展的标志被潜移默化定义为现代化、城市化。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下,传统村落经济结构、文化脉络面临的不是调整融合,而是替换。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总是伴随历史发展动态变化,生态系统脉络内各要素在不同时期根据村落需要不断引入新基因,其动态演化特点决定在开发过程中引入异质性文化元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新进入的经济或文化元素如果对原有村落系统脉络冲击过大,有直接替换、抹除原有脉络主根茎的风险,这时候就需要慎重处理。因为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是在较长的历史演进中慢慢形成的,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潜力,具有损毁后不可恢复的特征。
中国传统村落开发如果不能弥合原生态保护与商业化利用的二元语境,村落的保护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村落发展就将变为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传统与现代、原生态与商业化的简单对耗和你退我进的零和博弈,这对村落的可持续开发是不利的。因此,传统村落开发急需一种能平衡二者,推进村落顺畅、有序吸纳新元素,并保留中华文化根脉和精神场域的新理论载体和视角。
(二)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演化联动性意识不足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村落在国内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整体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衰败。这与国家大系统强势的辐射拉力有关,也跟村落开发过程中的系统性破坏有关。村落的系统性破坏往往来自于对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整体观和生态系统脉络演化动态联动观念的缺失。生态系统脉络中各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融合的关系,任何一部分要素的变化往往都牵动整个系统脉络的联动变化。对屯堡村落进行实地调研发现,许多村落在开发建设时,没有考虑到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联动性特征,对系统脉络内各要素是分开考量的,这就造成开发中破坏、越开发越破坏的现象,而这种破坏往往是不可修复的。比如,部分屯堡村落在开发时强调对历史遗迹的保留,但是对遗迹与村落整体功能格局,遗迹与山体、河流等自然生境的功能共生关系不重视,导致遗迹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功能消解。村落历史记忆与文化功能的消解又使得村落独特性和文化体验感被剥离。以云山屯为例,作为建筑主体的部分民居被重建,不仅会瓦解村落原有军事联防物理空间格局,同时会影响村落历史记忆、文化基因的顺畅表达,对村落文化功能连续性、村落与自然生境的同构特征等产生联动破坏。再比如“地戏”“跳花灯”等屯堡民俗文化的退化、消逝,既影响村落文化肌理,也深刻影响族群形成脉络、村落物理空间格局等要素的活态表达甚至失去其意义表达路径。传统村落开发过程中生态系统脉络的演进联动观念缺失是村落文化精神空间和物理空间破碎化、功能失衡、退化乃至消失的主要原因。这种破坏与国家大系统、村落小系统经济势差造成的被动退化不同,是一种主动、无意识,甚至是善意的蚕食。不能立足具体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和其演化联动特点进行的开发本质上是粗放式、一刀切式的开发力量推动的。这是旅游体验性需求不断强化的趋势下,中国传统村落逆流化丧失独特性、文化基因多样性并渐趋同质化、同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欠缺立体、多元的村落开发机制
改革开放后,伴随快速的城市化,中国实际上开启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去农村化。中国传统村落的消失、萎缩与城市经济的虹吸效应几乎同步,仅在2000年至2010年就消失了至少90万的自然村。[17]政府对传统村落的重视程度随着村落的消逝逐渐提高。2011年9月6日,冯骥才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希望政府推进现存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和记录工作。[18]2012年4月1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2012年12月17日,国内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制定专门规划,启动针对性工程,大力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此后,中央和各级政府针对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法律法规加速推出,社会各界对传统村落重视程度空前提升。但国内目前对传统村落保护、开发以政府推动为主,并且推动力单向从上至下,尚未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村落开发推动合力,无法针对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多样性形成有效呼应。中国传统村落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至关重要,这是由中国广阔的国土面积和厚重的历史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多样性特征也同时决定了村落开发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的政策辅助机制和更多元的开发、保护参与方。以英国为例,该国国土面积、自然生境多样性、传统村落区域类型丰富度远不及我国,但却建立了极为立体、多元的村落保护机制。该机制通过国家机构与地方组织的协作,对传统村落提供有力的保护。其中央政府通过提供必要资金支持和指导意见,授权地方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具体操作的权利,既限制了政府的过度干预和越位,也最广泛地调动了社会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使各地有足够的空间依照区域文化传统因地制宜地探索开发新模式。[4]247
目前,中国传统村落的开发参与力量呈现极度不平衡和缺失的状态。以天龙屯堡为例,该村落是旅游开发力度最大,合作机制建设最为完善的屯堡村落。村落开发之初就建立了政府、旅游公司、旅行社、村民旅游协会四者合一的合作机制。[19]但作为开发主体力量的政府和旅游公司对村落开发具有排他性主导权,且本能带有追逐政绩和经济效益的倾向,对村落保护和深度有序开发的能力、意愿都不足。因此,村落开发之后出现保护力度不足,生态系统脉络不断被抹除,村落文化、空间功能退化,村落独特性被消解的窘境。村落旅游发展由于村落个性、体验感的削弱陷入倒退。天龙屯堡的现状折射出中国传统村落开发过程中参与方或推动力量极不多元的现状,村落开发主体研究视角抽象停留于政府、旅游公司、村民等简单化的划分方式上。政府的权限划定,各级政府差异化的职责分工,属性、诉求各不相同的社会组织分类等都应是形成立体化村落开发系统的基础。由于性质差别,不同组织或参与力量在开发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目的。只有更多元、平衡的参与方和更具牵制的权利结构才能避免传统村落在开发中快速向失衡的利益陷坑中滑落。
四、生态系统脉络演化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村落开发
传统村落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来自于各自不同的生态系统脉络特征,中国传统村落开发需要在生态系统脉络演化的视角下进行。
首先,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开发必须保证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完整性。保留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完整性是对村落生命体功能整体性的维护和延续,关乎中国传统村落是否能保持文化基因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开发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保留的完整性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具有持续性的演化特征,村落自然生境、历史脉络、文化肌理、物理空间格局变迁是常态。传统自给自足经济方式的萎缩和相应社会伦理结构的重置是不可阻挡的,村落经济需要吸纳新的、适合具体村落发展的产业,也需要改善文化土壤适应新的社会产业结构和伦理关系。在国家宏观大系统中,传统村落需要更新、代谢具有时代适应性的文化基因、经济元素以保持稳定、发展与复兴。但传统村落引进外来经济、文化元素时不能贪功冒进,而是要辩证、有序进行,使引进元素有效融合进原有村落生态系统脉络之中,形成稳定、和谐的新系统脉络平衡点,同时不切断原有系统脉络主根茎,保留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村落精神场域、文化土壤厚度和村落整体性功能。以鲍家屯农业水利遗迹为例,其始建于明初,成形在明末,运行至今。鲍家屯农业水利体系是较为完整的屯堡农业水利体系,以型江河为源,移马坝为起始枢纽,利用引水、蓄水、分水等方式,将河道一分为二,形成新老两个干渠,一个门口塘、三个水仓,然后通过二级坝,将水分配到村中不同位置,实现全村不同高度农地的灌溉。[20]鲍家屯农业水利体系从明朝沿用至今,起到了村落灌溉、防洪等作用,体现出屯堡人对自然的共生适应,为我们展现和了解明初之后的中国农业水利系统提供了机会,是汉民族的农业技术文明在贵州地区传播、实践的代表。改革开放后,由于地理交通的便利、村落耕地的相对富余,鲍家屯是为数不多的人口和空间均实现较大增长的屯堡村落,不断膨胀的村落对农业水利设施再建设的需求不言而喻。在这一过程中,鲍家屯没有为了经济生产的便利而肆意地毁坏原有的水利遗迹,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原有水利遗迹相辅相成,既保证了村落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恰当地保留了村落水利遗迹的历史面貌。
其次,对中国传统村落开发要从村落生态系统脉络演化的动态联动视角出发,开发策略和方案应该避免因为局部要素的改变而联动性地过度破坏其它要素乃至村落生态系统脉络的功能整体性,防止对村落文化资源,尤其是隐性文化资源的不可逆消耗,为中国传统村落延续和开发保留富有民族特征的文化土壤,避免在开发中形成快速内耗。这符合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传统村落保持文化基因型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的基础。
最后,中国传统村落开发需要建立更立体、多元的村落保护、开发机制,以便与国内复杂的区域文化多样性、族群脉络多样性乃至村落生态系统脉络多样性形成有效呼应,为社会各界创造更多的参与空间,释放积极性,并赋予更多组织机构发言、参与的权利,将更多极化的力量凝聚进传统村落开发的智囊团中,使开发实现更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推动各级政府、资本、村落保护组织、非遗保护组织、旅游公司、专业化的开发策划机构等参与方形成职责权属划分、厘定更细致并且协调性、相互反馈能力更强的新机制,实现保护和开发交融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