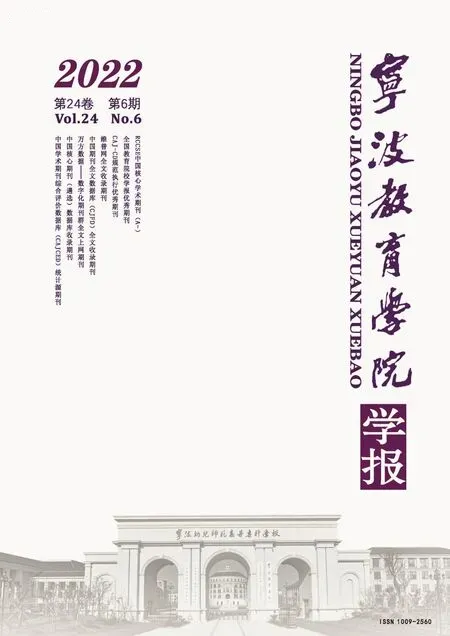基于理想类型的大学课程协同治理机制
黄志兵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发展规划办公室,浙江 宁波 315336)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发布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的新动力:社会变革与发展”公报指出,“扩大教育机会必然对高等教育质量带来挑战,但确保教育质量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1]。《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在于高质量发展。课程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载体。在高等教育领域,人们通常把大学课程当作是高等教育的“黑匣子”[2]226,这个“黑匣子”可以折射出高等教育理念、模式与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大学课程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从早期的自由教育课程到15世纪末开始的专业性课程,从源于19世纪柏林大学的学术性课程到20世纪中期兴起的通识性课程,以及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社会条件下的职业性课程,大学的课程总是维持通识性、学科性、职业性之间微妙的平衡。本文拟基于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透视大学课程的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大学课程的协同治理机制。
一、大学课程的理想类型
围绕着通识性、学科性与职业性,今天的大学课程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识性课程、学科性课程和职业性课程等三种理想类型。所谓理想类型,是基于某种视角对现实中某类成分的抽象化[3]。可见,这种理想类型是基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的一种抽象化概念。以通识性课程、学科性课程与职业性课程作为大学课程的理想类型,实际上是基于现实的大学课程实践,而又高于大学课程实践。运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对大学课程进行剖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大学课程的发展趋势,为大学课程治理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一)通识性课程
通识性课程源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课程和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教育课程,它强调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代表古希腊进步教育的自由教育课程,无论是普罗泰戈拉等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倡的辩证法、文法、修辞学等“三艺”课程,还是后来由柏拉图倡导的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等“四艺”课程,从内容上来看并无“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因为当时课程设置的唯一依据是“培养完整的人”。在文艺复兴运动过程中,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课程逐渐演变成为人文教育课程。19世纪后期,自由教育课程最终在美国演变为通识性课程。经典名著课程是通识性课程的经典模式,其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经典名著有效融入通识性课程,使大学生在与经典对话中增长心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实现“完人”教育目标。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曾指出,“学习经典名著能使学生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从而获得通识教育的永恒性和广博性,成为一个健全的人”[4]。在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盛行的今天,美国的大学开始意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新入学的大学生必须学习通识性课程。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是当前美国大学通识性课程的典型代表。这些核心课程嵌入一些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事件。通过学习这些重大事件,大学生能自觉地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并将自身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作为通识性课程,真正做到了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一体,更好地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提升。因此,从培养人的视角来讲,通识性课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未来,不仅能够促进大学自身的组织建设,提升学术文化与教育水平,有利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激发学习热情,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凝聚互信与共识,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也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是提升国家和民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5],都是大学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理想类型。
(二)学科性课程
学科性课程是以学科、专业为背景的课程。以专业为背景的学科性课程,亦称之为专业性课程。自专业教育开始,专业性课程也随之产生。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强调学术性或学科性。从高等教育历史来看,15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学开设了法学、医学、神学等专业,并设置与这些专业相关的课程,培养律师、医师、教师、教会人员、官员等专业人才[6]。19世纪开始,随着近代大学的学科分化,专业性课程不断增多。现代大学的系科是按学科、专业逻辑细分出来的,专业化程度较高,通过与相应的职业分类相对应,彼此之间处于分裂状态。这些专业化系科“在提供课程方面,各系的排他性避免了教师岗位和课程设置的重复”[7]。这导致专业性课程亦处于分裂状态。专业性课程的意义在于能够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以满足社会上相关职业的需要。但专业性课程的过度强化削弱了通识性课程的可能性。这种倾向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接受专业性课程的学习后专业能力得到提升却缺乏基本的教养。当今多数大学生的兴趣随着专业性课程的学习而发生变化,他们的学习目标是为了“找到好工作”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8]。以学科为背景的学科性课程,亦称之为学术性课程。随着19世纪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的兴起,大学的课程开始向纯学术性课程发展。在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的指导下,学术性课程把学生的培养与科研训练紧密结合。19世纪中期后,美国借鉴德国大学理念,开始有研究型大学的范式。此后,大学的专业性课程向学术性课程转变。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等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现代大学应该把训练和研究联系起来[9]。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学术性课程所倡导的综合能力培养取向得到了社会认可。然而,因为对科研的高标准与高要求,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性课程在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课程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使得大学在提升整体实力的同时削弱了本科教学活动。“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生、药剂师和教师等,但只需要数量有限的科学家”[10]。因此,只有把专业性课程与学术性课程有机融合,才能使学科性课程发展成为既能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又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理想类型。
(三)职业性课程
职业性课程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用课程。从自由教育实施的角度出发,亚里士多德将当时的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教育课程,即追寻理性自由的博雅课程;另一类则是非自由教育课程,即培养工匠技艺的实用课程。很显然,培养工匠技艺的实用课程实质上一种职业性课程。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最初的农业、手工业领域的学徒制系统的操作练习,可以说是职业性课程的雏形。近代大学职业性课程多出现在非大学类高等教育机构里。例如英国高等教育的“双轨制”下,大学与多科技术学院等同是高等教育机构,但两者却有着一些性质上的差别。多科技术学院相当于职业性学院,多实行职业教育,不具有独立授予学位的权利。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职业性课程得到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经过职业性课程学习后获得职业技能,并能顺利就业。有学者认为,现代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已退化成为单纯的职业培训中心[11]。“在过去20年中,职业化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为找到报酬优厚的工作而忧心忡忡的学生们,要求学校的课程更加具有针对性。”[2]13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美国大学开始重视职业性课程,以满足人们对实用知识的迫切需求。威斯康星大学课程可以说是美国职业性课程的经典之作。早在19世纪末威斯康星的课程便开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针对威斯康星州的支柱产业——乳品业,开设了向民众传授奶牛养殖及乳品加工技术的短期农学课程;围绕“大学为州服务”这一思想,威斯康星大学向全州公民及其子女提供相关的职业性课程。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课程以学科、专业为逻辑进行安排,对社会的需求关切度不够,从而导致大学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职业性课程之于传统课程的价值在于为大学课程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类型。
二、大学课程的协同治理机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大学都必须满足实用职业的要求,但是大学却提出新要求,即把实用知识收纳在整体的知识范围之内。”[12]这意味着,从培养能够满足局部需要的人才走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大学课程发展的必然。对于大学而言,每一种课程类型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并不存在孰优孰劣。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三类课程各自的优势,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完善大学课程的治理机制。
(一)学科性课程:建立基于学校自主的政校协同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必须依据国家颁布的专业、学科目录设置专业、学科。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制定、教学指导、教学评估、课程评估等措施来进行管理,政府拥有主要的课程资源管理权,大学在课程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尚未真正确立。因此,落实大学学科性课程治理,需要做到政校协同。首先,政府要从“管理者”向“引导者”转变。根据场域理论,如果政府部门对学术场域管控严格,将导致学术场域内的行动者失去自主性[13]。所以,政府要进一步落实大学在课程制度建设中的自主权,转变“管理者”角色,在信息服务、规划、拨款等方面成为一个“引导者”角色,充分利用市场来传递社会需求,引导大学课程变革,引入第三方组织对大学课程进行认证和评估。其次,大学要正确行使自主权。“自主权”不等于“学校领导说了算”,需要学校内部利益相关者共同来行使自主权,构建大学师生民主参与课程教学的制度。不言而喻,教授是大学“高深学问”的传播者、创造者和应用者,这决定了教授对课程的开设、实施等享有基本的权力。学生是课程教学的直接受益者。学校应充分吸收广大学生的意见,把课程的选择权和自主权还给学生。基于此,应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课程制度,成立由教授、学生等利益主体组成的课程设置委员会,并真正使各利益相关者在课程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作用。
(二)通识性课程:建立基于跨学科组织的学科专业协同机制
“特殊技能将逐渐无益于培养兼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青年,取而代之的是思考、推理和分析能力。”[14]随着跨学科现象不断涌现,大学更要注重通识性课程的开发与设计,关注学生核心素养提升。而现实是,大学为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更关注“见效快、能上手”的职业性课程,这导致大学生所学的知识多是碎片化的,毕业后虽有一门技能,却不知如何合乎逻辑地思考与应用[15]。因此,为维系大学生知识的结构化与体系化,需构建基于跨学科组织的学科专业协同治理机制,加强相关学科专业之间的协同,使每门课程自成开放性体系,实施基于跨学科专业的课程教学。实践中,课程的设置权在学院,学院往往按照自身专业要求来设置课程。而各个学院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教育组织,学科专业的协同融合面临挑战。作为一种理想类型,通识性课程的跨学科特点突出,设置时需要跨学科教师的协同参与,这些教师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学科,组成“一个由教师广泛参与的柔性的学科专业协同组织”[16]——跨学科组织。著名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跨学科综合化课程有两种方式[17]:一种是从学科入手,通过探讨该领域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来研究各门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并为课程提供一种提纲挈领式的结构;另一种是从问题入手,各门学科在解决问题中达到融合。因此,通识性课程要突破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建立基于跨学科组织的学科专业协同治理机制,基于问题来构建课程内容,促进通识性课程与学科性课程、职业性课程协同发展。
(三)职业性课程治理:建立基于市场需求的产教融合发展机制
美国课程开发专家泰勒认为,课程目标有社会、学生与学科三个来源[18]。从市场角度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性课程必然要基于就业市场、生源市场与资源市场的需求来开发与设置。每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意味着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和新的职业性课程被开发和设置。职业性课程治理就是要基于市场需求,形成产教融合发展机制。首先,要处理好“产”与“教”之间的关系。职业性课程作为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类型,培养社会企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产”与“教”的共同目标,这也是产教融合发展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在产教合作互动中,大学与产业、行业至少在经济、人才、知识和责任四个层面拥有有效结合点,为构建大学与产业、行业有效互动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入口[19]。然而,在职业性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产教双方在各自角色、价值取向等方面难免会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要充分体现产业发展的需要,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和职业性,并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发展机制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内在规律,注意课程结构安排的科学性,合理安排知识结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例。其次,积极推进职业性课程的模块化、项目化。学校应与企业行业协同改造、开发课程,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教学内容,整合课程知识点,并延伸和深化知识体系,形成模块化、项目化的职业性课程。“项目化工作室制”[20]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形式。也就是说,大学教师把自己承担的项目进行优化后,成立“学生工作室”,工作室设有相应的工作岗位,保证每个进入工作室工作的学生承担与各自专业相关的工作。项目化课程教学主要是以师生互动、生生合作的方式开展。学生在这种项目化课程教学环境当中会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主动学习、分析、思考,主动创新知识、应用知识,并从中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