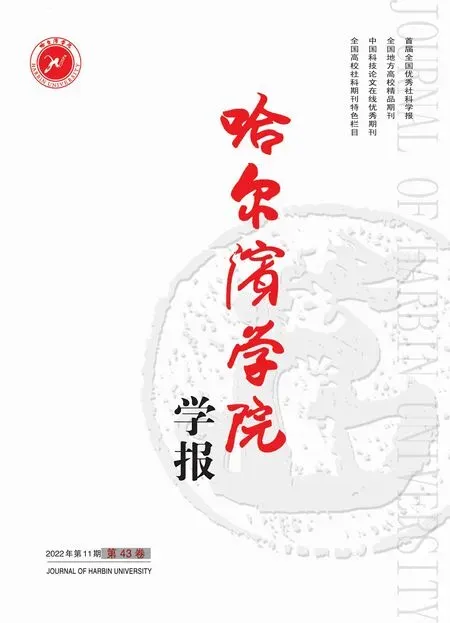混沌中的乌托邦:《英伦见闻录》中的田园诗
张奇才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代表作《英伦见闻录》(The Sketch Book)于1820年出版后受到英美文学界的关注。学界对于这本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中的两篇短篇故事《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上。这两个短篇被誉为“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故事”。[1](P305)由于研究重点集中于上述两部短篇小说,对于整部作品的系统性的研究较少,而从生态批评角度的研究就更为缺乏。然而,汉森(Jessica Allen Hanssen)的《欧文〈英伦见闻录〉中的跨国叙事性和田园主义》一文以《英伦见闻录》(以下简写为《见闻录》)整本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书中的文艺流放叙事(narration of artistic exile)与田园主义的关系。[2]汉森对于书中的叙事和田园主义的态度是否定的。她认为欧文试图弥合英美两国爱好、设想和历史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从而迎合大西洋两岸的读者的预期和品味;《见闻录》之所以广受好评,其原因在于书中展示的图景反映了两国的长处,而非他们的弊端。汉森认为,书中的英格兰是田园诗般的、传统的、没有威胁的;书中呈现的内容是他认为读者希望读到的,他希望获得赞誉,寻找归属感并且获得一种特殊身份。在这样一个田园诗般的乡村场景中,即便是苦难也显得甜美,所有的人都不需要为工作而操劳。通过这样的设置,欧文向美国和英国读者展现了他们各自最好的一面:对于美国人来说,美丽的乡村可以成为他们在新大陆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汉森最大的问题在于她对田园诗的过于绝对化的论断,她认为书中的田园诗一无是处。此外,她还无视《见闻录》中揭露的社会弊病以及作者对社会批判的态度。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田园诗虽然因逃避遁世为人诟病,但其勾勒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的生态图景,给人以希望和生态启示。欧文并未回避在乌托邦的阴影下存在的丑恶,他直面社会问题,在作品中流露出他的批判性。
一、田园诗
特奥克里特(Theocritus,c.308-c.240 BC)被誉为第一位田园诗诗人,但“真正对英美田园诗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70-19 BC)”。[3]在他的《牧歌》(Eclogues)里,诗人发现了阿卡迪亚(Arcadia)这一融合了神话和现实的理想田园,《牧歌》也成为了英美田园诗的源头。
田园诗这一体裁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里不断发展,“田园诗”定义的外延也从最初的一种严格的文学形式扩展到对乡村生活的一种虚构的或者理想化的模仿。只要是描写和歌颂乡村生活、自然环境的写作都可以称之为田园诗。[3](P84)伴随着田园诗的发展,这一体裁受到了广大批评者的诟病。田园诗为表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良好的载体。[4](P83)此外,田园诗暗含的遁世和逃避的态度默许了对待社会不公所表现出的麻木和胆怯,它根本无法成为变革根深蒂固的社会体制的催化剂。[4](P83)
但是田园诗在绿色书写和批判现实的事业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虽然田园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在政治上追求“无为”的代名词,田园诗里总是蕴含着一种吸引作家和批判者的乌托邦的意味,敦促着他们寻找一种更加美好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愿景。[5](P52)虽然田园诗总是以一种怀旧的目光感伤那已经消逝的过去,田园诗倡导的理想主义,尤其在美国这一国度,蕴含着一种肯定和追求更新、更好的世界的想象的潜力。[5](P52)田园诗会勾勒出乌托邦的理想的图景,但这并不意味着田园诗里不存在矛盾和张力。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虽然田园诗描绘了理想化的情感和意象,田园诗中“总是存在着与其他经验的张力:如冬与夏之间的张力;享乐与丧失之间的张力;收获与劳作之间的张力;歌唱与旅程之间的张力;过去、将来与现在之间的张力”。[6](P18)田园诗总是存在于“反讽”的阴影之下,它如同一种鬼魅的存在,总是会意识到正是那挥之不去的被压抑了的暴力促成了它勾勒的理想世界。因此,在极力逃脱这脱节的时代的时候,田园诗与这个时代发生交锋。
二、乌托邦
提氐卢斯你啊,在榉树繁枝造就的华盖下斜卧,
……
他允许我的牛犊在林间徘徊嬉戏,
也使我如我所愿,恣意吹着我的牧笛。[7](P3)
在维吉尔的《牧歌》的第一首诗歌最开始的几行中,提氐卢斯躺在树下,周围是他的羊群,他惬意地吹着笛子。这幅景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田园诗描绘的理想状态中重要的元素:乡村田园;牧羊人吹奏笛子所象征的艺术;牧羊人和牛羊的和谐相处。这些要素在《见闻录》中也有着浓墨重彩的表现。
当贝弗利(Robert Beverley)在《弗吉尼亚州的历史和现在》(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一书中把弗吉尼亚比作“世界的花园”时,他指涉的是神话意义上的花园。花园代指的是最原初的和谐、美丽和富足。在贝弗利看来,弗吉尼亚就是当代的具有原始风味的伊甸园,在园内居住着道德高尚的土著居民。[8](P15-16)这一意义上的花园将贝弗利渴望天堂的情感与各国神话勾连起来。而当贝弗利说到弗吉尼亚的花园太少了的时候,此时他口中的花园是指实体的、人为开垦培育的花园。美国的景色总是原滋原味,没有人工的痕迹。欧文在《见闻录》中描写的美国正是处于这种天然去雕饰的状态中,他是这样描写哈德逊溪流的:“这样一条野涧清流,使我们浪漫的幽居地野趣盎然,美景处处,足以让一个寻奇揽胜的人写满大部分见闻札记。有时溪水从奇石峭壁上飞泻而下,形成小瀑布,树木伸出宽大的余枝覆盖其上,长长的无名野草也像流苏一般从溪边垂吊而下,滴着钻石般晶莹璀璨的水珠。有时在密林幽深的沟壑,激流汹涌,轰鸣山谷,回荡林间,在此狂奔过后,悄悄流到无隐无饰的天光之下,汇成无比娴静端庄的河流,引人无限遐思。”[9](P226)
相比之下,英格兰的土地总是表现出人工雕琢的痕迹。欧文表示:“岛国很大一部分都是平地,若非人为雕饰,定然单调无趣”;“在耕种土地和所谓园艺学上的情趣,英国人称得上举世无双”;“英国的公园风光最让人印象深刻。宽大的草坪如同一片鲜绿的地毯,上面点缀着灌木丛和大树,堆积着厚厚的落叶……一些乡村教堂或树林雕像,在岁月的流逝中变潮变腐,长满青苔,更增添了一种神圣和隐逸之美”。[9](P35-37)在乡村之中,美丽的风景中点缀着牧场和整齐的村舍之类人工的痕迹。风景被人力整理地秩序井然。当涉及到对自然和环境的管控时,很多人是持赞成态度的。卡森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合理的适应”(reasonable accommodation),[10](P261)“精心的管控”(sensitive “management”)。[10](P80)在《见闻录》中英国人就很好地遵循了这一原则,他们改造自然,但是他们的农场和村舍与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构成了美好的图画。
在论述田园诗中的反作用力时,马克斯介绍了田园诗中的死亡意象的存在。“在17世纪,尼古拉·普桑(Poussin)和其他山水画家将象征死亡的栩栩如生的骷髅意象引进最细腻的风景画中。为了使这个死亡象征(memento mori)的意义更为确切,他们有时候插入印花题句‘我也在阿卡狄亚’(Et in Arcadia Ego)”。[11](P17)在《见闻录》中,死亡被融入风景之中,并非作为一种反作用力的存在,而是为风景注入了更多的和谐因素。在英国南部一些偏远乡村,如有年轻的未婚女子去世,会在葬礼上举行“最精巧最美丽的一个仪式”。[9](P88-89)一位年龄、体型和样貌相似的年轻女孩会将一个白色花环置于死者胸前,随后再将其挂到死者在教堂常坐的座位上。不仅仅是死者的身体会得到装饰,死者的坟墓同样会得到装饰。“伊夫林在其作品《森林志》中说:‘我们用花朵和芬芳的植株装饰他们的坟墓,只是以此象征人的生命,《圣经》中有这样的喻句,生命是一种渐渐凋零的美,根茎深埋于耻辱中,却在荣耀中再次升起’。”[9](P90)生命是一种美,死亡虽结束了这种美,肉身会“坠入‘黑暗和蠕虫’的世界”,[9](P40)而这种生命的美却通过死亡以元素的转换和新的形态到达新的荣耀。如欧文在书中所说:“世上万物均有灭亡的一天,但同时,组成万物的元素却永久不灭。”[9](P46)这里欧文在有意和无意间呼应了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出版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观点,有机物和无机物、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弗兰肯斯坦的生命正是来自于那些已经没有生命的尸体。书中的英国村民对于死亡怀有较为乐观的态度,所以他们将葬礼艺术化。“我怀疑,当地村民在为爱人的坟墓编织新鲜美丽的花环时,是否想象自己在践行诗意幻想中的一个仪式,想象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诗人。”[9](P97)
为年轻的未婚女子去世举办葬礼时体现出了浓重的艺术气息,艺术(art)也就步入了田园风景。对于“art”有不同的解读。在《牧歌》中,“art”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吹奏笛子。在解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he Tempest)时,马克斯将普洛斯彼罗的“art”解读为技艺。[11](P38)普洛斯彼罗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并且取得胜利也正是“依赖于技艺(art)——类似于科学技术的善意的法术(magic)”。[11](P38)“读过《金枝》(The Golden Bough)或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著作的人知道,法术(magic)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尤其是人在面对物质自然时必须保持的姿态问题上,它们心照不宣。”[11](P38)在《见闻录》中,“magic”(法术或魔法)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当魔法成为《撰书术》中撰书者追求的最高目标时,魔法成为一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语。“时有一人在小纸片上写下点儿什么,然后按铃,出现一个仆役,悄声取走纸片,滑出房间,不久后抱着沉重的书卷返回,之前那人就一头扎入书堆中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我怀疑自己碰上了一群魔法师,正沉迷于神秘科学的研究。”[9](P44-45)这些专注的撰书者可以使读者联系起《格列佛游记》中飞岛国中的科学家。他们试图从黄瓜里提取阳光,将粪便还原为食物,即便身上沾满污物也浑然不觉。这些忘我的撰书者所追求的魔法竟然是“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识。[9](P45)显然,《见闻录》所推崇的“art”艺术并非这种征服的、控制性的魔法。艺术和魔法在《见闻录》中更多地指代以阅读为底蕴的想象力。在书中,藏书的地方会被比作“施了魔法的城堡”。[9](P44)魔法更多地关乎心灵而非理智。莎士比亚被欧文在书中誉为伟大的诗人,“所有作家里头,他最可能永垂不朽。其他人用脑子写作,他却是用心写作,所以用心的人总能读懂他”。[9](P87)阅读可以丰富想象力是无疑的。想象力在风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艾狄生表明,视觉是最理想的官能,也是我们从想象活动中获得快感的真正来源……它(想象力)提供了明显而容易获得的快感:‘只要双眼睁开,景象便会进来’。”[11](P67)通过想象,当叙述者在垂钓时,他可以在脑海中徜徉在著名作家艾萨克·沃尔顿(Isaac Walton)的关于垂钓的诗篇和章节中,更加深有体会地融入到垂钓的过程和周围的风景之中。当叙述者在城堡中漫步时,通过想象他可以和历史上的人物展开对话。通过想象,叙述者可以看见不复存在的《亨利四世》中的猪头酒馆里的热闹非凡。想象使得本已美丽的风景罩上了魔幻色彩。通过想象,被囚禁的皇家诗人詹姆士可以在脑海中享受到自由:“这就是想象力的神圣之处:不可抑止,无法禁闭。现实世界被关在大门外时,它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以神术魔力,变幻出各种美妙的形体和绚烂之景,照亮阴暗的地牢,使孤独之所热闹纷呈。”[9](P51)
《见闻录》中的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谐。当叙述者跟随布雷斯布里奇先生来到他的家的时候,布雷斯布里奇立刻就被他的宠物狗给围住了。“特雷、布兰奇、甜心,哦,小狗——所有狗都在朝着我叫!……这些忠实的动物团团围住了他,大肆亲吻爱抚他。”[9](P129)这里的画面反映了主人和狗之间的亲密,也展示了人类给予狗的尊重,每条狗都有自己的名字,一旦拥有了名字,狗就拥有了自己的独自的个性,不再是“犬科动物”这一模糊的概念。书中最和谐的场景里总是有动物的存在。囚禁中的詹姆斯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画面就是“那动物潇洒驰骋的世界”。[9](P53)此外,人类也经常被比喻作动物、植物,深化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当詹姆斯被囚禁的时候,他被比作一只“笼中的夜莺”。当女孩因为失恋而心碎时,她被比作了一棵正在枯萎的树。
三、混沌
汉森认为,《见闻录》中的英格兰是田园诗般的、传统的,“在叙述者表述的英国的乡村,我们发现不了受苦的佃农和流离失所的农夫,在叙述者描写的英格兰所处的时代,这些问题正是当时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叙述者描写的乡村的天堂里,农夫们个个举止端庄高雅,农民整齐温馨的农舍(好像每个农民都有农舍的样子)显示了他们高贵的品味”。[2](P10)汉森认为,为了讨好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读者并且获得他们的好评,欧文不敢揭露社会丑恶,因为这样会冒犯他们。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在作为英美田园诗源头的维吉尔的《牧歌》中,第一首诗歌描绘的不仅仅是理想化的田园乐趣。在维吉尔开始勾画这理想的图景的时候,他也揭示了来自于乡村之外威胁着乡村的充满敌意的世界。在乡村之外,罗马这样的大城市,组织严密的权力、权威、抑制、痛苦和无序等都构成了对乡村神话的侵入。在理想世界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田园诗表现了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所说的“在混沌中的片刻安宁”。欧文发现并在《见闻录》中揭示了农民的苦难,并且对于造成他们苦难的帝国扩张予以抨击。
农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公在《见闻录》许多篇章中均有体现。在《寡妇与她的儿子》中,“我陷入了沉思,世间有等级区分,入了土仍有阶层划分”。[9](P65)穷人在生前就受苦,到了死后,他们仍被看作是低人一等,连一场中规中矩的葬礼都无权享受。葬礼“一切马马虎虎,遵照形式进行,冷漠无情”。[9](P65)阶级意识成功地做到了深入人心,即便权贵可以选择对农民们平等对待,底层的农民们也清晰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权贵交往时会表现出“惯有的尊敬的态度”。[9](P61)《寡妇与她的儿子》还表现了农民的贫苦的生活,“有一年农业收成不好,小伙子只好冒着风险去了附近一条河边,以一艘小船做起了摆渡营生”。[9](P67)欧文没有清楚地交待农业收成不好的原因,但是清楚无误的是农民家庭的经济困难。这一困难在小伙子被抓到海上做苦力后更加地激化了。原本就体弱的父亲越来越郁郁寡欢,最终死去。寡妇年老体衰,无法再养活自己,只能接受教区的救助。在《圣诞日》中,当老先生按照古老的习俗邀请穷人到家里欢度节日时,“村里所有的流浪汉都涌到庄园里头,一周内聚集到附近的乞丐,比教区人事一年打发的人还要多”。[9](P144)乞丐的数目之大也说明了乡村生活的穷苦。
在《见闻录》中,殖民扩张的影响已经触及到乡村。在《钓鱼翁》中,叙述者被一位钓鱼老人的从容豁达,与世无争的气质所打动。但是随着叙述者对钓鱼老人的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许多与最初那位融入自然的老人的形象相左的事实。老人看起来无牵无挂,过着超然闲逸的生活,但是他之所以会极具耐心地教导两位乡下学徒的原因,就在于他期望着其中一位学徒(即将继承乡村酒馆的经营权)能在酒馆里能给他特殊的照顾。老人装着一支木质假腿。这样一个半机械人似乎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但是这个老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白鲸》中用鲸骨做义肢的亚哈,而亚哈的终极目标就是捕杀被许多学者认作自然象征的白鲸。老人曾经是海军,老人的住所也按照海军军舰的营房的风格布置。房顶上是船形的的风向标,屋内的家装也是航海风格。一个吊床从房顶上悬吊下来,白天就捆扎起来节省空间。架子上摆放的书籍是航海书和航海历。老人的一条腿在坎伯当海战中被炮弹炸掉。坎伯当海战正是英国和荷兰争夺海上霸权的一场战争,是两国殖民扩张过程因利益冲突所致。老人还养了一只黑猫和一只鹦鹉,这些细节都直指鲁滨逊·克鲁索。鲁滨逊也曾参加过航行,在荒岛上占领土地,驯化动物,他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先锋的代言人。钓鱼的老人同样也保留着殖民扩张的种种痕迹。即便在宁静的乡村里,读者也可以发现殖民扩张的不和谐的存在。
欧文在一定程度否定并抨击殖民扩张。在《海上之旅》中,叙述者虽然把殖民扩张的主要工具轮船誉为“人类发明的这一伟大丰碑”,[9](P2)但是他即刻就开始关注大海航行给水手带来的苦难,众多的水手“连纪念物都没有留下一个,人们只知道,船儿离开港口,‘从此杳无音讯’”。[9](P2)殖民扩张给帝国带去的是利益,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只有悲伤。《寡妇与她的儿子》中被抓到海上干苦力的小伙子很可能也成为了水手,回来时筋疲力尽,苟延残喘,成为了殖民扩张的牺牲品。对于那些直接参与了殖民扩张的武士,叙述者的态度只有轻蔑。“往昔那些英雄,对我或我这样的人有何益处?他们征服的国家,我不曾享有半亩土,他们获得的荣耀桂冠,我未得继承半点儿,他们树立起的莽夫勇武之榜样,我没机会,也没那喜好去效仿。”[9](P73)
欧文在《见闻录》中描绘了混沌中的宁静的场景。在这乌托邦的国度里,有着艺术气质的人们以道德情操耕耘、美化了乡村的景色,在此美景中,死亡也不再让人恐惧。这一和谐的蓝图可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给予启示。与此同时,欧文并未无视宁静外的混沌——那威胁理想田园的社会弊病。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不公、贫困,以及殖民扩张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伤痛。欧文的田园诗集合了光明和丑恶,需要我们的辩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