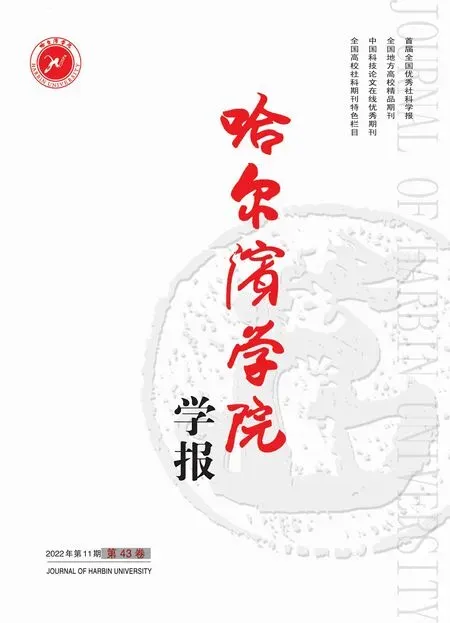苏童《河岸》中历史和命运书写的理性维度
钱嫣荷
(滁州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苏童在作品《河岸》中,通过精巧的叙事安排,围绕历史和个体人生命运进行了深刻的理性认识,展现出历史、人生虚无荒诞的一面。苏童通过三个维度在叙事中构建理性认识,即无法考证的历史起源背后的理性思考,突发因素背景所蕴藏的理性思考,以及对虚无历史本质解构背后的理性思考。这三大理性维度之间是由大到小、层层深入的关系,首先从“无法考证的历史起源”这一宏大视角着眼,从烈士邓少香的事迹切入,阐释了其模糊的历史身份;在此基础之上,又将突发因素植入叙事之中来主导人物命运,反映了历史背景下个体的人生命运状况,最后从一个个具体化的词汇意象入手来探寻虚无的历史本质。由此可见,写作逻辑体现出由模糊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的变化。除了对历史、命运的理性认识,这三个维度也展现出苏童对历史叙事的一种重新书写,让历史成为了文本中一种纯粹的叙事语境或者情境,从而能够更为清晰和理性化地表述历史和个体人生命运之间的关联。
一、无法考证的历史起源背后的理性思考
苏童作为20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先锋作家之一,其在小说叙事中,非常善于将“历史”模糊化,让他笔下的故事没有确切的历史起源,这种先锋写作完全颠覆了遵循历史规律和历史特征的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写作范式,使“历史”成为文本中一种纯粹的叙事语境或情境,于是具体的历史性被消解,文本获得了极大的想象力空间。在《河岸》中,苏童让历史丢弃了具体的时间所指,成为一种叙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拥有巨大意义或想象力空间的超验能指。[1]具体而言,苏童为库文轩、库东亮这两位主人公的故事事先设定了一个模糊、无法考证的历史起源,即他们先人邓少香烈士的事迹。这种设定反映了苏童对于历史的一些崭新思考。众所周知,以苏童为代表的那一代先锋作家群体在早期写作上强调要远离现实,躲入历史的最深处,即个人对历史最深刻的记忆之中。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商品消费主义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兴盛导致文学热度递减,先锋作家们开始意识到文学的纯粹性让他们在大众面前显得更为孤独、个性,于是他们纷纷躲入自己对于历史的记忆深处,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认知开始私人书写,在作品中表达哲思和生存之悟。在他们书写的小说故事中,“先辈”或是先验性地缺席,或是先验性地死亡,从而终结了小说故事的历史起源,让历史无证可考以及展现出自身没有确指的虚无化本质。这种阉割历史起源的写作方式在与苏童同时代的作家余华的作品里也会经常看到,无论是在《往事与刑罚》还是《难逃劫数》中,余华都精心构建了一个没有历史时间和历史地点,充斥着荒诞、阴谋、死亡、罪行的乌有之乡,这也是余华对历史的深刻记忆和认知。同样,苏童也是如此,通过对人性的反映、对历史与人物命运之间复杂关系的展现,以揭示自己对历史虚无且荒诞一面的深刻认知。[2]
在《河岸》中,烈士邓少香的事迹是整部小说叙事的基点,后面的情节都以此铺垫展开,然而邓少香具体的历史身份又是极为模糊不清和不真实的。邓少香不仅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某位人物,甚至小说中也根本就没有很清晰地交代她的人生轨迹。苏童在《河岸》中之所以如此设定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叙事的起源,其实大有寓意。苏童曾深受过20世纪著名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影响,在德里达看来,叙事中一切的“在场”都是对“不在”的填补,但这种填补并非因为暂时的缺席而是因为本源出现了永恒的缺席,于是对“不在”的填补进一步加剧了本源的缺席。简而言之,对本源的追溯越是急迫、深刻,就越深刻地揭示出本源的永恒缺席。正是根据于此,苏童通过精心制造一位历史身份模糊的人物作为叙事起源,就是为了更深刻直接地揭示历史起源的缺席和不可考证。既然历史起源无法追溯,不可考证,那么对于历史的真实性就可以持可疑或否定的态度。这正是苏童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叙事所反映出的历史观,这在上文也已论述过。而苏童在叙事安排上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他事先制造了一个起源,而后又通过这个起源的模糊性在写作中埋入了怀疑的种子,并随之以此为基点在接下来的叙事中铺展开许多精彩情节。纵观《河岸》整篇小说叙事,作为叙事起点和故事历史源头的邓少香烈士身份虽然模糊可疑,但是却给家族带来了荣耀,不过最后也间接地导致了两位主人公命运的坎坷。这种在人物生存发展过程所展现出的命运落差,不但让叙事起点的设定显得更有悬念性,让情节在推进中不断引人入胜,而且还使得结局的讽刺意味更为深刻,令人震撼。总之,苏童在叙事上通过对邓少香的模糊历史身份进行巧妙的安排设置,不但表达出自己对历史的一些深入思考,还让作品的叙事发展更具故事性,能发人深思。
二、突发因素背景所蕴藏的理性思考
苏童的小说作品充满了绵软细腻的动人抒情,展现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对人类隐秘情感的洞察,这使得其小说具备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姿态。而其作品中精致、诡谲、优美、凄美的语言修辞,更是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语言风范,发扬了汉语言婉约的诗意特质。所以苏童的小说总是会被文学评论家贴上诗性的标签,读者总会被其叙事中,瞬间迸发而出的诗意火花所吸引。[3]例如在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里,苏童是这样描绘一个女人的分娩场景:“蒋氏干瘦发黑的胴体在诞生生命的前后变得丰硕美丽,像一株被日光放大的野菊花尽情燃烧。”苏童将被命运折磨成干瘦发黑模样的女性苦难与女性丰硕美丽,犹如野菊花般燃烧的生存壮美,一起通过诗意的语言和自己独特的生命感性体验展现出来,反映了生命的不屈精神。这是一种苏童式的诗性感悟,但在《河岸》里却很少看到这些,反而里面充斥的尽是关于人性与命运的理性思考。而为了展现出自己的此类理性思考,苏童在叙事中植入了很多突发的偶然性因素,以承载自己的命运观,揭示命运的荒诞性。
在《河岸》里,突发偶然因素一般包括偶然事件,以及突然迸发的能够驱使人物行为的心理冲动。在偶然事件中,不得不提的是鱼形胎记的突然出现,这可谓是《河岸》全篇叙事中最先发生的偶然事件。当鱼形胎记出现,小说中对其的指认情节尽显滑稽、讽刺意味:“封老四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在男孩们的屁股前走来走去,他先淘汰了四个无关的屁股,留下三个,仔细地辨别那三个小屁股上的青色胎记,他的手始终卖着关子,高举不落,举得周围的群众都紧张起来,育婴员从各自的感情出发,七嘴八舌地叫起来,左边,右边!拍左边的,拍右边的!最后封老四的手终于落下来,啪的一声,不是左边的,也不是右边的,他拍了中间一只小屁股,那是最小最瘦也最黑的屁股。封老四说,是这个,胎记最像一条鱼,就是他,一定是他!”于是,就根据他人胡乱、随意的指认,库文轩在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被认定为邓文香烈士的后裔,这让其人生命运第一次发生了大转变。从此库文轩作为烈士遗孤开始在岸上受到各种生活上的优待。但是后来,当他的鱼形胎记遭到怀疑,他的所有待遇也都被取消。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曾经岸上风光无限,被众人艳羡的库文轩就被隔离起来,遭到审查。最后他连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只能在河上漂泊,成为一名落魄的渔户。而苏童通过对库文轩这种由偶然事件所导致的命运落差的详尽叙述,将特殊时代背景下个人人生的荒诞性和戏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对命运无常性、偶然性的感慨。除了在叙事中植入偶然事件,苏童还善于通过描述人物瞬间的心理冲动这种突发的偶然因素来反映人生和命运发展的荒诞性、偶然性。在《河岸》中,库东亮这位人物角色的命运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库东亮一开始之所以要去和父亲库文轩一起生活,是因为他突然对河岸上的生活充满期待。然而,正是库东亮当初一时的冲动和期待,使得他后来的命运与父亲的命运彻底绑定在了一起。事实上,库东亮的很多生活行为与生活抉择都是受自己内心的心理冲动主导,完全缺乏理性思考。除了上述所说的因为一时出现的心理渴望选择了和父亲一起生活外,他还因一时的青春期躁动在理发店和别人发生冲突。而最能体现其易冲动性的是偷窃石碑的经历。在准备偷窃前,库东亮其实未做过一丝一毫的准备,他的偷窃行为完全源于偶然出现的念头:“刹那间我脑子里灵光一闪,热血沸腾,一个辉煌而疯狂的念头诞生了,我不能空手而归吗,我要留下纪念碑吗,我要把纪念碑带回家,我要把邓少香烈士的英魂还给我父亲。”
总之,纵观库东亮的人生,推动他命运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其内心的心理冲动,这种偶然的因素会时不时地对他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人生推波助澜,主导着他的人生方向,将其命运引入荒诞之中。最后,库东亮的生命轨迹和他父亲库文轩一样,充满了偶然性、戏剧性,他莫名地过上好生活又莫名地落魄,成为河流上的流浪汉。如果说苏童将一个不可考证的历史起源和人物身份作为《河岸》这部小说叙事的基点模式是为了让叙事更为精彩有内涵,表达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那么其又将各种突发因素植入叙事之中来主导人物命运、不断推进情节发展,则是为了反映历史背景下个体的人生命运状况,展现出了自己对于人性的关怀、思考。足见,在《河岸》中,苏童的理性视角不仅仅注视的是宏观化的历史本身,还有那些处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诸多人物命运。正因如此,苏童的这篇小说字里行间都散发出了人文精神的光辉,将特殊历史背景中的人物命运刻画得细腻而又悲悯动人。[4]
三、对虚无历史本质解构背后的理性思考
在《河岸》中,苏童制造了许多词汇意象,蕴藏着深刻的隐喻,而其具体的能指意义又包含着一种解构的意味。但苏童的解构并不是无端的批判和否定,而是立足于历史本体的一种极具洞察力的理性思考。苏童正是通过词语意象意义的无限播散,以及在不断更迭的叙事语境中的不断被消解,来反映出历史的虚无本质,实现对主体所赋予的历史属性的解构。在这部小说中,最为明显和具有深刻隐喻意义的词汇意象就是“河”“岸”。“岸”象征着人类生活的居所,是滋生罪恶的土壤。而“岸”的对立面就是“河”,因“河”具有流动属性,所以它象征着被流放驱逐。小说中,库文轩和他的家人一开始被认定为烈士后裔,所以得到特殊照顾,摇身变成了掌握权力的书记,在“岸”上过着优越的生活,而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让库文轩变得放浪不羁。[5]后来,当库文轩的烈士后裔身份遭到周围人的怀疑时,他的一些恶劣行径被人不断揭发,于是他从岸上被驱逐出去,成为在河上漂泊的一位贫困渔户。总之,在对库文轩人生轨迹的叙述中,苏童巧妙地通过“河”“岸”意象概括了他不同时期的命运,并通过两个意象的对立展现了库文轩命运的大起大落,实现了对其身份的消解,即从显赫一时的书记沦落为一无所有的渔民,而这种身份的消解实质上也意味着对库文命运以及与主导他命运的特殊时代历史背景实现了解构,揭示了历史和人生命运荒诞、虚无的一面。除了“河”“岸”,小说中还有很多极具隐喻意义,并带有解构意味的重要意象,例如鱼形胎记和石碑等。《河岸》中,鱼形胎记在所指上真假难辨,既明确又模糊,具体而言是,它作为烈士后代的胎记曾确定了库文轩的烈士家属身份,但是后来却又成了质疑其身份的证据。而库文轩的人生轨迹正是在对鱼形胎记进行确认和否定中起伏不定、大起大落。足见,鱼形胎记是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意象,除了主导故事情节发展外,它更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隐喻着烈士的优越血统。苏童表面上看似是在写鱼形胎记摆布个体的命运,其实质却是在表达对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顽固思想深处历史血统论的批判、解构。而石碑意象作为对历史的承载,隐喻的就是历史本身。它对烈士历史事迹的记录彰显了库文轩身份的尊贵。可见,石碑与鱼形胎记一样,都是库文轩烈士后裔这一光荣身份的象征。无怪乎库文轩当上书记后,非常注重保护石碑,哪怕后来他被流放到河上,对石碑仍念念不忘。另外,苏童还以石碑坚挺的存在隐喻男性雄性魅力,石碑和鱼形胎记所确保的库文轩历史血统正确性与他的男性魅力值成正比关系,当石碑上的烈士功绩受人敬仰、膜拜的时候,正是库文轩仗着烈士后裔身份在岸上耀武扬威,不断释放性冲动的时候,而之后当他无法保护石碑,他的性冲动也随之枯萎。苏童通过石碑的双重隐喻,即对历史和男性雄性魅力的隐喻,在叙事情境中展现了历史这一宏伟、激情的符号和个体性狂欢的消长关系,最后用个体性欲的枯萎来象征历史的崩塌,从而彻底解构了历史,反映出历史的虚无本质。[6]
另外,《河岸》中还出现了日记、小铁梅、红灯等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意象。日记意象在所指上有两重意思,它既是记录库文轩风流韵事的罪证,又是库东亮获得性启蒙的源头,承载着青春期的他对慧仙的怦然心动。虽然库文轩的不耻行为让日记散发着罪恶,但是它也被烙上了库东亮青春的印记。而从日记的能指上看,实质上其隐喻着一种生命原始力量的传承。不过,日记内容中闪烁的生命活力却最终招致命运的嘲讽。苏童通过日记意象展现了自己对人性的洞察力和基本关怀。而小铁梅、红灯这两个象征革命身份的人物意象,则体现了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政治对个体存在状态的深刻影响。小铁梅和红灯都是慧仙为了能够逆转被命运而变换的身份。但是这种迷失和抛弃自我的方式却没有让她得到救赎,反而让其最终从一个受周围人崇拜的名人,变成一个落魄的剃头匠。苏童正是通过叙述慧仙人生的无常、荒诞,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政治信仰和个体生存状态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纵观上述的日记、小铁梅、红灯等意象,它们都具备反讽性,而这种反讽也正是一种对意象意义在无限播散中的消解。实质上,它们也与河、岸、石碑等词汇意象一样,都是围绕着历史和人生命运来实现意义上的建构、解构。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河岸》在写作手法上有着明显的炫技色彩,缺乏自然性,这是因为苏童一改往常的写作方式,不再通过直觉、感性思维来进行诗意化叙述,不再将历史完全置入虚拟化和审美化的语境之中,而是重视对历史和人物命运进行理性思考,以理性化、逻辑化的写作法则来进行叙事,所以《河岸》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了写作上的匠气色彩,具有不少刻意的写作痕迹。这体现了苏童对自我写作范式的一种更新,虽然《河岸》太过匠气,但是在苏童的匠心独运之下,这部小说也很好地表达出了自己深刻的历史观,反映出了自己对人性和人生命运的洞察等。而在理性的洞察背后,是苏童对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个体的深切同情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