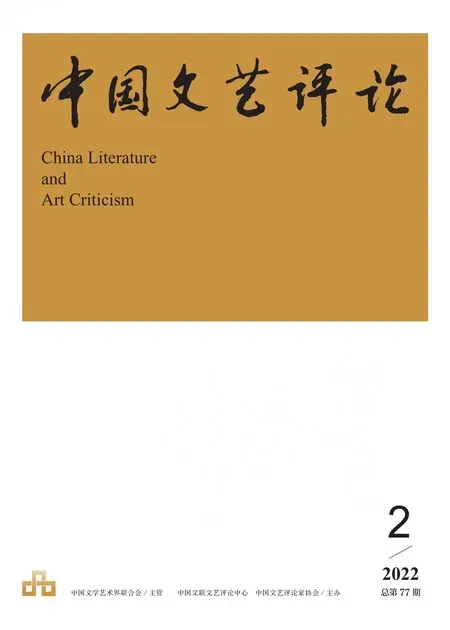“元宇宙”何以成为文艺“新生”的契机?
■ 杨 光
刚刚过去的2021年无疑是“元宇宙”元年。恰如赋予其名称的那篇科幻小说,“元宇宙”的降临终将在未来引发一场“雪崩”。面对这又一个“大事件”,人们或欣喜地惊叹于其即将带来的壮丽,或恐惧地对其潜藏的危险发出战栗的预警,或悲喜交加地等待着、冷眼旁观。但无论悲喜亦或漠然,“元宇宙”的到来似乎势不可挡,如同生命的洪流总要继续。人类纪里的一系列技术事件已然反复证明了如下观点:没有人可以逃离技术,因为“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技术事件”。即便是“后人类”也仍旧处在“技术—人”的历史延长线上而非决然地断裂。雪崩发生时,没有谁是无辜的,文艺也不例外。问题只在于,“元宇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赋予文艺“新生”以契机,而不会沦为将其“终结”的黑洞?
“元宇宙”是Meta(元)和Universe(宇宙)的合体。最浅显的意义上,Meta,即初始,Universe,即万象。因此,“Metaverse”一词毫不隐藏其创立某种包罗万象之初始的宏大企图。正是这股近乎创世纪般的气势激发着扎克伯格等数字技术贵族们的资本想象力,亦进而催生了人人竞言“元宇宙”的心理原动力。然而,沉浸在狂热畅想曲中的人们却大多忘记了“宇宙”在英语中的另一个名字——“Cosmos”,秩序。当扎克伯格把Facebook更名为Meta时,这个删除“Universe”的行为似乎不是一时疏忽。如果“宇宙”不仅仅意味着“万象”,也意味着“秩序”,其完整的含义是“有秩序的万象”。那么,任何的“元宇宙”畅想及其实践就不得不明确它究竟要将何种秩序赋予万象。而一旦言及“秩序”,数字技术资本的隐形操纵之手几乎将无所遁形。或许数字化生存已经多年的“两栖”人类对一个包罗万象的拟真“平行宇宙”的出现不会过度抵触,但如果让人们都认同这个宇宙的“万象”只能以数字技术的资本秩序为基底,一个超级数码版的迪斯尼,试问谁会心甘情愿?因此,可以认为,“元宇宙”必须面对其自身提出的一个宇宙论新题:不是能否包罗万象,而是怎样包罗万象?就文艺而言,对此问题的直面与探索蕴藏着伴随“元宇宙”降临而来的新生契机。
有观点指出,文艺其实早就是“元宇宙”了。倘若对此断言中漠视技术论形而上学的可能倾向施加一定限制,则此断言具有部分的真理性。其真理性在于: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文艺形式,在“技艺”的人造物意义上,其实一直都与技术物的历史进化相伴而行,宛如一对孪生子。无论是对感知方式的延伸与形塑,还是非具身式的具身化显现,亦或通过虚构的“谎言”将“真实”的存在深藏于谜底,文艺的物质与想象世界往往在诸多方面都先于“元宇宙”等技术物将其运行肌理与文化企图含纳其中。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机器人(Robot)、安卓(Android)、阿凡达(Avatar)、赛博格(Cyborg)直到元宇宙等技术新名词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宗教神话、剧本或小说等文艺词源背景的内因。此内因突破了语言学范式,属于技术论的形而上学。而之所以说此断言的真理性只是部分的,理由则在于,如果因为“技艺之物”对“技术之物”具有基于孪生的先在性就过于轻易地将“元宇宙”万象秩序的建立权拱手相让,这既是对文艺自身责任的懒惰放弃,也是对数字时代以来文艺价值“失向”现状的视而不见。
继机械技术、电气化技术之后的数字时代中,随着一波波新技术样态和产业形态的涌现,各式各样的所谓“新”文艺亦层出不穷。网络文学、数码文艺、交互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后人类艺术以及在“元宇宙”话语中频频露面的NFT艺术等,曾经的技艺之物在今天不断追逐着技术之物的千变万化,随之起舞亦疲于奔命,如同束缚于数字蛛网上的蚊蚋闪闪发亮。文艺追逐新技术的勇气固然可嘉,但若在追逐的过程中被技术带偏了自己的节奏,其美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价值维度被技术的单一标准消减于无形,那么不得不说这种追逐是彻头彻尾的盲从。亦由此,所谓的数字文艺之“新”也不过是如时尚变幻般的流变循环,一种失去方向感的横冲直撞,一种丰富无比的空洞,无秩序的“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