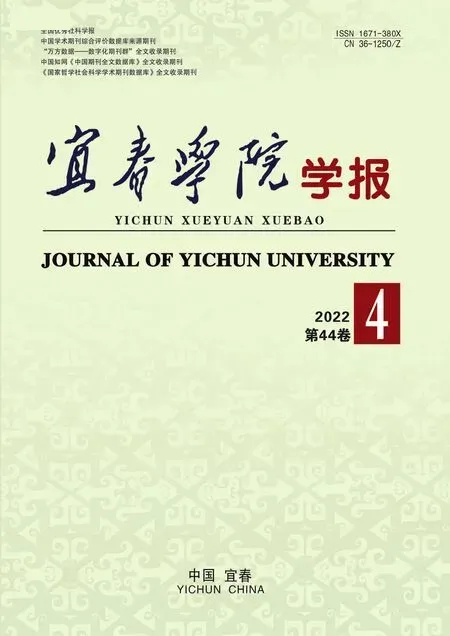福、德及两者的统一:康德幸福观的三大核心内容
王道林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作为哲学史上的贮水池,①康德的调和始于其对人的双重性的判断,将人视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并以此作为幸福观的出发点。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指出,人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作为感性存在物,它的欲求的满足是一种正当需求,非但如此,人对感性幸福的追求也还是人的一种责任,因为对自己处境的不满,生活上的忧患和困苦往往导致不负责任。[2](P48)
因此在康德幸福观中,若想达到真正的幸福,不仅需要思考人在感性方面的满足,同时也需要辅之以道德,作为能够配得此福的条件,并通过“三大悬设”论证了“德福一致”的可能,以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为幸福的实现找到了确证。不仅包含西方理性派幸福观的观点,而且也表现出感性派幸福观对其思想的影响,同时在德福一致问题上,又会发现与西方基督教彼岸幸福观的某些观点相契合。
一、感性幸福论:“福”的满足
(一)感性幸福论的地位:人的本质要求之一
康德认为追求感性层面的幸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也是合理的要求。他还认为,如果把至善的第二个要素即自身幸福实际上省略掉了,把这要素仅仅建立于行动和对自己人格价值的满足中,并因而只将它包括在对道德思维方式的意识之中,但在其中,他们通过他们自己本性的声音本来就已经能够被充分驳倒了。[3](P174)可见,追求感性幸福乃有限存在的个体之自然目的,是不争之事实。
而且对于感性幸福在其整个幸福观中的地位,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幸福的意图’是一切有理性的东西……确定无疑的前提,是每一个人所先天确有的前提,属于每个人的本质。”[2](P66-67)所以,满足人们感性幸福的需求实乃人之本质,是不可被否认的。但是就“至善”这个更高意义的价值而言,这种感性幸福的意图带来的实践活动往往与德性指导下的实践相悖,换言之,尽管幸福是至善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幸福却不完全等于至善。对于幸福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考量。
(二)感性幸福论的概念边界:“福”与“德”间的不可通约性
在日常的实践中,我们经常面临为了道德牺牲幸福,或为了幸福而放弃道德的两难境地。事实上,关于幸福与道德间关系的争论,一直都是古今中外伦理学讨论的重点。在这里我们以斯多葛学派为例,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早在希腊化时代,斯多葛学派就提出禁欲主义幸福观。②黑格尔曾这样评价,人必须依照本性而生活,这就是说,依照道德而生活;因为(理性的)本性引导我们走向道德。这就是最高的善、一切活动的目的;依照本性而生活即是过理性的生活。[5](P32)
乍一看,选择理性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斯多葛学派的理性生活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伦理相距甚远,这里的理性是抽象的、外化的、独立于人本身存在,在功能性上也是无所不包的并且以“神”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个目的论的世界里,理性指导下的德性生活是“神”指引给我们的本性的生活,亦即幸福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同样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人是双重性的存在,德性作为一种内在的声音,只是实现幸福的一个条件。尤其对于感性幸福的实现而言,欲望的满足始终是不能绕开的话题。禁欲主义忽视感性而片面强调理性的选择,显然不是真正的幸福。
从人的双重性角度出发,康德认为,感性的满足是幸福实现不可忽略的一环。人就他属于感官世界而言是一个有需求的存在者,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当然有一个不可拒绝的感性方面的任务,要照顾到自己的利益。[3](P84)
对于斯多葛学派以及基督教神学所主张的禁欲主义幸福观,康德对幸福与德性的关系进行了追问,最终认定这是不可通约的两个概念。并指出,对于幸福而言,我们就欲求或厌恶一个客体,那么这种事只要它和我们的感性及它所引起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相关时就会发生。[3](P82)另一方面,对于德性的目的——善而言,善与恶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意志的关系,只要这意志由理性法则规定去使某物成为自己的客体;善和恶真正说来是与行动而不是与个人的感觉状态相关的。[3](P82)简言之,幸福代表感性方面的满足,而德性则是与我们内在的理性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两者是不同质的概念,不可通约。
(三)感性幸福论的局限:有条件的“善”
尽管感性幸福与德性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但不妨碍通过德性的原则对人追求感性幸福的实践进行评价。尽管康德相信人的善良意志,但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也指出,任何的实践规律,没有不是把可能行为看做是善良的,从而对一个可以被理性实践地决定的主体来说,是必然的。所以,所有的命令式,都是必然地按照某种善良意志规律来规定行为的公式。[2](P65)而且这是一条假言命令,换言之,人追逐感性幸福这样一条命令式,只是一种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成为善良的实践活动,是以“幸福”为目的而非旨向“善”的假言命令。在康德哲学中,假言命令只是相对的“善”。③
既然幸福是具有双重性的主体本身的必然追求,但是以感性幸福为目的“命令式”又是无法提供绝对的善的假言命令。因此,对理性幸福的考察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理性幸福论:“德”的追求
(一)理性幸福论的地位:将“福”上升为“善”的必要条件
既然以感性幸福为目的“命令式”先天地就是假言命令,那么如何将这种在质料层面上为我们意志提供内在规定性的低级别欲求能力上升为一种高级别欲求能力?康德认为首先需要摆脱经验性质料的限制,以一种纯然的形式去规定我们的意志,并以此影响我们的实践原则,将个人追求幸福的原则上升为一种“善”的道德法则。正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所述:“在一个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意志的东西上,自然的真正目的就是保存它,使它生活舒适,一句话就是幸福,……,人们是为了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它作为最高的条件,当然远在个人意图之上。”[2](P44-45)换言之,理性虽然不是满足感性幸福的手段,但是理性的存在使得我们有了更高的目标。因此,若想追溯这种高级别的欲求能力,达到“至善”,必须发挥实践理性在实践行为中的建构性作用,以求为自身立法。
(二)理性幸福论的作用:以道德法则约束幸福原则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先对“原则”与“法则”在概念上加以界定。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开篇,康德便对这组概念予以说明,如果这个条件只被主体看作对他的意志有效的,这些原理就是主观的,或者是一些准则(笔者注:原则);但如果那个条件被认识到是客观的、即作为对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这些原理就是客观的,或者是一些实践的法则。[3](P21)显然,原则是一种主观性与相对性的主体欲求,正相反,法则体现的则是客观性与绝对性的理性。
在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上,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以同一性原则进行解释的。经验主义的幸福观从感性的维度出发,将幸福建立于欲望的满足上,视幸福原则等同于道德法则,亦将幸福原则作为评判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理性主义的幸福观从理性的维度出发,不仅重视理性的作用,甚至将理性本身绝对化,将其作用无限夸大。他们排除了经验性因素的影响,将道德法则视为我们实践活动的唯一原则,并逐渐走向禁欲主义。这两派虽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但均为管窥蠡测之见。对此争论,作为“贮水池”的康德,从人的双重性出发进行了调和。
在康德看来,实现幸福是人的本质需求,因此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幸福原则便理所应当地成为我们实践的根据。但是纯然依靠幸福原则指导的实践活动只是相对的“善”。由于人是两重性的存在,因此感性方面的需求并非需求之全体,理性使人有了更高的目标。这样,便在感性方面对于幸福追求的自然意图上增加了理性的道德法则的约束。同时,康德也指出两者间的矛盾是不可否认的,幸福原则本身会阻止理性的道德法则发挥作用,④但在实践领域内,理性的道德法则并不会阻碍实践的自然发展。⑤所以,理性并非谋求幸福之工具,它是为了更高的目的。也正因于此,人类才有别于动物,才能摆脱掉自然法则之枷锁,拥有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以道德律作为其实践活动的最终根据,也就是道德法则的作用,这也是幸福原则所无法企及的。
(三)理性幸福论的评价:对感性幸福论的补充与超越
正如上文所述,幸福原则属于感性的范畴,道德法则则分属于理性的范畴。在人这种双重性的存在中,这两个看似矛盾,理应相互排斥的概念,却在意志中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幸福是我们一切爱好的满足。出自幸福动机的实践规律我称之为实用的规律;但如果有这样一种实践规律,它在动机上没有别的,只是要配得上幸福,那我就称它为道德的。前者建议我们,如果要享有幸福的话必须做什么,后者命令我们,仅仅为了配得上幸福我们应当怎样做。[6](P612-613)
在康德上述回答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幸福”,一种是出自幸福动机的实践,即在幸福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这种实践活动在上文已经证明过,只是相对的“善”。因此这种幸福原则无法作为道德法则来指导实践,是一种“消极的”幸福。而“为了配得上幸福”中的“幸福”就不再是纯然感性的幸福,而是在幸福原则基础上,将道德法则指导下的德行作为配享其的条件的幸福。在道德法则的引领下,这种幸福是绝对的善,故是一种“积极的”幸福。
这样的结合使得原本属于形式层面的道德法则与质料层面的幸福原则在人的意志中实现了统一。此处的统一只是康德的一个设想,究竟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又是如何实现统一的,便是康德在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中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德性与幸福两者究竟作何关系。有德之人是否一定会享有幸福?
三、德福一致:感性幸福与理性幸福的统一
(一)德与福的关系: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
尽管在实践理性中道德法则与幸福原则是互相补充的关系,道德法则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作为配享幸福的条件之一,使追求幸福的实践活动不再只受幸福原则的指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结合只是一种或然性,有德之人往往未必有福。可以说道德法则与幸福原则的结合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应有”,并与质料世界中的“现有”大相径庭。如何调和“应有”与“现有”间的矛盾,德福之间是否存在一致的必然性?对此,在纯粹实践理性辨证论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一节中,康德进行了关系的梳理。
一方面两者不同质,所以无法借助分析命题的形式去理解,另一方面两者间的综合联结也存在矛盾,因为从因果律的角度出发,两者的关系仅存在两种可能,即幸福原则决定了道德法则的内容,或者道德法则规定了幸福原则的范围。⑥但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能的。⑦所以两者间的关系成了实践理性的一组二律背反。
(二)对伦理学史上德与福关系的批判
传统西方伦理学对德福间关系的构建一般是根据同一律的方式,将两者间的关系理解为,“有德即有福”或“有福即有德”这种分析命题的形式;但是如果借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来解释此问题,无论人类的理性以多么缜密的方式将两者的关系诠释的天衣无缝,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这些证词却又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若想以确定的、必然的形式规定德与福间的关系,以往的以分析关系出发的解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它在现实问题面前总是陷入无尽的二律背反。因此康德先对以分析关系解释德福一致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希望将其纳入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之下。
康德在纯粹理性在规定至善概念时的辨证论一章中,对以往伦理学思想史上的德福之辨进行了梳理,康德认为在以往的德福之辨中,伊壁鸠鲁派与斯多亚派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学派。尽管两派观点大相径庭,但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是遵循同一律的原则,以分析命题的形式去诠释德福间的关系,力图在两个概念间的等同性上有所突破,也因此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伊壁鸠鲁派的观点是感性立场的,认为德性的概念已经被包括在追求幸福这一原则之中了。但是斯多亚派的观点却截然相反,他们的观点更具理性味道,即在追求道德的实践中人们已然收获了幸福的情感。因此,对于“至善”,两派各执一端,要么德性至上,要么幸福之上。但这样单向度的观点对于作为双重性存在的人而言,皆为一隅之说。
对此,康德大刀阔斧地打破分析判断的藩篱,以综合判断的形式重新诠释该问题,并通过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给予该命题以必然性的保障。德福间关系并非分析判断般地将谓词视为包含于主词之中的存在,相反,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关系。在康德看来,德行是配享幸福的资格,是幸福的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尽管德性生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实现善的一个必要手段,但由于人是双重性的存在,若想达到“至善”还需辅之以幸福作为充分条件,在“至善”中,德福一致得以实现。
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德福相悖的事例,康德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两者间的统一并非绝对必然的结果,掺杂大量经验性因素后的德福相悖是一种偶然性的结果,纯然状态下两者间是必然统一的。既然在经验世界,由于大量质料性因素的影响德与福无法实现必然的统一,那就对环境进行“提纯”,最终在“纯而不杂”的环境中,康德通过上帝存在、灵魂不朽以及自由意志,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来保证在来世,有德行的人必会享受到公正的上帝在天国准备好的幸福,完成了两者的必然统一。
(三)德与福统一的条件: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
众所周知,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分别是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以及自由意志。这其中前两大悬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作为先验幻相被批判掉了。此番重提,是否自相矛盾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驳倒的原因在于,它们属于本体界,对于理性知识而言毫无帮助,一旦混进现象界的知识领域,还使理性陷入无穷的二律背反。但康德认为这两个命题在实践理性中确有用途。⑧为了“至善”的追求,在实践理性中重新恢复它们是非常有必要的。⑨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在实践理性中,上帝、灵魂、自由意志这些先验理念获得了客观实在性,但这并不是“上帝”的复活,这里的客观实在性并非现象界的客观实在,它们仍旧不是认识的对象,只是为了“至善”在本体界的先验悬设。
作为实现“至善”的必要“悬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三大悬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文本中,康德对其存在之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首先是“灵魂不朽”,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在分析论部分,在幸福与德行之间划清了界限,认为两者间先天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但是在辨证论部分,在探讨“至善”这一话题时,康德又重拾幸福,希望在“至善”中实现两者的统一。从分析论的“德福分离”到辨证论的“德福统一”,其实也代表了实践理性追溯无限的精神特质。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一样,同属理性的范畴,因此存在追求无限完满对象的倾向。由于“至善”本身就意味着完满的“善”,“至善”在现世的实现是一个可以通过道德律来规定的意志的必然客体。但在这个意志中意向与道德律的完全结合却是至善的至上条件。[3](P167)显然,意向与道德律的完全结合的实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因此对于现世有限理性的存在者而言,这种对无限性存在的追溯是极其困难的。有限与无限这组二律背反又开始困扰我们的理性。对此康德提出,在同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某种无限持续下去的生存和人格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3](P168)因此,作为实践理性“悬设”的灵魂不朽是“至善”实现的理论之必须。
“灵魂不朽”解决了至善的“最先和最重要的部分”[3](P170)即德性存在的合法性。但对于“至善”的另一大要素——“幸福”,康德发现,仅依靠“灵魂不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上帝存在”保障幸福的实现。由于纯粹理性本身又有着追逐“至善”的诉求,而且幸福又是不可忽视的人的自然诉求之一,所以“至善”的出现使得幸福与德性这两个原本不同质的内容在一定的基础上“通约”,亦即有德之人必有福报。为了在现世满足这样的条件,实践理性需要一个拥有某种符合道德意向的原因性的至上的自然原因。[3](P172)所以这个既具有道德上的至高无上性、不被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所困扰的,同时又是产生自然的原因的原因的“上帝”,便作为“悬设”在实践理性中迎来新生。
尽管之前两段所论证的“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实际上已经将德性与幸福统一于“至善”之中了,但是康德认为仍旧需要“自由意志”作为“总论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对此康德是这样回答的。“自由意志”来源于对感官世界的独立性及按照理知世界的法则规定其意志的能力,亦即自由这个必要的前提。[3](P181)即作为压轴出现的“自由意志”是“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两大悬设的根据。其实早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中,康德便已经埋下伏笔:“这些假定(笔者注: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也由于自由概念的实在性而带上了实践意义的实在性,即能够现实地对人的行为起作用。”[3](P2)
康德认为,正因为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所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反复提到的先验的自由便在实践理性中找到了自身的实在性。通过道德律在实践中的应用,将纯粹理性提出的先验自由转化为客观实在。因此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生成了如下的理论进路,康德认为掺杂进质料的、非纯粹的原则,无法在实践中收获普遍的“善”。在这过程中,经验性的质料因素被排除殆尽,这种先验的形式最终是由理性演绎得出的,由于排除掉了经验性的质料,因此自然规律对此法则便不再起任何效用,所以作为理性意志的自由规律便成了该法则的主要原因。由于在为人对自身立法的过程中,自由在实践理性中收获了客观实在性。并且在实践理性对无限性不断追溯的本质中,“至善”成为可能,所以是自由决定至善。因此作为维系“至善”之可能的另两大悬设也在“自由意志”中找到了合理性的依据。故此,“自由意志”便作为“总论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的总纲性“悬设”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也构成了康德幸福哲学甚至伦理学体系的奠基石。
综上,“德福一致”作为康德幸福观中最为核心的命题,本文认为如下两大理论前提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德福一致”的实现需要实践理性先验的“三大悬设”来维系。这其中“灵魂不朽”赋予了有限理性的存在者——人以追溯无限的可能;“上帝存在”为德行以配享幸福设立了绝对的尺度,对人的意识起了范导性的作用;“自由意志”作为总纲性的“悬设”,是使人们可以选择德性生活的重要前提,是“德福一致”可能的理论基石。第二,“先验自我”的设定是“德福一致”的逻辑出发点。正是在“先验自我”的基础之上,使得“德福一致”这种原本在经验世界仅具有偶然性的理念,在先验的理念中找到了必然性的依据。这便为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向“至善”的信仰之路。而且与中世纪对上帝信仰的宗教狂热不同的是,这个信仰更多地诉诸于人类的理性,在内在超越性本质的影响下,使人们不断地“内省”并在“外求”中实现“至善”。
作为哲学史上的“蓄水池”,康德哲学糅百家之所长,在哲学界掀起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开创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先验哲学体系;另外,作为哲学史上的“放水池”,康德哲学源源不竭地为后来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以致在费希特、费尔巴哈、密尔甚至现代西方哲学重要代表叔本华的幸福观中都能够看见康德的影响。但不能否定的是,康德哲学所言之幸福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善良意志”,德福间应然的一致在冰冷的现实前往往不堪一击。对此,马克思在现实的维度上展开了批判,他通过经验的方法,将道德问题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分析,探寻人类不幸福的原因,设计那些与现行制度结构不同的,同时容许由劳动者控制的无产阶级、无等级社会的制度结构。[8](P165)在从先验到经验之跃中,实现了对康德幸福观的发展。
注释:
①安倍能成认为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处于贮水池的位置,康德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之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1](P16)
②斯多葛学派认为:福与道德两者是冲突的。一切有道德的人都是严肃的,因为他们从来不谈论愉快的事情,也不听别人谈论愉快的事情。[4](P176)
③康德认为:假言命令只代表从一定的可能角度,或者从一定的现实角度来看,一种行为是善良的。[2](P65)
④康德认为:自然要防止把理性用于实践,并让它不作此非分之想,凭它那薄弱的省察力,自己就能设想出一个达到幸福的计划和完成计划的手段。自然不但为自己选择目的,也选择手段。它周密地考虑,把两者完全托付给本能。[2](P44)
⑤这是因为康德认为:人是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它作为最高的条件,当然远在个人意图之上。[2](P45)
⑥本文的观点是对康德解释,原文是:对幸福的欲求必须是德行的准则的动因,要么德行准则必须是对幸福起作用的原因。[3](P156)
⑦对于前者,康德认为:如果把意志的规定根据置于对人的幸福的追求中的那些准则根本不是道德的,也不能建立起任何德行。[3](P156)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幸福;对于后者,康德认为幸福是基于自然与他的全部目的、同样也与他的意志的本质性的规定根据相一致之上的。但是,道德律作为一种自由的法则,是通过应当完全独立于自然、也独立于它与我们的欲求能力的协调一致的那些规定根据来发布命令的。[3](P171)道德律是一种超感性的法则,因此不可能是感性世界中幸福的原因。
⑧这是因为在康德看来,它们虽然并不拓展思辨的知识,然而却普遍地赋予思辨理性的诸理念以客观实在性,并使思辨理性对于那些它本来甚至哪怕自以为能断言其可能性都无法做到的概念具有了权利。[3](P181)
⑨对此海涅曾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实践的理性也不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他毁灭了上帝存在的一切证明正是为了向我们指明,如果我们关于上帝的存在一无所知,这会有多么大的不便吗?他做的几乎象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我的一位朋友那样聪明,这人打碎了葛廷根城格隆德街上所有的路灯,并站在黑暗里,向我们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灯实际必要性的长篇演说,他说,他在理论上打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指明,如果没有这些路灯,我们便什么也看不见。”[7](P113)
——评《当代中国青年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