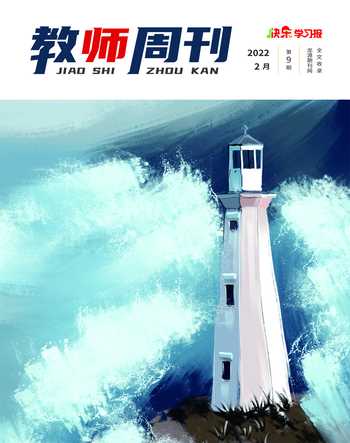“有形诗”与“无形画”
晋铭鸿
摘要:T·S·艾略特是现代主义文学领军式的文学巨匠,在诗歌、戏剧以及文学评论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艾略特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其主题是揭露现代西方世界的贫瘠和荒芜。本文以《情歌》的诗文为出发点,通过分析诗文与图像是如何在诗人与读者间往返跳跃,并打破和颠覆莱辛所阐述的诗画界限观,通过结合威廉·布莱克的诗画合体艺术观,论证诗与画是时和空、动和静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同时阐述诗画之间的相互阐释性。
关键词:《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诗与画;合体艺术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因此不同的艺术之间也同样具有通约性。陈永国曾指出:“任意学科之间看似相互对立,实则互相补充。”文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与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姻缘联系,人们往往把它们称为姊妹艺术。而本文主要以艾略特的《情歌》为例,论述诗文与图像的通约性,以及布莱克合体艺术中的诗与画如何在统一体中形成差异与对立,激发想象力,引发对心灵视像的呼唤,并与后现代思维观念相呼应。
探讨西方对于诗与画的美学研究不可逾越的理论著作当属于1766年,德国著名作家和文藝理论家莱辛(Gotthold E. Lessing)出版的美学著作《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Laoccon),而在《拉奥孔》发表二十二年之后的1788年布莱克的合体艺术产生了。如果说莱辛把诗和画之间勾勒出了一道分割线,那么布莱克所做的就是把诗与画放到如东方太极的统一体中,即相互分庭抗礼,又和谐统一,看似冲突对立,实则相互构成,互相补充。莱辛认为诗歌(或文字艺术)与绘画(或造型艺术)分属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莱辛认为时间与空间是有辩证关系的:画化动为静,就“画中有诗”;诗化静为动,就“诗中有画”。绘画和诗文分属空间和时间、静态和动态、视觉和听觉的艺术。而布莱克以独具一格的方式将诗文本与图像融进一个版面。在某些作品中,诗文本与同一版面中的图像形成相互构成和补充的关系,诗配以图使得诗文本更具感性和生动性,而有了诗文本,图像的意义也更为具体鲜明,二者在丰富对方思想和内涵方面相得益彰,互通共融。
在《情歌》中,是“有形诗”和“无形画”的相互孕育、相互阐发、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诗是“有形”诗,画是“无形”画。布莱克诗画合体艺术的最早研究者之一海格斯特罗姆(Jean H. Hagstrum)在他的专著《威廉·布莱克:诗人与画家》(William Blake:Poet and Painter)中首次用“合体艺术”(composite art)来定义布莱克诗画合一的艺术作品。布莱克合体艺术摒弃了文艺的模仿观,其合体艺术中的视觉符号所引发的深意及其对内心直觉与想象力的彰显,最终指向了对视觉形象本身的超越。
一、诗人的情景图像
“画中有诗”与“诗中有画”的审美接受心理不同。“画中有诗”是在想象与联想的基础上感知,而后表现为对绘画符号的破解和对诗性意蕴的领悟;而“画中的诗”也能够呈现意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会把当前感受到的组成“画”的物质性条件,如色彩、线条等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诉诸人的感觉器官,使其变为某种媒介,从而通过这种媒介进行联想和想象,从而得到相关的意象。
对《情歌》中的“无形画”的阐述:一方面是诗人创作之前的视觉世界图像,而非实物绘画作品;另一方面是视觉世界图像所表现出的对某种理论和情感的再现和模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精炼的概括了“模仿”概念的可能意义:忠实地模仿自然、理想化地模仿自然、模仿理念。艺术家对自然的模仿,不只是单纯的模仿外在,同时还要模仿内在的理念,即上帝所创造的观念。艺术的模仿不仅真实的再现实在,也要呈现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同苏格拉底所说的床的三种形式之一的自然的床,大概得说它的神造的。就像人类的各种感受和情感就是天生的自然存在的。”艺术模仿的对象被引向另那个永恒的、比可见世界更加完美的世界。如果可见世界的局限非要存在,那就让它通过各种象征去探索永恒之美的踪迹好了。如果对于诗人来说,把可见世界看作一幅“无形画”,诗人模仿的不单纯是可见的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客观世界中所呈现的审美理念,并通过语言艺术的媒介向读者大众表现出来。
T·S·艾略特以作家敏锐的时代嗅觉捕捉到了现代主义的“荒原”特点,通过诗歌《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来再现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颓败全景,表达了一战后人们普遍失望和迷茫的情绪,以及对战后世界的不安和迷失的无奈。《情歌》中“麻醉的病人”、“手术桌”、“半冷清的街”、“下等歇夜旅店”、“铺锯末的饭馆”、“快要干涸的水抗”、“黄色的烟”、“黄色的雾”等客观现实景物的呈现和描写,让无论哪个时代的读者也同艾略特一起看见了那个时代的工业发展和物欲横流,感受到了人们心中被颓废、懒惰、荒芜、无信仰和空虚充斥着。诗歌中呈现的景物便是艾略特用肉眼看到的客观景象,但是客观景物的选择的罗列和呈现的顺序却像是一幅接着一幅的连绵的图画,描绘了二十世纪破败的西方世界,表现社会与现实的荒谬、混乱、邪恶和丑陋。艾略特不只是看到了自然的客观世界,而且看到了自然世界背后人们迷惘和颓废的精神世界。
对于诗人创作之前的视觉图像,中国女作家郑敏也曾明确的表述过,她创作诗文《金黄的稻束》的灵感来自于现实中一片收割后的稻束。金黄的稻束们在那一刻给郑敏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它们静穆的姿态让她仿佛亲眼见到了永恒。我们可以把客观世界中的金黄稻束看作是对彼时的郑敏产生强烈心灵和精神的震颤图画,从图画中获得精神的召唤,并用诗文给予表达。可见诗人从客观事物引起深思,同时兼具画面感与精神性,现实中的金黄稻束的静谧和沉静通过诗人的笔尖流向了诗文中的字里行间。正如艾略特受现实世界景物的感召和唤发一样,郑敏在创作《金黄的稻束》时被一片寂静的金色稻田所震撼,从而引起思想的飞扬和心灵对世界的感悟。
任何的文学和艺术创作都来自于对客观的自然物质世界的模仿,但同时创作又超越单纯的模仿并且加注了创作者的精神的感召和心灵的温度。如果把客观世界看作一幅关乎世界的图像,而艺术的模仿是对自然的模仿,也是对理念的模仿。艺术的模仿对象变成那个超验世界时,艺术就是在模仿某种理念,这种理念是绝对、完美的存在,永恒不变,或者成为上帝的形象。诗人创作之前的灵感与其说来自于客观世界,不如说是对自然的模仿,对人类理念的模仿。
二、读者的视觉图像
“诗”是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暗示,使接受者积极调动回忆、联想等功能来唤起记忆和想象的。通过语言呈现的具有暗示性和象征性的意象,能够强化或激发艺术主体的创性思维。“诗中有画”是先通过对文本的感知,从而阐发出想象与联想。我们知道,通过语言呈现的意象总是具有较大程度的暗示性和象征性。黑格尔曾说:“语言在唤起一种具体图景时,并非用感官去感知一种眼前外在事物,而永远是在心领神会。” 黑格尔提到的“心领”和“神会”,就“诗中画”的审美接受而言突出表现在对诗歌语言符号的破解及重组。
审美接受者首先感知到的是具有含混性、复杂性以及多样性特点的诗歌语言,通过“前理解”对得到的语言符号进行分解,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暗示,积极调动回忆、联想等功能,对这些语言符号进行重组,也就是二次创造,将抽象语言具象化,最终还原为形象或者图像浮现在脑海中。伊瑟尔认为,作家在其创作出的艺术文本中隐藏了一种“召唤结构”,引导读者在进行阅读的时候走进该文本的这一“召唤结构”,(或称为文本的“空白点”)中,对原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和补充,也就是再创造。“一般而言,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令人们不断地加以理解和解释,永远不能穷尽其意蕴。” 它唤起读者的视觉记忆、情绪信息,触发读者的情思,使欣赏主体和被欣赏客体相交融,最后完成审美移情,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
对《情歌》中的“无形画”的另一方面论述是读者所“看”到的情景图像,即读者阅读文本之后在脑海中的想象和心灵的震颤所激发出的带有色彩的画面。诗文中所呈现的视觉图像越出了文字符号图像之外,揭露现代西方世界的贫瘠和荒芜,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崩塌以及人们处在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感觉之中徘徊。生活在现代时期的人们正在经历一种精神上的死亡,这是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艾略特不但对男主人公普鲁弗洛克进行意识流式的心理描写,同时诗歌中所呈现的景物同样衬托出普鲁弗洛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懦弱心态。“趁黄昏正铺展在天际”、“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蹭着它的背,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鼻子和嘴,把舌头舔进黄昏的各个角落”、“让黄色的烟雾溜过大街”,其中“铺展、蹭、擦、舔、溜”等动词表现出一个动作的连续性,延展性,粘稠性,暗示着主人公不具有雷厉风行的坚毅性格,预示着优柔寡断的性格必然会让他在求得心上人爱慕的失败。
文字符号具有图像性,这意味着文字具有向空间延展和生发的潜质。但由字母组成的西方拼音文字与其所指的客观物不发生直接关联,更体现出“人为符号”的抽象性。由拼音文字建构的诗语言,其意义的传达需要通过在时间中延展的语言叙述来完成,而与文字本身无关。然而,在布莱克合体艺术中,诗文本如画般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更多地体现在诗的文字及文本的呈現方式中。这使得西方拼音文字的特质在他的合体艺术中发生某种转化,向着空间延展,引发了文字本身唤起的想象力和心灵的跃动。
另外,诗歌的文字本身,包括排版就具有符号图像性。开篇艾略特引用的但丁的《地狱篇》、重复的“房间里的女人们来往穿梭,谈论着米开朗琪罗”、排列着的“早已熟悉”、“早已领教”、“早已熟悉”;三句“值不值得”等都像是一幅幅的图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随着读者的阅读进程所呈现的图像体现出了现代主义的“荒原”特点,召唤出人们在所处时代的无作为和无助感。主人公普鲁弗洛克最后反问自己“我敢吃下一只桃子吗?”,可见他不但优柔寡断而且还胆小如鼠。他把自己心仪的心上人看作是充满致命和诱惑性的女海妖,没有抵制她们的曼妙美丽和美妙歌声的诱惑结果就是死亡。笔者认为普鲁弗兰克不是“溺亡”在女海妖的美丽和歌声里,而是“溺亡”在了20世纪初充满荒谬、混乱、邪恶和丑陋的“荒原”时代里。
三、总结
 布莱克合体艺术展示了更加活跃和复杂的诗画关系,呈现出诗画关系在相互统一中的差异和矛盾,最终引发了对视觉的超越而走向了由想象力主导的心灵视像。这正是布莱克艺术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布莱克的合体艺术在T·S·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到体现。布莱克体现的艺术思想与华兹华斯及柯尔律治的视觉艺术观及他们所持的诗画观不同。布莱克的艺术观认为诗文的图像化、空间化,图像的叙事化、时间化,以及诗画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唤醒了由视觉引发的对物象的直接感悟和对逻辑理性权威的否定,激发了心灵的直觉想象。20世纪初西方精神颓败的现实世界的“无形画”给诗人创作之前提供写作素材;读者通过作家所书写的字里行间“看”到、感受到当时西方物欲横流的客观世界和精神颓废的精神世界。视觉并非对想象的压制,而是从图像和书写层面对想象力的唤醒。布莱克的诗画合体艺术观与浪漫主义诗学观所推崇的想象力在另一层面上达到了契合,并与后现代哲学对语音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观的批判产生呼应。
布莱克合体艺术展示了更加活跃和复杂的诗画关系,呈现出诗画关系在相互统一中的差异和矛盾,最终引发了对视觉的超越而走向了由想象力主导的心灵视像。这正是布莱克艺术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布莱克的合体艺术在T·S·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到体现。布莱克体现的艺术思想与华兹华斯及柯尔律治的视觉艺术观及他们所持的诗画观不同。布莱克的艺术观认为诗文的图像化、空间化,图像的叙事化、时间化,以及诗画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唤醒了由视觉引发的对物象的直接感悟和对逻辑理性权威的否定,激发了心灵的直觉想象。20世纪初西方精神颓败的现实世界的“无形画”给诗人创作之前提供写作素材;读者通过作家所书写的字里行间“看”到、感受到当时西方物欲横流的客观世界和精神颓废的精神世界。视觉并非对想象的压制,而是从图像和书写层面对想象力的唤醒。布莱克的诗画合体艺术观与浪漫主义诗学观所推崇的想象力在另一层面上达到了契合,并与后现代哲学对语音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观的批判产生呼应。
参考文献:
[1]程婷婷.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心理学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120-121+158.
[2]于宏英.中国诗画交融艺术活动的审美心理过程[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章燕.论布莱克诗画合体艺术及其与西方“诗如画”传统的关系[J].外国文学,2016(06):36-45.
[4]郑敏口述,祁雪晶、项健采访整理:《郑敏:跨越世纪的诗哲人生》,见《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名家口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页,第473页.
[5]李涵之.西方艺术学中的“模仿论”[J].美苑,2015(06):8-13.
[6]赵旻.诗画之辨——浅析莱辛的《拉奥孔》[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28(01):124-125.
注释:
①赵旻.诗画之辨——浅析莱辛的《拉奥孔》[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28(01):124-125.
②程婷婷.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心理学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120-121+158.
③李涵之.西方藝术学中的“模仿论”[J].美苑,2015(06):8-13.
④郑敏口述,祁雪晶、项健采访整理:《郑敏:跨越世纪的诗哲人生》,见《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名家口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页,第473页.
⑤李涵之.西方艺术学中的“模仿论”[J].美苑,2015(06):8-13.
⑥于宏英.中国诗画交融艺术活动的审美心理过程[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⑦于宏英.中国诗画交融艺术活动的审美心理过程[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⑧章燕.论布莱克诗画合体艺术及其与西方“诗如画”传统的关系[J].外国文学,2016(06):3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