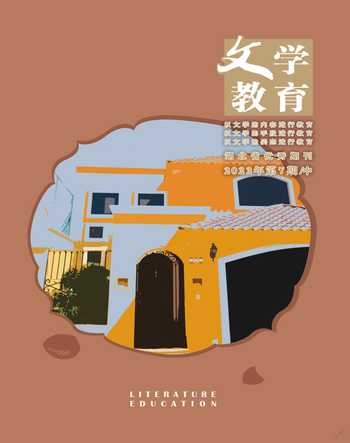隐逸思想在马致远散曲中的体现
王萌 斯琴塔娜
内容摘要:隐逸,是元散曲的主调之一,而马致远则是这一主调的领唱者,老庄哲学中愤世嫉俗、时命大谬的思想,超脱功名、不谴是非的归隐观,道法自然的生存哲学,慷慨风流的生活态度在马致远隐逸散曲中时有体现,从精神、文化上影响着此类散曲的创作。
关键词:马致远 散曲 隐逸 老庄思想
元代人贾仲明称誉马致远为“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认为他是“战文场”的“曲状元”。由于独特的社会历史原因,隐逸成为元人散曲创作所流行的重要主题。据隋树森的《全元散曲》,马致远现存130多首曲子,其中叹世归隐类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目前学界对于马致远隐逸类散曲研究多集中于其内在意蕴的探究和以马致远为例看待整个元代社会大都文人的隐逸文化为主;对于老庄思想与元散曲关系的研究也多为综述性影响分析。1990年杨栋在《愤世·避世·审美超越——试论马致远散曲的隐逸主题》认为,“马致远的隐逸倾向与老庄哲学在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上具有一致性。”[6]此后学界对于马致远散曲中的老庄色彩研究多从其愤世嫉俗,悲世归隐之类入手,本文在肯定前人对马致远此类散曲中含有老庄愤世归隐思想的研究基础上,加入老庄哲学中关于生命生存哲学的积极思想,兼用意象分析在其隐逸类散曲中老庄思想的表现,进而探究马致远此类散曲中为何会含有老庄思想。
一.隐逸思想在马致远散曲中的表现
1.愤世嫉俗,时命大谬
《庄子》有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2](6.p121)庄子将“时命大谬”视为士人隐逸的主要原因。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道东篱醉了也。[1](p269-270)
元代文人常通过纸笔来揭露抨击社会,而老庄思想中对于社会的批判意义恰与马致远愤世而隐的思想不谋而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3](77.p39)。老庄思想中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成分与马致远对于似“密匝匝蚁排兵”般追名逐利之辈的厌恶、对如“乱纷纷蜂酿蜜”混乱嘈杂之事的无聊、对像“急攘攘蝇争血”似丑恶官场的讥讽是相通的。老庄思想中的愤世嫉俗是马致远痛击于黑暗社会的武器。
在【双调·夜行船】《秋思》中,【落梅风】改自元杂剧家郑廷玉的《看钱奴》,写天帝恩赐下,一贫民成为富翁,之后便为富不仁,“天教你富。莫太奢。没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到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1](p269)借古讽今,讥讽社会上“看钱奴”们的鄙俗,可见马致远隐逸散曲中老、庄愤世思想的端倪。
马致远曾写过“且念鲰生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1](p273),这里的“鲰生”一直以来学界认为是作者自谦的说法,“鲰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的《张良传》,是沛公说自己听信小人谗言,故“鯫生”有小人之意,作表示轻蔑的骂人语。若将“且念鲰生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中的“鲰生”当另一意思来解读,也可以说马致远对于自己曾经写诗求官的做法是轻蔑的,他仕途不顺,表达的是对于黑暗的官场生活已经看透。元代特殊的社会制度、汉人的身份、九儒十丐的地位,致使马致远在仕途上处于一个尴尬位置,这样的经历符合庄子所说的“时命大谬”,所以才有了“二十年漂泊生涯”的悲辛。
2.超脱功名,不谴是非
【南吕·四块玉】《叹世》:两鬓皤,中年过,图甚区区苦张罗。人间宠辱都参破。种春风二顷田……倒大来闲快活。[1](p237)
人到中年,生命过半,在“人间宠辱都参破”后才明晓原来“争名利,夺富贵,都是痴。”马致远晚年对人间的荣辱得失失去了热情,回首只觉得过往人生不过是在“半世逢场作戏”。他还在【双调·拨不断】中感叹: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一场恶梦。[1](p253)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功成身退,天之道。”[4](p4)人生如梦,荣华富贵终归会化为尘土,贪恋一枕黄粱不如“闲身跳出红尘外”。蒙元时期知识分子文人出路颇窄,由于“英俊沉下僚”,马致远无法施展抱负,既无法反抗,又不想与世沉浮,内心苦闷彷徨,退隐山林是最好的选择。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影响着马致远。
【般涉调·哨遍】:半世逢场作戏。险些儿误了终焉计。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老正宜……成趣南园。对榻青山。绕门绿水。[1](p262)
据隋树森《全元散曲》,马致远所含“东篱”意象的曲子共七首,除【般涉调·哨遍】外,【双调·夜行船】《秋思》“道东篱醉了也”[1](p269-270)、【双调·蟾宫曲】《叹世》“东篱半世蹉跎”[1](p242)、【双调·清江引】《野兴》“东篱本是风月主”[1](p244)、【双调·拨不断】“白衣盼杀东篱客”[1](p253)、【双调·新水令】《题西湖》“黄菊绽东篱下”[1](p266)、【双调·行香子】“对东篱。思北海。忆南楼”[1](p271)。
“东篱”的意象运用,是马致远对于归隐之心的明示,“东篱”出自陶渊明《饮酒》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东篱”是陶公隐逸品性的代言。马致远字东篱,对陶渊明很是崇拜,陶渊明诗作中颇得老庄之范,魏晋之际又大开“玄学”之风,“清谈”、“玄学”与老庄关系大为密切,陶与玄学、道家的结合都给予了马致远隐逸类散曲创作上的灵感。
马致远想要从恬淡的隐士生活中寻求精神解脱,进一步体现了老、庄视富贵于浮云的思想。他“旁观世态”,脱离虚无的名利场,回归自然,在“东篱”中受到了自然的反悟,动乱社会下反而更应该珍惜生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生活在绿水青山之间。《庄子》中有云:“与天和者,谓之天乐。”[2](5.p104)马致远在“对榻青山,绕门绿水”中感悟到老庄思想,超脱功名,不谴是非。
3.道法自然的生存哲学
马致远多用意象来表现老庄思想,像【双调·清江引】《野兴》(其七):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是搭儿快活闲住处。[1](p243)中的“东篱”。再如【南吕·四块玉】《恬退》:翠竹边。青松侧……太平幸得闲身在。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1](p233)
“五柳”取自陶渊明的自号:五柳先生,陶渊明有作《五柳先生传》,文中表达了他不慕名利、安贫乐道的品格,追求田园山水间闲适的生活乐趣,这正是对老庄生存哲学的继承。“归去来”这一意象在马致远的曲子中共出现了四次,都是在【南吕·四块玉】《恬退》中,分别是“三倾田。五亩宅。归去来”、“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和“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1](p233),另外还有【南吕·金字经】中的“且做樵夫隐去来”[1](p243)。在“归去来”出自陶渊明的辞赋《归去来兮辞》,此文是作者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书,陶渊明洁身自好,不与官场同流合污的情操,向往田园安稳闲逸的生活情趣启发了马致远对人生的思考,陶渊明作品中继承着老庄思想中乐天自然的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马致远的共鸣,使他和老、庄通过陶公的“介质”相连结,老庄的生存哲学寄托了作者的生活理想。“三径”是指王莽当政时期,蒋诩归乡隐居,用荆棘塞门,修设有三径,只和求仲、羊仲交往,此意象意在点明作者本人志存高洁,归隐山林,是对老庄超然恬淡哲学的承袭。
再如【双调·清江引】《野兴》(其八):西村日长人事少。一个新蝉噪……又早蜂儿闹。高枕上梦随蝶去了。[1](p244)
“梦蝶”出自《庄子》中“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2](10.p235-236)“梦随蝶”化用庄生梦蝶的典故,取“梦蝶”的意象,蕴含有人生变幻无常之意,在【双调·夜行船】中也有“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1](p269)一句。世事无常,处世生存当遵循道法自然的大宇宙观,跳出红尘之外,不为名利所累,追求舒适闲在的生活。正如庄子所说的:“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2](7.p142)
【南吕·四块玉】《叹世》: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暖后休。[1](p237)
曲中命里无时莫强求的洒脱态度也是同样的“与天和者”。此时的“莫刚求”显示出马致远的入仕执念已然放下,转而积极地回归田园,真正做到了“知忘是非,心之适也”,这是老庄道法自然的生存哲学带给他的态度转变。
(四)倜傥风流的生活态度
【双调·清江引】《野兴》(其一):樵夫觉来山月底。钓叟来寻觅。你把柴斧抛。我把鱼船弃。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1](p243)
“樵夫”无所畏惧抛了“柴斧”,在山野间肆意睡去,醒来不觉夜色已深,“钓叟”弃了渔船前来寻“樵夫”,想一起去找个安稳处闲坐,这和庄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2](9.p202)有异曲同工之妙。“樵夫”一意象也出现在【南吕·金字经】“担头担明月。斧磨石上苔。且做樵夫隐去来”[1](p243),这里的“樵夫”也是自由于山林间的。“樵夫”“钓叟”的行为是啸傲江湖的洒脱,也是作者弃世隐逸的决绝。另,在【双调·新水令】《题西湖》中“功名已在渔樵话”[1](p266),也有处“渔樵”意象,此“渔樵”并不是指渔夫樵夫,而是借“渔樵”代指隐逸之事,是作者对归隐的肯定。他选择隐逸,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自我解脱,这是一种积极的生存态度,是与自己求仕之心的和解。马致远仰慕于老庄思想中“心意自得”的风流情怀,于隐逸类作品中展现出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潇洒行为。正因如此,在元代文人略有消极的隐逸散曲中,马致远的作品却带有一种“另类”的豪荡之感,与众不同。
【南吕·金字经】:絮飞飘白雪。鲊香荷叶风。且向江头作钓翁……风波梦。一场幻化中。[1](p238)
想做“钓翁”,赏人间似白雪般飘飞的杨絮,静闻风吹池塘送来的荷香和用红曲腌制的鲊鱼香,纵使功名未济身穷不富又何妨。官场风波皆梦幻,山林烟火原是真。摒弃世俗之心后积极生活,马致远将“心意自得”表现到了极致。除“钓叟来寻觅”和“且向江头作钓翁”外,在马致远此类散曲中“钓翁”、“渔夫”、“钓叟”之类意象还出现两次,分别是《野兴》中的“绿蓑衣紫罗袍谁是主。两件儿都无济。便作钓鱼人”[1](p243)和【双调·寿阳曲】《江天暮雪》中的“钓鱼人一蓑归去”[1](p246),这里的“钓鱼人”都是决绝抛下“紫罗袍”而穿上“绿蓑衣”的倜傥人。如此超脱的行为也正是作者对老庄“心意自得”潇洒思想的外化。老庄哲学中关于寻求自然逍遥的思想,风流倜傥的积极态度被马致远借鉴于他隐逸类散曲的字句之间。
二.马致远散曲中隐逸思想的成因分析
1.社会原因
元代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实行“四等人制”,不同的民族在任职、科举、刑律等方面有不同的待遇,由于社会地位限制,汉族文人想要入仕并非易事。诸如马致远类的作家,他们深感自己的生不逢时,常在作品中愤慨世情,发出满腹牢骚,开始慕隐乐道。元代社会黑暗,权豪势要横行,贪官酷吏是非不分,知识分子文人深感社会环境险恶,马致远隐逸思想的产生也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老庄中含有的愤世嫉俗、时命大谬的思想与马致远不谋而合,被马致远隐含于散曲创作中用来表达自己对于黑暗社会的不满与反抗。
2.隐逸风气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隐逸传统,最早可溯于尧时的许由,自老、庄起,后代隐士皆以道家为隐逸“偶像”,老庄思想颇受士子文人推崇。宽泛来说,隐逸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消極避世、乱世而隐,当推魏晋,犹以竹林七子、陶渊明为首;一类是好慕名士风流、执着于山林之间,如宋代“梅妻鹤子”的林逋;一类是为了出世而隐,以李唐为盛,唐代有“终南捷径”一说,如卢藏用就是因隐居终南山被召。与魏晋相似,元代文人归隐十分常见。此时,作为革新的道教,全真教的盛行加重了士人厌世遁世的思想。元代文人或多或少地继承着老、庄避世而隐的思想,多为不得已而隐。马致远不同,他有做官的经历,曾因向孛儿只斤·真金献诗开启了他在大都的仕途生涯,后随着太子真金的去世被调往杭州。汉人求仕的艰难消磨了他对高官厚禄的追求,底层百姓的民不聊生打击了他的佐国之心,士子文人当下退世隐逸的风气、道家不慕名利归隐田园的思想,都对他迷茫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除散曲外,马致远还创作了许多脱胎于道教故事的神仙道化剧如《黄粱梦》《陈抟高卧》等。他在参透半生浮名虚妄后选择退隐,虽缘于对社会的愤懑,但时人的隐逸之风也推进了他这一思想的形成。老庄思想使他的归隐不似主流般消极,他悟道了生存哲学,诚心追求闲适生活,是有豪放风流的意味。
3.个人经历
有“佐国心,拿云手”的马致远在青年时期有入仕抱负。马致远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但后来萌生了退隐的想法,这源于对蒙元现实社会失望,愤世归隐。“他在宦海沉浮中混迹了大半生,夙志未酬,饮恨终生。他曾长久痛苦地徘徊在仕进与隐退的交叉路口。”[5]马致远仕途不顺,屈沉下僚,因愤世而向往“钓翁”、“樵夫”的生活,产生归隐之心。老子那种“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类而行。”崇尚“逍遥”、顺时而为,脱离红尘的避世归隐思想,与马致远超脱功名、不谴是非的隐逸思想再一次相合。马致远对官场失望后,开始寄情山水回归田园,推崇名士的归隐生活。老庄思想实际上在马致远的隐逸生活中起到了心灵宽慰的作用。
总而言之,老庄思想表现在马致远隐逸类散曲中,除了有时命大谬的愤世思想,超脱功名、不谴是非的隐逸精神外也有珍惜生命的生命哲学、闲适安舒的生存哲学、逍遥慷慨的积极生活态度。马致远与这些思想共情,融其在隐逸散曲的创作中,让此类散曲含有浓郁的老庄色彩。马致远对老庄哲学的推崇不仅仅是受元代社会现实的影响,也与他仕途多舛的经历和元代当时文人隐逸之风的盛行有关。
参考文献
[1]隋树森.全元散曲[M].中华书局.1964,2.
[2]《庄子10卷》华南真经卷.四部丛刊景明世德堂刊本.
[3]《老子2卷》七十七章.老子道德经下篇.古逸从书景唐写本.
[4]《老子2卷》九章.老子道德经上篇.古逸从书景唐写本.
[5]刘荫柏.马致远及其剧作论考[D].中国艺术研究院,1990,8.
[6]杨栋.愤世·避世·审美超越——试论马致远散曲的隐逸主题[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2.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