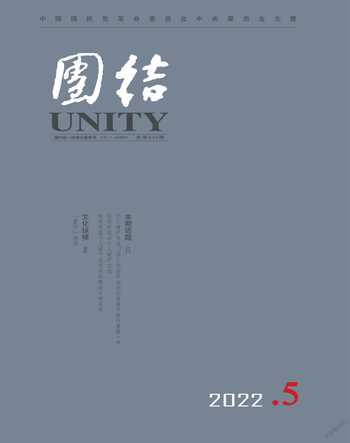深山密林间的慢火车
2022年3月2日下午3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春天的中国”特别直播节目正式播出。随着金黄色的油菜花在现场连线镜头中的惊艳亮相,全中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春日里的嘉阳小火车”上。
这是四川南部的乐山市犍为县石溪镇。
在这里,每天你都能听到“呜——呜——”的汽笛声,一列古老的、轨距仅762毫米的蒸汽小火车,用它特有的方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蒸汽式动力,窄窄的铁轨,燃煤炉瞳门,满是煤灰的司炉,岁月仿佛回到了十八世纪。
初夏,我第一次走进芭蕉沟,走近这列小火车。绚烂的阳光穿过蓝得耀眼的天空,使远处的崇山变得和眼前的草木一样青翠,跃进站旁边林立的楼房,离蔚的草木都亮得有一点发烫。这是一个由纯净透明的空气创造出的世界。透明的空气中,隐约传来尖锐的汽笛声,一声又一声,仿佛是一团溶入空气定格影像与岁月的图钉,更像一把缓慢划破天空的锋利刀刃。群山如黛,芭蕉似屏,这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像一个充满魔法的皮囊,被图钉紧紧锁定在蓝得令人叫绝的天穹中,迷人的乡野风光与原始工业革命的符号,这些你只能在脑海与梦境中串联的细节,在我的眼中如光阴长河中升起的浮萍,依次铺展开来。窄小铁轨上斑驳铁锈中沉尘的岁月,又仿佛被汽笛声这把锋利的刀刃依次划开了。宁静与沧桑, 唯美与古朴,这些原来你只能在词典中、隔着冰冷的纸张抚触的文字,瞬间,便生动与形象了,它们如瓢泼大雨,从天际一一飞流而下。
站在窄小的铁轨边,夏日的阳光在汽笛声中如晚风下颤动的绸纱,小火车的身影就在这绸纱中鲜亮起来,就像一块藏在深闺的老古董,越来越近。古老的小火车头大口大口吞吐着乳白色的蒸汽,仿佛一位历经尘世起伏的蹒跚老者,又犹如一轮满载历史与岁月的巨轮。
一块工业文明的活化石
“说起芭蕉沟,心里凉悠悠,跟到工人走,又有纸烟抽,再过三五年,还有娃儿逗。”这首流传于解放初期的民谣,印证了芭蕉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嘉阳集团的前身嘉阳煤矿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是四川最早的中英合资企业。从建矿至今已产煤两千多万吨,为抗战军需和新中国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闻名中外的四川犍为嘉阳小火车,东起岷江之滨的犍为县石溪镇,西至犍为县与沐川县黄丹交界的芭蕉沟镇,人们因之又习惯地称之为“芭石铁路”。冒着蒸汽的嘉阳小火车终日来回奔波于这一段全长19.8公里的窄軌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芭蕉沟的小火车因其权属嘉阳煤矿,人们又亲切地称之为“嘉阳小火车”。嘉阳小火车使用的机车是我国运用国外技术自行改进生产的三号机车(因这种机车煤耗高、能效低,国家已于1972年发文禁止再生产。目前芭石铁路上还有4台机车在正常工作,专做客运)。因轨距仅762毫米,只有普通列车轨距的一半左右,所以又被称为“寸轨”,比我们熟知的《林海雪原》中的森林小火车还要袖珍,简直就像是一列游乐园中的儿童玩具列车。嘉阳小火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运营的寸轨客运蒸汽火车,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原生态的工业革命活景观”、“活着的18世纪工业革命博物馆”、“最后的蒸汽机”,又被誉为“工业革命的活化石”。
79岁的刘云华老人是芭石铁路首批7名火车司机之一,也是芭石铁路全线通车试运行的第一趟火车司机,至今仍能清晰回忆起小火车首发时的情景:
1959年7月12日下午,芭石铁路首趟火车从始发站黄村站出发,拉了3个煤车。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铁路的轨距不是762毫米而是600毫米;首趟煤车的牵引机车也不是蒸汽机车,而是用“雪佛莱”汽车引擎改制的轨型汽车,长约3米,前部为驾驶室,后部为斗车,内装石头以负重牵引。煤车厢除车轴外几乎是全木结构,厢底是木材板,厢体用竹篾编成,长约2米,一个车厢装煤2吨多。
“火车一开上路,真像马拉牛车,全身都在抖。”刘云华老人回忆道。
从1959年起,芭石小火车角色缓慢发生着变化,起初只是为了运煤。以后,又顺便接送矿工上下井,再后来,便发展到搭载当地农民进出大山,又曾经红火了很长一段时期。进入21世纪,小火车成为了当地发展旅游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着摇头晃脑的小火车来到这座古朴的小镇,小火车俨然成为小镇与山外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2006年,嘉阳小火车与芭石铁路一道被乐山市市政府命名为“工业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又被评为四川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嘉阳小火车·芭蕉沟·黄村井旅游矿井”申报国家矿山公园成功,并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
一辆独一无二的火车
在芭石铁路的一处小站,等候小火车的我,目睹小火车缓慢进站,几位当地的农民,正从车厢中向下驱赶着三头肥壮的猪。那些坐车的猪大概也是坐上了瘾,死活不肯下车。两位农民一位在前死拉着猪的耳朵,另一位高高抬起猪的后脚,劳力费神把猪一头头赶下了车。猪的尖叫声压过了露台候车室的喧杂。一位等候上车的当地中年人开玩笑说:“人和猪儿混杂的火车。”四周候车的人便全笑起来了。
检票上车后按号入座。看外形,各个车厢大小不等。客运列车共有7节客车车厢,每节车厢仅约4米长,车厢之间互不相通,每一节车厢都配有一位售票员、检票员和乘警。由于小火车早就不堪重负,所以检票员不仅要负责旅客上下的开门关门,还要负责在列车下坡时控制刹车手轮以协助司机降低车速。车厢两边排列着两排十分简陋的长条木凳座位,每节车厢共有20个座位可供对号入座。遇到赶场天或者周末学生回家,车上车下人头攒挤、熙熙攘攘,拥挤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大城市的春运高峰。在小火车每个站台,售票处都有坐票与站票之分,但票价并没有区别。
坐在简陋车厢里,乘客与售票员、乘警一路谈笑风生,窗外,时速20公里的小火车晃晃悠悠于蜿蜒曲折的崇山峻岭之间。在画屏般的田园风光中,大山深处慢步的小火车,如一支画笔,它穿越深沟幽谷,爬越悬崖峭壁,在大片碧绿的森林与密布的层层梯田间,一一描绘出田野的宁静与空寂;在芭石铁路一处处幽深的隧道口,它又如一首浪漫主义的激情乐章;隧道的这一头,小火车呼吸氧气清澈的血液,吐着乳白色的蒸汽,在隧道的另一边,它飞舞漫天的煤渣,像小提琴弦丝上脱落的松香粉末。
蜜蜂岩站位于芭石铁路的中部,由于受狭窄地形限制,火车到这里不能正常转弯,故必须在此掉头,于是人们便按照詹天佑发明的“人”字形铁路线路来使机车掉头。遥想一百多年前,京张铁路青龙桥段上,詹天佑的“人”字形铁路线路,被世人称为“一个伟大创举”,百年后,在芭蕉沟,蜜蜂岩段上的“人”字形铁路线路,便成为无比珍贵的活化石了。
火车到达芭沟站时,我在站台巧遇驾驶这列火车的司机老刘师傅。关于小火车,刘师傅一脸自豪:“我的师傅岑正明现年79岁。他是嘉阳小火车的第一任司机,他还有好几个第一哦:嘉阳煤矿中的第一批中共党员、第一个省劳动模范、省内学历最低的小火车专家、四川带徒弟最多的小火车司机。”据了解,岑正明祖居四川荣县老龙场,出身雇农。9岁时,大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一去杳无音讯,父亲一气之下上吊身亡。接着,母亲又活活饿死。岑正明19岁到嘉阳卖苦力,原为推煤工。1959年芭石铁路通车前,矿里派岑正明等6人去重庆天府煤矿学习小火车驾驶技术。回来后,他们一看全傻眼了:铁道全是泥土路基,小火车一上路就剧烈摇晃,有人便说:“算啦!这碗饭不好吃,弄不好,性命要丢在这铁路上!”6人中便有5人打起了退堂鼓,唯独岑正明没有动摇,他一人顶起了小火车司机重任。
说完这些,刘师傅匆忙跳上了火车头,慢火车又将开往下一个站点,阵阵汽笛声和蒸汽扑面而来。当小火车火渐渐走远后,一切的轰轰烈烈便烟消云散于透明的空气与连绵的大山之中,船形的芭沟镇就又从透明的空气与连绵的大山之中浮现上来。小火车每天都会定时穿越这个美丽而幽静的老镇,那尖锐的汽笛声,已被当地居民视为标准时间和报时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火车似一个如期而至的情人,在芭蕉沟,留下一个深情的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芭蕉沟像是一个天然的静音器,滤掉了小火车一切的嘈杂与浮躁。
一颗垂暮沉寂的心脏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芭蕉沟镇一年四季如春,没有工业污染,是一处天然的避暑胜地。这里是川西南民居建筑保护较好、风格较统一的地方,小角楼民居建筑群、苏式建筑特色突出。除此之外,沟内还有芭蕉石、情人榕、白石崖、红瓦寺、猴子坡等自然景观。这几年,随着芭蕉沟镇煤炭资源的逐步枯竭,部分矿井早已关闭,芭蕉沟镇林立的老式楼房,也从热闹到寂静到今天的时而热闹时而寂静。年轻人为了生計,大多搬迁了出去,小镇只留了些老人与孩子,一老一少,独守着垂暮的老镇。
清晨,雾气弥漫,大自然清新的气息浸润着我的肉体。一层层轻纱般浮动的白雾如条条哈达环绕在小镇四周,时隐时现的炊烟在林立的房舍中飘舞游荡,广袤的绿色与穿梭的小火车互相衬托,呈现出一幅绮丽斑斓的田园景色。
雨雾中的芭蕉沟镇,灰色瓦片仿佛是一块收藏苔藓的化石,苔藓仿佛是一双悬挂晶亮水珠的眼睛。它们像一粒击中时光的子弹,让光阴硕大的躯体应声倒下,脚步戛然而止。走在狭小而安宁的镇上,古老的柏油马路,窄窄的蜿蜒曲折,路两边梧桐树投下或阴或暗的影子,街沿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的筒子楼或瓦房。瓦房,灰瓦青墙、木门朱檐;筒子楼,红砖木板,陈旧凝重。一切显得那么错落有致,显得那么安静而整洁。房子大都平仄低矮,屋顶上,小巧而雕刻着花纹的黑色小瓦当,普通而不起眼,由于经年雨水冲刷而生出的青苔,像一层厚厚的油漆包裹着房屋的躯体。小巷路边的花花草草,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绿意盎然。小镇人家那面对着小巷洞开的门户,斑驳的痕迹,仿佛无时无刻不在向游人述说着这座老镇沧桑的历史。
我的印象中,芭蕉沟小镇的人们仿佛永远生活在世外桃源,与世无争地、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一天的事:喝茶聊天,自娱自乐。面对外界的星移斗转,芭蕉沟就像一条失宠的老街,了无生气,终日静静地眯着眼,昔日的繁华和热闹都深藏在层层的皱纹和浑浊的眼神里。尽管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但早晨七八点钟,老街还是醒了,卖早餐的支起了桌椅,老板早早烧开了水,装满开水的花花绿绿的水瓶摆放一地,卖花卷稀饭的早点铺升起一缕一缕的炊烟。这一切是那么的不紧不慢,是那么的宁静和谐。街上的铺子,这时也都慵懒地睁开了眼,五行八作的人们咳嗽着走出家门,拢了手踏在老街瘦骨嶙峋的身上,不知要把自己踱到哪里去。街上清清爽爽的,但保不准就会有谁拎一只大碗转出来,要一份麻辣鲜香的豆腐脑,也说不准谁会拿了零钱来买几枚大针一挂青线,一桩普通但足以维持小镇人家一天生计的交易瞬间便完成了。买卖就像一条永远也扯不断的细流,永远都那么不紧不慢地流下去。偶有一位老者和一条养了不知多少年的狗一起依偎屋檐下,任凭午后的阳光漫流而过,慢慢凝滞成一幅温馨画卷。
一条有希望的发展之路
在列车司机涂卫东眼中,小火车每次能加2.5吨煤,可供三个来回用。由于年代久远,奔跑了45年、每年运送约20万人的小火车已显疲惫。21世纪初,在当地关于小火车和这条铁路的存在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让公路替代铁路,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它的工业文明”,将它打造成旅游亮点。而嘉阳集团电视台工作人员张祥却说:“小火车运行起来,每年的维修费用200万元,而每个乘客的票价根本不够本。但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这列小火车还是保存下来,仍将继续自己的古老旅程。”
据同车厢的本次小火车列车长介绍,小火车真正开始面对游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来坐小火车的全是外国人,我们还专门为他们制作了火车票,一张长长的纸条条,上面盖有公司的章,他们拿到纸条,再写上自己的名字。我那时还小,刚上火车工作,那时票价全程还只要两元,外国人也一样。”我这次坐小火车进芭蕉沟,坐的是专门的观光车厢,一人一座,几乎不存在拥挤不堪的现象,票价是80元一张。“再后来,游客多了,我们就专挂了‘观光车厢’。”列车长说。
我手中有一套小火车的宣传卡片,是嘉阳集团制作的,很是精美,里外印满了小火车千姿百态的照片。张张图片中,小火车明亮而奔放,正自信而豪迈地驶向一片希望的田野。但随着我在小火车倒数第二站——与世隔绝的芭沟镇采访的深入,那条独一无二的窄轨背后的危机也隐隐约约浮出了水面。
夏日黄昏的芭沟镇凉爽宜人,空气格外清新,此时此刻,芭沟镇“百信旅店”的店主——31岁的张丽,正坐在自家旅馆那开阔的天井中和我聊着。2001年,就是她在全镇率先吃“螃蟹”,开起了私人旅店。从那时至今,对于旅游升温给小镇带来的变化,她家的旅店无疑一个是最为准确的温度计。“这片地下面的煤全挖光了,现在,工人全迁到山下的跃进矿上班了。”她双脚抬起用力踩了几下水泥地:“镇上现在只余下矿工家属、老人和没上学的孩子了。”
她用“炒得热,但没见到多大的效益”来总结自己对于小火车的印象。“芭沟镇没有什么景点,游人总是当天坐火车进来,当天又坐火车出去了。”
关于小火车的明天,芭沟老镇的未来,当地居民未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为嘉阳小火车的未来,却指明了一条有希望的发展之路。
长期以来,慢速的小火车是小镇通往外界的唯一的交通工具。2020年,当地投资2.1亿元,修建了塘芭快速公路,此公路为旅游环线公路,打破了芭沟镇只能依靠小火车出行的瓶颈,缩短了车程,大大提高了通车效率,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同时,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阳集团对于“嘉阳小火车”如何打造工矿遗产助力乡村观光的良性循环,以旅游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路,正在落地与实施:蒸汽小火车环保技改项目、景区风情小镇改造、景点的联合开发等一系列建设工程,纷纷上马。而当地的旅游人数,从2015年起,每年都在快速递增,古老的“工业革命活化石”正华丽转身,蜕变为乡村振兴的致富瑰宝。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小火车俨然已成为一块巨大的金字招牌。“今年‘五一’黄金大假外面来的人太多了,我的手机都被挤坏了。”一位车上的乘警,兴奋地给我谈及小火车日益增加的旅客量时,下意识用手摸了摸挂在腰间的手机。“那几天,每列车厢都站满了人,我都只好站进火车头里去了。”车厢里的售货员一边笑,一边手不停地补充着货物供给。
一道工文旅融合的必答题
嘉阳小火车、芭蕉沟矿区与黄村井旅游矿井,都属于工业遗产;而以“嘉阳小火车”为主角的旅游开发,属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利用与行业转型发展。
众所周知,具有历史、科技、艺术、社会价值的工业遗存遍布华夏大地。至2021年年底,在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近现代工业遗产有140多处,有190多项工业遗产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具体措施,包括“弘扬工业文化价值内涵”“推动工业旅游创新发展”“开展工业文化教育实践”“完善工业博物馆体系”以及“加大传播与交流”等。
以四川为例,这里广布的大量的“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如今绝大部分都成为工业遗存。但让人感到痛心的是,这些曾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重大贡献、见证了一段独特历史的“活化石”,随着工厂搬迁入城市、改革转制等原因,原有厂房废弃,人员迁离,很多工业遗产,如今人去楼空,厂房残壁断垣,厂区杂草丛生。如何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一批宝贵的工业遗产,助力老旧企业焕发新生;如何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批大部分位于偏远乡村中的工业遗产,助力乡村振兴,是一道工业文旅如何融合促进经济升级发展的必答题。
一是全面摸排工业遗产情况,加强整体保护。国家应全面开展以“三线建设遗产”为核心的工业遗产普查,确定工业遗产等级,并制定相应保护措施。加强核实遗址工作,落实原址保护措施。对有重大政治、经济以及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列入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规为参照,制定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相关法律,并将工业遗产保護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
三是加大工业遗产拆除、改建审查和许可工作的监管力度,最大限度避免破坏与过度开发利用。同时,积极开展工业遗产历史文物征集、博物馆建设等文化工作。
四是利用工业遗产资源,促进乡村振兴与文旅发展。以西南为例,绝大多数三线建设的工业遗存,当初都遵循“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地方偏僻,大多位于偏远的乡村,当地自然与生态环境优良,山青水绿,景色秀丽,现在反而成为旅游、康养的绝佳选择。如果合理利用好这批宝贵的工业遗产资源,利用好已有的住房与较完善的医院、学校、影院等配套设施,打造红色旅游路线,打造红色文旅品牌,对于乡村振兴与地方特色文旅发展,对于工业遗产“动态传承、可持续发展”与文旅事业,都是双赢的局面。
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上,首钢园成为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新标杆。而在东北,蒸汽机车旅游已成为铁岭乃至辽宁旅游的一张名片。保护利用好工业遗产,促进传统工业的转型发展,增加企业经济发展着力的新抓手,对于促进所在地区尤其是老工业区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其意义与价值,更显突出与关键。
(焦虎三,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研究员,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成都市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库成员/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