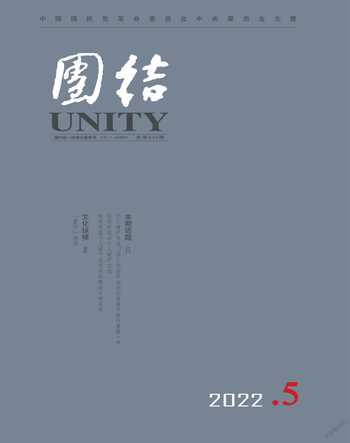“墨子”杂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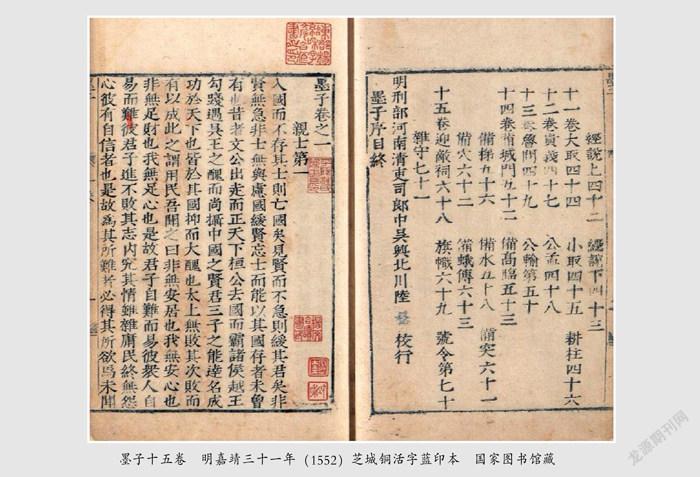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取名“墨子号”,此事让墨子再度声名大噪。如此命名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墨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科学家”,是“科学家的鼻祖”,是“科圣”;二是《墨子》中记录的“小孔成像”实验是世界上最早的光学实验,而这一实验“为量子通信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墨子之作为“大科学家”显然是一种“现代性”定义的产物。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墨子还是“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甚至是“一个实行的宗教家”(胡适)。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墨家师徒,也跟如今的社会革命集团一样,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依他们的政治观点去实践躬行的”(曹聚仁);“墨子具有小生产劳动者思想代表的特征”(李泽厚),“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其学说充满了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目的”,“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所吸收和利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墨子思想系统中,有形上的信,有知识的入门,也有价值的用”,“以西方哲学来说,他是比较合乎西方标准的哲学家,但以道德人格实践看,他又是道地的中国人”(王瓒源);“从哲学观点上看,墨家思想未免浅显,它没有儒家、道家般深奥的形上预设,所以虽然它曾对其他学派构成严重的挑战,但却为时不久”,“晚近中国对墨家复感兴趣,是缘于它功利主义的精神;而西方对它的关怀,则是鉴于墨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天意、泛爱之教义,在表面上极为相似”(陈荣捷)。“现代性”视域中的墨子形象虽然光怪陆离,但其核心不外强调墨子及其学派的“科学”“逻辑”“实践”“功利主义”“和平”和“牺牲”等精神。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表明了墨子、墨家和墨学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和阅读《墨子》,重估其思想和学术价值,以探索中华文化在儒、道两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可能性”。
墨子名气虽大,但和许多古代名人一样,历史记载极少。《史记》中无墨子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有言:“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汉书·艺文志》曰:“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后世学者虽多方考证,但关于墨子和墨家至今尚有多个谜团未解:
第一,墨子姓墨名翟吗?古代并无姓“墨”者,故一般以“墨”为“姓氏”之“氏”,故墨子氏墨名翟。至于“墨氏”之由来,大概是“墨台氏”或“墨夷氏”之简称。也有人认为,墨子姓翟名乌,“墨”则是其学派之名。战国诸家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皆无以“姓”为学派名者,故“墨”应为学派之名称。“墨”是黑色,也是一种徒刑。墨子及其弟子皆“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面黑如墨,又习惯于艰苦生活之磨炼,故自称为“墨”。
第二,墨子是哪国人?《史记》《汉书》都说墨子是宋国人,大概因其祖上为宋人之故。从清孙怡让开始,很多学者说墨子是鲁国人,根据是《墨子·贵义篇》的“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的“楚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等。也有人认为墨子是楚国人,他们说《墨子》中的“鲁”指的是楚国的鲁阳城,因为《鲁问篇》谈的都是楚国之事,而非鲁国之事,且墨子之观念与楚国一致,而与鲁国之传统观念大异其趣。以上诸说各有其论据,实难取舍。更有人认为墨子是印度人,称其说类似婆罗门教之教义,理由是“墨翟”是“貊狄”或“蛮狄”的同音转借,墨子“色黑”,印度人亦“色黑”,墨子“天志”“尚同”“兼爱”诸说,亦与婆罗门教相似。太虚大师云:“(墨家)或犹太摩西教之一派,兼传希腊科学、哲学者欤!墨子根本思想,以人类同出于天帝,故应以天之志为志,而上同天志,博爱全世界人类。天与人之交通,则寄于鬼神。而保傅人类以实现其兼爱,则需牺牲自己而刻苦为众,尤有藉于论辩、技艺之巧,以为觉济之工具。就近取譬,则如明季人中国之天主教徒,国人概称曰红毛,其徒亦于传拜神、爱人之教外,兼授天、算等,可为墨家之一比例。”(《墨子学辨序》)其说颇为有趣。
第三,墨子的生卒在何年?古代文献中并无关于墨子生平事迹的记载,现存《墨子》一书中虽有诸多墨子事迹的叙述,却无关其生卒年月,故后人关于墨子生卒年众说纷纭。汪中认为“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景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孙诒让则以为墨子“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章太炎以为“盖墨子去孔子亦四五十年矣”,胡适以为墨子约生于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公元前500至前490年),死于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公元前425至前416年),冯友兰以为墨子生卒年大概在公元前479至前381年之间,最新研究成果则认为墨子与鲁阳文君年龄相当,约生于公元前525年至公元前520年之间,卒于公元前438年(高华平,《墨子生卒年新考》)。这些说法均不能作为定论。我个人同意陈荣捷之说:“至于生平,则不甚明了。只能推定大约生于孔子卒前,而卒于孟子生前。”(《中國哲学文献选编》)
第四,墨家思想代表何种“阶级”?墨子创立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团体——墨者团体。《淮南子·泰族训》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庄子·天下篇》云:“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冯友兰认为墨家代表游侠,《中国哲学简史》云:“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周代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以此为生。这种人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比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学就是这种道德的发挥。”另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墨家代表“小生产者阶级”。李石岑说:“墨家主要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墨子以大匠的资格,因其绳墨精巧过人,遂得墨者的称号,而墨子以‘利于人’为号召,遂蔚成墨家的风尚,因而墨者遂成为道术之称。”(《中国哲学十讲》)李泽厚说:“先秦氏族传统逐渐崩毁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空前解放,使代表手工业的小生产劳动者思想的墨家一度显赫非常,成为与儒家并列而对抗的重要派别。这大概与当时比较自由的特定政治、思想条件,使作为社会生产力量的各种手工匠作失去原氏族结构的严密控制的情况有关。他们之中产生了墨子。似乎可以说,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是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或此书中的(不包括墨辩)。”(《墨家初探本》)这种“小生产劳动”说难以解释墨子思想的复杂性,难以解释《墨子》中所描述的严密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背后的专业思维和军事管理系统,更难以解释《墨辩》中的科学知识系统及其严密逻辑。
上述问题在学术和思想上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读《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今本《墨子》53篇,可分成5组:第一组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7篇,当为墨家后学作品;第二组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非儒》等24篇,多分成上、中、下三篇,当为墨子门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第三组为《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通常称为《墨辩》或《墨经》,为后期墨家作品,深受现代学者重视;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篇,乃墨家后学记述墨子及其弟子言论行事的作品,体裁颇近《论语》;第五组包括《备城门》《备高临》等11篇,主要讲军事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古今《墨子》注释中最重要者当属孙怡让之《墨子间诂》,治墨学者不可不读。
从思想上说,墨家以儒家为死敌,《墨子》几乎反对儒家的每一个具体主张。《墨子·公孟》云:“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非儒》亦云:“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墨家对儒家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彻底的、不妥协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自己的主张。
墨子的主张有“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十大理念,其中最有名的是“兼爱”之说。“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其意是指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其他一切人,坚持兼爱的人为“兼士”。“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 中》)“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 上》)只有“兼爱”才能创造一个“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兼爱”需以人格化的神圣存在为本,故主张“天志”“明鬼”;“兼爱”需有国家之绝对权威和政令统一,故主张“尚同”;“兼爱”需依靠贤人治理“昏乱”,故主张“尚贤”;“兼爱”需有和平的国际秩序,故主张“非攻”;“兼爱”需保证基本的物资供应,杜绝浪费,故主张“节用”“节葬”;“兼爱”需满足人民之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故“非乐”;“兼爱”需激励人人努力奋斗,故“非命”。这一切都需建立于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和逻辑思维之上,故主张“大取”“小取”。
墨子的思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具备“文化历史合法性”“经验认知合法性”和“人民权利合法性”的“三重合法性”,这是其能成为一时之“显学”,并于近现代今日吸引学人的根本原因。但墨子思想在历史上的式微是否因为其没有“一个终极发生的机制或天机”,从而导致其缺失了生生不息的“天机”和“天趣”?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能不能为其“建构”一个基于人之“生发中和本性”真实机制呢?《墨子·天志上》:“子墨子曰:其上事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在“尊天”“事鬼神”和“爱人”的中华文化根本识度下,曾经显赫一时的墨学当可恢复其内在的生命力。如此,墨子对我们的意义远大于“墨子号”的命名。
(李广良,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责编 刘玉霞)